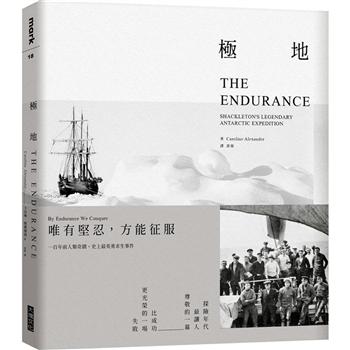英勇年代
多少年過去,那天的影像依然鮮明烙印在沃思禮船長 (Frank Worsley) 腦海中。
那是個七月天,時值南極的隆冬,伴隨著極地長夜而來的黑暗,已盤桓了好幾個星期。氣溫是華氏零下30度 (約攝氏零下24度)。放眼望去,船身四周的冰海一望無際,在明亮清澈的星空下顯得潔白而神祕。呼嘯的風聲,不時打斷艙內的交談聲。堅實的厚冰在遠方呻吟,那不祥的聲音透過大片冰層傳來,傳到沃思禮船長和身旁兩個同伴耳中。也有些時候,幾里外的小小騷動就引得他們的船陣陣顫抖與呻吟;千百萬噸重的厚冰因移動所造成的壓力,由遠而近,推壓到船的四周,揉擠那有彈性的船身,使得木製的船壁繃得緊緊的。
這時候,三人當中有人開口了:
「它快不行了⋯⋯船長,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你要趕快做決定。這艘船也許還可以撐幾個月,也可能只有幾星期,甚至幾天,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凡是被寒冰奪走的,就再也要不回來。」
時為1915年,說話的人,是鼎鼎大名的英國籍極地探險家,薛克頓爵士 (Sir Ernest Shackleton),他的副手懷爾德就站在一旁。他們所搭乘的船「堅忍號」,在南緯74度附近因海面結冰而被困在南極的威德爾海 (Weddell Sea)海域。此前,往南極探險的成果業已十分輝煌;薛克頓一行人千里迢迢南來,志在成為首支徒步橫越南極大陸的隊伍,企圖從所剩不多的「第一」中再創新紀錄。
1914年12月,「堅忍號」離開了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的捕鯨站,就此進入南極圈,向南行駛了一千多哩,距離預定停靠的南極大陸港口只剩100哩 (約160公里) 左右的航程。沒想到,海面上浮冰集結,「堅忍號」只好暫停行進。強勁的東北風時起時停,連吹了六天,把大塊浮冰全吹向南極大陸的冰棚,行進在浮冰群中的「堅忍號」也因此受困於其中。又過了幾天,氣溫驟降到華氏9度(約攝氏零下13度);寒冷的天氣凍硬了原先鬆軟的浮冰,要到來年春天才有融化的希望。在此同時,威德爾海中的流冰未曾停歇,帶著困在冰裡的「堅忍號」緩緩向北流去;原先即將駛達的目的地,眼看著愈來愈遠。
薛克頓在著手籌備這趟「帝國橫越南極洲遠征」(Imperial Trans-Antarctic Expedition) 時,已因前兩次極地探險而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他在其中一次遠征中,推進到距南極點只有100哩 (約160公里) 的地方,創下當時人類最接近南極的紀錄。這兩次的遠征雖然留下了許多值得後世留念的英勇事蹟,可惜都不曾達成最終目的:成為首支踏上南極點的隊伍。
1914年,薛克頓的遠征隊得以成行,但此時早有其他隊伍捷足先登,完成抵達南極點的壯舉。薛克頓在途中大膽更改目標,計畫由威德爾海海岸出發,徒步跨越南極大陸,抵達羅斯海 (Ross Sea) 海岸,寫下南極探險中唯一尚未完成的紀錄。「堅忍號」遠征的籌備工作煞費心力;其中最令薛克頓傷神的還是經費問題。當時薛克頓四十歲,以他全副的經驗與聲望在籌劃這次行動;那時的他當然還不知道,即將進行的跨越南極大陸會是另一次的失敗。然而,後人對於薛克頓的最深記憶,就來自這次未竟全功的「堅忍號」遠征。
二十世紀初期的南極探險,大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探險活動。南極既沒有兇猛的野獸,也沒有野蠻的原住民阻擋探險家的腳步。在南極,探險家面對的只是時速高達200哩 (約320公里) 的強風和華氏零下100度 (約攝氏零下73度) 的酷寒。南極探險其實是人與大自然原始力量的競爭,是人與自我耐力極限的競爭;這競爭如此單純,一點也不難理解。南極的特別之處,還在於這是一片純然由探險者發現的所在。在此之前,南極從沒有任何原住民;所以,在這段時期前進南極的探險家真可以大聲說,他們踏上了一塊從來不曾有人跡的土地。
1914年,「堅忍號」啟程南行,這年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遠征隊1917年返抵英國,大戰已接近尾聲。後人常視「堅忍號」遠征為極地探險之「英勇年代」 (Heroic Age) 的最後一次壯舉。若想理解這次企圖跨越南極之舉所含的意義與野心,應該要先知道歷來的南極探險者在英雄主義——與自我主義——的驅使下,承受了什麼樣的磨難。事實上,薛克頓得以在「堅忍號」事件中展現偉大的領導特質,要歸功於他昔日所經歷的瘋狂歷鍊。
極地探險的「英勇年代」,要從1901年8月算起,彼時英國海軍的史考特上校 (Robert Falcon Scott) 率領「發現號」 (Discovery) 向南極的麥克莫多峽灣 (McMurdo Sound) 出發。這支隊伍宣稱,此行是為追求科學進展,但其實這支首開南極探險之先河的遠征隊,所抱持的目標與往後幾支隊伍都一樣:矢志成為世上第一支踏上南極點的隊伍,為英國增光。史考特找了兩人同行:他的好友,動物學家威爾遜醫生 (Dr. Edward Wilson),以及二十八歲的薛克頓,一位商船上尉,曾隨船造訪非洲與遠東地區。1902年11月2日,史考特一行三人,帶著十九隻雪橇犬與五架載滿糧食與補給品的雪橇,從駐紮地向南極點出發。這趟歷程的挑戰之艱苦難以用筆墨形容,來回行程總共1600英哩 (約2560公里),要穿越一大片不曾為人知也從無地圖標示的區域,隊員絲毫不得半刻的輕鬆。
三人在日間來回接力搬運器材與補給品,有時借助雪橇犬,或者全憑人力拖拉。到了晚上,他們小心翼翼把數量稀少的食物均分成三份,並在鑽進各人冷冰冰的睡袋躺下之前,輪流誦讀達爾文的著作,結束一天活動。三人挨餓受凍,飽受壞血症之苦。雪橇犬接二連三病倒,最後只好宰殺病犬,把肉分給其他橇犬做食物。史考特領著隊,一路推進到南緯82度17分,離南極還有745哩 (約1200公里),終於不得不承認情況危急,勉強下令折返。此時的薛克頓因壞血症之故而吐血,有時病情嚴重到必須躺在雪橇上,由同伴拖著走。1903年2月3日,出發之後三個月,他們終於回到船上。回船之前的最後一段路程份外艱辛,因為那已是為了要保住生命的掙扎。
首次的南極徒步探險,似乎為往後的遠征建立起一套模式,探險家嚐盡百般苦頭的遭遇後來屢次重演,刻苦受難的英勇作為成了英國遠征隊的特色。然而,只要細讀這幾位探險家的日記便可以發現,這些磨難其實並非必要。威爾遜醫生在他們出發不到三週的某天,在日記裡寫道:「雪橇犬非常疲倦,前進得非常緩慢 (11月19日)⋯⋯今天的惡劣天氣使得狗兒難以招架,駕馭雪橇犬是最惱人的工作 (11月21日)⋯⋯雪橇犬非常疲倦且呆滯。驅使犬隻前進,變成糟糕透頂的差事 (11月24日)。」可憐的雪橇犬又累又倦,情況一天比一天差。威爾遜的日記忠實記載狗兒的狀況,令人不忍卒讀。
而史考特的日記讀來更令人驚心:「整體來說,目前我們的滑雪用具並沒有派上多大用場⋯⋯現在雪橇犬反而妨礙了行進,只能綁在雪橇上,讓牠們跟在後頭走。」他在1903年1月6日這麼寫著。隔天的日記裡他說:「隊員把所有的狗都放開來,三個人穩穩拖著雪橇走了七個小時,10哩 (約16公里) 的路程⋯⋯犬隻在雪橇邊走得相當穩健。」這是多麼驚人又難以想像的畫面:三個人把滑雪用具牢牢綑紮在雪橇上,旁邊伴著一群雪橇犬,辛辛苦苦以平均每小時1英哩 (約1.6公里) 的速度拖著雪橇在南極大陸上行進。在遠征隊出發前,史考特和兩名隊友都不曾花時間加強滑雪技巧,對於駕馭雪橇犬也是一竅不通。由此看來,他們遭遇的苦難並非必然,還不如說是由於想都想不到的無能所造成的。這些極地探險家之所以挨餓,不是因為碰上天災而喪失補給,而是因為當初根本沒有準備充份。三人之中,薛克頓挨餓得最嚴重,因為他的體格最魁梧,所需要的能量也最多。
除了這些準備上的不足,隊員三人之間的相處也不甚融洽。史考特與薛克頓的性格有著天壤之別,相處起來水火不容。史考特恪遵英國皇家海軍素來嚴格要求階級與規章的傳統,規定船上遵照僵硬的制度行事;甚至在「發現號」抵達南極海域後,還硬把船上一名不遵命令的船員扣上鐐銬,以示懲戒。反觀身上流著愛爾蘭血統的薛克頓,來自英國海軍商船隊,風度翩翩,輕輕鬆鬆就和船上的水手與軍官打成一片。薛克頓得以雀屏中選,純粹是因為史考特看中他的體格強健。長期置身於與塵囂隔絕的白色世界,每天重複著單調又艱苦的工作,日夜共處毫無個人隱私,三人必定在精神上承受了相當大的折磨。在這個組合中,威爾遜醫師顯然時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化解薛史兩人的衝突。多年後,威爾遜醫生才透露,有天大家用完早餐後,史考特沒名沒姓在喊:「死笨蛋,給我過來!」當時擔任史考特副手的威爾遜問史考特是不是在叫他,史考特回說不是。薛克頓便在一旁應道:「那你想必是叫我。」史考特說:「沒錯,你就是該死的笨蛋中的笨蛋。你要是膽敢再這樣跟我回話,我就給你好看。」三個成年人,孤軍置身於白茫茫的天涯海腳,怒目相視,惡言相向——當真有如一齣超現實的荒謬劇。
史考特一行三人回到「發現號」後,史考特以薛克頓病重為由,把他遣返英國。因無法完成全程而必須提早回國的薛克頓心感屈辱,但當他返抵國門,仍被舉國上下視為極地探險紀錄中南征最遠的英雄人物。倘若薛克頓與遠征隊同時返國,全國關切的焦點想當然爾不會落在他的身上;但如今只有他一個人先行返國,也就順理成章為遠征隊發言,集各方關注於一身。薛克頓心知肚明,有朝一日如果他打算自組遠征隊,那麼大眾對他的認可會有莫大助益。不論未來的情況如何演變,他決不再屈居人下,任人擺佈。
薛克頓出生於愛爾蘭的基爾德郡 (Kildare),父親是執業醫師,中產階級的家境不錯,童年時曾隨家人在都柏林住過一段短時間,最後全家搬到倫敦定居。薛克頓有八個姊妹一個弟弟,手足間親密融洽。薛克頓讀的是著名的達威契學院 (Dulwich College),十六歲時加入英國海軍商船隊。薛克頓在加入史考特的「英國國家南極遠征隊」之前,曾在頗具盛名的商船上擔任三副。年輕的薛克頓英俊迷人,儘管臉上表情深沈,但滿心憧憬著傳奇歷險,一生中幾度因此而落入探險尋寶的發財夢圈套裡。極地探險不僅符合薛克頓浪漫的性格,就現實層面而言,更能幫助他在階級至上的英國社會裡獲得立足之地。「發現號」之旅是他脫離中產階級身份進而躋身上流社會的跳板,也為他帶來更符合他個性的繽紛生活。
1904年,薛克頓終於和交往多時的心上人多曼小姐 (Emily Dorman)成婚。多曼小姐的父親是執業律師,家境富裕,擁有一份專屬於她的財產。這麼一來,薛克頓益發感到闖出自己名號的必要。薛克頓先後進入新聞界、商業界與政治圈,卻都不得意,後來還是把全副注意力放在最終目標上。1907年初,薛克頓獲得外來的金援,使他可以開始計畫新的遠征南極之旅。積極籌備了六個多月,薛克頓終於在同年8月順利率領「寧錄號」 (Nimrod) 向南極出發。
薛克頓從「發現號」遠征中獲得許多寶貴經驗,但他沒有把在極地探險所該具備的全部知識與技巧都學會。先「寧錄號」而去的多支遠征隊伍已經證明,唯有用雪橇犬拖拉雪橇才是可行的極地運輸方式,但「寧錄號」只帶了九隻雪橇犬,卻載運了十匹西伯利亞馬。此外,薛克頓本身的滑雪技巧也沒有多少長進;後來結果還證明,他在登山裝備方面的準備不夠。縱使準備不足,1908年10月29日,薛克頓仍然在三個隊友與四匹西伯利亞馬的陪伴下,從駐紮的羅伊茲角 (Cape Royds)出發,越過南極大冰障 (Great Ice Barrier),二度向南極點前進。以人力拖拉雪橇與挨餓受凍的艱苦歷程重演。在雪地上,西伯利亞馬滑倒又掙扎爬起的情境不斷出現;有時馬匹一不小心陷落鬆軟的雪堆,馬腹以下全受困於積雪中,又是另一番艱苦的掙扎。到最後,這幾匹完全派不上用場的西伯利亞馬,難逃被射殺當作食物的下場。1908年12月初,薛克頓和懷爾德、馬歇爾醫師 (Dr. Eric Marshall) 與亞當斯上尉 (Jameson Adams)四人,抵達無名大冰河的冰舌 (ice tongue) 地區。這條大冰河自緊鄰南極大冰障的連綿山峰流下,薛克頓把它命名為「畢爾德摩冰河」(Beardmore Glacier),以紀念此次遠征的主要贊助人之一。
這畢爾德摩冰河是遠征隊離開了一路而來的冰棚轉進山後南極高原的門戶。薛克頓眼前出現了一條令人走得膽戰心驚的通路。遠征隊員所穿的鞋沒有加裝防滑的冰爪,帶著沒有加上蹄鐵的僅存的馬「襪子」,艱苦爬上驚險萬分的冰舌。第三天,「襪子」跌入冰河裂縫中摔死。眾人飽受雪盲症、飢餓與凍瘡之苦,終於越過了畢爾德摩冰河,抵達南緯88度23分。此時他們距南極點大約只有100哩 (約160公里)。薛克頓檢視了遠征隊少得可憐的糧食,再看到眾人的體力每下愈況,忍痛決定放棄,趁還有一絲活命希望的當頭快快折回。
就在他們快要回到駐紮地時,亞當斯上尉病危。為了使隊友盡快就醫,薛克頓和懷爾德只好沿途拋棄不必要的裝備,以加快腳步趕回駐紮地。他們不眠不休趕了三十六小時的路,好不容易回到了駐紮地,卻發現留守人員已經全部撤離。所幸不久後,「寧錄號」載著搜救人員回到營地,打算在此過冬,等翌年春天再搜索遠征隊員的屍體,這才使得四人及時脫險。
「寧錄號」遠征的成果,比史考特的紀錄又向南推進了360哩 (約576公里)。薛克頓等人儘管在此行中吃了不少苦頭,但幸好全員獲救;更因為有新鮮馬肉補充營養,四人都因而沒有染患壞血症。遠征隊返抵英國,薛克頓再度成為英雄,並獲皇室授與爵位。薛克頓曾在不同的場合公開表示,他仍打算再籌組遠征隊,想要探勘濱臨羅斯海的阿德爾角 (Cape Adare) 以西地區;但他回國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想辦法賺錢,好償還「寧錄號」的債務。他在回國後的兩年裡巡迴演講,以口述方式把遠征過程集結成《南極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tarctic) 一書,書出版後旋即成為熱門暢銷書。他又把「寧錄號」改裝為博物館,民眾必須買門票才能入內參觀。這時,史考特帶著英國人民的祈禱與祝福,再次踏上南極遠征的路途。債臺高築的薛克頓只能留在英國,從報紙的頭條獲知史考特的遠征進展。
多少年過去,那天的影像依然鮮明烙印在沃思禮船長 (Frank Worsley) 腦海中。
那是個七月天,時值南極的隆冬,伴隨著極地長夜而來的黑暗,已盤桓了好幾個星期。氣溫是華氏零下30度 (約攝氏零下24度)。放眼望去,船身四周的冰海一望無際,在明亮清澈的星空下顯得潔白而神祕。呼嘯的風聲,不時打斷艙內的交談聲。堅實的厚冰在遠方呻吟,那不祥的聲音透過大片冰層傳來,傳到沃思禮船長和身旁兩個同伴耳中。也有些時候,幾里外的小小騷動就引得他們的船陣陣顫抖與呻吟;千百萬噸重的厚冰因移動所造成的壓力,由遠而近,推壓到船的四周,揉擠那有彈性的船身,使得木製的船壁繃得緊緊的。
這時候,三人當中有人開口了:
「它快不行了⋯⋯船長,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你要趕快做決定。這艘船也許還可以撐幾個月,也可能只有幾星期,甚至幾天,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凡是被寒冰奪走的,就再也要不回來。」
時為1915年,說話的人,是鼎鼎大名的英國籍極地探險家,薛克頓爵士 (Sir Ernest Shackleton),他的副手懷爾德就站在一旁。他們所搭乘的船「堅忍號」,在南緯74度附近因海面結冰而被困在南極的威德爾海 (Weddell Sea)海域。此前,往南極探險的成果業已十分輝煌;薛克頓一行人千里迢迢南來,志在成為首支徒步橫越南極大陸的隊伍,企圖從所剩不多的「第一」中再創新紀錄。
1914年12月,「堅忍號」離開了南喬治亞島 (South Georgia) 的捕鯨站,就此進入南極圈,向南行駛了一千多哩,距離預定停靠的南極大陸港口只剩100哩 (約160公里) 左右的航程。沒想到,海面上浮冰集結,「堅忍號」只好暫停行進。強勁的東北風時起時停,連吹了六天,把大塊浮冰全吹向南極大陸的冰棚,行進在浮冰群中的「堅忍號」也因此受困於其中。又過了幾天,氣溫驟降到華氏9度(約攝氏零下13度);寒冷的天氣凍硬了原先鬆軟的浮冰,要到來年春天才有融化的希望。在此同時,威德爾海中的流冰未曾停歇,帶著困在冰裡的「堅忍號」緩緩向北流去;原先即將駛達的目的地,眼看著愈來愈遠。
薛克頓在著手籌備這趟「帝國橫越南極洲遠征」(Imperial Trans-Antarctic Expedition) 時,已因前兩次極地探險而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他在其中一次遠征中,推進到距南極點只有100哩 (約160公里) 的地方,創下當時人類最接近南極的紀錄。這兩次的遠征雖然留下了許多值得後世留念的英勇事蹟,可惜都不曾達成最終目的:成為首支踏上南極點的隊伍。
1914年,薛克頓的遠征隊得以成行,但此時早有其他隊伍捷足先登,完成抵達南極點的壯舉。薛克頓在途中大膽更改目標,計畫由威德爾海海岸出發,徒步跨越南極大陸,抵達羅斯海 (Ross Sea) 海岸,寫下南極探險中唯一尚未完成的紀錄。「堅忍號」遠征的籌備工作煞費心力;其中最令薛克頓傷神的還是經費問題。當時薛克頓四十歲,以他全副的經驗與聲望在籌劃這次行動;那時的他當然還不知道,即將進行的跨越南極大陸會是另一次的失敗。然而,後人對於薛克頓的最深記憶,就來自這次未竟全功的「堅忍號」遠征。
二十世紀初期的南極探險,大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探險活動。南極既沒有兇猛的野獸,也沒有野蠻的原住民阻擋探險家的腳步。在南極,探險家面對的只是時速高達200哩 (約320公里) 的強風和華氏零下100度 (約攝氏零下73度) 的酷寒。南極探險其實是人與大自然原始力量的競爭,是人與自我耐力極限的競爭;這競爭如此單純,一點也不難理解。南極的特別之處,還在於這是一片純然由探險者發現的所在。在此之前,南極從沒有任何原住民;所以,在這段時期前進南極的探險家真可以大聲說,他們踏上了一塊從來不曾有人跡的土地。
1914年,「堅忍號」啟程南行,這年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遠征隊1917年返抵英國,大戰已接近尾聲。後人常視「堅忍號」遠征為極地探險之「英勇年代」 (Heroic Age) 的最後一次壯舉。若想理解這次企圖跨越南極之舉所含的意義與野心,應該要先知道歷來的南極探險者在英雄主義——與自我主義——的驅使下,承受了什麼樣的磨難。事實上,薛克頓得以在「堅忍號」事件中展現偉大的領導特質,要歸功於他昔日所經歷的瘋狂歷鍊。
極地探險的「英勇年代」,要從1901年8月算起,彼時英國海軍的史考特上校 (Robert Falcon Scott) 率領「發現號」 (Discovery) 向南極的麥克莫多峽灣 (McMurdo Sound) 出發。這支隊伍宣稱,此行是為追求科學進展,但其實這支首開南極探險之先河的遠征隊,所抱持的目標與往後幾支隊伍都一樣:矢志成為世上第一支踏上南極點的隊伍,為英國增光。史考特找了兩人同行:他的好友,動物學家威爾遜醫生 (Dr. Edward Wilson),以及二十八歲的薛克頓,一位商船上尉,曾隨船造訪非洲與遠東地區。1902年11月2日,史考特一行三人,帶著十九隻雪橇犬與五架載滿糧食與補給品的雪橇,從駐紮地向南極點出發。這趟歷程的挑戰之艱苦難以用筆墨形容,來回行程總共1600英哩 (約2560公里),要穿越一大片不曾為人知也從無地圖標示的區域,隊員絲毫不得半刻的輕鬆。
三人在日間來回接力搬運器材與補給品,有時借助雪橇犬,或者全憑人力拖拉。到了晚上,他們小心翼翼把數量稀少的食物均分成三份,並在鑽進各人冷冰冰的睡袋躺下之前,輪流誦讀達爾文的著作,結束一天活動。三人挨餓受凍,飽受壞血症之苦。雪橇犬接二連三病倒,最後只好宰殺病犬,把肉分給其他橇犬做食物。史考特領著隊,一路推進到南緯82度17分,離南極還有745哩 (約1200公里),終於不得不承認情況危急,勉強下令折返。此時的薛克頓因壞血症之故而吐血,有時病情嚴重到必須躺在雪橇上,由同伴拖著走。1903年2月3日,出發之後三個月,他們終於回到船上。回船之前的最後一段路程份外艱辛,因為那已是為了要保住生命的掙扎。
首次的南極徒步探險,似乎為往後的遠征建立起一套模式,探險家嚐盡百般苦頭的遭遇後來屢次重演,刻苦受難的英勇作為成了英國遠征隊的特色。然而,只要細讀這幾位探險家的日記便可以發現,這些磨難其實並非必要。威爾遜醫生在他們出發不到三週的某天,在日記裡寫道:「雪橇犬非常疲倦,前進得非常緩慢 (11月19日)⋯⋯今天的惡劣天氣使得狗兒難以招架,駕馭雪橇犬是最惱人的工作 (11月21日)⋯⋯雪橇犬非常疲倦且呆滯。驅使犬隻前進,變成糟糕透頂的差事 (11月24日)。」可憐的雪橇犬又累又倦,情況一天比一天差。威爾遜的日記忠實記載狗兒的狀況,令人不忍卒讀。
而史考特的日記讀來更令人驚心:「整體來說,目前我們的滑雪用具並沒有派上多大用場⋯⋯現在雪橇犬反而妨礙了行進,只能綁在雪橇上,讓牠們跟在後頭走。」他在1903年1月6日這麼寫著。隔天的日記裡他說:「隊員把所有的狗都放開來,三個人穩穩拖著雪橇走了七個小時,10哩 (約16公里) 的路程⋯⋯犬隻在雪橇邊走得相當穩健。」這是多麼驚人又難以想像的畫面:三個人把滑雪用具牢牢綑紮在雪橇上,旁邊伴著一群雪橇犬,辛辛苦苦以平均每小時1英哩 (約1.6公里) 的速度拖著雪橇在南極大陸上行進。在遠征隊出發前,史考特和兩名隊友都不曾花時間加強滑雪技巧,對於駕馭雪橇犬也是一竅不通。由此看來,他們遭遇的苦難並非必然,還不如說是由於想都想不到的無能所造成的。這些極地探險家之所以挨餓,不是因為碰上天災而喪失補給,而是因為當初根本沒有準備充份。三人之中,薛克頓挨餓得最嚴重,因為他的體格最魁梧,所需要的能量也最多。
除了這些準備上的不足,隊員三人之間的相處也不甚融洽。史考特與薛克頓的性格有著天壤之別,相處起來水火不容。史考特恪遵英國皇家海軍素來嚴格要求階級與規章的傳統,規定船上遵照僵硬的制度行事;甚至在「發現號」抵達南極海域後,還硬把船上一名不遵命令的船員扣上鐐銬,以示懲戒。反觀身上流著愛爾蘭血統的薛克頓,來自英國海軍商船隊,風度翩翩,輕輕鬆鬆就和船上的水手與軍官打成一片。薛克頓得以雀屏中選,純粹是因為史考特看中他的體格強健。長期置身於與塵囂隔絕的白色世界,每天重複著單調又艱苦的工作,日夜共處毫無個人隱私,三人必定在精神上承受了相當大的折磨。在這個組合中,威爾遜醫師顯然時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化解薛史兩人的衝突。多年後,威爾遜醫生才透露,有天大家用完早餐後,史考特沒名沒姓在喊:「死笨蛋,給我過來!」當時擔任史考特副手的威爾遜問史考特是不是在叫他,史考特回說不是。薛克頓便在一旁應道:「那你想必是叫我。」史考特說:「沒錯,你就是該死的笨蛋中的笨蛋。你要是膽敢再這樣跟我回話,我就給你好看。」三個成年人,孤軍置身於白茫茫的天涯海腳,怒目相視,惡言相向——當真有如一齣超現實的荒謬劇。
史考特一行三人回到「發現號」後,史考特以薛克頓病重為由,把他遣返英國。因無法完成全程而必須提早回國的薛克頓心感屈辱,但當他返抵國門,仍被舉國上下視為極地探險紀錄中南征最遠的英雄人物。倘若薛克頓與遠征隊同時返國,全國關切的焦點想當然爾不會落在他的身上;但如今只有他一個人先行返國,也就順理成章為遠征隊發言,集各方關注於一身。薛克頓心知肚明,有朝一日如果他打算自組遠征隊,那麼大眾對他的認可會有莫大助益。不論未來的情況如何演變,他決不再屈居人下,任人擺佈。
薛克頓出生於愛爾蘭的基爾德郡 (Kildare),父親是執業醫師,中產階級的家境不錯,童年時曾隨家人在都柏林住過一段短時間,最後全家搬到倫敦定居。薛克頓有八個姊妹一個弟弟,手足間親密融洽。薛克頓讀的是著名的達威契學院 (Dulwich College),十六歲時加入英國海軍商船隊。薛克頓在加入史考特的「英國國家南極遠征隊」之前,曾在頗具盛名的商船上擔任三副。年輕的薛克頓英俊迷人,儘管臉上表情深沈,但滿心憧憬著傳奇歷險,一生中幾度因此而落入探險尋寶的發財夢圈套裡。極地探險不僅符合薛克頓浪漫的性格,就現實層面而言,更能幫助他在階級至上的英國社會裡獲得立足之地。「發現號」之旅是他脫離中產階級身份進而躋身上流社會的跳板,也為他帶來更符合他個性的繽紛生活。
1904年,薛克頓終於和交往多時的心上人多曼小姐 (Emily Dorman)成婚。多曼小姐的父親是執業律師,家境富裕,擁有一份專屬於她的財產。這麼一來,薛克頓益發感到闖出自己名號的必要。薛克頓先後進入新聞界、商業界與政治圈,卻都不得意,後來還是把全副注意力放在最終目標上。1907年初,薛克頓獲得外來的金援,使他可以開始計畫新的遠征南極之旅。積極籌備了六個多月,薛克頓終於在同年8月順利率領「寧錄號」 (Nimrod) 向南極出發。
薛克頓從「發現號」遠征中獲得許多寶貴經驗,但他沒有把在極地探險所該具備的全部知識與技巧都學會。先「寧錄號」而去的多支遠征隊伍已經證明,唯有用雪橇犬拖拉雪橇才是可行的極地運輸方式,但「寧錄號」只帶了九隻雪橇犬,卻載運了十匹西伯利亞馬。此外,薛克頓本身的滑雪技巧也沒有多少長進;後來結果還證明,他在登山裝備方面的準備不夠。縱使準備不足,1908年10月29日,薛克頓仍然在三個隊友與四匹西伯利亞馬的陪伴下,從駐紮的羅伊茲角 (Cape Royds)出發,越過南極大冰障 (Great Ice Barrier),二度向南極點前進。以人力拖拉雪橇與挨餓受凍的艱苦歷程重演。在雪地上,西伯利亞馬滑倒又掙扎爬起的情境不斷出現;有時馬匹一不小心陷落鬆軟的雪堆,馬腹以下全受困於積雪中,又是另一番艱苦的掙扎。到最後,這幾匹完全派不上用場的西伯利亞馬,難逃被射殺當作食物的下場。1908年12月初,薛克頓和懷爾德、馬歇爾醫師 (Dr. Eric Marshall) 與亞當斯上尉 (Jameson Adams)四人,抵達無名大冰河的冰舌 (ice tongue) 地區。這條大冰河自緊鄰南極大冰障的連綿山峰流下,薛克頓把它命名為「畢爾德摩冰河」(Beardmore Glacier),以紀念此次遠征的主要贊助人之一。
這畢爾德摩冰河是遠征隊離開了一路而來的冰棚轉進山後南極高原的門戶。薛克頓眼前出現了一條令人走得膽戰心驚的通路。遠征隊員所穿的鞋沒有加裝防滑的冰爪,帶著沒有加上蹄鐵的僅存的馬「襪子」,艱苦爬上驚險萬分的冰舌。第三天,「襪子」跌入冰河裂縫中摔死。眾人飽受雪盲症、飢餓與凍瘡之苦,終於越過了畢爾德摩冰河,抵達南緯88度23分。此時他們距南極點大約只有100哩 (約160公里)。薛克頓檢視了遠征隊少得可憐的糧食,再看到眾人的體力每下愈況,忍痛決定放棄,趁還有一絲活命希望的當頭快快折回。
就在他們快要回到駐紮地時,亞當斯上尉病危。為了使隊友盡快就醫,薛克頓和懷爾德只好沿途拋棄不必要的裝備,以加快腳步趕回駐紮地。他們不眠不休趕了三十六小時的路,好不容易回到了駐紮地,卻發現留守人員已經全部撤離。所幸不久後,「寧錄號」載著搜救人員回到營地,打算在此過冬,等翌年春天再搜索遠征隊員的屍體,這才使得四人及時脫險。
「寧錄號」遠征的成果,比史考特的紀錄又向南推進了360哩 (約576公里)。薛克頓等人儘管在此行中吃了不少苦頭,但幸好全員獲救;更因為有新鮮馬肉補充營養,四人都因而沒有染患壞血症。遠征隊返抵英國,薛克頓再度成為英雄,並獲皇室授與爵位。薛克頓曾在不同的場合公開表示,他仍打算再籌組遠征隊,想要探勘濱臨羅斯海的阿德爾角 (Cape Adare) 以西地區;但他回國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想辦法賺錢,好償還「寧錄號」的債務。他在回國後的兩年裡巡迴演講,以口述方式把遠征過程集結成《南極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tarctic) 一書,書出版後旋即成為熱門暢銷書。他又把「寧錄號」改裝為博物館,民眾必須買門票才能入內參觀。這時,史考特帶著英國人民的祈禱與祝福,再次踏上南極遠征的路途。債臺高築的薛克頓只能留在英國,從報紙的頭條獲知史考特的遠征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