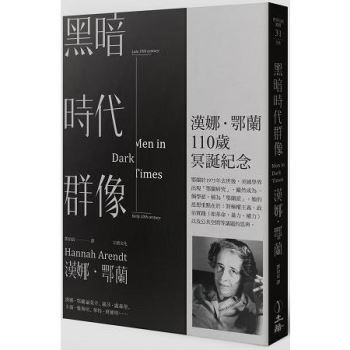〈黑暗時代的人本精神〉
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不在少數,它們的公共領域總是一片模糊,社會則是一片混沌,以致少有人會去過問公共事務,眾所關心的,無非是切身的利益,但求獨善其身。活在這樣的時代並受其形塑的人,對社會與公共領域大多不具好感,儘可能敬而遠之,甚至乾脆視而不見,拋諸腦後──彷彿這個世界只是一個讓人可以躲在它背後的表象 ──但求這個介於他們中間的中介空間最好不要介入他們彼此之間的了解。在這樣的時代裡,如果沒有意外,常會出現一種極為特別的人本觀念。要了解這種情形,不妨去看看《智者拿丹》(Nathan the Wise,譯註:萊辛早期的詩劇作品,強調宗教的寬容),在整部戲裡,無所不在的主題正是:「能夠生而為人也就夠了」,而有如主旋律般貫穿其間,與之相呼應的訴求則是:「做我的朋友吧」。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在《魔笛》(The Magic Flute,譯註:莫扎特歌劇作品,劇作家為Emanuel Schikaneder)中看到同一類的人本精神。絕不像我們所熟悉的十八世紀人本理論,突顯的只是基本的人本觀念,根植於其上的卻是國族、民族、種族與宗教的分歧和人類的分裂;這種人本精神則是比較完整的、充實的。如果真有這種人本精神存在,那麼自然會有一種現象,要求行為應該符合「人之所以為人」,並主張人與自然的行為是一體的、同一的。十八世紀時,提倡這種人本觀念最不遺餘力、影響也最大的莫過於盧梭,對他來說,全人類共有的人本特質並非表現於理性而在於惻隱之心,亦即他所說的:不忍見同類受苦之心。在這方面,萊辛所見亦同,他曾說,最優秀的人就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但萊辛卻擔心同情心的一視同仁,亦即他所強調的,對壞人也「心懷同樣的惻隱」。但對盧梭來說,這卻不是問題;在以他的理想為依歸的法國革命精神中,他就看到了「博愛」這種人本的極致。萊辛卻別有所見,在他的心目中,友善──有選擇性的、有別於一視同仁的同情──才是人本真正的體現。
在談萊辛的友善觀念及其與公共事務相關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花上一點點時間,了解一下十八世紀對博愛的認知。對於博愛,萊辛也頗用過心思,他所說的「人道情懷」,指的就是以手足之情待人,縱使這個人是來自一個以恨為出發點,並以「非人」方式對待別人的世界。總之,我們的用意是要強調,在黑暗時代,這種以兄弟之情來彰顯人本的情形乃最為常見。當時代變得極端的黑暗,某些群體甚至因此無處可以容身時,其所想所行全都是退縮的,是自外於這個世界的,這時候,這種人本精神也就會自然流露。從歷史上來看,人本精神中的博愛情懷,每每出現在受迫害與受奴役的族群中;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當時的猶太人,在文化圈裡還算是新人,在他們中間就不難發現這種相濡以沫的情懷。這種情懷也是邊緣族群特有的本事。也正是憑藉著這種本事,社會的邊緣族群總能夠克服一切;但是,所要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隨之而來的,常是社會地位的徹底喪失,以及與社會對應的所有管道全面萎縮──在這個我們與他人共有的社會中,先是從我們賴以自我定位的常識開始,繼之以我們賴以認同這個社會的審美與品味──在極端的情況中,這種邊緣化往往長達好幾個世紀,我們大可稱之為無世界狀態(worldlessness),而無世界狀態無以名之,只能說它是野蠻狀態了。
彷彿人性的有機演化,處於受迫害的壓力之下,受迫害者彼此緊緊相依相靠,我們所說的那個社會中介空間便隨之消失(迫害未發生前,也正是這個中介空間使他們彼此分開),並因而在人際關係中產生一種溫情;對於這種有如物理現象的溫情,凡是接觸過這類族群的人,無不印象深刻。說它有如物理現象,我當然不是在貶抑受迫害者的這種溫情;事實上,它一旦成形之後,就會發展出一種純然的良善,那是人類無法在其他情況下培養出來的。這種溫情同時也是生命力的來源,是一種只要能夠活著便自然流露的喜樂,也就是說,對世俗所說的那種受侮辱者與受傷害者而言,生命之於他們,就是完完全全地活在其中。但是,講到這裡,我們切不可忘記,在那樣的環境之下,之所以能夠形成那樣的魔力與熱望,實在是因為這個世界的邊緣人仍然熱愛著這個世界,才能夠擁有那種甘之如飴的本事。
法國革命在博愛之外又加上了自由與平等,後二者在人類的公共領域中一直都是主要的項目,但是,在受壓迫者與受迫害者和受剝削者與受侮辱者中,亦即十八世紀所謂的「不幸者」和十九世紀的「悲慘者」中,博愛卻有著它固有的地位。萊辛與盧梭的同情(雖然內容頗有不同),在發現並肯定人性的普世一致上,以及首度在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譯註:法國大革命領導人之一,1758-1794)革命中成為中心的訴求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此以後,惻隱之心也就成為歐洲革命史上不可分割與顛撲不破的一部分。時至今日,惻隱之心更被視為是純乎自然的悲憫,每個人只要看到有人受苦,儘管與自己非親非故,都會油然而生同情;因此,這種情懷大可以拿來當作一個理想的基礎,擴展到全人類,建立一個天下一家的社會。十八世紀的人本主義者正是要透過革命的手段,企圖用惻隱之心將不幸者與悲慘者結合起來,亦即匯成一股以兄弟之情貫穿其間的力量;但是,很快地卻發現,這種人本主義的精華全在於社會邊緣人才擁有的那種特質,根本無法向外擴散,也是非邊緣人無法輕易擁有的。光是惻隱之心或不忍人之心顯然是不夠的。現代革命高舉同情弱勢的大旗,企圖改善不幸者的命運,而不是去建立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正義,因此而造成的傷害,在這裡我們就不談了;但是,為了多少了解我們自己與現代人的想法,有必要稍微回顧一下古代世界,看看在公共事務上涉足比我們深的古人,他們是如何看待惻隱之心與人本精神的。
無論今古,至少有一點是一致的,亦即都認為惻隱之心是純乎自然的,跟恐懼一樣,是人皆有之的。也正因為如此,現代人對同情心給予極高的評價,而古人的態度卻大不相同,也就不免令人感到詫異了。古人深知同情之心乃屬人的本性,跟恐懼一樣,若非刻意地予以排除,我們是無法抗拒的;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最富有同情心的人還不夠資格被稱為最優秀的人,反倒是最令人敬畏的人才足以當之。同情與害怕這兩種心性的傾向都是十足被動的,不可能具有行動力;亞里斯多德將同情與恐懼放在一起討論,理由即在於此。然而,這樣一來有可能將事情整個弄擰,不是將同情貶成了恐懼──好像別人受苦也會使我們自己感到恐懼似的──要不就是根本不敢去同情別人──好像在恐懼中我們就只能同情自己似的。更令人驚訝的是,在西塞羅(譯註:Marcus Tullius Cicero,羅馬哲學家,106-43 BC)的《托斯卡拉論爭》(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III 21)中,斯多噶學派居然將同情與嫉妒等量齊觀:「為別人的不幸而心有戚戚的人,對別人的幸運也會心有戚戚。」西塞羅自己對此也有類似的想法,在《托斯卡拉論爭》(IV 56)中他就說:「有能力的話就伸出援手,何必要可憐人家?難道不出於同情,我們就不能施予援手嗎?」換句話說,難道人類竟是如此吝嗇,非要看到別人受苦,受到自己感同身受的驅策,才會去採取人道的行動?
評斷這些心性的傾向時,我們很難不觸及無私的問題,或者更進一步說,對別人慷慨大度的問題,事實上,就「人本精神」一詞的終極意義來說,這才是它的先決條件。很明顯地,分享喜悅當然是好過於分擔痛苦。令人高興的事通常都是好的話題,而悲傷則否。在與他人的對話中,對方整個人與他所說的話都洋溢著歡喜,聊起來就絕對不同於一般的談話或討論事情。我們可以說,這是因為談話的調性是愉悅的。擋在這種歡喜前面的則是嫉妒,而說到人本,這種見不得別人好的心態乃是更等而下之的。但是,同情的對立面並不是嫉妒而是殘忍;殘忍之為一種心性的傾向,與同情可說是如出一轍,只不過它是一種變態,是喜樂中自然會有痛苦的一種感受。問題是,樂與苦都說不出口,儘管可能發出聲音,卻無法形諸言語,更不用說去跟別人說了。
以上所講的,不過是換一種說法來說明一個現象,亦即對於那些不屬於受侮辱者與受傷害者的人來說,天下一家的人本主義並不真能夠打動他們,就算他們贊同這種理念,頂多也只是出於同情而已。對於這個世界上不同地位的人,邊緣族群的溫情根本缺乏感染力,遑論給他們加上一份社會責任,至於邊緣族群甘之如飴的那種悲苦,他們當然更是無從體會了。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黑暗時代」中,溫情乃是一種光明的替代品,對那些不恥於社會現狀,寧願躲在暗無天日中求個心安理得的人來說,自有其另類的魅力。躲在沒有能見度的混沌之中,大可以置之不理那個清晰可見的世界,只要靠著一群緊緊靠在一起的人,溫情與博愛就能夠補償那個非常態的現實,儘管所到之處的人際關係都是一種無世界狀態,同那個全體人類所共有的世界一點關係都沒有。在這種無世界狀態與非常態的現實中,很容易得到一個結論,亦即全體人類所共有的成分並不是這個世界,而是某種「人的特質」。至於這種「人的特質」是什麼,那就因人而異了;有人說理性是人類共有的特質,有人卻說,某一種情感,例如惻隱之心,才是人類皆有的。但是,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與情感主義(譯註:情感主義〔sentimentalism〕,盛行於十八世紀的理論,主張所有關於這個世界的信念都決定於情感)就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兩者同樣都會引發極大的激情,讓個別的人產生人類本是一家的感覺。但無論怎麼說,侷限在一個沒有能見度的混沌領域中,也就跟那個清晰可見的共同世界斷絕了關係,理性與情感也都只是心理上的替代品而已。
由此可見,這種「人的特質」及其隨之而來的博愛情懷,只有在「黑暗時代」才得以彰顯,也正因如此,在這個世界上它是無法得到普遍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在一個能見度高的光明環境中,他們則會像鬼魅般地消失於無形。這種受侮辱者與受傷害者的人本精神往往倏忽即過,但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影響力,事實上剛好相反,它反而使得侮辱與傷害持續不斷,倒是在公共領域上,它的作用還真的不大。
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不在少數,它們的公共領域總是一片模糊,社會則是一片混沌,以致少有人會去過問公共事務,眾所關心的,無非是切身的利益,但求獨善其身。活在這樣的時代並受其形塑的人,對社會與公共領域大多不具好感,儘可能敬而遠之,甚至乾脆視而不見,拋諸腦後──彷彿這個世界只是一個讓人可以躲在它背後的表象 ──但求這個介於他們中間的中介空間最好不要介入他們彼此之間的了解。在這樣的時代裡,如果沒有意外,常會出現一種極為特別的人本觀念。要了解這種情形,不妨去看看《智者拿丹》(Nathan the Wise,譯註:萊辛早期的詩劇作品,強調宗教的寬容),在整部戲裡,無所不在的主題正是:「能夠生而為人也就夠了」,而有如主旋律般貫穿其間,與之相呼應的訴求則是:「做我的朋友吧」。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在《魔笛》(The Magic Flute,譯註:莫扎特歌劇作品,劇作家為Emanuel Schikaneder)中看到同一類的人本精神。絕不像我們所熟悉的十八世紀人本理論,突顯的只是基本的人本觀念,根植於其上的卻是國族、民族、種族與宗教的分歧和人類的分裂;這種人本精神則是比較完整的、充實的。如果真有這種人本精神存在,那麼自然會有一種現象,要求行為應該符合「人之所以為人」,並主張人與自然的行為是一體的、同一的。十八世紀時,提倡這種人本觀念最不遺餘力、影響也最大的莫過於盧梭,對他來說,全人類共有的人本特質並非表現於理性而在於惻隱之心,亦即他所說的:不忍見同類受苦之心。在這方面,萊辛所見亦同,他曾說,最優秀的人就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但萊辛卻擔心同情心的一視同仁,亦即他所強調的,對壞人也「心懷同樣的惻隱」。但對盧梭來說,這卻不是問題;在以他的理想為依歸的法國革命精神中,他就看到了「博愛」這種人本的極致。萊辛卻別有所見,在他的心目中,友善──有選擇性的、有別於一視同仁的同情──才是人本真正的體現。
在談萊辛的友善觀念及其與公共事務相關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花上一點點時間,了解一下十八世紀對博愛的認知。對於博愛,萊辛也頗用過心思,他所說的「人道情懷」,指的就是以手足之情待人,縱使這個人是來自一個以恨為出發點,並以「非人」方式對待別人的世界。總之,我們的用意是要強調,在黑暗時代,這種以兄弟之情來彰顯人本的情形乃最為常見。當時代變得極端的黑暗,某些群體甚至因此無處可以容身時,其所想所行全都是退縮的,是自外於這個世界的,這時候,這種人本精神也就會自然流露。從歷史上來看,人本精神中的博愛情懷,每每出現在受迫害與受奴役的族群中;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當時的猶太人,在文化圈裡還算是新人,在他們中間就不難發現這種相濡以沫的情懷。這種情懷也是邊緣族群特有的本事。也正是憑藉著這種本事,社會的邊緣族群總能夠克服一切;但是,所要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隨之而來的,常是社會地位的徹底喪失,以及與社會對應的所有管道全面萎縮──在這個我們與他人共有的社會中,先是從我們賴以自我定位的常識開始,繼之以我們賴以認同這個社會的審美與品味──在極端的情況中,這種邊緣化往往長達好幾個世紀,我們大可稱之為無世界狀態(worldlessness),而無世界狀態無以名之,只能說它是野蠻狀態了。
彷彿人性的有機演化,處於受迫害的壓力之下,受迫害者彼此緊緊相依相靠,我們所說的那個社會中介空間便隨之消失(迫害未發生前,也正是這個中介空間使他們彼此分開),並因而在人際關係中產生一種溫情;對於這種有如物理現象的溫情,凡是接觸過這類族群的人,無不印象深刻。說它有如物理現象,我當然不是在貶抑受迫害者的這種溫情;事實上,它一旦成形之後,就會發展出一種純然的良善,那是人類無法在其他情況下培養出來的。這種溫情同時也是生命力的來源,是一種只要能夠活著便自然流露的喜樂,也就是說,對世俗所說的那種受侮辱者與受傷害者而言,生命之於他們,就是完完全全地活在其中。但是,講到這裡,我們切不可忘記,在那樣的環境之下,之所以能夠形成那樣的魔力與熱望,實在是因為這個世界的邊緣人仍然熱愛著這個世界,才能夠擁有那種甘之如飴的本事。
法國革命在博愛之外又加上了自由與平等,後二者在人類的公共領域中一直都是主要的項目,但是,在受壓迫者與受迫害者和受剝削者與受侮辱者中,亦即十八世紀所謂的「不幸者」和十九世紀的「悲慘者」中,博愛卻有著它固有的地位。萊辛與盧梭的同情(雖然內容頗有不同),在發現並肯定人性的普世一致上,以及首度在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譯註:法國大革命領導人之一,1758-1794)革命中成為中心的訴求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此以後,惻隱之心也就成為歐洲革命史上不可分割與顛撲不破的一部分。時至今日,惻隱之心更被視為是純乎自然的悲憫,每個人只要看到有人受苦,儘管與自己非親非故,都會油然而生同情;因此,這種情懷大可以拿來當作一個理想的基礎,擴展到全人類,建立一個天下一家的社會。十八世紀的人本主義者正是要透過革命的手段,企圖用惻隱之心將不幸者與悲慘者結合起來,亦即匯成一股以兄弟之情貫穿其間的力量;但是,很快地卻發現,這種人本主義的精華全在於社會邊緣人才擁有的那種特質,根本無法向外擴散,也是非邊緣人無法輕易擁有的。光是惻隱之心或不忍人之心顯然是不夠的。現代革命高舉同情弱勢的大旗,企圖改善不幸者的命運,而不是去建立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正義,因此而造成的傷害,在這裡我們就不談了;但是,為了多少了解我們自己與現代人的想法,有必要稍微回顧一下古代世界,看看在公共事務上涉足比我們深的古人,他們是如何看待惻隱之心與人本精神的。
無論今古,至少有一點是一致的,亦即都認為惻隱之心是純乎自然的,跟恐懼一樣,是人皆有之的。也正因為如此,現代人對同情心給予極高的評價,而古人的態度卻大不相同,也就不免令人感到詫異了。古人深知同情之心乃屬人的本性,跟恐懼一樣,若非刻意地予以排除,我們是無法抗拒的;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最富有同情心的人還不夠資格被稱為最優秀的人,反倒是最令人敬畏的人才足以當之。同情與害怕這兩種心性的傾向都是十足被動的,不可能具有行動力;亞里斯多德將同情與恐懼放在一起討論,理由即在於此。然而,這樣一來有可能將事情整個弄擰,不是將同情貶成了恐懼──好像別人受苦也會使我們自己感到恐懼似的──要不就是根本不敢去同情別人──好像在恐懼中我們就只能同情自己似的。更令人驚訝的是,在西塞羅(譯註:Marcus Tullius Cicero,羅馬哲學家,106-43 BC)的《托斯卡拉論爭》(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III 21)中,斯多噶學派居然將同情與嫉妒等量齊觀:「為別人的不幸而心有戚戚的人,對別人的幸運也會心有戚戚。」西塞羅自己對此也有類似的想法,在《托斯卡拉論爭》(IV 56)中他就說:「有能力的話就伸出援手,何必要可憐人家?難道不出於同情,我們就不能施予援手嗎?」換句話說,難道人類竟是如此吝嗇,非要看到別人受苦,受到自己感同身受的驅策,才會去採取人道的行動?
評斷這些心性的傾向時,我們很難不觸及無私的問題,或者更進一步說,對別人慷慨大度的問題,事實上,就「人本精神」一詞的終極意義來說,這才是它的先決條件。很明顯地,分享喜悅當然是好過於分擔痛苦。令人高興的事通常都是好的話題,而悲傷則否。在與他人的對話中,對方整個人與他所說的話都洋溢著歡喜,聊起來就絕對不同於一般的談話或討論事情。我們可以說,這是因為談話的調性是愉悅的。擋在這種歡喜前面的則是嫉妒,而說到人本,這種見不得別人好的心態乃是更等而下之的。但是,同情的對立面並不是嫉妒而是殘忍;殘忍之為一種心性的傾向,與同情可說是如出一轍,只不過它是一種變態,是喜樂中自然會有痛苦的一種感受。問題是,樂與苦都說不出口,儘管可能發出聲音,卻無法形諸言語,更不用說去跟別人說了。
以上所講的,不過是換一種說法來說明一個現象,亦即對於那些不屬於受侮辱者與受傷害者的人來說,天下一家的人本主義並不真能夠打動他們,就算他們贊同這種理念,頂多也只是出於同情而已。對於這個世界上不同地位的人,邊緣族群的溫情根本缺乏感染力,遑論給他們加上一份社會責任,至於邊緣族群甘之如飴的那種悲苦,他們當然更是無從體會了。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黑暗時代」中,溫情乃是一種光明的替代品,對那些不恥於社會現狀,寧願躲在暗無天日中求個心安理得的人來說,自有其另類的魅力。躲在沒有能見度的混沌之中,大可以置之不理那個清晰可見的世界,只要靠著一群緊緊靠在一起的人,溫情與博愛就能夠補償那個非常態的現實,儘管所到之處的人際關係都是一種無世界狀態,同那個全體人類所共有的世界一點關係都沒有。在這種無世界狀態與非常態的現實中,很容易得到一個結論,亦即全體人類所共有的成分並不是這個世界,而是某種「人的特質」。至於這種「人的特質」是什麼,那就因人而異了;有人說理性是人類共有的特質,有人卻說,某一種情感,例如惻隱之心,才是人類皆有的。但是,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與情感主義(譯註:情感主義〔sentimentalism〕,盛行於十八世紀的理論,主張所有關於這個世界的信念都決定於情感)就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兩者同樣都會引發極大的激情,讓個別的人產生人類本是一家的感覺。但無論怎麼說,侷限在一個沒有能見度的混沌領域中,也就跟那個清晰可見的共同世界斷絕了關係,理性與情感也都只是心理上的替代品而已。
由此可見,這種「人的特質」及其隨之而來的博愛情懷,只有在「黑暗時代」才得以彰顯,也正因如此,在這個世界上它是無法得到普遍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在一個能見度高的光明環境中,他們則會像鬼魅般地消失於無形。這種受侮辱者與受傷害者的人本精神往往倏忽即過,但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影響力,事實上剛好相反,它反而使得侮辱與傷害持續不斷,倒是在公共領域上,它的作用還真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