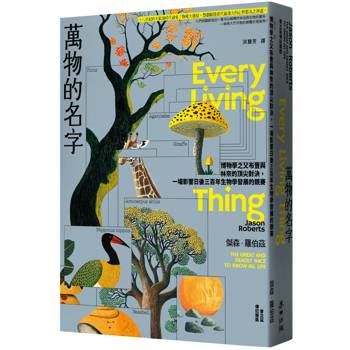關於卡爾.林奈的出生與童年,流傳著許多傳奇故事。家人和後人都試圖將他塑造成命中注定要踏上植物學聖殿的天選之子。一些可能虛構的傳說聲稱,這男孩出生時頂著一頭雪白的頭髮,那是「森林精靈」的標誌,後來頭髮才逐漸變成棕色。據傳,他襁褓時期異常躁動,難以安撫,唯獨母親在他的搖籃上方放上花束,才能讓他平靜下來。「鮮花成了卡爾最早、也最鍾愛的玩具。」
一位早期的傳記作家寫道,「父親有時會帶著剛滿週歲的小卡爾到花園,把他放在草地上,在他手裡放朵小花,讓他自得其樂。」
當時牧師宅邸百花齊放。林奈牧師已接替岳父成為本堂牧師,並舉家搬到斯滕布羅胡爾特的牧師宅。由於不必在教區內四處奔波,園藝成了他的嗜好。這位牧師的花園規模可觀,種植了數百種花卉。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那座別出心裁的「花宴」。那是一個圓形堆高的土台,布置得像張餐桌,上面精心栽培的植物宛如一道道豐盛的佳餚。餐桌邊緣的灌木則是修剪成賓客的模樣,彷彿正在用餐。據說年幼的卡爾常在這些想像的「賓客」陪伴下玩耍數個小時,還會花更多的時間照料附近一小塊屬於他的小園地。一位早期的傳記作家記載,這孩子「總終日流連田野林間尋覓花朵……其慈母曾嘆道,每當他覓得新花,就迫不及待拆解剖析,因為這小傢伙總是想盡可能深入探索自然的奧祕。」
甚至有故事記載,有人抓到小卡爾偷偷把花朵夾進家中的聖經裡。據說他解釋:「聖經是生命之書,若把花夾在書頁間,一定能永保花色,因為聖經會讓它們永遠活著。」
(中略)
在這片荒廢的花園裡,攝爾修斯通常能享受獨處時光,靜靜思索這些問題。但這個特別的春日,當他沿著殘存的小徑繞行時,卻看見另一人的身影。一位年輕人坐在長椅上,專注在筆記本上塗寫著。
他個子很小,不到五英尺高,身材瘦弱,幾乎像個精靈。他沒戴假髮,可見他不是有錢的紳士。他身上的衣服不只破舊,還不合身、搭配紊亂,好像是偷來或撿來的。一件磨得發白的外套,鬆垮垮掛在他瘦削的肩膀上。從他鞋子的破洞,可以看到塞進去的報紙碎片。
烏普薩拉大學裡有不少勉強度日的窮學生,但眼前這位看起來不像學生,反而更像乞丐。攝爾修斯走近才發現,這位年輕人不是在寫字,而是在現場寫生,用生硬、毫無美感的筆觸描繪著附近的一朵花。從明顯缺乏藝術美感(和技巧)來看,這顯然不是靜物寫生,而是在繪製植物圖譜。那朵花看來是研究用的實例。
「你在觀察什麼?」教授問道。
年輕人禮貌回答,但他不是回瑞典的俗名,而是引用了法國植物學家約瑟夫.皮頓.德.杜納福爾命名的冷門學名。這讓攝爾修斯很驚訝,他知道杜納福爾的植物分類系統是出了名的難學,需要死背六百九十八個類別。「你懂植物嗎?修過植物學嗎?」攝爾修斯追問:「你叫什麼名字?」
「卡爾.林奈。」
「哪裡人?」其實從這年輕人的鄉下口音,大概已經能猜到答案。他說起話來帶著鄉下人那種輕飄飄、不強調重音的腔調,口音很重,一聽就知道是農家子弟。
攝爾修斯隨手指向周圍的植物:「你認得這個嗎?那個呢?」林奈對答如流,接著還主動辨識周邊的雜草。
看來他不只是個勤奮的學生,還是個自學成才的植物行家。「你採集過多少植物標本?」教授問道。
「六百多種本地野花。」這數字是植物園現存品種的三倍。
攝爾修斯打量著這位不尋常的年輕人,他雖衣衫襤褸,但談吐像個大學教授。後來著名的博物學家約翰.繆爾如此描述林奈生命中的這個轉折點:「他眼裡裝滿了植物,但肚子卻常餓得發疼。看來,飢餓的歷練,是上天眷顧者必經的磨難。」
攝爾修斯做了一個衝動的決定。他家食指浩繁,廚房總是相當繁忙。他說:「跟我來。」突然轉身,朝著三個街區外的住家走去。他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對方跟隨,也沒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幾分鐘後,林奈坐在攝爾修斯家的餐桌前狼吞虎嚥,他比兩年半前離開斯莫蘭省的那個青年瘦削許多,也更加堅韌。為了醫學教育,他輾轉兩所大學,幾近身無分文。
第一站是父親的母校:波羅的海沿岸的隆德大學。父親求學時,這裡還是繁華的大學城,但後來接連遭遇大火肆虐、鼠疫蔓延,再加上瑞典與丹麥軍隊的輪番占領,這座曾被稱為「哥特人的倫敦」的北歐最大城市,如今已失去昔日的風華。林奈抵達時,隆德正逐漸衰敗,人口縮減至不到一千二百人。整片街區荒無人煙,只剩鵝群與野豬出沒。隆德大學的醫學院更是凋零,僅剩年邁的約翰.馮.多貝爾教授,對著寥寥數十名學生敷衍地喃喃授課。
林奈別無選擇,只能盡力適應。他在基利安.斯托貝歐斯醫生的家租了間閣樓。這位醫生雖與大學無關,但收藏了大量醫學、地質、化石方面的書籍,可惜他的書庫一直鎖著,只有他的德裔助手庫拉斯能接觸。庫拉斯是年輕的醫學院學生,林奈與他達成協議:他幫庫拉斯補習,以換取偷偷借閱那些藏書的機會。夜深人靜時,庫拉斯悄悄把書偷出來交給林奈。林奈徹夜苦讀,在翌日早上歸還,以免房東發現。可惜,好景不長。某日凌晨兩點,失眠的斯托貝歐斯醫生舉著蠟燭在屋裡閒晃,發現這位房客伏案酣睡,身邊放著幾本禁書。
斯托貝歐斯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對眼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醫生搖醒林奈,考問他偷讀的內容後,更是另眼相待。庫拉斯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因為不久後,斯托貝歐斯就把林奈當成愛徒栽培,不僅讓他自由進出書房、提供他免費餐點,還帶他一起出診。林奈後來回憶道:「他待我如子,而非學生。」但這份恩情終究難以消除他心中的鬱結。畢竟,斯托貝歐斯的提攜,改變不了隆德城的頹勢。在這座日漸衰敗的城市裡,讀著名存實亡的醫學院,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後略)
Chapter6 ─耐心的極致
在蒙巴德,布豐為自己設計了一套最有效率的生活方式,力求身心維持在最佳狀態以延年益壽。
他和他的偶像牛頓不同,牛頓終身獨居禁欲(伏爾泰說他「毫無熱情,亦無弱點」),布豐深知自己天性貪圖享樂,容易怠惰放縱。為了對抗這種天性,他制定了嚴格的作息:每日清晨五點,貼身男僕約瑟夫必會準時出現,奉命無論如何都要叫醒他。約瑟夫認真執行這項任務,有時甚至得把主人拖下床。某日早晨,約瑟夫怎麼哄勸布豐起床都沒用,只好朝他熟睡的身軀潑了一盆冰水,隨即逃到隔壁房間,擔心自己做得太過分。沒想到,主人搖鈴召喚他回來。布豐平靜地說:「給我拿乾淨的襯衣來,但下次,我們盡量別折騰自己,這樣對我們彼此都好。」
說完還賞了約瑟夫三法郎作為獎勵。
布豐起床後,還會準備一個鐘頭左右,才會踏出寢室。他堅持每天盛裝打扮,這樣做不是為了賓客,只是為了自己。他認為正裝打扮有助集中精神,即便獨處時,那份莊重感也能時時刻刻提醒他莫忘初心。等髮型師為他卷好頭髮、撲上髮粉後,他會趁著晨光初現,步行穿過蒙巴德的街道,前往布豐公園。
他沿著古老堡壘的斜坡緩步上行,如今這裡已圍起柵欄,建成階梯平台,四周林木環繞。那裡有兩間靜室供他使用。一間是主工作室,是公園邊緣的單間結構,內部極其簡樸,常被誤認為園藝棚。
一間在殘存的中世紀塔樓內,石砌的圓形空間隔熱良好,是天然的避暑空間。這兩個房間的陳設相同,都只有一張寫字檯、一個壁爐、一幅牛頓爵士的肖像。除了遠山的景色以外,沒有別的干擾。誠如一位稀客所言:
在那空蕩蕩的房間裡,他坐在一張木製的寫字檯前沉思、寫作。面前沒有紙張,也沒有堆積的書籍,那些學究式的累贅只會妨礙布豐的思緒。一個深思熟慮的主題,純粹的冥想,絕對的靜謐與孤獨,這些才是他的研究素材與工具。
他寫作時,全憑先前閱讀的記憶和自己的沉思,從不翻閱書籍或筆記。但這不是因為他喜歡幽閉的空間,這些房間之所以狹小,是因為他把整座公園當成工作室,隨著靈感的湧現,在靜室與戶外來來回回。另一位訪客描述:「他走來走去,長時間深入思考他想寫的內容。可以說,他先讓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奇妙中以汲取養分,待思緒蓬勃湧現,才提筆寫下數行,隨即又繼續散步或沉思。」
上午九點,他會暫停下來,快速吃個早餐。他的早餐永遠都是一個麵包捲,配兩杯葡萄酒。接著,他又繼續工作到下午兩點,再與家人、朋友或賓客悠閒共進午餐。餐後,他會小睡片刻,然後又獨自在花園裡散步。
這段午後漫步對他很重要,若有賓客或傭人在園中巧遇他,他們都知道最好裝作沒看見。下午五點,他會回到靜室,在工作兩小時後,結束一天的工作。為了維持工作環境的簡樸,以便翌日早上繼續工作,他會把手稿交給秘書謄寫成一份乾淨的副本,添加到正在撰寫的文稿中,原稿則直接扔進壁爐焚毀。
後世史家每每為此扼腕,布豐習慣在用完手稿後就焚毀。他認為這些手稿對他的創作過程來說,就如同木屑之於木匠一般多餘。他向一位訪客解釋:「我燒盡一切手稿。待我死後,片紙不留。若非如此,我永遠無法完成工作,遲早會被自己的手稿淹沒。」
晚上七點開始,是他一天中最熱鬧的沙龍時光。賓客喝著葡萄酒暢談,多數人都懂得在來之前先吃飽,因為布豐向來不吃晚餐,他堅持空腹到隔天。九點整,他便告退就寢。
他維持這樣的作息整整五十年。雖然待在巴黎時無法那麼規律,但他會盡量維持這種以沉思為核心的生活步調。對於這種嚴格自律的獨處時光,他一點也不覺得苦悶,反倒如他晚年回憶所言:「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樂趣所在。」
你必須長時間關注你研究的主題。漸漸地,它自然會展開,開始發展。你會感覺到彷彿有股微小的電流擊中頭部,同時觸動心臟,這就是靈光乍現的時刻,也是體會工作樂趣的瞬間……比起追求榮耀,我更醉心於這種靈感的喜悅。榮耀是隨之而來的點綴。該來的,終究會來,它幾乎一定會到。
======
布豐與林奈同於一七○七年出生,兩人都傾盡畢生心血編纂巨著,意圖涵蓋自然界的全貌,但都未能如願。然而,他們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林奈是系統分類學派(systematist)的代表人物,這個學派的自然史學家將命名和標籤視為首要之務,遠比其他研究重要。布豐研究自然的方式比較複雜,他從來不覺得有必要為自然貼標籤。這種思想或許可稱為「複雜主義」(complexism)。
在林奈眼中,自然是名詞,所有的物種自創世以來恆定不變,有如一幅靜止的畫作。對布豐而言,自然是動詞,是不斷變化的漩渦。林奈認為分類就是知識:若不將生命整理為整齊的類別,那要如何了解萬物?布豐則認為分類是過度簡化,雖然實務上有用,卻可能埋下根本的誤解。林奈認為單一實例可以代表其所屬的物種,展現其獨到「本質」。布豐則認為物種是流動的,冥冥之中有未知的力量,在時間的長河裡連結所有的生命。
一位早期的傳記作家寫道,「父親有時會帶著剛滿週歲的小卡爾到花園,把他放在草地上,在他手裡放朵小花,讓他自得其樂。」
當時牧師宅邸百花齊放。林奈牧師已接替岳父成為本堂牧師,並舉家搬到斯滕布羅胡爾特的牧師宅。由於不必在教區內四處奔波,園藝成了他的嗜好。這位牧師的花園規模可觀,種植了數百種花卉。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那座別出心裁的「花宴」。那是一個圓形堆高的土台,布置得像張餐桌,上面精心栽培的植物宛如一道道豐盛的佳餚。餐桌邊緣的灌木則是修剪成賓客的模樣,彷彿正在用餐。據說年幼的卡爾常在這些想像的「賓客」陪伴下玩耍數個小時,還會花更多的時間照料附近一小塊屬於他的小園地。一位早期的傳記作家記載,這孩子「總終日流連田野林間尋覓花朵……其慈母曾嘆道,每當他覓得新花,就迫不及待拆解剖析,因為這小傢伙總是想盡可能深入探索自然的奧祕。」
甚至有故事記載,有人抓到小卡爾偷偷把花朵夾進家中的聖經裡。據說他解釋:「聖經是生命之書,若把花夾在書頁間,一定能永保花色,因為聖經會讓它們永遠活著。」
(中略)
在這片荒廢的花園裡,攝爾修斯通常能享受獨處時光,靜靜思索這些問題。但這個特別的春日,當他沿著殘存的小徑繞行時,卻看見另一人的身影。一位年輕人坐在長椅上,專注在筆記本上塗寫著。
他個子很小,不到五英尺高,身材瘦弱,幾乎像個精靈。他沒戴假髮,可見他不是有錢的紳士。他身上的衣服不只破舊,還不合身、搭配紊亂,好像是偷來或撿來的。一件磨得發白的外套,鬆垮垮掛在他瘦削的肩膀上。從他鞋子的破洞,可以看到塞進去的報紙碎片。
烏普薩拉大學裡有不少勉強度日的窮學生,但眼前這位看起來不像學生,反而更像乞丐。攝爾修斯走近才發現,這位年輕人不是在寫字,而是在現場寫生,用生硬、毫無美感的筆觸描繪著附近的一朵花。從明顯缺乏藝術美感(和技巧)來看,這顯然不是靜物寫生,而是在繪製植物圖譜。那朵花看來是研究用的實例。
「你在觀察什麼?」教授問道。
年輕人禮貌回答,但他不是回瑞典的俗名,而是引用了法國植物學家約瑟夫.皮頓.德.杜納福爾命名的冷門學名。這讓攝爾修斯很驚訝,他知道杜納福爾的植物分類系統是出了名的難學,需要死背六百九十八個類別。「你懂植物嗎?修過植物學嗎?」攝爾修斯追問:「你叫什麼名字?」
「卡爾.林奈。」
「哪裡人?」其實從這年輕人的鄉下口音,大概已經能猜到答案。他說起話來帶著鄉下人那種輕飄飄、不強調重音的腔調,口音很重,一聽就知道是農家子弟。
攝爾修斯隨手指向周圍的植物:「你認得這個嗎?那個呢?」林奈對答如流,接著還主動辨識周邊的雜草。
看來他不只是個勤奮的學生,還是個自學成才的植物行家。「你採集過多少植物標本?」教授問道。
「六百多種本地野花。」這數字是植物園現存品種的三倍。
攝爾修斯打量著這位不尋常的年輕人,他雖衣衫襤褸,但談吐像個大學教授。後來著名的博物學家約翰.繆爾如此描述林奈生命中的這個轉折點:「他眼裡裝滿了植物,但肚子卻常餓得發疼。看來,飢餓的歷練,是上天眷顧者必經的磨難。」
攝爾修斯做了一個衝動的決定。他家食指浩繁,廚房總是相當繁忙。他說:「跟我來。」突然轉身,朝著三個街區外的住家走去。他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對方跟隨,也沒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幾分鐘後,林奈坐在攝爾修斯家的餐桌前狼吞虎嚥,他比兩年半前離開斯莫蘭省的那個青年瘦削許多,也更加堅韌。為了醫學教育,他輾轉兩所大學,幾近身無分文。
第一站是父親的母校:波羅的海沿岸的隆德大學。父親求學時,這裡還是繁華的大學城,但後來接連遭遇大火肆虐、鼠疫蔓延,再加上瑞典與丹麥軍隊的輪番占領,這座曾被稱為「哥特人的倫敦」的北歐最大城市,如今已失去昔日的風華。林奈抵達時,隆德正逐漸衰敗,人口縮減至不到一千二百人。整片街區荒無人煙,只剩鵝群與野豬出沒。隆德大學的醫學院更是凋零,僅剩年邁的約翰.馮.多貝爾教授,對著寥寥數十名學生敷衍地喃喃授課。
林奈別無選擇,只能盡力適應。他在基利安.斯托貝歐斯醫生的家租了間閣樓。這位醫生雖與大學無關,但收藏了大量醫學、地質、化石方面的書籍,可惜他的書庫一直鎖著,只有他的德裔助手庫拉斯能接觸。庫拉斯是年輕的醫學院學生,林奈與他達成協議:他幫庫拉斯補習,以換取偷偷借閱那些藏書的機會。夜深人靜時,庫拉斯悄悄把書偷出來交給林奈。林奈徹夜苦讀,在翌日早上歸還,以免房東發現。可惜,好景不長。某日凌晨兩點,失眠的斯托貝歐斯醫生舉著蠟燭在屋裡閒晃,發現這位房客伏案酣睡,身邊放著幾本禁書。
斯托貝歐斯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對眼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醫生搖醒林奈,考問他偷讀的內容後,更是另眼相待。庫拉斯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因為不久後,斯托貝歐斯就把林奈當成愛徒栽培,不僅讓他自由進出書房、提供他免費餐點,還帶他一起出診。林奈後來回憶道:「他待我如子,而非學生。」但這份恩情終究難以消除他心中的鬱結。畢竟,斯托貝歐斯的提攜,改變不了隆德城的頹勢。在這座日漸衰敗的城市裡,讀著名存實亡的醫學院,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後略)
Chapter6 ─耐心的極致
在蒙巴德,布豐為自己設計了一套最有效率的生活方式,力求身心維持在最佳狀態以延年益壽。
他和他的偶像牛頓不同,牛頓終身獨居禁欲(伏爾泰說他「毫無熱情,亦無弱點」),布豐深知自己天性貪圖享樂,容易怠惰放縱。為了對抗這種天性,他制定了嚴格的作息:每日清晨五點,貼身男僕約瑟夫必會準時出現,奉命無論如何都要叫醒他。約瑟夫認真執行這項任務,有時甚至得把主人拖下床。某日早晨,約瑟夫怎麼哄勸布豐起床都沒用,只好朝他熟睡的身軀潑了一盆冰水,隨即逃到隔壁房間,擔心自己做得太過分。沒想到,主人搖鈴召喚他回來。布豐平靜地說:「給我拿乾淨的襯衣來,但下次,我們盡量別折騰自己,這樣對我們彼此都好。」
說完還賞了約瑟夫三法郎作為獎勵。
布豐起床後,還會準備一個鐘頭左右,才會踏出寢室。他堅持每天盛裝打扮,這樣做不是為了賓客,只是為了自己。他認為正裝打扮有助集中精神,即便獨處時,那份莊重感也能時時刻刻提醒他莫忘初心。等髮型師為他卷好頭髮、撲上髮粉後,他會趁著晨光初現,步行穿過蒙巴德的街道,前往布豐公園。
他沿著古老堡壘的斜坡緩步上行,如今這裡已圍起柵欄,建成階梯平台,四周林木環繞。那裡有兩間靜室供他使用。一間是主工作室,是公園邊緣的單間結構,內部極其簡樸,常被誤認為園藝棚。
一間在殘存的中世紀塔樓內,石砌的圓形空間隔熱良好,是天然的避暑空間。這兩個房間的陳設相同,都只有一張寫字檯、一個壁爐、一幅牛頓爵士的肖像。除了遠山的景色以外,沒有別的干擾。誠如一位稀客所言:
在那空蕩蕩的房間裡,他坐在一張木製的寫字檯前沉思、寫作。面前沒有紙張,也沒有堆積的書籍,那些學究式的累贅只會妨礙布豐的思緒。一個深思熟慮的主題,純粹的冥想,絕對的靜謐與孤獨,這些才是他的研究素材與工具。
他寫作時,全憑先前閱讀的記憶和自己的沉思,從不翻閱書籍或筆記。但這不是因為他喜歡幽閉的空間,這些房間之所以狹小,是因為他把整座公園當成工作室,隨著靈感的湧現,在靜室與戶外來來回回。另一位訪客描述:「他走來走去,長時間深入思考他想寫的內容。可以說,他先讓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奇妙中以汲取養分,待思緒蓬勃湧現,才提筆寫下數行,隨即又繼續散步或沉思。」
上午九點,他會暫停下來,快速吃個早餐。他的早餐永遠都是一個麵包捲,配兩杯葡萄酒。接著,他又繼續工作到下午兩點,再與家人、朋友或賓客悠閒共進午餐。餐後,他會小睡片刻,然後又獨自在花園裡散步。
這段午後漫步對他很重要,若有賓客或傭人在園中巧遇他,他們都知道最好裝作沒看見。下午五點,他會回到靜室,在工作兩小時後,結束一天的工作。為了維持工作環境的簡樸,以便翌日早上繼續工作,他會把手稿交給秘書謄寫成一份乾淨的副本,添加到正在撰寫的文稿中,原稿則直接扔進壁爐焚毀。
後世史家每每為此扼腕,布豐習慣在用完手稿後就焚毀。他認為這些手稿對他的創作過程來說,就如同木屑之於木匠一般多餘。他向一位訪客解釋:「我燒盡一切手稿。待我死後,片紙不留。若非如此,我永遠無法完成工作,遲早會被自己的手稿淹沒。」
晚上七點開始,是他一天中最熱鬧的沙龍時光。賓客喝著葡萄酒暢談,多數人都懂得在來之前先吃飽,因為布豐向來不吃晚餐,他堅持空腹到隔天。九點整,他便告退就寢。
他維持這樣的作息整整五十年。雖然待在巴黎時無法那麼規律,但他會盡量維持這種以沉思為核心的生活步調。對於這種嚴格自律的獨處時光,他一點也不覺得苦悶,反倒如他晚年回憶所言:「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樂趣所在。」
你必須長時間關注你研究的主題。漸漸地,它自然會展開,開始發展。你會感覺到彷彿有股微小的電流擊中頭部,同時觸動心臟,這就是靈光乍現的時刻,也是體會工作樂趣的瞬間……比起追求榮耀,我更醉心於這種靈感的喜悅。榮耀是隨之而來的點綴。該來的,終究會來,它幾乎一定會到。
======
布豐與林奈同於一七○七年出生,兩人都傾盡畢生心血編纂巨著,意圖涵蓋自然界的全貌,但都未能如願。然而,他們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林奈是系統分類學派(systematist)的代表人物,這個學派的自然史學家將命名和標籤視為首要之務,遠比其他研究重要。布豐研究自然的方式比較複雜,他從來不覺得有必要為自然貼標籤。這種思想或許可稱為「複雜主義」(complexism)。
在林奈眼中,自然是名詞,所有的物種自創世以來恆定不變,有如一幅靜止的畫作。對布豐而言,自然是動詞,是不斷變化的漩渦。林奈認為分類就是知識:若不將生命整理為整齊的類別,那要如何了解萬物?布豐則認為分類是過度簡化,雖然實務上有用,卻可能埋下根本的誤解。林奈認為單一實例可以代表其所屬的物種,展現其獨到「本質」。布豐則認為物種是流動的,冥冥之中有未知的力量,在時間的長河裡連結所有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