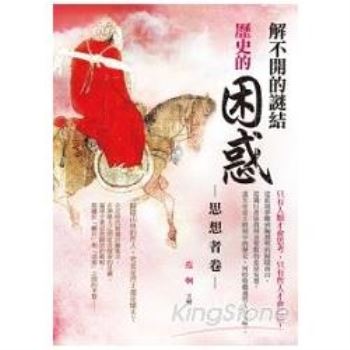在中國歷史上,每位換屆初政的帝王都致力於前代衰敗教訓的總結,以期自己的家天下能夠萬世千秋。蕭道成這位「常有四海之心」的南齊新帝亦不例外。他鑑於劉宋骨肉相殘,清談誤國的前車之鑑,始重務實從儉,削減藩王勢力,推行儒術等等,保證了南齊兩代帝王統治十四年間相安無事。由於劉瓛的儒業冠於當時,甚至被尊為「關西孔子」,都下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於其門下,劉瓛的弟子一時身價陡增。蕭道成曾召劉瓛入華林園請教為政之道,連當時頗負盛譽的佛學家王子良也登門受教。因此,范縝初入仕途可謂通達,官拜尚書殿中郎,使儒術左右言路。至齊武帝蕭賾時,范縝等儒臣鑑於南北之間戰亂不絕的狀況,力主與北魏實行和親政策,化干戈為玉帛,歲通聘好。武帝特意遴選才學之士通使南北,作為和平使者,范縝及從弟范雲、蕭琛、嚴幼明、裴昭明等儒學者皆在膺選之列,奔南走北,成為北魏王朝的知名人物。此時期,范縝盡施所學,頗受朝廷器重,使南朝顯示振興儒業的一線曙光。
范縝從來也沒有想到像劉邦、項羽那樣去奢望「取而代之」,他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就是恢復儒教所鼓吹的社會秩序。在官居顯職之後,他似乎感到實現這一目標已十分現實,於是竭力報效朝廷,一改入仕前那種「卓越不群」和「危言高論」的舊模樣。劉宋和南齊的諸多皇帝似乎都未找到一種治世有效的思想和理論,這使得佛、道、儒三教在當時互爭雄長,都具有各自的勢力範圍,又以佛、儒二家影響為大。齊武帝時,文惠太子蕭長懋篤信釋老,以王子良居住的西邸為佛教聖地,扶植起一大批名僧教徒,終日講說佛法微言大意。於是,佛教能否成為治理國家的理論問題,便歷史地被提了出來。
從佛教初入中國的漢代迄於南北朝,是外域異質文化進入中國,並使中國傳統文化在與佛教文化的全面碰撞後之顯現新姿的重要時期。據梁釋慧皎撰《高僧傳》記載,從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年)至梁武帝天監十八年(五一九年)的四百五十三年間,著名佛教徒就達二百五十七人。於是,皇帝倡導於上,僧徒鼓噪於下,更兼佛教本身體大思精的佛理教義、體系完備的禪門戒律、深邃美奐的哲思和仙境,日益征服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大有取代儒、道而躍居國教之勢。
在佛教咄咄逼人的攻勢下,道教雖相形見絀,卻也不甘居頹流。進入南北朝以後,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詡奉太上老君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道教廓清混亂,發展為北天師道。由於寇謙之宣稱以「佐國扶命」為宗旨,因此得到魏太武帝和儒臣崔浩等人的支持。在南朝劉宋時代,廬山道士陸修靜「總括三洞」,匯歸一脈,改革五斗米道而發展為南天師道,亦稱「意在王者遵奉」。這樣,道教經過全面整頓之後,似也有了與佛教相抗衡的力量。
而一直作為統治理論的儒教,自東漢以後雖幾度浮沉,至南朝「關西孔子」劉瓛的大力扶植鼓吹,也有重振雄風之勢,加之其弟子門生遍及朝廷要樞,擁有范縝等一批堅定的擁護者,儒學便因政治實力也取得鼎足而立的地位。
佛門修來世,解決現實問題如隔靴搔癢。
道法重今生,丹鼎和符籙亦無濟國事民生。
儒家講秩序,國家也許會因此而獲得穩定發展。
范縝在三教爭弘的紛紜膠葛之中,十分現實地選擇了儒術。他十分清楚地看出,對於泛濫成災的佛經道藏和演成大勢的求佛問道風氣,僅靠一紙詔書或行政干預手段是無濟於事的。對於精神的毒風霧瘴,只能用精神的武器去摧毀。他遍搜古代思想武庫,繼承了王充等思想家的思想,以「神滅」為論點,向彌漫時風的佛道學說發起衝擊。
此時,王子良在西邸的佛事活動盛極一時,廣招名公碩輔,其中蕭衍(後來的梁武帝)、沈約、謝脁、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皆為西邸常客,號稱「八友」。范縝也在應邀之列,卻不願加入這些由佛門精銳組成的顯貴行列之中。王子良精信釋教,本欲邀范縝以壯聲勢,卻不料請進一位佛門剋星。
范縝在西邸「盛稱無佛」,不啻在大婚喜筵內樹起弔孝的幡幢,頓時激起洶洶非議,一場舌戰在佛堂內掀起。王子良集合起名僧一齊上陣,首先發難,聲勢奪人地問道:「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劈面而來的一句,道出佛家的理論支柱││因果報應。
這使我們不禁想到「生於西域林木之上」的唐代佛教詩人王梵志的名詩,其詩曰:
世間日月明,皎皎照眾生。
貴者乘車馬,賤者膊擔行。
富者前生種,賤者慳貧生。
貧富有殊業,業報自相迎。
聞強造功德,吃著自身榮。
智者天上去,愚者入深坑。
說得何等淺顯易懂,何等明白曉暢!為了死後「天上去」,來生「乘車馬」,芸芸眾生,都來拜佛吧!
不料,范縝成竹在胸,答詞更妙,導因果之論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