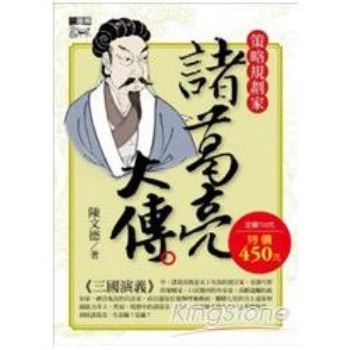第一篇 孔明出山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圯。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梁父吟>
第一章 亂世童年
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鍛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官逼民反,農民起義
東漢王朝後半段的百年間,朝廷裡外戚和宦官急著奪權,地方豪族則忙著兼併土地及累積財富。貧富懸殊嚴重,破產的農民流浪四方,被饑饉及窮困追著四處跑,在以農立國的中國古代社會,農民失去田地,成為浪人,勢必導致社會重大的動亂。
順帝以後的二十年間,無法生存而流亡各地的貧民集團,不得不揭竿起義,爭取最起碼的生存空間。但傳統的史書,例如《後漢書》及《資治通鑑》等,大多以「妖賊」或「盜賊」稱之,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諸葛亮日後大老闆劉備的長期宿敵曹操,在平定兗州後,曾將三十餘萬黃巾黨人收編為「青州軍」,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同情立場,面對農民起義的政治領袖。
這些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大多帶有濃厚宗教色彩,他們分別被稱為「無上將軍」、「黃帝」或「黑帝」,組織龐大而鬆懈,全靠宗教力量結合。在這一系列的民變事件中,以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的黃巾黨人事變規模最大,影響也最深。
黃巾黨人的領袖是鉅鹿人(河北省南部)張角,是位非常有名的民間密醫,以神秘的宗教醫術,醫療患病的農民。張角的治療法,是讓患者先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入飲之。先不問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張角的治病是宗教性大於醫療性的。這樣子的治病法,即使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仍到處流行著,在醫學不發達的當時,影響力自然更大了。張角的弟子遍佈全國各地,都擅長這種神水醫療術,由於碰到苦難當頭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脹,總稱為「太平道」。
據張角自己的說法,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傳授的《太平清領書》,囑咐他推展太平道以救世。在數十年間,以青州(現山東省)為中心,遍佈冀、徐、荊、揚、兗、豫等州。擁有數十萬信徒,盤據在十三州中的三分之二江山。
到了光和年間,太平道的影響力,已不止於下階層的農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於官僚也趨之若騖。依《後漢書》記載,執宦官主流派集團牛耳的大常侍張讓,便與張角有相當密切的來往。
眼見太平道急速膨脹,朝廷有志之士自然產生了危機意識。清流派的楊賜,首先上書主張一方面招撫流民,給予土地耕種,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搜捕太平道在各地的領袖,以削弱其組織力量。劉陶、樂松、袁貴等也聯名上書靈帝,主張逮捕張角,以免事件繼續擴大。
由於親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靈帝在軟硬政策間舉棋不定,終於消息外洩,反而使張角加速強化其組織。不久,張角便將全國信徒分為三十六「方」,大「方」編組萬餘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均由直屬子弟統領指揮。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並封其弟張寶為「地公將軍」,張梁為「人公將軍」,共同統率著三十六萬人馬。
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向信徒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當年正好是甲子年,是六十年干支歲月的重新開始。張角決定在是年三月五日,散佈各地的三十六萬信徒同時起義。依照中國傳說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的循環理論,漢王朝屬火德、剋火者土,因此代替漢王朝者應屬土德。黃土高原和黃土平原的土都是黃色的,所以太平道信徒,均以黃色頭巾為標幟,這也是黃巾黨人的由來。
負責攻打洛陽的大方馬元義,行動不夠謹慎,三月三日未到便陰謀敗露被捕,同行的黨人有數千人遇害。靈帝到此才恍然大悟,發出逮捕張角的通緝令。
迫不得已,張角會同兩位弟弟,提早一個月起義。雖然準備不周,仍有七州二十八郡響應,頭綁黃色頭巾的黨人,攻擊官府,佔領田園,不少郡縣官吏聞風而逃,《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黃巾黨人的主要戰場,在洛陽附近的潁川地區,北起冀州西南區,南至南陽一帶。朝廷以何皇后之兄何進為河南尹,負責攻防總指揮,實際負責作戰的是司隸軍區中最精銳的師團,分別由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北中郎將盧植率領。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一章回便是劉備在涿郡募集義兵,響應政府號召,共同對抗黃巾黨人民變的情節。劉備在此認識關羽和張飛,留下了「桃園三結義」的千古美談。
戰爭初期,黃巾黨人聲勢浩大,張角和盧植大戰於冀州,盧植軍團寡不敵眾,被迫向南撤退。防守在潁川附近的朱軍團亦遭擊退,南陽太守甚至在會戰中陣亡。
為了保護京城洛陽的安全,皇甫嵩將主力部隊佈防在潁川附近。張角以數萬兵馬層層包圍,皇甫嵩親往前線視察,他看到黃巾黨人均以茅草結營,乃趁夜色掩護,以火攻戰術突擊,張角軍團大亂,佈防在潁川南岸的朱軍團也趁機反攻,洛陽方面前來救援的典軍校尉曹操,率領騎兵部隊及時趕到,三方面夾擊下,黃巾黨人大敗,死傷高達數萬人,這也是朝廷部隊第一次成功阻擋黃巾黨人攻擊的正式記錄。
靈帝中平元年八月,張角病死;十月,人公將軍張梁的軍團在潁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傷三萬餘人,張梁本人也在潰敗中遭到擊殺;十一月,地公將軍張寶也戰死在南陽會戰中,黃巾黨人的主力部隊,到此完全殲滅。
但散居各地的黃巾黨人仍遙相呼應。并州的白波軍、冀州的黑山軍、益州和青州的黃巾軍,聲勢浩大,均讓各地方政府頭痛不已。皇甫嵩等雖在洛陽附近獲得絕對勝利,但在數度大規模會戰後,主力部隊也遭到了重創,根本無力再協助各地方政府剿亂。朝廷為了鞏固地方秩序,平定黨人的作亂,也不得不強化北方首長的行政權及軍事權。
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年)三月,朝廷接受江夏太守劉焉建議,擴大部分嚴重動亂地區刺史的權限,並改稱「牧」。劉焉為益州牧,黃琬為豫州牧,劉虞為幽州牧。《資治通鑑》記載:「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這些地方州牧,權限逐步擴大,漸漸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失去了指揮權和控制力,終於釀成了漢末群雄割據的局面,東漢王朝也步入名存實亡的境地了。
動盪社會,流浪孤兒
黃巾黨人起義的那個甲子年二月,諸葛亮正好滿四歲。
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時出任泰山郡郡丞,泰山郡中的泰山是中國自古以來有名的靈山,諸葛亮便在這附近渡過他最早期的童年。
諸葛亮本籍在瑯琊郡,當時稱為陽都縣,約在今山東省臨沂縣和沂南縣之間,同屬於山東省的西北區。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
泰山之南有魯國,北方則有齊國,瀕山臨海間有塊相當肥沃的平原,或產桑樹和麻類植物,麻、絹等織製品便成了這裡的名產。主要的大城市臨沼位於渤海及泰山間,這裡的人一向思慮較深,並且好作議論,行事從不輕舉妄動,這些人個別能力都很強,但集體作戰力則偏弱,是典型的工商社會,國家的經濟力旺盛而活躍,住民大約可分成士、農、工商、工、坐商等五種職業。
思慮周密,好作議論,絕不輕舉妄動的性格,的確相當明顯地可以在諸葛亮身上發現。
從姜太公在齊地建國以來,這裡一向便是南北貨貿易重心,經濟力量旺盛,因此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地方為高,東漢到六朝時代,有不少名人皆出身於此,例如協助苻堅建立前秦帝國的王導,不朽的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顏氏家訓》作者顏之推,及唐代書聖顏真卿等,都是當地的名家豪族。
另一個特色是齊國的兵學思想。齊軍一向以怯戰出名,因此更用心於研究戰爭的技巧和方法。姜太公的兵法學是戰爭的原則,也是生意者的策略。一代兵學宗師孫武,也是齊國人,《孫子兵法》中的準備和應變工夫,相信和齊國傳統的處世哲學有關。《鬼谷子兵法》,也是以齊國為其發源地,孫臏、龐涓,甚至於蘇秦、張儀都是在這裡學成的。除了在襄陽地區居住時,和當地的名士學者切磋研習外,諸葛亮的思想、言行及人生觀,顯然也是和齊國傳統的文化有關。
韋昭寫的《吳書》中記載:諸葛亮的先祖原姓葛氏,居住在瑯琊郡諸縣,當時他們整族人不知在什麼原因下,遷往陽都縣。由於陽都縣裡也住有很多葛氏人家,為了有所區別,乃將諸縣遷移過來的葛氏,稱之為諸葛氏。
諸葛亮的祖父諸葛豐曾任東漢王朝的司隸校尉(京城警備總監),他是位負責盡職的官員,個性剛強正直,執起法來,任何權勢都毫不在意。
官位高居侍中的外戚許章,平常假借皇威為非作歹,諸葛豐下令逮捕,許章逃往禁宮,要求皇帝保護。諸葛豐也曾正式上文彈劾許章,並要求嚴厲處分,以免傷害皇權。雖然皇帝有意調節兩人的爭執,但諸葛豐義正詞嚴,皇帝不得已,祇得處分許章。然不久,諸葛豐便被免除司隸校尉之職務,並且廢為庶人,不過諸葛豐這種高風亮節、執法嚴正的個性,顯然也遺傳在諸葛亮的身上。
諸葛亮之父諸葛珪,曾任泰山郡郡丞(主任秘書),其妻章氏。兩人共育有四位子女,諸葛亮排行老三,長兄諸葛瑾,弟弟諸葛均,另有姊姊一人。九歲時母親章氏去世,為了照顧年幼的子女,父親另娶了後母,但三年後父親也去世了。喪失雙親的諸葛兄弟,由於後母無力扶養他們,全靠叔父諸葛玄接濟。長兄諸葛瑾大諸葛亮七歲,母親去世前,曾在洛陽太學府遊學,專攻《毛詩》、《尚書》、《左傳春秋》,成績優異。母親去世時,他為了服喪及照顧弟妹,毅然放棄學業,返回家鄉。
瑯琊郡屬徐州,黃巾黨人起義初期,這裡也備受干擾,但當朝廷派來武夫出身的陶謙為徐州刺史後,動亂總算平息了下來。其後的董卓之亂,關東諸侯勤王起義的戰爭,徐州在陶謙力保中立的政策下,總算未受波及。所以當洛陽一帶陷入戰亂時,不少人「流移東出,多依徐土」。但就在漢獻帝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起,雄據兗州的曹操,其父曹嵩在徐州意外被害,曹操乃興兵攻打徐州,陶謙雖奮勇抵抗,但整個徐州立刻陷入兵荒馬亂中,位於徐州北部的瑯琊郡也遭到波及。有些地方甚至「雞犬亦盡,墟色無復行人」。負責一家安危的諸葛玄,不得不設法離開家鄉,暫避戰亂。
隔年,諸葛亮十四歲的時候,諸葛玄被反董卓集團的南區領袖--揚州軍閥頭子袁術任命為豫章郡太守(今江西南昌附近)。諸葛玄帶著年幼的諸葛亮姊弟們前往赴任。並藉以暫避禍亂。但年紀已二十一歲的諸葛瑾,必須擔負重建家聲的責任,因此他決定另找生路,以免寄人籬下,幾經思索後,和繼母遠赴江東。一家人從此離散,各奔東西。
從徐州北部經由豫州,南下到豫章的路途上,這幾年的兵荒馬亂最為嚴重,曹操及陶謙間數度惡戰、不少農民叛變都發生在這地方。青少年期的諸葛亮親眼目睹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更不幸的是,諸葛玄到任後不久,東漢朝廷又派朱皓為豫章太守,使豫章太守的位置鬧了雙胞。不過朱皓上任的時候,由揚州刺史劉鏢處借得大批軍隊,直接向「非正牌」的諸葛玄施壓。諸葛玄方面,袁術雖然聲勢浩大,但正和曹操準備交戰中,自顧不暇,根本無法給諸葛玄任何實質的幫助。何況自己非朝廷命官,名不正言不順,勢單力薄,自然無力抵擋,為了顧全面子及家人安全,祇得匆匆撤離。
家鄉是不願也不可能回去,諸葛玄祇好將諸葛亮一家帶到荊州的襄陽城,去依靠老朋友荊州刺史劉表了。荊州刺史劉表早年也名列「八俊」之一,聲望崇高,是清流派在官場中的主要領袖之一。他不贊成捲入不必要的爭執中,所以一向閉關自守,既未參加董卓和反董卓聯盟間的戰爭,對袁紹、袁術兄弟間的明爭暗鬥,也保持中立,所以荊州內部還算安穩,不太受漢末戰亂的影響,而且文風鼎盛,是個相當不錯的「避難港」。
不過,由山東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北,輾轉千里之遠,光是逆著長江到荊州,就要有十幾天的舟楫顛簸之苦,對年輕的諸葛亮而言,倒也增長了不少見識,流離之間,也更體念了家園及和平的重要性。
雖然劉表很高興、也頗熱誠地接待了諸葛玄。但丟掉了官職的他,祇得委屈在劉表府裡當幕僚,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對於一個高傲又有原則的知識分子,這種打擊幾乎比生活上的困苦還要大,因此一年後,諸葛玄便憂鬱成疾,一病不起了。幸好劉表仍顧念舊情,承擔起諸葛亮一家的物質生活,諸葛玄在這一年內,結交的一些文人名士,給了這個喪失大家長的家庭,不少精神上的鼓勵及支持。
由於劉表的關係,諸葛亮的姊姊嫁給了荊襄名門龐德公的姪兒龐山民,總算了卻一樁心願。十六歲的諸葛亮決定帶領弟弟獨立生活,不再接受荊州襄陽府的「人道援助」。他將叔父僅有的些微財產變賣,直接去晉見劉表,表明自立更生的意願,劉表非常高興,便幫助他們以極少的代價,在襄陽城西二十多里一個叫做隆中的地方,將這兩個年輕的兄弟安頓下來,兩個男的自行耕種,這年正是漢獻帝建安二年(西元一九七年),「流浪兩兄弟」找到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展開半耕半讀的隱居生涯。
〔陳文德說評〕中國的官場和文人們,一說到法治,總喜歡以自己為正義化身般地高喊「亂世用重典」、「殺一儆百」的口號,當今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便曾公開表示,最看不慣台灣民眾的不守法行為,為了表明對公權力維護的決心,在就任之初,不斷使出強硬的手段,認為嚴刑峻法,便能建立法治的精神,殊不知台灣民眾,甚至可以說整體的中國人,一向缺乏法治觀念的現象,祇是一種結果,並非原因。
中國人缺乏法治觀念,最主要在於缺乏有效的法令制度,這倒不是指中國缺乏白紙黑字的律令,這方面倒有點如司法院長林洋港早年的自詡:「健康的牛,毛比較多。」中國的律令規章一向多如牛毛,甚至多到制定法令的政府官員都懶得執行。
其實,林洋港先生的話倒不見得不對,面對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相互關係的規章,自然有必要詳細而清楚。但問題是中國的制法相關人員,一向喜歡規定得嚴厲些,甚至苛薄些,以表示自己的「正義」及「權威」,執法時又以放一馬的態度,表達自己的人情味及慈愛,因此法令雖汗牛充棟,但執法時則千變萬化,空有法令卻又一味的「人治」,哪裡有可能建立「法治」的精神?
誠如立法委員謝長廷先生所說的笑話:「中國人的法律規定,一向是有些人可以作,有些人卻不可以作,有時候可以作,有時候又不可以作。」
制法嚴、執法鬆,缺乏標準,自然要特權橫行;大家有樣看樣,有力量的公開違法,沒有力量的從後門走捷徑。在政府單位走動的「黃牛」,比戲院不知要多出幾十倍,在這樣的情勢下,又如何建立及培養民眾的法治精神?
孟德斯鳩的《法意》一書,主要在限制有權力者的擅用權力,制度的目的,不在統治「老百姓」,而是制衡權力單位的濫權。已故政治學者鄒文海先生,曾有如下名言:「法治不在要求人民守法,而是要求政府守法,因為不論是法治或人治、人民總是被迫要守法。」
如果國家的基本大法,法治政府應有的制衡精神,在權宜及方便的藉口下,被破壞得慘不忍睹,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四十餘年管理,繳出了一張「亂民」的成績單,其原因何在,應該相當清楚,郝院長似乎也沒有什麼抱怨的「權利」了。
東漢晚年的黃巾黨人民變,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中國的「老百姓」,幾千年來一直是被欺侮的一群,官員可以耍特權,佔盡一切便宜後,把人民逼得生存下去都很困難了,還反過來指責那些企圖也撈點「特權」來生存的「亂民」及「刁民」。中國數千年來的悲劇,似乎便是一直在這個窠臼裡面「繞圈子」。
我們不怕沒有法律,最怕的是法令根本作不到,或許無法徹底的執行,七折八扣的「講人情」,最後祇能製造一大群特權、及一輩子的混亂而已。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圯。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梁父吟>
第一章 亂世童年
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鍛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官逼民反,農民起義
東漢王朝後半段的百年間,朝廷裡外戚和宦官急著奪權,地方豪族則忙著兼併土地及累積財富。貧富懸殊嚴重,破產的農民流浪四方,被饑饉及窮困追著四處跑,在以農立國的中國古代社會,農民失去田地,成為浪人,勢必導致社會重大的動亂。
順帝以後的二十年間,無法生存而流亡各地的貧民集團,不得不揭竿起義,爭取最起碼的生存空間。但傳統的史書,例如《後漢書》及《資治通鑑》等,大多以「妖賊」或「盜賊」稱之,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諸葛亮日後大老闆劉備的長期宿敵曹操,在平定兗州後,曾將三十餘萬黃巾黨人收編為「青州軍」,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同情立場,面對農民起義的政治領袖。
這些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大多帶有濃厚宗教色彩,他們分別被稱為「無上將軍」、「黃帝」或「黑帝」,組織龐大而鬆懈,全靠宗教力量結合。在這一系列的民變事件中,以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的黃巾黨人事變規模最大,影響也最深。
黃巾黨人的領袖是鉅鹿人(河北省南部)張角,是位非常有名的民間密醫,以神秘的宗教醫術,醫療患病的農民。張角的治療法,是讓患者先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入飲之。先不問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張角的治病是宗教性大於醫療性的。這樣子的治病法,即使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仍到處流行著,在醫學不發達的當時,影響力自然更大了。張角的弟子遍佈全國各地,都擅長這種神水醫療術,由於碰到苦難當頭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脹,總稱為「太平道」。
據張角自己的說法,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傳授的《太平清領書》,囑咐他推展太平道以救世。在數十年間,以青州(現山東省)為中心,遍佈冀、徐、荊、揚、兗、豫等州。擁有數十萬信徒,盤據在十三州中的三分之二江山。
到了光和年間,太平道的影響力,已不止於下階層的農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於官僚也趨之若騖。依《後漢書》記載,執宦官主流派集團牛耳的大常侍張讓,便與張角有相當密切的來往。
眼見太平道急速膨脹,朝廷有志之士自然產生了危機意識。清流派的楊賜,首先上書主張一方面招撫流民,給予土地耕種,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搜捕太平道在各地的領袖,以削弱其組織力量。劉陶、樂松、袁貴等也聯名上書靈帝,主張逮捕張角,以免事件繼續擴大。
由於親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靈帝在軟硬政策間舉棋不定,終於消息外洩,反而使張角加速強化其組織。不久,張角便將全國信徒分為三十六「方」,大「方」編組萬餘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均由直屬子弟統領指揮。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並封其弟張寶為「地公將軍」,張梁為「人公將軍」,共同統率著三十六萬人馬。
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向信徒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當年正好是甲子年,是六十年干支歲月的重新開始。張角決定在是年三月五日,散佈各地的三十六萬信徒同時起義。依照中國傳說的五行思想,金、木、水、火、土的循環理論,漢王朝屬火德、剋火者土,因此代替漢王朝者應屬土德。黃土高原和黃土平原的土都是黃色的,所以太平道信徒,均以黃色頭巾為標幟,這也是黃巾黨人的由來。
負責攻打洛陽的大方馬元義,行動不夠謹慎,三月三日未到便陰謀敗露被捕,同行的黨人有數千人遇害。靈帝到此才恍然大悟,發出逮捕張角的通緝令。
迫不得已,張角會同兩位弟弟,提早一個月起義。雖然準備不周,仍有七州二十八郡響應,頭綁黃色頭巾的黨人,攻擊官府,佔領田園,不少郡縣官吏聞風而逃,《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黃巾黨人的主要戰場,在洛陽附近的潁川地區,北起冀州西南區,南至南陽一帶。朝廷以何皇后之兄何進為河南尹,負責攻防總指揮,實際負責作戰的是司隸軍區中最精銳的師團,分別由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北中郎將盧植率領。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一章回便是劉備在涿郡募集義兵,響應政府號召,共同對抗黃巾黨人民變的情節。劉備在此認識關羽和張飛,留下了「桃園三結義」的千古美談。
戰爭初期,黃巾黨人聲勢浩大,張角和盧植大戰於冀州,盧植軍團寡不敵眾,被迫向南撤退。防守在潁川附近的朱軍團亦遭擊退,南陽太守甚至在會戰中陣亡。
為了保護京城洛陽的安全,皇甫嵩將主力部隊佈防在潁川附近。張角以數萬兵馬層層包圍,皇甫嵩親往前線視察,他看到黃巾黨人均以茅草結營,乃趁夜色掩護,以火攻戰術突擊,張角軍團大亂,佈防在潁川南岸的朱軍團也趁機反攻,洛陽方面前來救援的典軍校尉曹操,率領騎兵部隊及時趕到,三方面夾擊下,黃巾黨人大敗,死傷高達數萬人,這也是朝廷部隊第一次成功阻擋黃巾黨人攻擊的正式記錄。
靈帝中平元年八月,張角病死;十月,人公將軍張梁的軍團在潁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傷三萬餘人,張梁本人也在潰敗中遭到擊殺;十一月,地公將軍張寶也戰死在南陽會戰中,黃巾黨人的主力部隊,到此完全殲滅。
但散居各地的黃巾黨人仍遙相呼應。并州的白波軍、冀州的黑山軍、益州和青州的黃巾軍,聲勢浩大,均讓各地方政府頭痛不已。皇甫嵩等雖在洛陽附近獲得絕對勝利,但在數度大規模會戰後,主力部隊也遭到了重創,根本無力再協助各地方政府剿亂。朝廷為了鞏固地方秩序,平定黨人的作亂,也不得不強化北方首長的行政權及軍事權。
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年)三月,朝廷接受江夏太守劉焉建議,擴大部分嚴重動亂地區刺史的權限,並改稱「牧」。劉焉為益州牧,黃琬為豫州牧,劉虞為幽州牧。《資治通鑑》記載:「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這些地方州牧,權限逐步擴大,漸漸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失去了指揮權和控制力,終於釀成了漢末群雄割據的局面,東漢王朝也步入名存實亡的境地了。
動盪社會,流浪孤兒
黃巾黨人起義的那個甲子年二月,諸葛亮正好滿四歲。
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時出任泰山郡郡丞,泰山郡中的泰山是中國自古以來有名的靈山,諸葛亮便在這附近渡過他最早期的童年。
諸葛亮本籍在瑯琊郡,當時稱為陽都縣,約在今山東省臨沂縣和沂南縣之間,同屬於山東省的西北區。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載:
泰山之南有魯國,北方則有齊國,瀕山臨海間有塊相當肥沃的平原,或產桑樹和麻類植物,麻、絹等織製品便成了這裡的名產。主要的大城市臨沼位於渤海及泰山間,這裡的人一向思慮較深,並且好作議論,行事從不輕舉妄動,這些人個別能力都很強,但集體作戰力則偏弱,是典型的工商社會,國家的經濟力旺盛而活躍,住民大約可分成士、農、工商、工、坐商等五種職業。
思慮周密,好作議論,絕不輕舉妄動的性格,的確相當明顯地可以在諸葛亮身上發現。
從姜太公在齊地建國以來,這裡一向便是南北貨貿易重心,經濟力量旺盛,因此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地方為高,東漢到六朝時代,有不少名人皆出身於此,例如協助苻堅建立前秦帝國的王導,不朽的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顏氏家訓》作者顏之推,及唐代書聖顏真卿等,都是當地的名家豪族。
另一個特色是齊國的兵學思想。齊軍一向以怯戰出名,因此更用心於研究戰爭的技巧和方法。姜太公的兵法學是戰爭的原則,也是生意者的策略。一代兵學宗師孫武,也是齊國人,《孫子兵法》中的準備和應變工夫,相信和齊國傳統的處世哲學有關。《鬼谷子兵法》,也是以齊國為其發源地,孫臏、龐涓,甚至於蘇秦、張儀都是在這裡學成的。除了在襄陽地區居住時,和當地的名士學者切磋研習外,諸葛亮的思想、言行及人生觀,顯然也是和齊國傳統的文化有關。
韋昭寫的《吳書》中記載:諸葛亮的先祖原姓葛氏,居住在瑯琊郡諸縣,當時他們整族人不知在什麼原因下,遷往陽都縣。由於陽都縣裡也住有很多葛氏人家,為了有所區別,乃將諸縣遷移過來的葛氏,稱之為諸葛氏。
諸葛亮的祖父諸葛豐曾任東漢王朝的司隸校尉(京城警備總監),他是位負責盡職的官員,個性剛強正直,執起法來,任何權勢都毫不在意。
官位高居侍中的外戚許章,平常假借皇威為非作歹,諸葛豐下令逮捕,許章逃往禁宮,要求皇帝保護。諸葛豐也曾正式上文彈劾許章,並要求嚴厲處分,以免傷害皇權。雖然皇帝有意調節兩人的爭執,但諸葛豐義正詞嚴,皇帝不得已,祇得處分許章。然不久,諸葛豐便被免除司隸校尉之職務,並且廢為庶人,不過諸葛豐這種高風亮節、執法嚴正的個性,顯然也遺傳在諸葛亮的身上。
諸葛亮之父諸葛珪,曾任泰山郡郡丞(主任秘書),其妻章氏。兩人共育有四位子女,諸葛亮排行老三,長兄諸葛瑾,弟弟諸葛均,另有姊姊一人。九歲時母親章氏去世,為了照顧年幼的子女,父親另娶了後母,但三年後父親也去世了。喪失雙親的諸葛兄弟,由於後母無力扶養他們,全靠叔父諸葛玄接濟。長兄諸葛瑾大諸葛亮七歲,母親去世前,曾在洛陽太學府遊學,專攻《毛詩》、《尚書》、《左傳春秋》,成績優異。母親去世時,他為了服喪及照顧弟妹,毅然放棄學業,返回家鄉。
瑯琊郡屬徐州,黃巾黨人起義初期,這裡也備受干擾,但當朝廷派來武夫出身的陶謙為徐州刺史後,動亂總算平息了下來。其後的董卓之亂,關東諸侯勤王起義的戰爭,徐州在陶謙力保中立的政策下,總算未受波及。所以當洛陽一帶陷入戰亂時,不少人「流移東出,多依徐土」。但就在漢獻帝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起,雄據兗州的曹操,其父曹嵩在徐州意外被害,曹操乃興兵攻打徐州,陶謙雖奮勇抵抗,但整個徐州立刻陷入兵荒馬亂中,位於徐州北部的瑯琊郡也遭到波及。有些地方甚至「雞犬亦盡,墟色無復行人」。負責一家安危的諸葛玄,不得不設法離開家鄉,暫避戰亂。
隔年,諸葛亮十四歲的時候,諸葛玄被反董卓集團的南區領袖--揚州軍閥頭子袁術任命為豫章郡太守(今江西南昌附近)。諸葛玄帶著年幼的諸葛亮姊弟們前往赴任。並藉以暫避禍亂。但年紀已二十一歲的諸葛瑾,必須擔負重建家聲的責任,因此他決定另找生路,以免寄人籬下,幾經思索後,和繼母遠赴江東。一家人從此離散,各奔東西。
從徐州北部經由豫州,南下到豫章的路途上,這幾年的兵荒馬亂最為嚴重,曹操及陶謙間數度惡戰、不少農民叛變都發生在這地方。青少年期的諸葛亮親眼目睹戰爭對社會所帶來的惡果,土地荒廢,人民妻離子散,農村經濟嚴重破產,善良百姓被迫拿起刀劍而走險,從事盜匪生涯。這種悲慘情境,對諸葛亮的人生觀想必有著深遠的影響。
更不幸的是,諸葛玄到任後不久,東漢朝廷又派朱皓為豫章太守,使豫章太守的位置鬧了雙胞。不過朱皓上任的時候,由揚州刺史劉鏢處借得大批軍隊,直接向「非正牌」的諸葛玄施壓。諸葛玄方面,袁術雖然聲勢浩大,但正和曹操準備交戰中,自顧不暇,根本無法給諸葛玄任何實質的幫助。何況自己非朝廷命官,名不正言不順,勢單力薄,自然無力抵擋,為了顧全面子及家人安全,祇得匆匆撤離。
家鄉是不願也不可能回去,諸葛玄祇好將諸葛亮一家帶到荊州的襄陽城,去依靠老朋友荊州刺史劉表了。荊州刺史劉表早年也名列「八俊」之一,聲望崇高,是清流派在官場中的主要領袖之一。他不贊成捲入不必要的爭執中,所以一向閉關自守,既未參加董卓和反董卓聯盟間的戰爭,對袁紹、袁術兄弟間的明爭暗鬥,也保持中立,所以荊州內部還算安穩,不太受漢末戰亂的影響,而且文風鼎盛,是個相當不錯的「避難港」。
不過,由山東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北,輾轉千里之遠,光是逆著長江到荊州,就要有十幾天的舟楫顛簸之苦,對年輕的諸葛亮而言,倒也增長了不少見識,流離之間,也更體念了家園及和平的重要性。
雖然劉表很高興、也頗熱誠地接待了諸葛玄。但丟掉了官職的他,祇得委屈在劉表府裡當幕僚,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對於一個高傲又有原則的知識分子,這種打擊幾乎比生活上的困苦還要大,因此一年後,諸葛玄便憂鬱成疾,一病不起了。幸好劉表仍顧念舊情,承擔起諸葛亮一家的物質生活,諸葛玄在這一年內,結交的一些文人名士,給了這個喪失大家長的家庭,不少精神上的鼓勵及支持。
由於劉表的關係,諸葛亮的姊姊嫁給了荊襄名門龐德公的姪兒龐山民,總算了卻一樁心願。十六歲的諸葛亮決定帶領弟弟獨立生活,不再接受荊州襄陽府的「人道援助」。他將叔父僅有的些微財產變賣,直接去晉見劉表,表明自立更生的意願,劉表非常高興,便幫助他們以極少的代價,在襄陽城西二十多里一個叫做隆中的地方,將這兩個年輕的兄弟安頓下來,兩個男的自行耕種,這年正是漢獻帝建安二年(西元一九七年),「流浪兩兄弟」找到了他們的第二故鄉,展開半耕半讀的隱居生涯。
〔陳文德說評〕中國的官場和文人們,一說到法治,總喜歡以自己為正義化身般地高喊「亂世用重典」、「殺一儆百」的口號,當今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便曾公開表示,最看不慣台灣民眾的不守法行為,為了表明對公權力維護的決心,在就任之初,不斷使出強硬的手段,認為嚴刑峻法,便能建立法治的精神,殊不知台灣民眾,甚至可以說整體的中國人,一向缺乏法治觀念的現象,祇是一種結果,並非原因。
中國人缺乏法治觀念,最主要在於缺乏有效的法令制度,這倒不是指中國缺乏白紙黑字的律令,這方面倒有點如司法院長林洋港早年的自詡:「健康的牛,毛比較多。」中國的律令規章一向多如牛毛,甚至多到制定法令的政府官員都懶得執行。
其實,林洋港先生的話倒不見得不對,面對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相互關係的規章,自然有必要詳細而清楚。但問題是中國的制法相關人員,一向喜歡規定得嚴厲些,甚至苛薄些,以表示自己的「正義」及「權威」,執法時又以放一馬的態度,表達自己的人情味及慈愛,因此法令雖汗牛充棟,但執法時則千變萬化,空有法令卻又一味的「人治」,哪裡有可能建立「法治」的精神?
誠如立法委員謝長廷先生所說的笑話:「中國人的法律規定,一向是有些人可以作,有些人卻不可以作,有時候可以作,有時候又不可以作。」
制法嚴、執法鬆,缺乏標準,自然要特權橫行;大家有樣看樣,有力量的公開違法,沒有力量的從後門走捷徑。在政府單位走動的「黃牛」,比戲院不知要多出幾十倍,在這樣的情勢下,又如何建立及培養民眾的法治精神?
孟德斯鳩的《法意》一書,主要在限制有權力者的擅用權力,制度的目的,不在統治「老百姓」,而是制衡權力單位的濫權。已故政治學者鄒文海先生,曾有如下名言:「法治不在要求人民守法,而是要求政府守法,因為不論是法治或人治、人民總是被迫要守法。」
如果國家的基本大法,法治政府應有的制衡精神,在權宜及方便的藉口下,被破壞得慘不忍睹,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四十餘年管理,繳出了一張「亂民」的成績單,其原因何在,應該相當清楚,郝院長似乎也沒有什麼抱怨的「權利」了。
東漢晚年的黃巾黨人民變,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中國的「老百姓」,幾千年來一直是被欺侮的一群,官員可以耍特權,佔盡一切便宜後,把人民逼得生存下去都很困難了,還反過來指責那些企圖也撈點「特權」來生存的「亂民」及「刁民」。中國數千年來的悲劇,似乎便是一直在這個窠臼裡面「繞圈子」。
我們不怕沒有法律,最怕的是法令根本作不到,或許無法徹底的執行,七折八扣的「講人情」,最後祇能製造一大群特權、及一輩子的混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