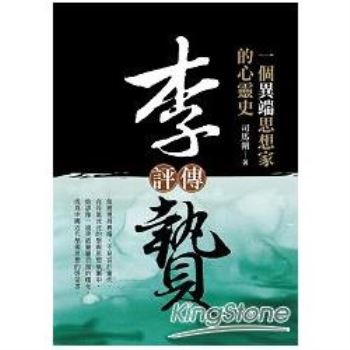佛陀之光
削髮麻城
話說萬曆十二年(西元一五八四年)七月分,李贄的摯友耿定理突然病逝。因與其兄耿定向不諧,李贄深切感受到繼續住在耿家已是興味索然了。可是,不在耿家,又往何處落腳呢?幸好,三年來新結識的耿門弟子中,麻城來的周思敬(字友山)、周思久(字柳塘)兄弟對李贄甚為欽佩和關愛。
周家是鄰縣麻城的殷實人家,尤其是弟弟周思敬,更是對李贄甚為膺服。周思敬,張居正門生,曾任按察使等職,又是耿定向的好友。隆慶初年曾為耿定向向張居正說情。張居正「奪情」主閣時,鄒元標力諫,為張所惡,有生命危險,周友山憤而相救。周認識耿定理,通過定理而認識其兄,並進而以師事之。後又將其女嫁給耿定理之子耿汝思。可見周氏與耿家的關係非同一般。李贄在黃安的三年中,他與周氏兄弟的恩師耿定向性情和學術觀點的差異,大家都是心中有數的。雖如此,周氏兄弟仍能不避嫌疑,邀請李贄到麻城講學,一直與李贄保持密切的關係。
這次耿定理新逝,他們料定李贄會很不自在,處境為難,於是十月分主動將李贄接到麻城去住,可是因一時無合適的安排之處,李贄又返回黃安耿家。第二年(西元一五八五年)夏,李贄把夫人黃氏和女兒送回福建泉州老家,自己來到麻城,暫住於屬於周家財產的維摩庵。維摩庵是專為女性信徒而創建的,對李贄來說並非合適的久居之地。所以,萬曆十六年(西元一五八八年),李贄又遷至離縣城三十裡的龍潭湖。以龍潭湖為中心,隔水相望有二寺,湖北有芝佛寺,因建寺時掘地得三根酷似佛像的芝草而名。湖南即有龍湖寺。其實,此前李贄與耿定理及周氏兄弟等就來此聚眾講學。現在,李贄總算有了個既安定又合適的家了。
自命為「流寓客子」,李贄還是不稱意,他知道,來到黃安、麻城沒幾年,他已是這裡的一方名人,來看他的人很多,抱各種目的的都有。不管好意還是壞意,在他看來,都是打擾,因為他要靜心讀書。為了能盡可能將各種煩心的應酬減少到最低限度,為獲得更多的自由,他決定剃髮,真正與僧為伍:既然是官也辭了,老婆也送走了,自己也早已實實際際地住到寺院裡來了,剃掉這幾根禿髮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
有一天,他發現好長時間沒洗頭了,覺著頭皮老是癢,於是就打水好生地打掃了一下個人衛生。打掃之後,頓覺一陣清爽,妙不可言。正在得意,突然想到:這幾根所剩無多的禿髮還留著它做甚?徒然藏汙納垢,洗起來又甚是麻煩,不如乾脆剃了的痛快。於是,說做就做,不一時,幾根頭髮就被除掉了。剃了頭,李贄得意地到處摸了摸,對身邊的僧人說:「好,好,還是沒毛的好,卓老我今天又清淨了一根,從此與你們諸位算是真正的志同道合了,哈哈哈哈……」清脆的笑聲灑落了一院,驚起了樹上的小鳥。
之後,李贄還特意寫了幾首詩以明心跡:
空潭一老醜,剃髮便為僧。願度沙眾,長明日月燈。(其一)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其二)
李贄後來還提到另外的原因:
我之所以剃髮,是因為泉州老家的人時時期望著我回去,又時時不遠千里地派人來給我施加壓力,又用許多俗事勉強我,於是我就用剃髮向他們表示我絕不回去的意思,也絕不再管任何俗事。再加上這裡的人們沒見識,在他們眼裡,我是個跟所有人都不一樣的不可思議的異端。既然如此,不如我乾脆就當他個異端,也好了了這些人的一樁心願。
千萬別小瞧了這次剃頭事件。
依祖宗傳統的說法,這皮膚毛髮是受之於父母,不要求你榮華富貴,也不要求你光宗耀祖,最不濟了,你也要保護好這些個東西。它們是父母給子女的信物,是血緣親情,義務與權利的見證,所以並不是你可以隨意發落的。從對待這幾根頭髮的態度上,完全可以見出你對父母是否有足夠的孝心等等,只有那些棄絕五倫的僧人們才會輕意將父母賜給他們的東西割去,而信奉孔孟之道的禮義之邦的人們絕對做不出此等不忠不孝的事體來。
它們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有時候就成了漢族人的標識,在民族衝突激烈時,這頭髮就更成了關係生命安危的事情。據說,漢族的大老爺們本來是不留長辮子的,只是滿族入主中原後,為了掃漢人的臉面,才強迫漢族男人留起了大辮子。想來當時的漢族男子漢們肯定心裡也不高興,只是時間長了,我們後人已全然想像不出當時的具體情形。可三百年後,這世道又給變了回去,讓剛剛才適應了留大辮子,並看著自己這副尊容越來越順眼的漢族男人們一下回不過神兒來。據說太平軍時,有過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極端選擇,這大概算是把頭髮的意義強調到了極點。就連離我們最近的辛亥革命,也是從對頭髮的革命開始的。那些已參加了革命軍的青年人,站在城門口,手裡威風凜凜地持一把剪刀,以極優美的動作非常利索地剪下了鄉下人的大辮子,全不顧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那快意當不亞於菜市口的劊子手們一刀切下了「六君子」的頭顱。頭髮有時是那樣的重要,在魯迅先生的《風波》裡,頭髮的去留已成了革命與復辟,一家人的生死,整個社會的進步與反動的晴雨表。說來也不能怪後人,若不是祖先賦予它那麼多東西,後人會在這幾根黃毛上費許多心思,打諸般主意嗎?「始作俑者,其無後矣!」
可事情並沒有李贄想像得那麼簡單。他的朋友鄧鼎石聽說他剃了髮,悲痛得痛哭流涕。更有趣的是,鄧鼎石的母親聽了此事後,也大為震驚,並且把自己的兒子責備了半天,命令她兒子無論如何都要說服李贄回心轉意,再把頭髮留起來。她對兒子說:「你去告訴你的朋友李贄,就說我為他剃髮的事難過得一整天都沒吃飯,飯端來我也沒法兒下嚥。這樣,我看他李贄還留不留頭髮!你今天要是有本事把李贄勸過來,老娘我就承認你是個真正的孝子,承認你是個真正的好官,否則全是扯淡!」
李贄剃去了幾根禿髮,差點導致災難發生,區區一髮,可謂小乎?好在李贄沒有接受這種心理攻勢,還是堅持他那顆禿頭。事過之後,李贄感慨萬端:「唉,我費了多少心思才終於實現了剃頭的願望……我剃這幾根本屬於我自己的頭髮,難道容易嗎?就只是為了少受人管束才決定剃髮,這容易嗎?寫到這裡,我自己就禁不住鼻子發酸。你們這些人可千萬不要以為剃頭髮是件好事,不要以為輕易地就能靠別人布施生活。」
這樣一來,剃髮於李贄也是大有深意的事,他要以此向社會的各方面,向家鄉的親人與父母官,向寄寓之地的父母官及所有人表明他追求自由和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總要有一個安身落腳之地,此謂之「家」。李贄已拋棄了那個由妻室兒女所組成的對中國人來說是最本質意義的家,又離開了朋友的寓居之「家」。可他還有個臭皮囊,這皮囊需要庇護,需要歇息。再清高,這件俗事總是免不了的。故而佛家雖出離妻室之家,仍需要伽藍精舍之庇護,即因此也。還是老子說得好:吾之有患,在吾有身,若吾無身,又有何患?因此,李贄的落戶龍湖,並不能只理解為一種出家,實際上又是一種尋求庇護的意義。自己的家不願回,朋友的家已不便久留,他總要有個落腳之處。因此,這與其說是出家,倒不如說是尋家。
如果如此來理解李贄的定居龍湖,則其削髮之舉,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龍湖是僧院。李贄若想長期久居於此,不削髮可以嗎?因此,削髮不過是李贄在龍湖久居的一種生存策略,否則,勢必會先給這裡的僧人,最終給自己帶來不便。
剃髮也是一種文化、一種儀式,對文化學家來說,儀式恰屬於人類文化最基本、最外在的操作層面。
看來,古代印度的智者與中國的聖賢在頭髮上有著大致相同的見解,都把頭發作為文化儀式的方便信物。佛教信徒之削髮,據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剃髮以作為佛門弟子出家的特徵,以區別於其他宗教的出家人。《因果經》上說:那時太子便用利劍斬斷自己的鬚髮,併發誓言:從現在削髮起,願斷除一切煩惱和習俗業障。此大概即是僧人剃髮的來由,並成了斷除一切煩惱的象徵。《智度論》說:剃頭、身著染衣、持缽乞食,這是破除僧人驕慢的方法。依此,則剃髮又有了戒驕的意義。
削髮麻城
話說萬曆十二年(西元一五八四年)七月分,李贄的摯友耿定理突然病逝。因與其兄耿定向不諧,李贄深切感受到繼續住在耿家已是興味索然了。可是,不在耿家,又往何處落腳呢?幸好,三年來新結識的耿門弟子中,麻城來的周思敬(字友山)、周思久(字柳塘)兄弟對李贄甚為欽佩和關愛。
周家是鄰縣麻城的殷實人家,尤其是弟弟周思敬,更是對李贄甚為膺服。周思敬,張居正門生,曾任按察使等職,又是耿定向的好友。隆慶初年曾為耿定向向張居正說情。張居正「奪情」主閣時,鄒元標力諫,為張所惡,有生命危險,周友山憤而相救。周認識耿定理,通過定理而認識其兄,並進而以師事之。後又將其女嫁給耿定理之子耿汝思。可見周氏與耿家的關係非同一般。李贄在黃安的三年中,他與周氏兄弟的恩師耿定向性情和學術觀點的差異,大家都是心中有數的。雖如此,周氏兄弟仍能不避嫌疑,邀請李贄到麻城講學,一直與李贄保持密切的關係。
這次耿定理新逝,他們料定李贄會很不自在,處境為難,於是十月分主動將李贄接到麻城去住,可是因一時無合適的安排之處,李贄又返回黃安耿家。第二年(西元一五八五年)夏,李贄把夫人黃氏和女兒送回福建泉州老家,自己來到麻城,暫住於屬於周家財產的維摩庵。維摩庵是專為女性信徒而創建的,對李贄來說並非合適的久居之地。所以,萬曆十六年(西元一五八八年),李贄又遷至離縣城三十裡的龍潭湖。以龍潭湖為中心,隔水相望有二寺,湖北有芝佛寺,因建寺時掘地得三根酷似佛像的芝草而名。湖南即有龍湖寺。其實,此前李贄與耿定理及周氏兄弟等就來此聚眾講學。現在,李贄總算有了個既安定又合適的家了。
自命為「流寓客子」,李贄還是不稱意,他知道,來到黃安、麻城沒幾年,他已是這裡的一方名人,來看他的人很多,抱各種目的的都有。不管好意還是壞意,在他看來,都是打擾,因為他要靜心讀書。為了能盡可能將各種煩心的應酬減少到最低限度,為獲得更多的自由,他決定剃髮,真正與僧為伍:既然是官也辭了,老婆也送走了,自己也早已實實際際地住到寺院裡來了,剃掉這幾根禿髮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
有一天,他發現好長時間沒洗頭了,覺著頭皮老是癢,於是就打水好生地打掃了一下個人衛生。打掃之後,頓覺一陣清爽,妙不可言。正在得意,突然想到:這幾根所剩無多的禿髮還留著它做甚?徒然藏汙納垢,洗起來又甚是麻煩,不如乾脆剃了的痛快。於是,說做就做,不一時,幾根頭髮就被除掉了。剃了頭,李贄得意地到處摸了摸,對身邊的僧人說:「好,好,還是沒毛的好,卓老我今天又清淨了一根,從此與你們諸位算是真正的志同道合了,哈哈哈哈……」清脆的笑聲灑落了一院,驚起了樹上的小鳥。
之後,李贄還特意寫了幾首詩以明心跡:
空潭一老醜,剃髮便為僧。願度沙眾,長明日月燈。(其一)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其二)
李贄後來還提到另外的原因:
我之所以剃髮,是因為泉州老家的人時時期望著我回去,又時時不遠千里地派人來給我施加壓力,又用許多俗事勉強我,於是我就用剃髮向他們表示我絕不回去的意思,也絕不再管任何俗事。再加上這裡的人們沒見識,在他們眼裡,我是個跟所有人都不一樣的不可思議的異端。既然如此,不如我乾脆就當他個異端,也好了了這些人的一樁心願。
千萬別小瞧了這次剃頭事件。
依祖宗傳統的說法,這皮膚毛髮是受之於父母,不要求你榮華富貴,也不要求你光宗耀祖,最不濟了,你也要保護好這些個東西。它們是父母給子女的信物,是血緣親情,義務與權利的見證,所以並不是你可以隨意發落的。從對待這幾根頭髮的態度上,完全可以見出你對父母是否有足夠的孝心等等,只有那些棄絕五倫的僧人們才會輕意將父母賜給他們的東西割去,而信奉孔孟之道的禮義之邦的人們絕對做不出此等不忠不孝的事體來。
它們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有時候就成了漢族人的標識,在民族衝突激烈時,這頭髮就更成了關係生命安危的事情。據說,漢族的大老爺們本來是不留長辮子的,只是滿族入主中原後,為了掃漢人的臉面,才強迫漢族男人留起了大辮子。想來當時的漢族男子漢們肯定心裡也不高興,只是時間長了,我們後人已全然想像不出當時的具體情形。可三百年後,這世道又給變了回去,讓剛剛才適應了留大辮子,並看著自己這副尊容越來越順眼的漢族男人們一下回不過神兒來。據說太平軍時,有過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極端選擇,這大概算是把頭髮的意義強調到了極點。就連離我們最近的辛亥革命,也是從對頭髮的革命開始的。那些已參加了革命軍的青年人,站在城門口,手裡威風凜凜地持一把剪刀,以極優美的動作非常利索地剪下了鄉下人的大辮子,全不顧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那快意當不亞於菜市口的劊子手們一刀切下了「六君子」的頭顱。頭髮有時是那樣的重要,在魯迅先生的《風波》裡,頭髮的去留已成了革命與復辟,一家人的生死,整個社會的進步與反動的晴雨表。說來也不能怪後人,若不是祖先賦予它那麼多東西,後人會在這幾根黃毛上費許多心思,打諸般主意嗎?「始作俑者,其無後矣!」
可事情並沒有李贄想像得那麼簡單。他的朋友鄧鼎石聽說他剃了髮,悲痛得痛哭流涕。更有趣的是,鄧鼎石的母親聽了此事後,也大為震驚,並且把自己的兒子責備了半天,命令她兒子無論如何都要說服李贄回心轉意,再把頭髮留起來。她對兒子說:「你去告訴你的朋友李贄,就說我為他剃髮的事難過得一整天都沒吃飯,飯端來我也沒法兒下嚥。這樣,我看他李贄還留不留頭髮!你今天要是有本事把李贄勸過來,老娘我就承認你是個真正的孝子,承認你是個真正的好官,否則全是扯淡!」
李贄剃去了幾根禿髮,差點導致災難發生,區區一髮,可謂小乎?好在李贄沒有接受這種心理攻勢,還是堅持他那顆禿頭。事過之後,李贄感慨萬端:「唉,我費了多少心思才終於實現了剃頭的願望……我剃這幾根本屬於我自己的頭髮,難道容易嗎?就只是為了少受人管束才決定剃髮,這容易嗎?寫到這裡,我自己就禁不住鼻子發酸。你們這些人可千萬不要以為剃頭髮是件好事,不要以為輕易地就能靠別人布施生活。」
這樣一來,剃髮於李贄也是大有深意的事,他要以此向社會的各方面,向家鄉的親人與父母官,向寄寓之地的父母官及所有人表明他追求自由和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總要有一個安身落腳之地,此謂之「家」。李贄已拋棄了那個由妻室兒女所組成的對中國人來說是最本質意義的家,又離開了朋友的寓居之「家」。可他還有個臭皮囊,這皮囊需要庇護,需要歇息。再清高,這件俗事總是免不了的。故而佛家雖出離妻室之家,仍需要伽藍精舍之庇護,即因此也。還是老子說得好:吾之有患,在吾有身,若吾無身,又有何患?因此,李贄的落戶龍湖,並不能只理解為一種出家,實際上又是一種尋求庇護的意義。自己的家不願回,朋友的家已不便久留,他總要有個落腳之處。因此,這與其說是出家,倒不如說是尋家。
如果如此來理解李贄的定居龍湖,則其削髮之舉,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龍湖是僧院。李贄若想長期久居於此,不削髮可以嗎?因此,削髮不過是李贄在龍湖久居的一種生存策略,否則,勢必會先給這裡的僧人,最終給自己帶來不便。
剃髮也是一種文化、一種儀式,對文化學家來說,儀式恰屬於人類文化最基本、最外在的操作層面。
看來,古代印度的智者與中國的聖賢在頭髮上有著大致相同的見解,都把頭發作為文化儀式的方便信物。佛教信徒之削髮,據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剃髮以作為佛門弟子出家的特徵,以區別於其他宗教的出家人。《因果經》上說:那時太子便用利劍斬斷自己的鬚髮,併發誓言:從現在削髮起,願斷除一切煩惱和習俗業障。此大概即是僧人剃髮的來由,並成了斷除一切煩惱的象徵。《智度論》說:剃頭、身著染衣、持缽乞食,這是破除僧人驕慢的方法。依此,則剃髮又有了戒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