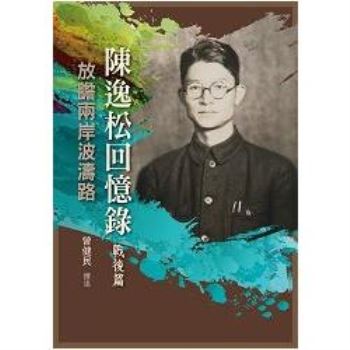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e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e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要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
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
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要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
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e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e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要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
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
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要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
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