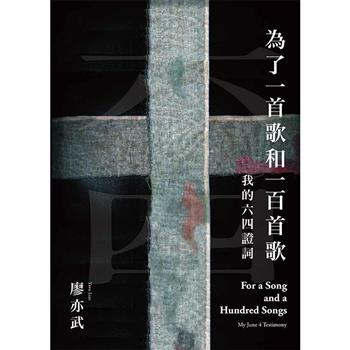第一部—東窗事發
1. 飛飛
1988(0000),四個汽車輪子的年頭,我姐姐飛飛殞於車禍,享年三十七歲。關於這件事,我寫過眾多格調淒美的詩文。我有意迴避了血腥和污穢,以為這樣才符合逝者超凡脫俗的稟性,在真相與永恆之間,我選擇了容易杜撰的永恆,那是任何浪漫藝人都輕車熟路的玄想天地,飛飛在其間變幻,飄升,與萬物彙聚。「一種出自血緣的宗教,」我吹噓道,卻忘了死者也有眼睛。飛飛肯定不滿意她弟弟的那些」流溢著靜態光芒」的裝飾性文字。
龍年陽曆四月的一個兇日,我懷揣「姐車禍身亡」的電報,辭別淚人似的阿霞,乘船轉車,顛簸兩夜,從川東山城涪陵趕往千里之外的川西重鎮綿陽,由於班船誤點,我不得不在重慶耽擱一個白天,邂逅了一位醫生詩友,並相偕下了館子。真是活見鬼,我居然高談闊論,胃口極好,卻感覺不是自己的嘴巴在說和吃。一個聲音提醒我應該哀傷,但在明媚的春日下我無法哀傷。始終和風細雨般的飛飛,牙齒整齊潔白,兩腮瞬動著針孔一樣深的酒渦,她怎麼可能同車禍連在一塊?
晚上十點登車就睡,夤夜醒來冷汗涔涔,車廂內水泄不通,人類與垃圾混合發酵的悶臭薰得我胃酸直冒。我禁不住抵窗幹嘔,一線薄如刀刃的寒風嗖地切入,痛及肺腑。我灌了一大口涼水,呻吟道:「這狂奔的太平間。」
飛飛披散著長髮,站在窗外。我急忙低下頭。隨著目的地的逼近,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怕看她的遺體,雖然我已經在夢魘裏「看」過了。
出了綿陽火車站,直奔紅星路八十七號大院內那棟熟悉的舊樓房,飛飛的屍骨塞滿了腦袋,一根莫須有的棍子抵著我趨前,直到抬手敲門的剎那才鬆開。
沒有門,我在一種鄉間巫術中虛敲了兩下,家人吃驚的神情令我如夢初醒。「姐,」我在屋子裏四處搜尋著,「姐呢?」
沒人理睬我。屋子已經拾掇過了,祭幛厚厚地疊在旮旯裏,晚風起處,陽臺外飄飛著處理花圈殘餘的黑灰。親屬們層巒疊嶂地圍布四周,像客廳舊家俱的一部份,拱衛著中央那隻驚心動魄的骨灰盒。
「怎麼現在才到?」妹妹小飛責怪道。
「我們等了你三天,」姐夫控訴道,「天氣太暖,不能再等了。」
「飛飛死不瞑目啊。」父親歎息。
我掏出電報,傻子一般捉摸了好半天,方醒悟到電報竟誤期了兩天!
「這咋可能?!」親屬們面面相覷。如遭電殛,我的淚水嘩地傾瀉而出,飛飛呀,是你的在天之靈使電報延誤,你太瞭解二毛怕死的本性了。
恐懼在耳鳴中潮起潮落,我解開紅綢,從骨灰裏尋覓飛飛,「就這麼一點?」我惋惜道。
「這是她的全部。」姐夫急忙聲明。「我在焚屍爐前從頭守到尾,眼都沒眨。」
我無地自容。紅綢像一簇冷火,那細密的舌尖吮疼了我的手指。「等我臨終,就抱著你姐趕回李家坪老家。」父親說。「你爺你婆,大家都在一塊,九泉之下也不寂寞。」
「姐應該葬在成都,」妹妹反駁道,「她生前一直想回成都。」
「人死如燈滅,」我莫名其妙地嘀咕,「隨便吧。」
「咋能隨便呢?!」大毛嚷道。
✽✽✽✽✽✽
這是我平生第一位親人去世。雖然年初爺爺也去世了,但那遠在僻靜山鄉的老地主從未進入過我的生活,我對他的悼念是禮儀上的。而飛飛可是同一根藤結出的血緣之瓜,大毛、二毛、小飛對她的依戀之情不亞於母親。
飛飛勞碌一生,做小姑娘時,就習慣使用一個大腳盆包攬全家的髒衣服。嘩啦啦地搓出激情來時,就引吭高歌老電影插曲。她講的恐怖故事遠近聞名,停屍房,鐘鼓樓,吊死鬼的舌頭垂出三丈長的冰,嚇得弟妹們鑽被子,祗敢露一隻眼睛在外。有個夜半她突然失蹤,父母急得上房,我和小飛卻異口同聲證明飛飛喜歡鬼,到底讓她給撞上了。
姐弟幹仗,猴精大毛不是飛飛的對手,就挑唆呆子二毛一道演「三打白骨精」的戲。「豬八戒!」大毛念著京劇臺詞遞過一把掃帚,「你舞著釘耙先到妖精洞前叫陣,老孫隨後來也!」結果豬八戒和孫悟空加起來都不是白骨精的對手。「戲演反了!」我撅著屁股抗議,飛飛被激得哇哇怒吼,跟著拱入床底拖我們出來。
文革前夕,飛飛背井離鄉,剛剛遠走平武縣伐木廠,我們家就成了牛鬼蛇神的窩,被專政得解了體。有先見之明的飛飛在產熊貓的深山老林不僅免遭株連,相反卻渡過了一生中最舒心的時光。她塗改家庭成份混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飾演樣板戲《沙家濱》的主角阿慶嫂,轟動了縣城。母親乞今還保存著一張發黃的野外劇照,飛飛在雪原裏亭亭玉立,背景是簡陋的桌子和圍幕,「春來茶館」的招牌旁邊,隱現著刁德一、胡傳葵一瘦一肥兩瓣屁股。
那時飛飛的崇拜者足有一個團,知青大毛生活無著時,就不遠萬里去那兒混飯。我和小飛也先後沾光,並目睹一英俊小夥向她求愛未遂,竟連吞幾盒火柴自殺。飛飛潸然淚下卻不為所動。可後來,當她真的喜歡上一位解放軍連長時,卻因政審調查不合格而告吹。
時光如水,飛飛不知不覺認了命。嫁人,遷居,做了兩個女孩的母親,碌碌終日,為世人所稱道。大年初四我送她到成都火車站,在人山人海中湧至檢票口,她一把從我肩頭拽過旅行包挎上,再兩手抓住兩個孩子向前卷去,她身不由己地回頭高喊:「二毛,我走了!」自此永訣。
這是一個浮雕中的場景,我的喉嚨裏壘滿了石塊。飛飛的去世感動了街坊鄰里和獄中女犯,大夥兒湊錢買了許多祭幛,灑了許多淚。飛飛天生好心腸,怕見人哭,我擔心她的靈魂會被這麼多哭相累垮的。
她的確活得力不從心。今年春節,一家人圍坐火爐直至深夜,她說她準備出差回平武伐木廠,爭取掙一筆錢,讓全家一起去旅遊。「爸爸可以去江西故地尋根一趟,我呢,累了這麼多年,也該玩一次了。」
玩一次!車中七人,祗死她一個,那條崎嶇的林區公路她不知往返了多少回。當那面包車失控沖下陡坎,左前胎在崖邊懸空,她從車門甩出去,被十米開外的一根碗口粗的樹樁捅穿了腰部。人們將她緩緩取出來,那下半身浸泡在血裏。她的一位老朋友緊摟住她,不停地喚「飛飛,飛飛」,不停地催促司機趕路。她的唇貼著她的耳朵,似乎在呢喃某件舊事。咽氣的瞬間她抬了一下頭,臉頰白得像冬日一望無際的晴空。
✽✽✽✽✽✽
四個姐妹兄弟,先去她一個,這可太不公平了。在我的頭腦深處,汽車還在趕路,輪子輾過前額,激出一層層冷汗。有部美國電影叫《德克薩斯州的巴黎》,講一個身不由己的流浪漢沿著火車路軌尋根—不是他的出產地,而是他父母首次相遇作愛的原點,父親說那是巴黎。
以妓女和香水聞名的巴黎祗能在法國,因此美國境內的「巴黎」是一個放縱、虛幻的玩笑。我們都是惡作劇的產物吧?但上帝憑什麼對飛飛惡作劇?
我們的父母相識於江西,根據他們無意中洩露的隻言片語,我勾勒出家族的大致起因。班主五舅拖一京戲班子出川,在長江沿岸數省巡迴演出謀生,流落到鄱陽湖畔的某縣。五舅性情剛烈,得罪了當地惡霸,被活活打死,戲班群龍無首,頓作鳥獸散。我外婆牽著少女母親,戴孝收屍,葬五舅於城郊。正當她們在新墳前燒紙磕頭,訣別亡魂時,一位教書匠踏青而來。互相憑口音認了老鄉,這是命。
外婆臨終前將母親託付給父親,兩人卻吵吵嚷嚷生活了一輩子,其間幾多波折。母親道:「過日子呀,啥子愛不愛的。」於是有了四個子女。
翻著發黃的老照片,緩緩地追根朔源,是許多傳統家庭的樂趣。可惜我家從來沒有能證明父母早年恩怨的老照片,有幾張單人照,有一張外婆和父親、姐姐、哥哥的合照,比出土文物還要珍貴。
飛飛彌補了父母的缺憾,她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單調乏味的社會環境裏留下了許多豐富多彩的照片。影集摞起來有半人多高。百分之八十是黑白照。她精心地貯藏著這個家庭延續的每一階段,兩代人的光陰被濃縮其中。
血緣從江西境內的那座郊野老墳萌芽,越來越廣闊地在世上兜圈子,現在飛飛趕在父母之前繞回墳地了。
1. 飛飛
1988(0000),四個汽車輪子的年頭,我姐姐飛飛殞於車禍,享年三十七歲。關於這件事,我寫過眾多格調淒美的詩文。我有意迴避了血腥和污穢,以為這樣才符合逝者超凡脫俗的稟性,在真相與永恆之間,我選擇了容易杜撰的永恆,那是任何浪漫藝人都輕車熟路的玄想天地,飛飛在其間變幻,飄升,與萬物彙聚。「一種出自血緣的宗教,」我吹噓道,卻忘了死者也有眼睛。飛飛肯定不滿意她弟弟的那些」流溢著靜態光芒」的裝飾性文字。
龍年陽曆四月的一個兇日,我懷揣「姐車禍身亡」的電報,辭別淚人似的阿霞,乘船轉車,顛簸兩夜,從川東山城涪陵趕往千里之外的川西重鎮綿陽,由於班船誤點,我不得不在重慶耽擱一個白天,邂逅了一位醫生詩友,並相偕下了館子。真是活見鬼,我居然高談闊論,胃口極好,卻感覺不是自己的嘴巴在說和吃。一個聲音提醒我應該哀傷,但在明媚的春日下我無法哀傷。始終和風細雨般的飛飛,牙齒整齊潔白,兩腮瞬動著針孔一樣深的酒渦,她怎麼可能同車禍連在一塊?
晚上十點登車就睡,夤夜醒來冷汗涔涔,車廂內水泄不通,人類與垃圾混合發酵的悶臭薰得我胃酸直冒。我禁不住抵窗幹嘔,一線薄如刀刃的寒風嗖地切入,痛及肺腑。我灌了一大口涼水,呻吟道:「這狂奔的太平間。」
飛飛披散著長髮,站在窗外。我急忙低下頭。隨著目的地的逼近,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怕看她的遺體,雖然我已經在夢魘裏「看」過了。
出了綿陽火車站,直奔紅星路八十七號大院內那棟熟悉的舊樓房,飛飛的屍骨塞滿了腦袋,一根莫須有的棍子抵著我趨前,直到抬手敲門的剎那才鬆開。
沒有門,我在一種鄉間巫術中虛敲了兩下,家人吃驚的神情令我如夢初醒。「姐,」我在屋子裏四處搜尋著,「姐呢?」
沒人理睬我。屋子已經拾掇過了,祭幛厚厚地疊在旮旯裏,晚風起處,陽臺外飄飛著處理花圈殘餘的黑灰。親屬們層巒疊嶂地圍布四周,像客廳舊家俱的一部份,拱衛著中央那隻驚心動魄的骨灰盒。
「怎麼現在才到?」妹妹小飛責怪道。
「我們等了你三天,」姐夫控訴道,「天氣太暖,不能再等了。」
「飛飛死不瞑目啊。」父親歎息。
我掏出電報,傻子一般捉摸了好半天,方醒悟到電報竟誤期了兩天!
「這咋可能?!」親屬們面面相覷。如遭電殛,我的淚水嘩地傾瀉而出,飛飛呀,是你的在天之靈使電報延誤,你太瞭解二毛怕死的本性了。
恐懼在耳鳴中潮起潮落,我解開紅綢,從骨灰裏尋覓飛飛,「就這麼一點?」我惋惜道。
「這是她的全部。」姐夫急忙聲明。「我在焚屍爐前從頭守到尾,眼都沒眨。」
我無地自容。紅綢像一簇冷火,那細密的舌尖吮疼了我的手指。「等我臨終,就抱著你姐趕回李家坪老家。」父親說。「你爺你婆,大家都在一塊,九泉之下也不寂寞。」
「姐應該葬在成都,」妹妹反駁道,「她生前一直想回成都。」
「人死如燈滅,」我莫名其妙地嘀咕,「隨便吧。」
「咋能隨便呢?!」大毛嚷道。
✽✽✽✽✽✽
這是我平生第一位親人去世。雖然年初爺爺也去世了,但那遠在僻靜山鄉的老地主從未進入過我的生活,我對他的悼念是禮儀上的。而飛飛可是同一根藤結出的血緣之瓜,大毛、二毛、小飛對她的依戀之情不亞於母親。
飛飛勞碌一生,做小姑娘時,就習慣使用一個大腳盆包攬全家的髒衣服。嘩啦啦地搓出激情來時,就引吭高歌老電影插曲。她講的恐怖故事遠近聞名,停屍房,鐘鼓樓,吊死鬼的舌頭垂出三丈長的冰,嚇得弟妹們鑽被子,祗敢露一隻眼睛在外。有個夜半她突然失蹤,父母急得上房,我和小飛卻異口同聲證明飛飛喜歡鬼,到底讓她給撞上了。
姐弟幹仗,猴精大毛不是飛飛的對手,就挑唆呆子二毛一道演「三打白骨精」的戲。「豬八戒!」大毛念著京劇臺詞遞過一把掃帚,「你舞著釘耙先到妖精洞前叫陣,老孫隨後來也!」結果豬八戒和孫悟空加起來都不是白骨精的對手。「戲演反了!」我撅著屁股抗議,飛飛被激得哇哇怒吼,跟著拱入床底拖我們出來。
文革前夕,飛飛背井離鄉,剛剛遠走平武縣伐木廠,我們家就成了牛鬼蛇神的窩,被專政得解了體。有先見之明的飛飛在產熊貓的深山老林不僅免遭株連,相反卻渡過了一生中最舒心的時光。她塗改家庭成份混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飾演樣板戲《沙家濱》的主角阿慶嫂,轟動了縣城。母親乞今還保存著一張發黃的野外劇照,飛飛在雪原裏亭亭玉立,背景是簡陋的桌子和圍幕,「春來茶館」的招牌旁邊,隱現著刁德一、胡傳葵一瘦一肥兩瓣屁股。
那時飛飛的崇拜者足有一個團,知青大毛生活無著時,就不遠萬里去那兒混飯。我和小飛也先後沾光,並目睹一英俊小夥向她求愛未遂,竟連吞幾盒火柴自殺。飛飛潸然淚下卻不為所動。可後來,當她真的喜歡上一位解放軍連長時,卻因政審調查不合格而告吹。
時光如水,飛飛不知不覺認了命。嫁人,遷居,做了兩個女孩的母親,碌碌終日,為世人所稱道。大年初四我送她到成都火車站,在人山人海中湧至檢票口,她一把從我肩頭拽過旅行包挎上,再兩手抓住兩個孩子向前卷去,她身不由己地回頭高喊:「二毛,我走了!」自此永訣。
這是一個浮雕中的場景,我的喉嚨裏壘滿了石塊。飛飛的去世感動了街坊鄰里和獄中女犯,大夥兒湊錢買了許多祭幛,灑了許多淚。飛飛天生好心腸,怕見人哭,我擔心她的靈魂會被這麼多哭相累垮的。
她的確活得力不從心。今年春節,一家人圍坐火爐直至深夜,她說她準備出差回平武伐木廠,爭取掙一筆錢,讓全家一起去旅遊。「爸爸可以去江西故地尋根一趟,我呢,累了這麼多年,也該玩一次了。」
玩一次!車中七人,祗死她一個,那條崎嶇的林區公路她不知往返了多少回。當那面包車失控沖下陡坎,左前胎在崖邊懸空,她從車門甩出去,被十米開外的一根碗口粗的樹樁捅穿了腰部。人們將她緩緩取出來,那下半身浸泡在血裏。她的一位老朋友緊摟住她,不停地喚「飛飛,飛飛」,不停地催促司機趕路。她的唇貼著她的耳朵,似乎在呢喃某件舊事。咽氣的瞬間她抬了一下頭,臉頰白得像冬日一望無際的晴空。
✽✽✽✽✽✽
四個姐妹兄弟,先去她一個,這可太不公平了。在我的頭腦深處,汽車還在趕路,輪子輾過前額,激出一層層冷汗。有部美國電影叫《德克薩斯州的巴黎》,講一個身不由己的流浪漢沿著火車路軌尋根—不是他的出產地,而是他父母首次相遇作愛的原點,父親說那是巴黎。
以妓女和香水聞名的巴黎祗能在法國,因此美國境內的「巴黎」是一個放縱、虛幻的玩笑。我們都是惡作劇的產物吧?但上帝憑什麼對飛飛惡作劇?
我們的父母相識於江西,根據他們無意中洩露的隻言片語,我勾勒出家族的大致起因。班主五舅拖一京戲班子出川,在長江沿岸數省巡迴演出謀生,流落到鄱陽湖畔的某縣。五舅性情剛烈,得罪了當地惡霸,被活活打死,戲班群龍無首,頓作鳥獸散。我外婆牽著少女母親,戴孝收屍,葬五舅於城郊。正當她們在新墳前燒紙磕頭,訣別亡魂時,一位教書匠踏青而來。互相憑口音認了老鄉,這是命。
外婆臨終前將母親託付給父親,兩人卻吵吵嚷嚷生活了一輩子,其間幾多波折。母親道:「過日子呀,啥子愛不愛的。」於是有了四個子女。
翻著發黃的老照片,緩緩地追根朔源,是許多傳統家庭的樂趣。可惜我家從來沒有能證明父母早年恩怨的老照片,有幾張單人照,有一張外婆和父親、姐姐、哥哥的合照,比出土文物還要珍貴。
飛飛彌補了父母的缺憾,她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單調乏味的社會環境裏留下了許多豐富多彩的照片。影集摞起來有半人多高。百分之八十是黑白照。她精心地貯藏著這個家庭延續的每一階段,兩代人的光陰被濃縮其中。
血緣從江西境內的那座郊野老墳萌芽,越來越廣闊地在世上兜圈子,現在飛飛趕在父母之前繞回墳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