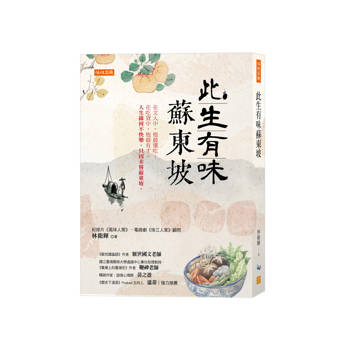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碗飯
到了京師,蘇洵在汴京買了一棟房子。這房子的環境不錯,傍依高槐古柳,前有花園可以種菜。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描述他們的新家:
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
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
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蘇軾兩兄弟參加吏部的典選(相當於面試)後,任職通知來了,蘇軾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轍授澠池縣主簿,官階等級均為最低的從九品。
三年前,蘇軾兩兄弟名譽京城,因母親去世而未能及時獲得任職,這次是補缺。但這樣的低起點,或許是低於兄弟兩人的預期,於是兩人選擇放棄,決定等第二年由仁宗特詔舉行的制科考試。
這種考試的門檻高,要由朝中大臣推薦,先經祕閣試,過關後再由皇帝親自策問。策問的內容每次都不一樣,從六個方面出題:一、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二、博達墳典,明於教化;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詳明政理,可使從政;五、洞識韜略,運籌決勝;六、軍謀宏遠,材任邊寄。這就是「六科取士」。
蘇軾兩兄弟這次策問的考題是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共有四人報考。此次制科考試祕閣試,主考官是司馬光、楊畋、沈遘,蘇軾兩兄弟也因此成為司馬光的門生。
這次考試的難度,就連蘇軾都說:「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意即在萬人之中選拔一人,考試沒有範圍、無所不問,答案還要完美無瑕,這必須好好準備。
於是,兩兄弟從家裡移往汴河南岸的懷遠驛讀書,目的是求清靜。在懷遠驛的日子裡,清靜歸清靜,但還多了清苦。南宋朱弁《曲洧舊聞》對這段日子有這樣的記載: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何物?」答曰:「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碗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吃皛飯。坡不復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唯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饑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
蘇軾和他的好友劉攽(字貢父)談起過去在懷遠驛讀書時,每日三餐只有白飯、白蘿蔔和鹽,戲稱為「三白飯」。劉攽是個愛開玩笑的人,過了一段日子,他發請柬請蘇軾去他家吃「皛飯」。
蘇軾已經忘記前事,以為劉攽讀書多,所謂皛飯必有典故,於是欣然前往。待見到飯桌上只有白飯、白蘿蔔和一碟鹽時,才發覺被劉攽所戲,不過蘇軾還是吃得津津有味。
蘇軾也是愛開玩笑的人,當然會還手。於是,吃完飯後蘇軾準備上馬告辭時,對劉貢父說:「明天到我家,我準備毳飯款待你。」劉貢父害怕被蘇軾戲弄,但又想知道毳飯到底是什麼,第二天便如約前往。
兩人聊了很久,早過了吃飯時間,劉貢父肚子餓得咕咕叫,便問蘇軾為何還不吃飯。蘇軾說:「再等一會兒。」劉貢父又問了好幾次,蘇軾也都給予同樣的答覆。最後,劉貢父說:「我餓得受不了了!」蘇軾才慢吞吞的說:「鹽也毛(音同某,沒有的意思),蘿蔔也毛,飯也毛,豈不是『毳』飯?」劉貢父捧腹大笑,說:「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報昨天的一箭之仇,但萬萬沒想到這一點!」蘇軾這才傳話擺飯,兩人一直吃到傍晚,劉貢父才回家。
經過認真的準備,加上這對兄弟是學霸,考試當然難不倒他們,最後仁宗皇帝評蘇軾為最高等級──三等。沒錯,三等已是當時最高。在宋代,制科一、二等是個虛設,以示皇帝並沒有那麼多不足供士人指摘,另一個用意思是「你再厲害也還是有很大進步空間」。同時參加考試的王介得了四等,而蘇轍經過一番爭議,最終也奪得四等,總共就錄取了這三個人。
仁宗皇帝在考試後高興的對皇后說,他為子孫得到兩個太平宰相:「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陳鵠《耆舊續聞》)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蘇軾,比如王安石。此時的王安石為翰林院的知制誥,這是一個負責為皇帝起草重要文件的職位,據南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載: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
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
王安石私底下對呂公著表示自己不喜歡蘇軾,看來蘇軾與王安石的矛盾,不僅僅是門戶之爭,還有文章風格之異,蘇軾註定一輩子與王安石水火不容。幸好此時王安石說了不算,仁宗說了才算。當然,仁宗說的太平宰相是期貨,做官還是要從基層開始歷練,蘇軾被授「將仕郎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將仕郎和大理寺評事是蘇軾的本官,又稱寄官,決定文官的工資待遇與品級,這個級別是八品;鳳翔府節度判官才是他的實職,比之前的福昌縣主簿高了不少。
在杭州做通判,簡直酒食地獄
在蘇軾留下來的詩詞中,更不乏紅裙白酒、風花雪月。宋代士大夫飲宴,不像我們只是喝酒吃飯,他們筵席過程中還有歌舞表演、吟詩作對。公務應酬有官伎、有錢人私人應酬則有家伎,蘇軾後來納的妾朝雲,就是在這時以家伎的身分到蘇軾家。隸身樂籍的官伎,由政府供養,非一州太守特批不得脫籍,工作由政府派遣,但只限於歌舞和陪酒,不得與官員私通。
宋代重文輕武,崇尚和平發展、不主動發動戰爭,社會安定、天下太平。士大夫的生活可謂自由、放浪、奢華,在女色方面尤其恣縱,蘇軾感嘆:「歷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書寄韻〉)他歷仕三朝的同事,不沾聲色之好的「完人」,他還一個也不曾見過。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蘇軾也不能免俗,尤其是此時的蘇軾文名甚盛,絕對是那個時代的「網紅」。名公巨卿、政治名流,各式名望出眾的人物,都以與蘇軾交往為話題。杭州又是大都市,中央派駐杭州的機構本來就不少,從京城來杭的官員也多,作為一州的副職,迎來送往當然少不了。
據宋代朱彧《萍洲可談》載,面對應酬,蘇軾曾向朋友訴苦:到杭州做通判簡直入酒食地獄。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既然常參加飲宴,置身眾香國裡,蘇軾也不可能做到一塵不染,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蘇軾在欣賞少女風情、享受衣袂間的香氣時,還是克制感情、節制有度的。
上級陳襄很喜歡在有美堂設宴,蘇軾在〈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中說「淒風瑟縮經弦柱,香霧淒迷著髻鬟」;在〈湖上夜歸〉中說「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他這是有距離的欣賞;在〈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首其二中說「西閣珠簾卷落暉,水沉煙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他勸同為通判的魯有開趕緊回家,家裡的妻妾正等著!
蘇軾偶爾也會找理由逃避飲宴,在〈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中他說「我生孤僻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白酒,但愁新進笑陳人」,居然用性格內向、老了、病了當藉口。此時的蘇軾才三十多歲就稱老病,說自己孤僻,誰信?
既然推不掉,那就中途溜了,在〈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中,他說「慣眠處士雲庵裡,倦醉佳人錦瑟旁」,這等好事誰不想?可惜自己無緣享受,因為「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
蘇軾是清醒的,他曾說:「平生嗜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風花雪月誰不喜歡?他開玩笑說自己喜歡吃烤羊肉,可不是吃素的,又借用韓愈〈答柳柳州食蝦蟆〉中「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入鄉隨俗;「烹蛇啖蛙蛤」,說明逢場作戲也未嘗不可,但他雖處流俗,也不為流俗所汙。
對於風月,蘇軾是有節制的參與,但對賞牡丹花,蘇軾卻十分痴迷。西湖邊的吉祥寺種了不少牡丹,蘇軾從外地出差回來後,到吉祥寺賞花,聽聞太守陳襄今年還沒來賞花,牡丹花期短、稍縱即逝,他為此著急,於是寫了〈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這首詩很直白,也很直爽,陳襄第二天就邀請大家同往吉祥寺賞牡丹,蘇軾又賦詩〈述古聞之明日即至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
蘇軾一生寫了不少關於牡丹花的詩詞,做為一名吃貨,他不僅欣賞牡丹花,還想吃牡丹花。剛到杭州不久,他就到明慶寺賞牡丹,並寫下〈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
牡丹花在密密的雨露中開得清秀美麗,夜晚在明亮閃爍的燈光下,它紅豔得像要燃燒一樣;明天,應該還是春天裡的陰天,花兒依然盛開不敗,所以不應忍心以酥煎而食之。是的,古人把牡丹花煎炸成酥吃。宋人祝穆《古今事文類聚》關於酥煎牡丹有軼聞: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次將牡丹花枝分遺朋友時,都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
蘇軾希望姹紫嫣紅久駐人間,能盡情聞其香、睹其豔、賞其美,他不願設想明天的驕陽將會奪去花的芳姿,也不忍像古人那樣煎而食之,珍愛牡丹之情溢於言表。
說到吃牡丹花,蘇軾在〈雨中看牡丹〉三首其三中還提到「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蕊」。宋人似乎很熱衷於酥炸牡丹花,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裡有牡丹生菜,說的是宋高宗吳皇后不愛殺生,要求宮裡御廚進生菜,一定要採一些牡丹花瓣和在裡面,「或用微麵裹,煠之以酥」。這就是蘇軾說的牡丹酥,類似於今天日本料理中的天婦羅。
古人吃牡丹,除了憐香惜玉,覺得吃進肚子比化作春泥是更好的歸宿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據說吃牡丹可以治眼疾。
明代萬曆年間的戲曲作家高濂,杭州人,也是養生專家。他的《遵生八牋》是古代養生學的集大成。他幼時患眼疾等疾病,因此多方搜尋奇藥祕方,終得以康復,遂博覽群書,記錄成此書,其祕訣之一就是煎食牡丹花。
宋人不可能穿越到明代,但蘇軾在杭州時總掛在嘴邊的病就是眼疾,在《東坡志林》裡他說: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與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痼,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鴆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為私記云。
蘇軾患結膜炎,有人告訴他不能吃生魚,他想聽勸,但嘴巴不同意,說:「我是你的口,它是你的眼,你不能厚眼薄口,眼睛患病關我什麼事,不應該廢我的口福。」蘇軾不知怎麼辦,嘴巴又對眼睛說:「改天我生病時,你看東西我也不攔你。」蘇軾想起管仲曾說:像怕生病一樣敬畏天威的人,是人中最上者;像流水一樣隨波逐流的人,則是人中的下等。貪圖安逸享樂如飲毒酒自殺,這是不應該的。《禮記》中說:君子能堅持莊嚴恭敬,就會在道德與事業上一天天強大,如果安樂放肆,就會一天天苟且偷安。我把這句話送給各位紳士,而自己以「畏威如疾」為行為標準。
連自己患病也拿來開玩笑,當然他也從病與吃中悟出一番人生道理,他眼中的風花雪月,風流得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