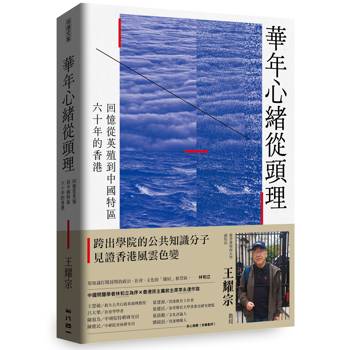自序:香港巨變的歷史畫軸
從小我喜歡看名人或偉人的自傳及傳記,一方面,可以知悉他們成長的歷程,不懈的鬥志;另一方面,亦以他們的成就激發自己向上奮鬥之心。科學家居禮夫人的傳記以及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自傳,令我印象最為深刻。居禮夫人躲在巴黎的實驗室內,耗盡心血,日日夜夜化解數以頓計的煤炭以抽取微量的「鈾」(uranium),令我永誌不忘。羅素自傳三冊,我省吃省用了好幾個月的零用錢,才可以買齊。他的一生,知行合一, 濃厚的人文關懷,學術上的專精與社會批判精神合於一身;自傳的自序,看得我熱血沸騰,至今感動不已,他是我一生中的楷模。
另一本對我人生觀有極重要影響的書,就是劉紹銘教授的《吃馬鈴薯的日子》。書中記錄了他少年時掙扎求學的動人故事,裡面引了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名言「Live life to the full」,此句話成為我一生追求美好生活,發揮個人潛能的動力根源。另外,存在主義的「存在先於本質」,哲學家沙特在他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一書所提出的「人的一生是他行動的總和」的理念,對我也有極大影響。
大約四、五年前,我從未想過會寫回憶錄。人們一向認為要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才會寫自傳。自己雖從事高等教育學術界多年,出版的論文、編著、講稿、政論及書評並不少,但多數並未彙編;自問並非遐邇聞名的學者,也非全身從政的「政治活動家」(political activist)。但在二○一九年反修例運動後,我的想法逐漸改變。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社會發生巨大的巨變;這是香港七十多年來的第三次重大改變: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第三次是二○二○年中實施人大常委會的國安法。
第三次的改變尤為重大。國安法的實施,改變了香港的整體價值觀,也改變了社會結構及政治運行的性質。簡言之,香港從一個以「個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變成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成為壓倒性的行為價值及標準。隨後,在「集體主義」的角度下,必有香港歷史的新論著出現。這樣,我們所熟悉的「歷史真相」將會慢慢消失。我是相信有「客觀真理」的,也相信有「歷史真相」的。在這種氛圍下,我決定寫回憶錄了,我要記錄下我自己的經歷,為後世留下紀錄,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經驗及故事。歷史論述是選擇性的,因此可以是多元的,多種論述可以並存;但「歷史事實」不可偽造。我個人的經歷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構成整體香港歷史的基礎。
人們一般稱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為「嬰兒潮一代」,我們是「嬰兒潮一代」,但我們在七十年代進入大學的一代,肯定是香港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巨變後的第一代 大學畢業生。我們的同輩朋友常常談及,我們一生何其幸運,得睹港英政府的施政,將香港從五十年代的「難民社會」,變成七、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之一,到新世紀「紐倫港」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得益於這個過程:變成豐裕的中產階級之一員,我們這一代實也是最有資格撰寫這幅香港社會巨變的歷史畫軸。
我八歲來港,心理受到極大衝擊,對四周社會事物充滿好奇心,並嘗試理解其變遷,這種好奇心至今不變。但我並非一個政治活動家,對現實政治我雖極為關心,但沒有投入活動, 我的投入只是言論及文字。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及哲學家阿隆(R. Aron)是我最欣賞的學者之一。他寫的自傳名為《投入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 engagé),正是我生平學思行動的寫照。我關心社會政治,但不全力投入,謹希望以觀察者的身分,保持清明洞照心態,提供客觀上的分析;另一方面,我亦知悉行動的重要,改變現實從不能只靠觀念。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在這兩端徘徊不已。回首前塵往事,物換星移,我對自己多年的工作表現是滿意的,生活也感到充實;生命沒有虛度;同時我也感到自己的幸運,能夠把興趣及職業融為一爐(Max Weber稱為「志業」vocation)而持續三十多年。年輕時候,每每著意於改變世界,及至年事漸長,方知外間事物複雜,不可預料因素太多了。我想對自己及朋友說,適當的年歲做適當的事。我的回憶錄寫到二○二二年移居澳洲止。我的心願是能在未來的歲月(也許十年後),再寫一本回憶錄的下集,以記述我在海外的生活及思考。雖然已屆暮年,可幹的事還可多呢!誠如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詩句所說:「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最後,我邀請了兩位老朋友林和立兄和李永達兄,為這本回憶錄撰寫序言及跋,我極度感謝他們的推許。林兄和我是中學同學,友誼已逾六十年;而認識達兄也有四十年了。
二○二四年二月廿四日 初稿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修訂稿
寫於澳洲布里斯本
從小我喜歡看名人或偉人的自傳及傳記,一方面,可以知悉他們成長的歷程,不懈的鬥志;另一方面,亦以他們的成就激發自己向上奮鬥之心。科學家居禮夫人的傳記以及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自傳,令我印象最為深刻。居禮夫人躲在巴黎的實驗室內,耗盡心血,日日夜夜化解數以頓計的煤炭以抽取微量的「鈾」(uranium),令我永誌不忘。羅素自傳三冊,我省吃省用了好幾個月的零用錢,才可以買齊。他的一生,知行合一, 濃厚的人文關懷,學術上的專精與社會批判精神合於一身;自傳的自序,看得我熱血沸騰,至今感動不已,他是我一生中的楷模。
另一本對我人生觀有極重要影響的書,就是劉紹銘教授的《吃馬鈴薯的日子》。書中記錄了他少年時掙扎求學的動人故事,裡面引了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名言「Live life to the full」,此句話成為我一生追求美好生活,發揮個人潛能的動力根源。另外,存在主義的「存在先於本質」,哲學家沙特在他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一書所提出的「人的一生是他行動的總和」的理念,對我也有極大影響。
大約四、五年前,我從未想過會寫回憶錄。人們一向認為要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才會寫自傳。自己雖從事高等教育學術界多年,出版的論文、編著、講稿、政論及書評並不少,但多數並未彙編;自問並非遐邇聞名的學者,也非全身從政的「政治活動家」(political activist)。但在二○一九年反修例運動後,我的想法逐漸改變。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社會發生巨大的巨變;這是香港七十多年來的第三次重大改變: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第三次是二○二○年中實施人大常委會的國安法。
第三次的改變尤為重大。國安法的實施,改變了香港的整體價值觀,也改變了社會結構及政治運行的性質。簡言之,香港從一個以「個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變成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成為壓倒性的行為價值及標準。隨後,在「集體主義」的角度下,必有香港歷史的新論著出現。這樣,我們所熟悉的「歷史真相」將會慢慢消失。我是相信有「客觀真理」的,也相信有「歷史真相」的。在這種氛圍下,我決定寫回憶錄了,我要記錄下我自己的經歷,為後世留下紀錄,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經驗及故事。歷史論述是選擇性的,因此可以是多元的,多種論述可以並存;但「歷史事實」不可偽造。我個人的經歷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構成整體香港歷史的基礎。
人們一般稱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為「嬰兒潮一代」,我們是「嬰兒潮一代」,但我們在七十年代進入大學的一代,肯定是香港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巨變後的第一代 大學畢業生。我們的同輩朋友常常談及,我們一生何其幸運,得睹港英政府的施政,將香港從五十年代的「難民社會」,變成七、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之一,到新世紀「紐倫港」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得益於這個過程:變成豐裕的中產階級之一員,我們這一代實也是最有資格撰寫這幅香港社會巨變的歷史畫軸。
我八歲來港,心理受到極大衝擊,對四周社會事物充滿好奇心,並嘗試理解其變遷,這種好奇心至今不變。但我並非一個政治活動家,對現實政治我雖極為關心,但沒有投入活動, 我的投入只是言論及文字。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及哲學家阿隆(R. Aron)是我最欣賞的學者之一。他寫的自傳名為《投入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 engagé),正是我生平學思行動的寫照。我關心社會政治,但不全力投入,謹希望以觀察者的身分,保持清明洞照心態,提供客觀上的分析;另一方面,我亦知悉行動的重要,改變現實從不能只靠觀念。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在這兩端徘徊不已。回首前塵往事,物換星移,我對自己多年的工作表現是滿意的,生活也感到充實;生命沒有虛度;同時我也感到自己的幸運,能夠把興趣及職業融為一爐(Max Weber稱為「志業」vocation)而持續三十多年。年輕時候,每每著意於改變世界,及至年事漸長,方知外間事物複雜,不可預料因素太多了。我想對自己及朋友說,適當的年歲做適當的事。我的回憶錄寫到二○二二年移居澳洲止。我的心願是能在未來的歲月(也許十年後),再寫一本回憶錄的下集,以記述我在海外的生活及思考。雖然已屆暮年,可幹的事還可多呢!誠如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詩句所說:「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最後,我邀請了兩位老朋友林和立兄和李永達兄,為這本回憶錄撰寫序言及跋,我極度感謝他們的推許。林兄和我是中學同學,友誼已逾六十年;而認識達兄也有四十年了。
二○二四年二月廿四日 初稿
二○二五年三月十日 修訂稿
寫於澳洲布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