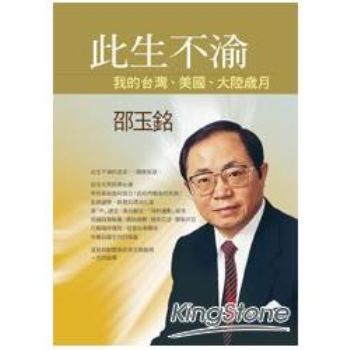我生於一九三九年,是東北九一八事變的第了解「滿洲國」的體制,但我知道當時東北是在日本統治之下,像所有東北人一樣,從小就有反日情懷。
二、父親抗日,投奔西安
一九四二年底,家父在農業大學參加一個祕密抗日組織—「反滿抗日救國會」。不幸事機洩漏,日本憲兵隊大肆抓人。父親決定逃離東北,但不敢將實情告知祖父母及母親,以免他們擔心,託詞要前往關內辦事,翌年春節即可返家。父親單身離家,留下媽媽和我。父親(一九一九─一九九七)在去世前,曾留一未出版的回憶錄手稿—《我的一生》,內中提及他離家時和我的一段對話:
當時行色匆匆、心神不定。這時銘兒約四歲,他愣愣望著我,我一時衝動將他抱在懷中,淚流滿面,銘兒問我:「爸爸您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來?」我說:「過年的時候回來……」銘兒又說:「那您為什麼哭了呢?」此話一出,家人哭成一團。
父親離家後,第一站先去河南省開封市,拜望當時曾在哈爾濱農業大學教書的張姓老師。父親一直在東北長大,到了開封,才對抗戰大局及國共關係有較深了解。父親因自小景仰國父孫中山先生,決定投靠國民政府,參加抗戰行列。由於河南屬汪精衛的偽南京維新政府管轄,日軍又出沒無常,父親決定前往由國民政府控制的陝西省西安市。
到了西安,父親已是人窮財盡。當時正巧中央警官學校正科班招生,該校校長為蔣中正委員長兼任。父親為了求學,也為了將來就業,決定報考。同榜學生兩百餘人,多為淪陷區各大專流亡學生,父親以第二名錄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入學。
三、母子萬里尋親
父親在赴西安前,寫信給祖父母及我母親,表示將進入後方,但並未說明確定去處。母親收到此信後,喜極而泣。
母親也出身地主之家,親母去世後,由後娘帶大,頗遭歧視,不給她念書。後母為其親生子女,僱一私塾老師在書房授課,不外念些《百家姓》、《千家詩》等書籍。當後母兄妹還未會背誦課文時,母親在隔壁偷聽,用心加上決心,已能朗朗上口,這更使其後母對她忌恨,時常遭受打罵。所以,對母親而言,二十一歲嫁給父親—既是家鄉首富之子,又是大學生,是她一生幸福之所寄。如今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是將去大後方,母親認定應是重慶地區,便本著「出嫁從夫」的傳統觀念,決定萬里尋夫。但祖父母因為考慮到時局動盪,對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婦道人家帶著幼子長途跋涉,堅決反對。然母親心意已決,祖父母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將孫子留在家裡,母親不同意,執意要攜子尋夫,祖父甚至以不給盤纏為要脅,但母親不為所動。
最後,在母親堅持下,祖母心軟,大概也怕她孫子旅途中無錢吃苦,偷偷塞了一份頗豐的盤纏給了母親。於是母子兩人,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萬里尋親之旅,母親時年三十,我六歲。
母親知道父親有位張老師住在開封,開封就成了第一站。我倆先從哈爾濱坐火車到山海關,再從山海關坐火車到開封。但一到開封車站,該站因有日軍軍車經過,已遭陳納德將軍所率領之飛虎隊轟炸,死傷慘重,屍體狼藉四處,百姓驚慌逃難、互相推擠,母親和我必須抓緊車站之鐵絲網,以防跌倒。
到了開封,母親找到張老師,在他家住了一個月。在開封又聯絡上父親在哈爾濱農大同學劉裕庭,他們夫婦此時也想到大後方追隨政府抗戰,經過他們的規畫,決定先到西安再往重慶。
由於此時隴海鐵路已被炸毀,我們從開封到西安只能先步行到陝西省潼關,共六百多公里,然後從潼關坐火車到西安。為了躲避日軍及皇協軍(由日本華北方面軍組成的偽軍),決定走鄉間小路。從開封先到鄭州,再經過十八盤等地,進入潼關。沿路若無汽車可坐時,就得坐板車、或騎驢、或步行。此時河南地區為不同部隊所控制,除日軍、皇協軍外,尚有中央政府軍、中共之新四軍,甚至地方土匪。母親必須一一因應,遇到地方土匪,有時還得交付「買路錢」。當時各地使用不同幣制,母親在東北時是用偽滿國幣,到了華北則用冀東政府儲備券,在中央政府控制地區則用法幣或關金券。她將各種錢幣藏在大衣內層,以免被沒收。
旅途中,旅館小又貴,有時無房間時,只能睡在旅館走道上,但也要付錢。路上有時找不到飯店,就只能用白水煮麵條,加點鹽巴或辣椒粉果腹。
走路對母親是很大的折磨,她有雙「解放腳」(即裹腳後又放開者),不良於行,一路疼痛不堪。加上環境衛生差,有時得喝河水,所以她在路上開始打擺子(即瘧疾),飽受忽冷忽熱、上吐下瀉的煎熬,她仍咬緊牙根,白天雞鳴即起趕路,天黑投宿。
沿途經過十八盤鄉時,旅程開始更加艱難,一路上除了上山就是下山,最高海拔達一千多米,素有「九山三水十八彎」之稱,境內大小山頭有一百多座。我年小走不動,母親只得僱一驢子,把我放在驢背上,如遇山勢過陡,就由驢伕抱我而行,母親則和劉太太相互扶持前進。由於母親打擺子,時好時壞,有一次她實在走不動了,自認大限已到,懇求劉氏夫婦將我帶到西安,她就死而無憾了。但劉氏夫婦堅決表示既然同行,生死同命,母親只得作罷,休息了一、兩天後,重新上路。我想母親最後有毅力走完全程,一是她對父親的熱愛,二是她一定要將我交給父親,以盡到做妻子的責任。
一行四人終於在三個月後抵達潼關,進入國軍控制地區。母親此時已身無分文,只好賣了兩件衣服,才能買火車票前往西安。母親到西安時,人瘦了一大圈。由於一路打擺子,加上喝的都是河水,以後一生再無月事,無法懷孕,這也注定我一生為獨子的命運。
在這漫長的旅程途中,時而遇到政府軍與日本軍作戰,或政府軍與八路軍開火。耳邊的槍聲、路邊的屍首、成串的難民,我雖只六歲,迄今仍難忘記。日後我陪父親參加東北同鄉聚會,大家總愛唱「流亡三部曲」,每當唱第一曲「松花江上」時,我就會想到這段流浪的經歷,不禁熱淚盈眶,不能自已。「松花江上」遂成為我生命中的第一首歌,那歌詞的每個字我都記得,像刻在心上一樣: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留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爹娘啊!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從哈爾濱到西安,可說是我「流亡」的第一部曲。
到了西安以後,劉叔叔(裕庭)有好幾天看到有位邵再新先生在《華北新聞》寫了一系列有關日本掌控偽滿洲國及其一路逃亡遭遇的文章,頗引起西安地區讀者注意。劉叔叔讀後,猜想是父親所寫,到報社打聽到父親地址,即來警校找尋父親。
好友異地重逢,當然是欣喜萬分,但令父親更驚訝的是我們母子已到西安。三人一見,抱頭痛哭,母子終於完成了尋夫與尋父之心願。
然而,在西安見到父親,並不是困厄的結束,而是另一段苦日子的開始。
父親在警校靠公費,只能自足,母親和我馬上面臨生活的問題。幸好有位同鄉徐景新營長,係胡宗南將軍部屬,願意僱我母親為管家。但母親不方便帶我上班,不得已將我寄託在西安市兒童教養院。該院由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創辦,收容軍眷兒童及貧苦孤兒。我原是想與父親團聚,才跋山涉水而來,不料現在竟連母親也無法陪在身邊,有如孤兒,只在週日才得和父母團聚。
教養院的生活非常清苦,孩子們穿的衣服是軍人的舊衣服或兒童織布自製的衣服。平時每天兩餐,以玉米、小麥、麩皮為主,有時不得不吃發了霉的高粱米和帶有沙粒的大米。居住的是草棚,遇到颳風下雨或寒冬大雪天氣,就淒苦不堪。還記得教養院衛生環境很差,很多院童都患有寄生蟲的毛病,而我第一次在茅坑看到蛔蟲時,嚇得魂都沒了。院內兒童除了上課學習外,還要從事生產勞動,學習謀生技能。
由於全家經濟困頓,父親必須常在《華北新聞》副刊寫些雜文或短篇小說,賺取稿費養家。當時在該報寫文章的還有名作家無名氏,他的名著《塔裡的女人》正在該報發表,非常轟動,父親得以相識。記得星期假日時,父親會用稿費買些牛、羊肉,而我同母親則到王寶釧苦守的寒窯附近野地摘些薺菜,一家人和父親的幾個同學一齊包餃子,算是吃頓團圓飯。但第二天我又得回到教養院,眼巴巴期盼下一個週日的到來。由於這個經驗,我一生對薺菜餃子情有獨鍾。
在教養院過了一年後,由於父親稿費增多,加上母親靠針線手工,做鞋賣錢,我才能進入西安一所小學念一年級及二年級。
四、返鄉東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父親尚未完成學業,迄一九四七年六月父親終於畢業,由於政府正進行接收東北工作,全部同學均被派往東北各省市實習。
從西安到東北途中發生了一件驚險萬分的趣事。當時搭的火車是運貨的板車,其中有塊木板掉了,留了一道很寬的縫隙,我身旁一位家父的杜姓同學,平躺其上倒還無妨,一翻身不小心竟掉到火車輪下。幸好他瘦骨嶙峋,僅受點擦傷,待車輪駛過才又緊追車廂而上,大家一面為他捏把冷汗、一面也慶幸他大難不死,此人後來在台灣位居高級文官,果有「後福」。
父親到瀋陽後,奉派遼寧省開原縣警察局實習,一家人借住瀋陽市鐵西區啤酒廠宿舍,我進小學念三年級。這時國軍與共軍為爭地盤已爆發許多軍事衝突。我九歲,對國共恩怨之歷史並不清楚,令我不解的是,國共共同抵抗日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但為何在抗戰之後,同是炎黃子孫也要殺得你死我活?有時爸爸給我講解,我似懂非懂,從未想到這個疑問跟隨了我一生。
在瀋陽時期,有幾件事讓我深深體驗到戰亂的災難與人性的險惡。
第一件事,有關住家附近啤酒廠的故事。該啤酒廠原是附近小朋友利用酒廠機器隙縫玩捉迷藏遊戲的地方。但在蘇聯軍隊占領期間(蘇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入東北,一九四六年五月始撤軍),將機器搜刮一空,整個廠房空空蕩蕩,所以到我去時,鄰居小孩再也無法玩捉迷藏了。當小朋友告訴我此事時,使我仇日之外,又多了個蘇聯。
第二件事,是一位開雜貨店老先生性侵幼童之事。我的一位同學常去那家店玩,每次總會帶幾個糖球回來,讓我好生羨慕。他在拗不過我對他的盤問後,終於告訴我:「只要你讓那老頭『為所欲為』,你也可以同我一樣有糖球吃。」當時我年幼,不懂何謂「讓那老頭『為所欲為』」,有天便傻呼呼地跟著去了。老頭給我糖球後,沒多久,就開始對我毛手毛腳,嚇得我拔腿就跑。戰亂期間,小孩子無錢買糖,這一位老人居然利用孩童弱點來滿足他的獸慾。
第三件事,是在戰亂中,不單是老人,連青少年也展現出人性的醜陋面。家父為了籌措逃難旅費,叫我在家門口擺地攤變賣家中藏書。擺了一天,眼看太陽西下,一本也沒賣出去。這時跑來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和我搭訕,對我先表示同情,然後說附近冰河對岸有人要買書,可以帶我去。我當然喜出望外,對這位大哥感激得不得了,馬上找個布袋把書都裝起來。這位大哥說怕我扛不動,就熱心地替我背著布袋,我就尾隨他走過冰河。孰料,才一過河,他拔腿就跑,我在後面拚命追,不僅未追上,連鞋子都跑掉了。最後,天黑回家,一方面害怕挨罵,一方面又充滿委屈和憤慨,不禁擁抱父母嚎啕大哭起來。
二、父親抗日,投奔西安
一九四二年底,家父在農業大學參加一個祕密抗日組織—「反滿抗日救國會」。不幸事機洩漏,日本憲兵隊大肆抓人。父親決定逃離東北,但不敢將實情告知祖父母及母親,以免他們擔心,託詞要前往關內辦事,翌年春節即可返家。父親單身離家,留下媽媽和我。父親(一九一九─一九九七)在去世前,曾留一未出版的回憶錄手稿—《我的一生》,內中提及他離家時和我的一段對話:
當時行色匆匆、心神不定。這時銘兒約四歲,他愣愣望著我,我一時衝動將他抱在懷中,淚流滿面,銘兒問我:「爸爸您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來?」我說:「過年的時候回來……」銘兒又說:「那您為什麼哭了呢?」此話一出,家人哭成一團。
父親離家後,第一站先去河南省開封市,拜望當時曾在哈爾濱農業大學教書的張姓老師。父親一直在東北長大,到了開封,才對抗戰大局及國共關係有較深了解。父親因自小景仰國父孫中山先生,決定投靠國民政府,參加抗戰行列。由於河南屬汪精衛的偽南京維新政府管轄,日軍又出沒無常,父親決定前往由國民政府控制的陝西省西安市。
到了西安,父親已是人窮財盡。當時正巧中央警官學校正科班招生,該校校長為蔣中正委員長兼任。父親為了求學,也為了將來就業,決定報考。同榜學生兩百餘人,多為淪陷區各大專流亡學生,父親以第二名錄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入學。
三、母子萬里尋親
父親在赴西安前,寫信給祖父母及我母親,表示將進入後方,但並未說明確定去處。母親收到此信後,喜極而泣。
母親也出身地主之家,親母去世後,由後娘帶大,頗遭歧視,不給她念書。後母為其親生子女,僱一私塾老師在書房授課,不外念些《百家姓》、《千家詩》等書籍。當後母兄妹還未會背誦課文時,母親在隔壁偷聽,用心加上決心,已能朗朗上口,這更使其後母對她忌恨,時常遭受打罵。所以,對母親而言,二十一歲嫁給父親—既是家鄉首富之子,又是大學生,是她一生幸福之所寄。如今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是將去大後方,母親認定應是重慶地區,便本著「出嫁從夫」的傳統觀念,決定萬里尋夫。但祖父母因為考慮到時局動盪,對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婦道人家帶著幼子長途跋涉,堅決反對。然母親心意已決,祖父母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將孫子留在家裡,母親不同意,執意要攜子尋夫,祖父甚至以不給盤纏為要脅,但母親不為所動。
最後,在母親堅持下,祖母心軟,大概也怕她孫子旅途中無錢吃苦,偷偷塞了一份頗豐的盤纏給了母親。於是母子兩人,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開始了為期四個月的萬里尋親之旅,母親時年三十,我六歲。
母親知道父親有位張老師住在開封,開封就成了第一站。我倆先從哈爾濱坐火車到山海關,再從山海關坐火車到開封。但一到開封車站,該站因有日軍軍車經過,已遭陳納德將軍所率領之飛虎隊轟炸,死傷慘重,屍體狼藉四處,百姓驚慌逃難、互相推擠,母親和我必須抓緊車站之鐵絲網,以防跌倒。
到了開封,母親找到張老師,在他家住了一個月。在開封又聯絡上父親在哈爾濱農大同學劉裕庭,他們夫婦此時也想到大後方追隨政府抗戰,經過他們的規畫,決定先到西安再往重慶。
由於此時隴海鐵路已被炸毀,我們從開封到西安只能先步行到陝西省潼關,共六百多公里,然後從潼關坐火車到西安。為了躲避日軍及皇協軍(由日本華北方面軍組成的偽軍),決定走鄉間小路。從開封先到鄭州,再經過十八盤等地,進入潼關。沿路若無汽車可坐時,就得坐板車、或騎驢、或步行。此時河南地區為不同部隊所控制,除日軍、皇協軍外,尚有中央政府軍、中共之新四軍,甚至地方土匪。母親必須一一因應,遇到地方土匪,有時還得交付「買路錢」。當時各地使用不同幣制,母親在東北時是用偽滿國幣,到了華北則用冀東政府儲備券,在中央政府控制地區則用法幣或關金券。她將各種錢幣藏在大衣內層,以免被沒收。
旅途中,旅館小又貴,有時無房間時,只能睡在旅館走道上,但也要付錢。路上有時找不到飯店,就只能用白水煮麵條,加點鹽巴或辣椒粉果腹。
走路對母親是很大的折磨,她有雙「解放腳」(即裹腳後又放開者),不良於行,一路疼痛不堪。加上環境衛生差,有時得喝河水,所以她在路上開始打擺子(即瘧疾),飽受忽冷忽熱、上吐下瀉的煎熬,她仍咬緊牙根,白天雞鳴即起趕路,天黑投宿。
沿途經過十八盤鄉時,旅程開始更加艱難,一路上除了上山就是下山,最高海拔達一千多米,素有「九山三水十八彎」之稱,境內大小山頭有一百多座。我年小走不動,母親只得僱一驢子,把我放在驢背上,如遇山勢過陡,就由驢伕抱我而行,母親則和劉太太相互扶持前進。由於母親打擺子,時好時壞,有一次她實在走不動了,自認大限已到,懇求劉氏夫婦將我帶到西安,她就死而無憾了。但劉氏夫婦堅決表示既然同行,生死同命,母親只得作罷,休息了一、兩天後,重新上路。我想母親最後有毅力走完全程,一是她對父親的熱愛,二是她一定要將我交給父親,以盡到做妻子的責任。
一行四人終於在三個月後抵達潼關,進入國軍控制地區。母親此時已身無分文,只好賣了兩件衣服,才能買火車票前往西安。母親到西安時,人瘦了一大圈。由於一路打擺子,加上喝的都是河水,以後一生再無月事,無法懷孕,這也注定我一生為獨子的命運。
在這漫長的旅程途中,時而遇到政府軍與日本軍作戰,或政府軍與八路軍開火。耳邊的槍聲、路邊的屍首、成串的難民,我雖只六歲,迄今仍難忘記。日後我陪父親參加東北同鄉聚會,大家總愛唱「流亡三部曲」,每當唱第一曲「松花江上」時,我就會想到這段流浪的經歷,不禁熱淚盈眶,不能自已。「松花江上」遂成為我生命中的第一首歌,那歌詞的每個字我都記得,像刻在心上一樣: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留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爹娘啊!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從哈爾濱到西安,可說是我「流亡」的第一部曲。
到了西安以後,劉叔叔(裕庭)有好幾天看到有位邵再新先生在《華北新聞》寫了一系列有關日本掌控偽滿洲國及其一路逃亡遭遇的文章,頗引起西安地區讀者注意。劉叔叔讀後,猜想是父親所寫,到報社打聽到父親地址,即來警校找尋父親。
好友異地重逢,當然是欣喜萬分,但令父親更驚訝的是我們母子已到西安。三人一見,抱頭痛哭,母子終於完成了尋夫與尋父之心願。
然而,在西安見到父親,並不是困厄的結束,而是另一段苦日子的開始。
父親在警校靠公費,只能自足,母親和我馬上面臨生活的問題。幸好有位同鄉徐景新營長,係胡宗南將軍部屬,願意僱我母親為管家。但母親不方便帶我上班,不得已將我寄託在西安市兒童教養院。該院由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創辦,收容軍眷兒童及貧苦孤兒。我原是想與父親團聚,才跋山涉水而來,不料現在竟連母親也無法陪在身邊,有如孤兒,只在週日才得和父母團聚。
教養院的生活非常清苦,孩子們穿的衣服是軍人的舊衣服或兒童織布自製的衣服。平時每天兩餐,以玉米、小麥、麩皮為主,有時不得不吃發了霉的高粱米和帶有沙粒的大米。居住的是草棚,遇到颳風下雨或寒冬大雪天氣,就淒苦不堪。還記得教養院衛生環境很差,很多院童都患有寄生蟲的毛病,而我第一次在茅坑看到蛔蟲時,嚇得魂都沒了。院內兒童除了上課學習外,還要從事生產勞動,學習謀生技能。
由於全家經濟困頓,父親必須常在《華北新聞》副刊寫些雜文或短篇小說,賺取稿費養家。當時在該報寫文章的還有名作家無名氏,他的名著《塔裡的女人》正在該報發表,非常轟動,父親得以相識。記得星期假日時,父親會用稿費買些牛、羊肉,而我同母親則到王寶釧苦守的寒窯附近野地摘些薺菜,一家人和父親的幾個同學一齊包餃子,算是吃頓團圓飯。但第二天我又得回到教養院,眼巴巴期盼下一個週日的到來。由於這個經驗,我一生對薺菜餃子情有獨鍾。
在教養院過了一年後,由於父親稿費增多,加上母親靠針線手工,做鞋賣錢,我才能進入西安一所小學念一年級及二年級。
四、返鄉東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父親尚未完成學業,迄一九四七年六月父親終於畢業,由於政府正進行接收東北工作,全部同學均被派往東北各省市實習。
從西安到東北途中發生了一件驚險萬分的趣事。當時搭的火車是運貨的板車,其中有塊木板掉了,留了一道很寬的縫隙,我身旁一位家父的杜姓同學,平躺其上倒還無妨,一翻身不小心竟掉到火車輪下。幸好他瘦骨嶙峋,僅受點擦傷,待車輪駛過才又緊追車廂而上,大家一面為他捏把冷汗、一面也慶幸他大難不死,此人後來在台灣位居高級文官,果有「後福」。
父親到瀋陽後,奉派遼寧省開原縣警察局實習,一家人借住瀋陽市鐵西區啤酒廠宿舍,我進小學念三年級。這時國軍與共軍為爭地盤已爆發許多軍事衝突。我九歲,對國共恩怨之歷史並不清楚,令我不解的是,國共共同抵抗日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但為何在抗戰之後,同是炎黃子孫也要殺得你死我活?有時爸爸給我講解,我似懂非懂,從未想到這個疑問跟隨了我一生。
在瀋陽時期,有幾件事讓我深深體驗到戰亂的災難與人性的險惡。
第一件事,有關住家附近啤酒廠的故事。該啤酒廠原是附近小朋友利用酒廠機器隙縫玩捉迷藏遊戲的地方。但在蘇聯軍隊占領期間(蘇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入東北,一九四六年五月始撤軍),將機器搜刮一空,整個廠房空空蕩蕩,所以到我去時,鄰居小孩再也無法玩捉迷藏了。當小朋友告訴我此事時,使我仇日之外,又多了個蘇聯。
第二件事,是一位開雜貨店老先生性侵幼童之事。我的一位同學常去那家店玩,每次總會帶幾個糖球回來,讓我好生羨慕。他在拗不過我對他的盤問後,終於告訴我:「只要你讓那老頭『為所欲為』,你也可以同我一樣有糖球吃。」當時我年幼,不懂何謂「讓那老頭『為所欲為』」,有天便傻呼呼地跟著去了。老頭給我糖球後,沒多久,就開始對我毛手毛腳,嚇得我拔腿就跑。戰亂期間,小孩子無錢買糖,這一位老人居然利用孩童弱點來滿足他的獸慾。
第三件事,是在戰亂中,不單是老人,連青少年也展現出人性的醜陋面。家父為了籌措逃難旅費,叫我在家門口擺地攤變賣家中藏書。擺了一天,眼看太陽西下,一本也沒賣出去。這時跑來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和我搭訕,對我先表示同情,然後說附近冰河對岸有人要買書,可以帶我去。我當然喜出望外,對這位大哥感激得不得了,馬上找個布袋把書都裝起來。這位大哥說怕我扛不動,就熱心地替我背著布袋,我就尾隨他走過冰河。孰料,才一過河,他拔腿就跑,我在後面拚命追,不僅未追上,連鞋子都跑掉了。最後,天黑回家,一方面害怕挨罵,一方面又充滿委屈和憤慨,不禁擁抱父母嚎啕大哭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