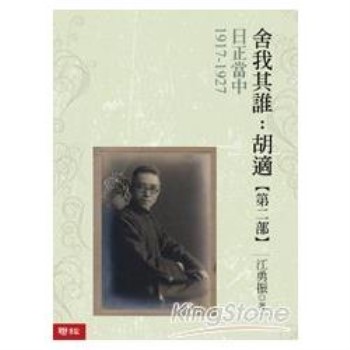序幕
胡適愛北京。陳衡哲在1927年底給胡適的一封信裡說:「在我們這些朋友當中,你可以算是最愛北京的一個人了。」當時,陳衡哲跟任鴻雋搬到了北京,胡適卻從美國回來以後就住在了上海。胡適這樣跟他們捉迷藏,她調侃胡適說,一定是因?他不願意跟他們住在「你的『最文明的北京城』 」裡。我們不知道胡適是什?時候開始愛上北京的。他在剛回國的時候,曾經在〈歸國雜感〉裡痛斥了北京、上海的髒亂,他說:「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在新近發現的《嘗試集》第二編的初稿本裡,有胡適在1918年6月7日所寫的一篇序。他在這篇自序中,仍然說到北京的「塵土」與「齷齪」:「自從我去年秋間來北京——塵土的北京,齷齪的北京——居然也會做了一些詩。」
胡適在1917年回國,到北京大學去任教的時候,北京究竟是什?樣子,除了他在〈歸國雜感〉裡說它髒亂以外,胡適並沒有進一步的描述。他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杜威以及其夫人在1919年訪問中國的時候,從美國人的觀點,倒是留下了一些寶貴的分析。杜威夫婦的觀感,毫無疑問地,是從美國社會當時的物質條件的標準來衡量北京的。然而,其可貴的地方就正在此處。因?它給了我們一個外來的、中國後來要花了一個世紀的時光來追趕的標準來盱衡當時落後的中國。杜威在到了北京以後,這樣地描述了北京的房子:
所有北京的房子就像我們〔美國〕的柴房,直接就蓋在地上。房子裡地上的石板跟底下
的土地就只有幾英寸之隔。一下大雨,院子裡就積滿了水。接下來,那院子就可以泥濘
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那濕氣沿著房子裡的牆角往上滲透,可以沿著牆壁往上爬伸
到兩英尺之高。我們昨天去拜訪一個中國朋友。他的家就是處於那種狀態之下,可是他
彷彿視若無睹,怡然自得。他如果想在自己家裡洗個澡,他就得付水夫雙倍的價錢。可
是,在忙完了煮水、打水的工作,洗了個澡以後,他還得找人一桶一桶地把用過的洗澡
水拿出去處理掉。
我們不知道杜威夫婦去拜訪的是不是胡適的家。然而,可以想像的,當時胡適住在南池子緞庫後胡同8號的房子也不會例外。這幢位在緞庫後胡同的四合院是胡適在1918年?了接江冬秀到北京來住而租下來的。胡適在緞庫後胡同租下來的這幢四合院的房子究竟是十七間還是十八間,他自己在家信裡並沒有一致的說法。但是,對這幢四合院,他在家信裡作了簡單的描述。他對江冬秀說:「我已租了一所新屋,預備五六日內搬進去住。這屋有九間正房,五間偏房(作廚房幾仆婢住房),兩間套房。離大學也不遠(與江朝宗〔注:江冬秀家鄉江村的名人,1917年間曾任代國務總理〕住宅相隔一巷)。房租每月二十元。」他在搬進去以後給他母親的信裡說:「我已於〔三月〕卅日搬入新寓居住。此屋很好,入校既便,出城也便。」
這就在在證明了在不同的文化裡生活的人,看到的東西往往有所不同。有些事物在一個社會裡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是夢寐以求的,人人都會巨細無遺的一覽無遺;反之,有些事物,由於一個社會裡的人習以?常,視若無睹。反而必須要等異文化的人,帶著不同的文化包袱與視野來點出。對胡適在緞庫後胡同8號的四合院,杜威夫人的描述跟胡適自己的描述就在著重點上大異其趣。杜威夫人?她子女所作的描述如下:
昨天我們去看了一個朋友〔胡適?〕的家。很有意思。我會想住在一間類似的房子裡。
那房子裡沒有水,就靠水夫每天打來。這幢小房子有十八個房間,中間是座院子。這就
意味著說,它有四個屋頂,從一廂到另一廂,就得走出屋外,即使寒暑表上的刻度是零
下二十度,也必須如此。屋內的地都是石板。我們並沒看所有的房間。有些窗子是紙糊
的,有些則裝有玻璃。夏天的時候,他們在院子裡搭著一個用席子編成的暫時的屋頂。
它比四個廂房的屋頂都要高,以便通風,而且可以用來遮蔭。
無怪乎胡適是到澡堂去洗澡的。其意義顯然非凡,所以在他寫日記最勤的時候,例如1921年到1922年之間,他每次上澡堂,都會在日記裡留下記錄。四合院裡不但沒有水、沒有洗浴的設施、沒有下水道,而且廚房的位置與設施,也讓杜威夫婦瞠目結舌:
中國家庭裡的廚房總是離飯廳好幾個英尺以外的另一間房子裡。通常的情形是,你必須
穿過露天的院子從廚房走到飯廳。由於我們到了北京以後一直沒下過雨,我不知道那傘
下之湯是否會走了樣……清華學堂,那有名的用庚款來辦的學堂,是新蓋的,是美國人
作主的。〔然而,〕它的廚房和餐廳相隔有四十英尺之遙。我就不描寫廚房的樣子了。
但是,你只要看到那泥?的斑駁與崩塌垂危之勢,沒有水槽,另一邊陰暗的屋子裡就一
面小窗,廚子吃自己的寒酸之食,晚上就睡在一條木板上,你就會覺得那簡直是中世紀
的活現。
當時的北京,不只住宅的設施讓杜威夫婦覺得回到了中世紀,北京的大環境以及街道設施也讓杜威夫婦大開了眼界。杜威夫人說:
北京的街道我想大概是世界最寬的。我們前面這條街沿著紅色的城牆,而且還有你們在
圖片上可以看到的偉岸的城門。這條路的中間鋪了柏油,柏油路面兩旁作?交通用的路
更寬。謝天謝地,北京有不錯的馬,所以重負不全是人拉的。兩旁的道路,因?流量和
使用的頻繁,都已經佈滿了深深的坑坑洞洞。這些坑洞裡的塵土細如灰,只要有人踏上
去、或者有車碾過,就立刻塵土飛揚。我們的房間朝南面對著這條馬路。整天,炎日穿
透了我們的竹簾,熱氣把那灰色的土灰帶進屋裡來。不管你碰觸到的是什?東西,包括
你的皮膚,都是一層灰。那是一種很奇怪的乾燥的感覺,讓你直覺地就想要找水來洗。
北京的沙塵是有名的。這點,連最愛北京的胡適自己都承認。比如說,他在1921年夏天接受商務印書館的邀約,到上海去?商務印書館作評鑒的工作。在上海的時候,他住在汪惕予那仿如「結廬在人境」的「蜷廬」。「蜷廬」位在斜橋路一號,占地十畝。胡適形容「蜷廬」的主人「鑿池造山,栽花種竹」,「雨住了,園子變成小湖了;水中都是園亭倒影,又一個新蜷廬了!」主人寂寞的時候,「把寂寞寄在古琴的弦子上。」9月7日,在他臨行回北京以前,他寫了一首詩:〈臨行贈蜷廬主人〉。這首詩的最後四句是:「多謝主人,我去了!兩天之後,滿身又是北京的塵土了!」但是,夏天是北京的雨季。北京的街道可是一下雨就成澤國。杜威在一個七月天的下午親眼目睹以後,把那景象描述給了他的子女看:
這裡現在是雨季的情況,我恐怕我並沒有?你們描寫出其中的萬分之一。昨天下午,我
們終於見識到了。我們屋前的這條馬路,在我們這側,成了一條一英尺半深的急流。青
年會所在的那條馬路,從馬路一側的屋牆到另一側的屋牆,圍成了一個湖泊。當然,水
並不深,不到六英寸深。然而,那條馬路比紐約的百老彙(Broadway)要寬得多多了,所
以很是壯觀。北京有著深可站人的下水道,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但還是應付不了那雨
量。
如果從紐約來的杜威夫婦?北京街道一雨就成澤國,而瞠目結舌,胡適則不然。就像杜威夫婦所說的,他已經習以?常到視若無睹的地步。比如說,胡適雖然在初到北京的時候抱怨過北京雨後的行不便。他在1918年5月11日的家信裡說:「昨日今日天雨可厭。北京最怕雨。一下雨,路便不可行了。車價貴至一倍多。」然而,才幾年的時間,他已經習以?常了。1922年6月24日,當時杜威夫婦已經離開中國一年了。當晚,胡適在日記裡說:「晚間到柯樂文〔Grover Clark〕家吃飯,談宗教問題;席上多愛談論的人,如Houghton〔侯屯〕, Embree〔恩布瑞〕, Clark〔柯樂文〕,談此事各有所主張。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滿了,我們更高談。」胡適興高采烈地在日記裡作了總結:
最後我?他們作一結束:一、不必向歷史裡去求事例來替宗教辯護,也不必向歷史裡去
求事例來反對宗教。因?沒有一個大宗教在歷史上不曾立過大功、犯過大罪的。二、現
在人多把「基督教」與「近代文化」混作一件事:這是不合的。即如協和醫校,分析起
來,百分之九十九是近代文化,百分之一是基督教。何必混作一件事?混作一事,所以
反對的人要向歷史裡去尋教會摧殘科學的事例來罵基督教了。三、宗教是一件個人的事,
誰也不能干涉誰的宗教。容忍的態度最好。
如果杜威夫婦把北京一雨就成澤國當成奇觀,百思不解?什?中國人能忍受得了,而不去思解決之道,胡適則可能覺得那只是雨大水不通的結果。雖然它造成了不便,然而,說不定正由於「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滿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反倒讓他們幾個「愛談論的人」,樂得乾脆拱起門來「更高談了。」
中國人的故步自封,從飲食起居上就可以彰顯出來。當時的中國在形式上已經不再能閉關自守了。外國人不但可以自由進出中國,甚至在中國還有租界。然而,中西的交流,甚至租界的存在,對中國人的影響似乎相當有限。杜威夫婦在日本訪問的時候去過一些日本人所住的西式的房子、或者加蓋的西式廂房。杜威夫人說:「所有〔日本〕的西式房子在風格上都很醜陋,但很舒適,是維多利亞中期的風格。」當然,拜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賜,日本有很多發了橫財的資本家。他們不但可以高價購置古董,而且可以蓋西式的豪宅。在經濟上落後的中國,自然無法跟日本相媲美。中國人住洋房的不是沒有,但
胡適愛北京。陳衡哲在1927年底給胡適的一封信裡說:「在我們這些朋友當中,你可以算是最愛北京的一個人了。」當時,陳衡哲跟任鴻雋搬到了北京,胡適卻從美國回來以後就住在了上海。胡適這樣跟他們捉迷藏,她調侃胡適說,一定是因?他不願意跟他們住在「你的『最文明的北京城』 」裡。我們不知道胡適是什?時候開始愛上北京的。他在剛回國的時候,曾經在〈歸國雜感〉裡痛斥了北京、上海的髒亂,他說:「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在新近發現的《嘗試集》第二編的初稿本裡,有胡適在1918年6月7日所寫的一篇序。他在這篇自序中,仍然說到北京的「塵土」與「齷齪」:「自從我去年秋間來北京——塵土的北京,齷齪的北京——居然也會做了一些詩。」
胡適在1917年回國,到北京大學去任教的時候,北京究竟是什?樣子,除了他在〈歸國雜感〉裡說它髒亂以外,胡適並沒有進一步的描述。他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杜威以及其夫人在1919年訪問中國的時候,從美國人的觀點,倒是留下了一些寶貴的分析。杜威夫婦的觀感,毫無疑問地,是從美國社會當時的物質條件的標準來衡量北京的。然而,其可貴的地方就正在此處。因?它給了我們一個外來的、中國後來要花了一個世紀的時光來追趕的標準來盱衡當時落後的中國。杜威在到了北京以後,這樣地描述了北京的房子:
所有北京的房子就像我們〔美國〕的柴房,直接就蓋在地上。房子裡地上的石板跟底下
的土地就只有幾英寸之隔。一下大雨,院子裡就積滿了水。接下來,那院子就可以泥濘
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那濕氣沿著房子裡的牆角往上滲透,可以沿著牆壁往上爬伸
到兩英尺之高。我們昨天去拜訪一個中國朋友。他的家就是處於那種狀態之下,可是他
彷彿視若無睹,怡然自得。他如果想在自己家裡洗個澡,他就得付水夫雙倍的價錢。可
是,在忙完了煮水、打水的工作,洗了個澡以後,他還得找人一桶一桶地把用過的洗澡
水拿出去處理掉。
我們不知道杜威夫婦去拜訪的是不是胡適的家。然而,可以想像的,當時胡適住在南池子緞庫後胡同8號的房子也不會例外。這幢位在緞庫後胡同的四合院是胡適在1918年?了接江冬秀到北京來住而租下來的。胡適在緞庫後胡同租下來的這幢四合院的房子究竟是十七間還是十八間,他自己在家信裡並沒有一致的說法。但是,對這幢四合院,他在家信裡作了簡單的描述。他對江冬秀說:「我已租了一所新屋,預備五六日內搬進去住。這屋有九間正房,五間偏房(作廚房幾仆婢住房),兩間套房。離大學也不遠(與江朝宗〔注:江冬秀家鄉江村的名人,1917年間曾任代國務總理〕住宅相隔一巷)。房租每月二十元。」他在搬進去以後給他母親的信裡說:「我已於〔三月〕卅日搬入新寓居住。此屋很好,入校既便,出城也便。」
這就在在證明了在不同的文化裡生活的人,看到的東西往往有所不同。有些事物在一個社會裡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是夢寐以求的,人人都會巨細無遺的一覽無遺;反之,有些事物,由於一個社會裡的人習以?常,視若無睹。反而必須要等異文化的人,帶著不同的文化包袱與視野來點出。對胡適在緞庫後胡同8號的四合院,杜威夫人的描述跟胡適自己的描述就在著重點上大異其趣。杜威夫人?她子女所作的描述如下:
昨天我們去看了一個朋友〔胡適?〕的家。很有意思。我會想住在一間類似的房子裡。
那房子裡沒有水,就靠水夫每天打來。這幢小房子有十八個房間,中間是座院子。這就
意味著說,它有四個屋頂,從一廂到另一廂,就得走出屋外,即使寒暑表上的刻度是零
下二十度,也必須如此。屋內的地都是石板。我們並沒看所有的房間。有些窗子是紙糊
的,有些則裝有玻璃。夏天的時候,他們在院子裡搭著一個用席子編成的暫時的屋頂。
它比四個廂房的屋頂都要高,以便通風,而且可以用來遮蔭。
無怪乎胡適是到澡堂去洗澡的。其意義顯然非凡,所以在他寫日記最勤的時候,例如1921年到1922年之間,他每次上澡堂,都會在日記裡留下記錄。四合院裡不但沒有水、沒有洗浴的設施、沒有下水道,而且廚房的位置與設施,也讓杜威夫婦瞠目結舌:
中國家庭裡的廚房總是離飯廳好幾個英尺以外的另一間房子裡。通常的情形是,你必須
穿過露天的院子從廚房走到飯廳。由於我們到了北京以後一直沒下過雨,我不知道那傘
下之湯是否會走了樣……清華學堂,那有名的用庚款來辦的學堂,是新蓋的,是美國人
作主的。〔然而,〕它的廚房和餐廳相隔有四十英尺之遙。我就不描寫廚房的樣子了。
但是,你只要看到那泥?的斑駁與崩塌垂危之勢,沒有水槽,另一邊陰暗的屋子裡就一
面小窗,廚子吃自己的寒酸之食,晚上就睡在一條木板上,你就會覺得那簡直是中世紀
的活現。
當時的北京,不只住宅的設施讓杜威夫婦覺得回到了中世紀,北京的大環境以及街道設施也讓杜威夫婦大開了眼界。杜威夫人說:
北京的街道我想大概是世界最寬的。我們前面這條街沿著紅色的城牆,而且還有你們在
圖片上可以看到的偉岸的城門。這條路的中間鋪了柏油,柏油路面兩旁作?交通用的路
更寬。謝天謝地,北京有不錯的馬,所以重負不全是人拉的。兩旁的道路,因?流量和
使用的頻繁,都已經佈滿了深深的坑坑洞洞。這些坑洞裡的塵土細如灰,只要有人踏上
去、或者有車碾過,就立刻塵土飛揚。我們的房間朝南面對著這條馬路。整天,炎日穿
透了我們的竹簾,熱氣把那灰色的土灰帶進屋裡來。不管你碰觸到的是什?東西,包括
你的皮膚,都是一層灰。那是一種很奇怪的乾燥的感覺,讓你直覺地就想要找水來洗。
北京的沙塵是有名的。這點,連最愛北京的胡適自己都承認。比如說,他在1921年夏天接受商務印書館的邀約,到上海去?商務印書館作評鑒的工作。在上海的時候,他住在汪惕予那仿如「結廬在人境」的「蜷廬」。「蜷廬」位在斜橋路一號,占地十畝。胡適形容「蜷廬」的主人「鑿池造山,栽花種竹」,「雨住了,園子變成小湖了;水中都是園亭倒影,又一個新蜷廬了!」主人寂寞的時候,「把寂寞寄在古琴的弦子上。」9月7日,在他臨行回北京以前,他寫了一首詩:〈臨行贈蜷廬主人〉。這首詩的最後四句是:「多謝主人,我去了!兩天之後,滿身又是北京的塵土了!」但是,夏天是北京的雨季。北京的街道可是一下雨就成澤國。杜威在一個七月天的下午親眼目睹以後,把那景象描述給了他的子女看:
這裡現在是雨季的情況,我恐怕我並沒有?你們描寫出其中的萬分之一。昨天下午,我
們終於見識到了。我們屋前的這條馬路,在我們這側,成了一條一英尺半深的急流。青
年會所在的那條馬路,從馬路一側的屋牆到另一側的屋牆,圍成了一個湖泊。當然,水
並不深,不到六英寸深。然而,那條馬路比紐約的百老彙(Broadway)要寬得多多了,所
以很是壯觀。北京有著深可站人的下水道,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但還是應付不了那雨
量。
如果從紐約來的杜威夫婦?北京街道一雨就成澤國,而瞠目結舌,胡適則不然。就像杜威夫婦所說的,他已經習以?常到視若無睹的地步。比如說,胡適雖然在初到北京的時候抱怨過北京雨後的行不便。他在1918年5月11日的家信裡說:「昨日今日天雨可厭。北京最怕雨。一下雨,路便不可行了。車價貴至一倍多。」然而,才幾年的時間,他已經習以?常了。1922年6月24日,當時杜威夫婦已經離開中國一年了。當晚,胡適在日記裡說:「晚間到柯樂文〔Grover Clark〕家吃飯,談宗教問題;席上多愛談論的人,如Houghton〔侯屯〕, Embree〔恩布瑞〕, Clark〔柯樂文〕,談此事各有所主張。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滿了,我們更高談。」胡適興高采烈地在日記裡作了總結:
最後我?他們作一結束:一、不必向歷史裡去求事例來替宗教辯護,也不必向歷史裡去
求事例來反對宗教。因?沒有一個大宗教在歷史上不曾立過大功、犯過大罪的。二、現
在人多把「基督教」與「近代文化」混作一件事:這是不合的。即如協和醫校,分析起
來,百分之九十九是近代文化,百分之一是基督教。何必混作一件事?混作一事,所以
反對的人要向歷史裡去尋教會摧殘科學的事例來罵基督教了。三、宗教是一件個人的事,
誰也不能干涉誰的宗教。容忍的態度最好。
如果杜威夫婦把北京一雨就成澤國當成奇觀,百思不解?什?中國人能忍受得了,而不去思解決之道,胡適則可能覺得那只是雨大水不通的結果。雖然它造成了不便,然而,說不定正由於「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滿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反倒讓他們幾個「愛談論的人」,樂得乾脆拱起門來「更高談了。」
中國人的故步自封,從飲食起居上就可以彰顯出來。當時的中國在形式上已經不再能閉關自守了。外國人不但可以自由進出中國,甚至在中國還有租界。然而,中西的交流,甚至租界的存在,對中國人的影響似乎相當有限。杜威夫婦在日本訪問的時候去過一些日本人所住的西式的房子、或者加蓋的西式廂房。杜威夫人說:「所有〔日本〕的西式房子在風格上都很醜陋,但很舒適,是維多利亞中期的風格。」當然,拜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賜,日本有很多發了橫財的資本家。他們不但可以高價購置古董,而且可以蓋西式的豪宅。在經濟上落後的中國,自然無法跟日本相媲美。中國人住洋房的不是沒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