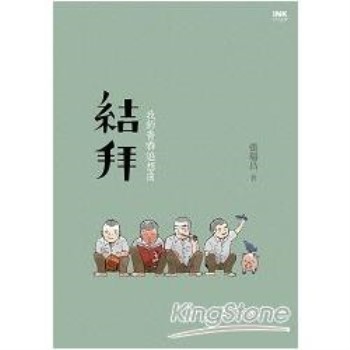鐵牛阿榮和芋仔冰城
「朝會後,二年十三班留下來做服裝儀容檢查。」
該死的教官竟然發動突襲,同學們怨聲四起,「幹,這穩死!」有人抱怨那個掛著兩顆梅花的,怎麼老是跟我們這班過不去,但陸軍找碴還不夠,一旁身穿藍色軍便服的少校教官也在旁監視,我們稱這個空軍少爺官是「一翦梅」。
陸空夾擊,逃都逃不掉。兩顆梅花彷彿在做部隊高裝檢般逐一巡視,穿白襪、沒繫銅扣腰帶、大盤帽摺得像艘船,一些不合格的同學都被點名出列,兩顆梅花帶著詭異的笑容,如一頭野狼穿梭在待宰羔羊群裡,直到腳步停在阿榮面前。
「你怎麼沒穿內衣?」「報告教官,天氣太熱了,這樣比較通風涼快」,「天氣熱更要穿,才不會長汗疹!」教官皺起眉頭追問,「別人至少還穿白襪,你怎麼連襪子都不穿,不怕得香港腳?」
「報告教官,我有穿襪子啊!」兩顆梅花睜大眼睛往阿榮抬起的左腳細瞧,「你穿絲襪?」「因為今天早上起床找不到襪子,只好跟我媽媽先借來穿。」阿榮一講完,有人噗嗤,有人捧著肚子,就連那個「一翦梅」也忍俊不住。
這不是阿榮頭一回鬧笑話,他是標準的天兵。便當永遠在第三節下課後吃完,每次敲桿一定會凸槌,打麻將時總是拿錯牌當相公。不要說教官沒轍,即使和他做同學的我,也經常被他搞到哭笑不得。
不過,我倒是和阿榮還不錯。剛升高二那年,他是留級生,就坐我旁邊,因為體格魁梧,長得黝黑,動不動就露出碗口大的胳臂和六塊肌,讓我將他跟「鐵牛運功散」裡頭那個打電話跟媽媽報平安的阿榮作聯想。
電視廣告中的阿榮壯得像一頭牛,現實世界裡的阿榮也不遑多讓。但更教人感動的是,阿榮有情有義,有代誌找他從不推卻,有他跟著出生入死,有時還有一種蝙蝠俠與羅賓的錯覺。
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自己是蝙蝠俠,只是每當有麻煩找上門時,他都挽袖相挺,打死不退。
一九八○年的台灣社會,升學主義當道,我的高中生活也像其他人一樣,充滿著許多困惑與不解。那時讀新潮文庫的尼采自傳《瞧!這個人》,讀得滿天全金條,如墜五里迷霧。有一天,和鄰近的省中死黨開講,聊起他們學校最近從台北師大附中來一個轉學生,結拜老夏直言那傢伙臭屁得要命,打算給對方來個下馬威。
苦悶的生命總是需要找尋出路,尤其是在虛無中找到存在的意義。就這樣,那個外地轉來的附中仔,倒楣地成了一群叛逆的在地高中生發洩不滿情緒、展現地盤勢力的祭品。
那天第八堂課結束後,我穿上黑夾克,準備一如往常地前往放學後和死黨們相聚的老地方碰頭。事先獲邀的阿榮,對執行這項「教訓」任務表露忠誠之意,二話不說,揹起書包,與我同行。
傍晚的美芳芋仔冰城早已聚攏一堆好事之徒。「人在哪裡?」、「好像還在補習班裡面」、「那就把他找出來」,五、六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的議論,惟有阿榮保持殺手的緘默,依靠在騎樓底下的摩托車旁,不發一語。
坦白說,我幾乎忘記那個附中轉學生長什麼模樣。印象中他應該有一百八十公分高,臉上帶著一點嬰兒肥,白白胖胖,但最重要的是,他一副吊兒郎當的屌樣,已構成被修理的必要條件。
整個衝突過程,剛開始有點像王家衛電影中的暴力美學。那個附中仔被「請」到冰果室門前,對方才剛報上名字,還來不及反應,我的第一拳就揮向右臉頰,老夏跟著往肚子招呼,連挨數拳的轉學生,一個踉蹌應聲倒地,側身翻轉時,將冰果室的幾張桌椅撞得東倒西歪。
阿榮始終都在旁觀看、沒有出手,他隨後扶起對方,搭著肩問候對方,「你還好吧!這裡要做生意,我們到附近的巷子裡談談。」
後來在暗巷內的對話內容,簡直跟周星馳主演的電影一樣無厘頭。
「幹,你不會站好嗎?」阿榮冷不防給附中仔一拳,對方摀著腹部幽幽地問道,「你們是為了秦小芳而來的嗎?」「誰是小芳?」我和阿榮面面相覷。「我只認得美芳芋仔冰啦!」「喔,那兩位大哥怎麼會找上我?」附中仔繼續哀怨地操著字正腔圓的國語回答。
「靠北,哪ㄟ拄著講北京話?」阿榮很無奈地問附中仔,「你外省不會講台語?還是有聽沒有懂?」「一點點」,那聲音細若蚊飛。「我跟你說,因為咱兄弟很多,雖然沒有要你擺一桌,但下禮拜你要拿一條長壽來陪對」,「一支菸就好?一支怎麼分?」「幹,你聽乎清楚,是一條,有十包那種的,不是一支啦!」
那一晚,我們就在補習街裡「雞同鴨講」。因為從沒用北京話吵過架,我和阿榮聯手應付那個附中仔,顯得渾身不對勁,有時還得做語言翻譯,雙方比手畫腳,就怕弄錯意思。
「碗糕咧,我是遇到外國人嗎?有夠累!」阿榮露出一副頭殼發燒的表情。
暗巷痛扁轉學生,並不是麻煩來找我,而是自己去找麻煩。事隔數日,我被那所省中教官找去談話,還指定我閱讀一篇刊載在當期《讀者文摘》裡的外電報導,文章主題是關於何謂勇氣。
這個素昧平生的省中教官,算是對我手下留情,他諄諄善誘,從「暴虎馮河」、「匹夫之勇」談起,然後要我寫讀後感,並且很客氣地說,「我和你們主任教官很熟,將來你畢業典禮那一天,我會去參加!」
天殺的,他抬出兩顆梅花來威脅,我的高中生涯快變成尼采筆下的「悲劇的誕生」。回家後,我左思右想,不敢怠慢,乖乖地繳了一篇文情並茂的讀書心得「論勇氣」。
那麼阿榮呢?他沒有留級,順利畢業,但從此音訊全無。我最後聽到的訊息是,聽說他騎的那輛野狼機車在警方臨檢時出了事。
三十年後,每回看到「鐵牛運功散」的電視廣告,我總會想起阿榮,還有那間已經消失無蹤的芋仔冰城。
老夏的山東老爹
幽暗的樓梯,稀微的賣場,在昏暗的空間裡亮著幾盞日光燈,那是我對中央市場地下街最初也是最後的畫面。中央市場隔壁的白雪大舞廳,恰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外頭是閃爍迷人的霓虹燈,旋轉門內不斷流竄出妖嬈哀怨的歌聲,和著音樂節拍、搖晃舞步,那是我揹著書包穿越有泊車小弟待命的走廊時唯一的想像。
白雪大舞廳從美軍駐台時就開始營業,是台中至今唯一還領有舞廳牌照的老店。我剛出社會在台中跑新聞時,曾跟著老鳥去「白雪」見識,但我根本不會跳交際舞,坐在沙發上活像個二愣子,這讓我想起讀高中時爆發十大槍擊通緝要犯「美國博」殺警事件,當年他的女友就是白雪大舞廳的紅牌。
然而,我真正懷念的不是五權路上的白雪大舞廳,而是每回開車經過的中央市場,因為我總是想起老夏的父親,他那鎮日埋首在堆積如山的牛仔褲的佝僂身影,一直深藏在我的記憶裡。對我而言,那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外省老爹印象,也是我最早接觸「芋仔加番薯」的人生經驗。
老夏是我的國中死黨,我們在自由路上那所沒有操場的明星國中同窗三年,他是成績永遠名列前茅的高材生,我則是在前段班裡載浮載沉的平庸之輩。老夏的父親是山東樂陵人,民國三十八年之後跟隨國府遷台,因媒妁之言和來自雲林虎尾的母親結婚。
隻身來台的外省男子娶窮困鄉下的年輕女孩是當年常見的婚姻組合,不過,老夏的父母無論是個性或外表都呈現鮮明的對比,記憶中,夏爸爸個頭瘦小,內向沉默寡言,夏媽媽則是身材高大,外向開朗健談。他們兩個人偶爾會拌嘴,但多數時候,我看到的夏爸爸是背負著人生滄桑和時代憂傷,他經常獨自一人看京劇、喝高粱。老夏告訴我,「父親身子很硬朗,每餐一杯高粱是他唯一的嗜好」,而這個生活習慣持續到八十幾歲離開人世。
對於死黨的追憶,我曾有一種鄉愁滿杯的感懷。少小離家從軍,歷經不斷流離遷徙的部隊生活,最後才落腳台中,我孩提時不解本省人的歷史悲情,對外省人的顛沛生命也似懂非懂,但卻隱約能感受到那老人啜飲烈酒、尋求慰藉的孤寂心境。
那時的中央市場專做平價牛仔褲的批發生意, 我的第一件牛仔褲「Bigstone」就是在那裡買的。此後,我們一家人的牛仔褲都是跟夏爸爸、夏媽媽交關。這也讓兩個背景南轅北轍的家庭有些熟絡,我和老夏不僅談得來,也還有著像哥兒們般的患難交情,而且是可以好到為了解決兄弟的疑難雜症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讀國三那年,老夏就曾掩護我,只是出師未捷,很快陣亡了。
那時十六歲的我,正值青少年叛逆階段,有一天和家人吵架而負氣離家,簡單地打包好隨身衣物,揹起書包、牽著鐵馬,準備出門要去流浪。小我一歲的大弟見狀紅著眼眶攔阻說:「哥,不要這樣嘛!」可我那目不識丁的阿嬤,卻不動聲色,緩緩地走到門口,然後語重心長地告訴她的長孫:「人生啊!一枝草一點露,你永遠要記得,天無絕人之路,擱再怎麼樣艱苦,都不要放棄!」
「朝會後,二年十三班留下來做服裝儀容檢查。」
該死的教官竟然發動突襲,同學們怨聲四起,「幹,這穩死!」有人抱怨那個掛著兩顆梅花的,怎麼老是跟我們這班過不去,但陸軍找碴還不夠,一旁身穿藍色軍便服的少校教官也在旁監視,我們稱這個空軍少爺官是「一翦梅」。
陸空夾擊,逃都逃不掉。兩顆梅花彷彿在做部隊高裝檢般逐一巡視,穿白襪、沒繫銅扣腰帶、大盤帽摺得像艘船,一些不合格的同學都被點名出列,兩顆梅花帶著詭異的笑容,如一頭野狼穿梭在待宰羔羊群裡,直到腳步停在阿榮面前。
「你怎麼沒穿內衣?」「報告教官,天氣太熱了,這樣比較通風涼快」,「天氣熱更要穿,才不會長汗疹!」教官皺起眉頭追問,「別人至少還穿白襪,你怎麼連襪子都不穿,不怕得香港腳?」
「報告教官,我有穿襪子啊!」兩顆梅花睜大眼睛往阿榮抬起的左腳細瞧,「你穿絲襪?」「因為今天早上起床找不到襪子,只好跟我媽媽先借來穿。」阿榮一講完,有人噗嗤,有人捧著肚子,就連那個「一翦梅」也忍俊不住。
這不是阿榮頭一回鬧笑話,他是標準的天兵。便當永遠在第三節下課後吃完,每次敲桿一定會凸槌,打麻將時總是拿錯牌當相公。不要說教官沒轍,即使和他做同學的我,也經常被他搞到哭笑不得。
不過,我倒是和阿榮還不錯。剛升高二那年,他是留級生,就坐我旁邊,因為體格魁梧,長得黝黑,動不動就露出碗口大的胳臂和六塊肌,讓我將他跟「鐵牛運功散」裡頭那個打電話跟媽媽報平安的阿榮作聯想。
電視廣告中的阿榮壯得像一頭牛,現實世界裡的阿榮也不遑多讓。但更教人感動的是,阿榮有情有義,有代誌找他從不推卻,有他跟著出生入死,有時還有一種蝙蝠俠與羅賓的錯覺。
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自己是蝙蝠俠,只是每當有麻煩找上門時,他都挽袖相挺,打死不退。
一九八○年的台灣社會,升學主義當道,我的高中生活也像其他人一樣,充滿著許多困惑與不解。那時讀新潮文庫的尼采自傳《瞧!這個人》,讀得滿天全金條,如墜五里迷霧。有一天,和鄰近的省中死黨開講,聊起他們學校最近從台北師大附中來一個轉學生,結拜老夏直言那傢伙臭屁得要命,打算給對方來個下馬威。
苦悶的生命總是需要找尋出路,尤其是在虛無中找到存在的意義。就這樣,那個外地轉來的附中仔,倒楣地成了一群叛逆的在地高中生發洩不滿情緒、展現地盤勢力的祭品。
那天第八堂課結束後,我穿上黑夾克,準備一如往常地前往放學後和死黨們相聚的老地方碰頭。事先獲邀的阿榮,對執行這項「教訓」任務表露忠誠之意,二話不說,揹起書包,與我同行。
傍晚的美芳芋仔冰城早已聚攏一堆好事之徒。「人在哪裡?」、「好像還在補習班裡面」、「那就把他找出來」,五、六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的議論,惟有阿榮保持殺手的緘默,依靠在騎樓底下的摩托車旁,不發一語。
坦白說,我幾乎忘記那個附中轉學生長什麼模樣。印象中他應該有一百八十公分高,臉上帶著一點嬰兒肥,白白胖胖,但最重要的是,他一副吊兒郎當的屌樣,已構成被修理的必要條件。
整個衝突過程,剛開始有點像王家衛電影中的暴力美學。那個附中仔被「請」到冰果室門前,對方才剛報上名字,還來不及反應,我的第一拳就揮向右臉頰,老夏跟著往肚子招呼,連挨數拳的轉學生,一個踉蹌應聲倒地,側身翻轉時,將冰果室的幾張桌椅撞得東倒西歪。
阿榮始終都在旁觀看、沒有出手,他隨後扶起對方,搭著肩問候對方,「你還好吧!這裡要做生意,我們到附近的巷子裡談談。」
後來在暗巷內的對話內容,簡直跟周星馳主演的電影一樣無厘頭。
「幹,你不會站好嗎?」阿榮冷不防給附中仔一拳,對方摀著腹部幽幽地問道,「你們是為了秦小芳而來的嗎?」「誰是小芳?」我和阿榮面面相覷。「我只認得美芳芋仔冰啦!」「喔,那兩位大哥怎麼會找上我?」附中仔繼續哀怨地操著字正腔圓的國語回答。
「靠北,哪ㄟ拄著講北京話?」阿榮很無奈地問附中仔,「你外省不會講台語?還是有聽沒有懂?」「一點點」,那聲音細若蚊飛。「我跟你說,因為咱兄弟很多,雖然沒有要你擺一桌,但下禮拜你要拿一條長壽來陪對」,「一支菸就好?一支怎麼分?」「幹,你聽乎清楚,是一條,有十包那種的,不是一支啦!」
那一晚,我們就在補習街裡「雞同鴨講」。因為從沒用北京話吵過架,我和阿榮聯手應付那個附中仔,顯得渾身不對勁,有時還得做語言翻譯,雙方比手畫腳,就怕弄錯意思。
「碗糕咧,我是遇到外國人嗎?有夠累!」阿榮露出一副頭殼發燒的表情。
暗巷痛扁轉學生,並不是麻煩來找我,而是自己去找麻煩。事隔數日,我被那所省中教官找去談話,還指定我閱讀一篇刊載在當期《讀者文摘》裡的外電報導,文章主題是關於何謂勇氣。
這個素昧平生的省中教官,算是對我手下留情,他諄諄善誘,從「暴虎馮河」、「匹夫之勇」談起,然後要我寫讀後感,並且很客氣地說,「我和你們主任教官很熟,將來你畢業典禮那一天,我會去參加!」
天殺的,他抬出兩顆梅花來威脅,我的高中生涯快變成尼采筆下的「悲劇的誕生」。回家後,我左思右想,不敢怠慢,乖乖地繳了一篇文情並茂的讀書心得「論勇氣」。
那麼阿榮呢?他沒有留級,順利畢業,但從此音訊全無。我最後聽到的訊息是,聽說他騎的那輛野狼機車在警方臨檢時出了事。
三十年後,每回看到「鐵牛運功散」的電視廣告,我總會想起阿榮,還有那間已經消失無蹤的芋仔冰城。
老夏的山東老爹
幽暗的樓梯,稀微的賣場,在昏暗的空間裡亮著幾盞日光燈,那是我對中央市場地下街最初也是最後的畫面。中央市場隔壁的白雪大舞廳,恰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外頭是閃爍迷人的霓虹燈,旋轉門內不斷流竄出妖嬈哀怨的歌聲,和著音樂節拍、搖晃舞步,那是我揹著書包穿越有泊車小弟待命的走廊時唯一的想像。
白雪大舞廳從美軍駐台時就開始營業,是台中至今唯一還領有舞廳牌照的老店。我剛出社會在台中跑新聞時,曾跟著老鳥去「白雪」見識,但我根本不會跳交際舞,坐在沙發上活像個二愣子,這讓我想起讀高中時爆發十大槍擊通緝要犯「美國博」殺警事件,當年他的女友就是白雪大舞廳的紅牌。
然而,我真正懷念的不是五權路上的白雪大舞廳,而是每回開車經過的中央市場,因為我總是想起老夏的父親,他那鎮日埋首在堆積如山的牛仔褲的佝僂身影,一直深藏在我的記憶裡。對我而言,那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外省老爹印象,也是我最早接觸「芋仔加番薯」的人生經驗。
老夏是我的國中死黨,我們在自由路上那所沒有操場的明星國中同窗三年,他是成績永遠名列前茅的高材生,我則是在前段班裡載浮載沉的平庸之輩。老夏的父親是山東樂陵人,民國三十八年之後跟隨國府遷台,因媒妁之言和來自雲林虎尾的母親結婚。
隻身來台的外省男子娶窮困鄉下的年輕女孩是當年常見的婚姻組合,不過,老夏的父母無論是個性或外表都呈現鮮明的對比,記憶中,夏爸爸個頭瘦小,內向沉默寡言,夏媽媽則是身材高大,外向開朗健談。他們兩個人偶爾會拌嘴,但多數時候,我看到的夏爸爸是背負著人生滄桑和時代憂傷,他經常獨自一人看京劇、喝高粱。老夏告訴我,「父親身子很硬朗,每餐一杯高粱是他唯一的嗜好」,而這個生活習慣持續到八十幾歲離開人世。
對於死黨的追憶,我曾有一種鄉愁滿杯的感懷。少小離家從軍,歷經不斷流離遷徙的部隊生活,最後才落腳台中,我孩提時不解本省人的歷史悲情,對外省人的顛沛生命也似懂非懂,但卻隱約能感受到那老人啜飲烈酒、尋求慰藉的孤寂心境。
那時的中央市場專做平價牛仔褲的批發生意, 我的第一件牛仔褲「Bigstone」就是在那裡買的。此後,我們一家人的牛仔褲都是跟夏爸爸、夏媽媽交關。這也讓兩個背景南轅北轍的家庭有些熟絡,我和老夏不僅談得來,也還有著像哥兒們般的患難交情,而且是可以好到為了解決兄弟的疑難雜症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讀國三那年,老夏就曾掩護我,只是出師未捷,很快陣亡了。
那時十六歲的我,正值青少年叛逆階段,有一天和家人吵架而負氣離家,簡單地打包好隨身衣物,揹起書包、牽著鐵馬,準備出門要去流浪。小我一歲的大弟見狀紅著眼眶攔阻說:「哥,不要這樣嘛!」可我那目不識丁的阿嬤,卻不動聲色,緩緩地走到門口,然後語重心長地告訴她的長孫:「人生啊!一枝草一點露,你永遠要記得,天無絕人之路,擱再怎麼樣艱苦,都不要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