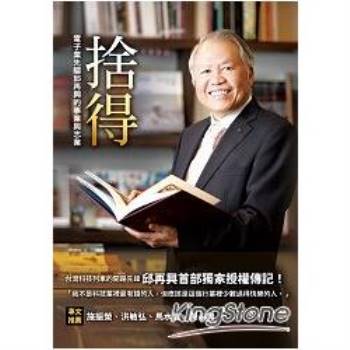<前言>在荒野之地,點一把小火
一九九○年代,我剛回到台灣,股市上萬點,整個社會氣氛非常浮躁,全民炒股,眼中只有金錢。那時候看似百業蓬勃發展,事實上是虛胖,不僅企業家不專注在本業,注意力全放在金融市場的金錢遊戲上,就連一般的販夫走卒也沉迷其中。
九○年代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幅景象是—媽媽不煮飯,全跑去號子裡看股票;賺了錢就全家上館子,賠了錢就回家發脾氣。不僅整個家庭的情緒隨著金錢而波動,連帶也影響對小孩的身教問題。
那是一個只有金錢沒有夢想的年代,我也曾經執著於拓展公司的業務,那個行為看似為了賺錢,但賺錢的背後,我是想成立一個可以媲美世界級公司的企業,我想利用科技改善各種人類的問題,所以我引進各種新產品。但九○年代的金錢遊戲並不是如此,裡面沒有夢想,只有一再膨脹的個人欲望。
以西方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從現代社會進入後現代社會,在後現代社會裡,人們藉由消費來尋求認同,金錢堆砌出來的生活風格、各種自我認同也暗示了,生活在這樣世代的我們面臨各種心靈空洞的危機。有西方的社會學者認為,在後現代社會裡,消費是唯一真實的存在,比如我們買名牌建立自我形象,把買豪宅、名車視為一種成功人生的表徵。我們越來越習慣,透過金錢去感知這個世界,無形之中,我們習於用錢去衡量一切。
西方學者認為,要扭轉這種過度消費的行為只有宗教,以宗教的教化手段,挽救現代人的心靈危機。例如,影響我很深的法鼓山聖嚴法師就有個名句:「想要的太多,而需要的不多。」一個人活在世上,其實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並不高,不丹國民生產毛額不高,但他們的人民卻是世上最快樂的,這代表人不必有太高的物質生活,也能活得很快樂;需要的東西並不多,多的是個人的欲望,想要的太多。
想要的太多,因為要得太多,於是得不到的也多,人生就因為得不到而變得不快樂。
願將自己收藏的「美」與眾人分享
在我的想法裡,宗教可以解救被金錢綑綁住的心靈,而藝術也和宗教一樣,解放人們的心,並且同時給予溫暖。不僅如此,當代的藝術也常常蘊含各種嚴肅的人生、社會的哲理思考,它不僅讓你個人情感得到滿足,同時也深具啟發性,逼迫你去思索各種問題。
所以,當我一九九○年回到台灣,成立「邱再興文教基金會」,並號召企業界、文化界、法律界的相關人士,一起為台灣的文化事業而努力。當時,我任職該基金會的董事長,由我的小學同學馬水龍老師任執行長。
基金會的主旨是培養藝術新秀,並提昇台灣社會的藝術水準。一九九一年成立「春秋樂集」,因為執行長是馬水龍老師,他是音樂專家,很了解台灣音樂圈需要怎樣的協助。因此,春秋樂集成為基金會第一個切入的文化事業。
我們鼓勵年輕的作曲家,創作當代音樂,發表過上百首曲子,其中大多為原創,是首次發表的作品。不只春秋樂集,基金會之後贊助的藝術家和藝術類別,大多是當代藝術,而且多是年輕的新秀。
早年,我收畫的時候,也跟著當時社會流行的畫作收,像是張大千、溥心畬的國畫,或是台灣日據時代的油畫,帶有濃厚印象派風格,構圖和色彩謹守古典美學的風格。這些畫作當然都具有一定的價值,但當時國外的藝術已經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了,各種前衛新鮮的嘗試卻一直沒有進到台灣,我覺得很可惜。
古典的油畫、國畫已經擁有一定的資源了,我想做一些沒人做,而且做了有意義的事,於是我選擇資助當代藝術。而從事當代藝術的人也大多是年輕藝術家,他們通常擁有滿腔的創意和想法,只是苦無一個平台和贊助者讓他們實現夢想。
夢想會使人的生活感到希望與豐滿,雖然新的藝術領域猶如荒野,但在這片荒野裡,我願意燃起一點小光,照亮前方漆黑的路,我陪伴大家一起前進。我也不清楚前方的路有多遠,能做的事有多少,但起碼我們可以試一試藝術還有什麼可能?人生、生活除了金錢,還有什麼可能?
很幸運的是,我們這些嘗試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這也是讓我不斷做下去的動力,這一點點小小的火光才得以延續下去,不至於熄滅。
於是,在一九九八年文建會的文馨獎特別獎頒給我們基金會,我們感到很意外,也很光榮。對於參賽,我們一向被動比較多,畢竟從事文化事業,我甚少仰賴政府補助,是有些朋友熱心協助,幫我們領報名表,要我們填資料,最後得了這個深感榮耀的獎項。
也許是因為得獎的鼓勵,我於隔年,在北投成立了美術館,一開始大多是展出我個人的收藏。我一開始的想法也是認為,我的收藏品這麼多,如果放在自己的倉庫,沒有空間展出、一個人欣賞都是相當可惜的事。
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我願意將自己收藏的「美」與眾人分享。
一九九九年,北投的鳳甲美術館正式對外開收,這個美術館以我的父親為名,感念父親的栽培恩情,也感謝那個年代每個曾經幫助過我的老師和親友們。開幕當時,我還請了二哥與我的小學老師到場剪綵,我們一家兄弟,大家受教育的機會不多,只有我有較好的教育機會,我很感謝大哥大姊們提供物質和學費,讓我能安心求學。
在荒野中燃起一股光和熱
人生一路走來的艱辛,讓我曉得,夢可以做得很大,但不能把夢做得不實際。
鳳甲美術館成立之外,我便自我衡量過我的能力,不會妄想成立一個與國際美術館相匹敵的展場,我把目標放在「社區」。社會各種力量都是得從基層開始扎根,我們從小學教育,也從社區關係切入。我們把美術館定位成社區型的展場,我們不僅策展,也提供講座,讓學生和民眾有各種接觸的機會。
我們不只辦視覺畫作的賞析,也辦音樂表演,例如我們現址的美術館,看似面積不大,但靈活運用下,可以利用活動性的隔間,把現場變成一個小型的表演場地。而所有入館的訪客都不收門票,經營全靠基金會贊助。
因為資金來源單純,我放手讓美術館的專業來領導,他們發揮的空間很大,本來一開始是靠我的收藏撐起來,沒多久之後,各方申請來展的藝術家已經輕易填滿各年度的檔期。
這把小火,不僅點在一開始冷門的當代藝術領域,就連規模也真的是「小」火,立足社區,從社區開始一步一步發揮影響力。時至今日,我敢說鳳甲不大,但鳳甲在台灣藝術圈卻占有一席之地。
很多人認為,當代藝術是專屬藝術菁英的小圈圈題材,在我眼裡,藝術沒有什麼菁英不菁英的問題,只有夠不夠好的差異。鳳甲美術館有常態性的兒童美術推廣課程,也常有親子共同參與的藝術活動。藝術要走入人群、走入社會,才會是活的,才能反應當代的生活狀態。
以近期的展覽為例,我們不僅關注兒童美學的培養,甚至把觸角伸到各種不同的社群裡,例如視障者。我們設計讓視障者在義工輔助之下,引導他們作畫。他們一輩子看不到,畫出來的作品又將會是什麼樣子呢?大出我意外的是,這些視障者畫出的作品,色彩都相當瑰麗,充滿情感的脈動。
那陣子,有客人來館參觀時,我總愛特別介紹這些視障者作品,在他們的作品裡,我沒有看到絕望,而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也相信,當這些視障者畫完作品之際,一定會獲得更大的力量。而觀看者如我們,也從這些色彩的傳遞裡得到更大的正面力量。這些就是藝術帶來的改變。
不只例行性的展出,每兩年一次的錄像展也是本館的特色之一。今年我們錄像展的主題非常有意思,是「鬼魂的迴返」。
這大概是私營美術館的好處,因為不收政府的經費,所以我們的題材很大膽,我們請不同的藝術家拍錄一支關於鬼魂的電影或影片。
不僅如此,我們在活動前也多次開辦了相關活動,例如我們請了乩童到現場與觀眾面談。台北市這個都市化成熟的地方,很多年輕人甚至是小孩,已經沒有機會親睹乩童「風采」。
我們是以社會學分析、文化分析的角度去看鬼魂,我們請不同的人來座談,將不同的觀點傳達出去。
二○一四年,我一直以為我的投入沒有太多人知道,不起眼的援助支持,沒想到竟能獲頒台北文化獎。得知獲獎的同時,我人在外國,接到電話,因為不是預期內的獎,當然也是相當開心。
因為有了這個獎項的肯定,也間接說明了,我雖然一路在荒野之地,不斷點燃了各地之火,而這火終於一點一點的累積,在荒野裡燃起了一股光和熱,對於後進來說,這些光與熱逐漸匯集,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了。
在挫折裡看見生命的課題
早年,我的夢想是成立一家可以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大企業,就像現在很多年輕人謀職,會把知名企業當成首選的心態類似,但人生的變化很大,有時候不是事事都能盡如人意。
結束環宇之後,我從母公司拿到一百多萬,當時算是一筆錢,但要創業其實不夠。當時公司賣給ITT(這家公司一年的營業額比台灣的GDP還大),我簽合約要在公司待滿兩年,這兩年待遇很高,開始有點儲蓄。在外國人的公司再怎麼做也就是這樣,後來我還是出來自己創業。
剛開始沒什麼錢創業,我先成立一個貿易公司,登記資本額二十萬,我借朋友的一個辦公室,靠三張桌子併在一起,慢慢做。
貿易公司比較不需要資本額,簡單的打字機就可以。貿易公司不需要本錢,但觸角可以非常廣,我不光只做高科技的東西,其中最大的客戶是拍立得,他們剛發明自動對焦,我就在台灣幫他們代工。我應該要自己開工廠來做,但錢不夠,就找工廠做,然後再將貨組裝好運回美國,這有點像仲介的角色。後來拍立得在台灣有很大的裝配線,也是我幫他們安排的。
美國後來找我做省電開關,一般電燈都有一個
一九九○年代,我剛回到台灣,股市上萬點,整個社會氣氛非常浮躁,全民炒股,眼中只有金錢。那時候看似百業蓬勃發展,事實上是虛胖,不僅企業家不專注在本業,注意力全放在金融市場的金錢遊戲上,就連一般的販夫走卒也沉迷其中。
九○年代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幅景象是—媽媽不煮飯,全跑去號子裡看股票;賺了錢就全家上館子,賠了錢就回家發脾氣。不僅整個家庭的情緒隨著金錢而波動,連帶也影響對小孩的身教問題。
那是一個只有金錢沒有夢想的年代,我也曾經執著於拓展公司的業務,那個行為看似為了賺錢,但賺錢的背後,我是想成立一個可以媲美世界級公司的企業,我想利用科技改善各種人類的問題,所以我引進各種新產品。但九○年代的金錢遊戲並不是如此,裡面沒有夢想,只有一再膨脹的個人欲望。
以西方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從現代社會進入後現代社會,在後現代社會裡,人們藉由消費來尋求認同,金錢堆砌出來的生活風格、各種自我認同也暗示了,生活在這樣世代的我們面臨各種心靈空洞的危機。有西方的社會學者認為,在後現代社會裡,消費是唯一真實的存在,比如我們買名牌建立自我形象,把買豪宅、名車視為一種成功人生的表徵。我們越來越習慣,透過金錢去感知這個世界,無形之中,我們習於用錢去衡量一切。
西方學者認為,要扭轉這種過度消費的行為只有宗教,以宗教的教化手段,挽救現代人的心靈危機。例如,影響我很深的法鼓山聖嚴法師就有個名句:「想要的太多,而需要的不多。」一個人活在世上,其實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並不高,不丹國民生產毛額不高,但他們的人民卻是世上最快樂的,這代表人不必有太高的物質生活,也能活得很快樂;需要的東西並不多,多的是個人的欲望,想要的太多。
想要的太多,因為要得太多,於是得不到的也多,人生就因為得不到而變得不快樂。
願將自己收藏的「美」與眾人分享
在我的想法裡,宗教可以解救被金錢綑綁住的心靈,而藝術也和宗教一樣,解放人們的心,並且同時給予溫暖。不僅如此,當代的藝術也常常蘊含各種嚴肅的人生、社會的哲理思考,它不僅讓你個人情感得到滿足,同時也深具啟發性,逼迫你去思索各種問題。
所以,當我一九九○年回到台灣,成立「邱再興文教基金會」,並號召企業界、文化界、法律界的相關人士,一起為台灣的文化事業而努力。當時,我任職該基金會的董事長,由我的小學同學馬水龍老師任執行長。
基金會的主旨是培養藝術新秀,並提昇台灣社會的藝術水準。一九九一年成立「春秋樂集」,因為執行長是馬水龍老師,他是音樂專家,很了解台灣音樂圈需要怎樣的協助。因此,春秋樂集成為基金會第一個切入的文化事業。
我們鼓勵年輕的作曲家,創作當代音樂,發表過上百首曲子,其中大多為原創,是首次發表的作品。不只春秋樂集,基金會之後贊助的藝術家和藝術類別,大多是當代藝術,而且多是年輕的新秀。
早年,我收畫的時候,也跟著當時社會流行的畫作收,像是張大千、溥心畬的國畫,或是台灣日據時代的油畫,帶有濃厚印象派風格,構圖和色彩謹守古典美學的風格。這些畫作當然都具有一定的價值,但當時國外的藝術已經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了,各種前衛新鮮的嘗試卻一直沒有進到台灣,我覺得很可惜。
古典的油畫、國畫已經擁有一定的資源了,我想做一些沒人做,而且做了有意義的事,於是我選擇資助當代藝術。而從事當代藝術的人也大多是年輕藝術家,他們通常擁有滿腔的創意和想法,只是苦無一個平台和贊助者讓他們實現夢想。
夢想會使人的生活感到希望與豐滿,雖然新的藝術領域猶如荒野,但在這片荒野裡,我願意燃起一點小光,照亮前方漆黑的路,我陪伴大家一起前進。我也不清楚前方的路有多遠,能做的事有多少,但起碼我們可以試一試藝術還有什麼可能?人生、生活除了金錢,還有什麼可能?
很幸運的是,我們這些嘗試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這也是讓我不斷做下去的動力,這一點點小小的火光才得以延續下去,不至於熄滅。
於是,在一九九八年文建會的文馨獎特別獎頒給我們基金會,我們感到很意外,也很光榮。對於參賽,我們一向被動比較多,畢竟從事文化事業,我甚少仰賴政府補助,是有些朋友熱心協助,幫我們領報名表,要我們填資料,最後得了這個深感榮耀的獎項。
也許是因為得獎的鼓勵,我於隔年,在北投成立了美術館,一開始大多是展出我個人的收藏。我一開始的想法也是認為,我的收藏品這麼多,如果放在自己的倉庫,沒有空間展出、一個人欣賞都是相當可惜的事。
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我願意將自己收藏的「美」與眾人分享。
一九九九年,北投的鳳甲美術館正式對外開收,這個美術館以我的父親為名,感念父親的栽培恩情,也感謝那個年代每個曾經幫助過我的老師和親友們。開幕當時,我還請了二哥與我的小學老師到場剪綵,我們一家兄弟,大家受教育的機會不多,只有我有較好的教育機會,我很感謝大哥大姊們提供物質和學費,讓我能安心求學。
在荒野中燃起一股光和熱
人生一路走來的艱辛,讓我曉得,夢可以做得很大,但不能把夢做得不實際。
鳳甲美術館成立之外,我便自我衡量過我的能力,不會妄想成立一個與國際美術館相匹敵的展場,我把目標放在「社區」。社會各種力量都是得從基層開始扎根,我們從小學教育,也從社區關係切入。我們把美術館定位成社區型的展場,我們不僅策展,也提供講座,讓學生和民眾有各種接觸的機會。
我們不只辦視覺畫作的賞析,也辦音樂表演,例如我們現址的美術館,看似面積不大,但靈活運用下,可以利用活動性的隔間,把現場變成一個小型的表演場地。而所有入館的訪客都不收門票,經營全靠基金會贊助。
因為資金來源單純,我放手讓美術館的專業來領導,他們發揮的空間很大,本來一開始是靠我的收藏撐起來,沒多久之後,各方申請來展的藝術家已經輕易填滿各年度的檔期。
這把小火,不僅點在一開始冷門的當代藝術領域,就連規模也真的是「小」火,立足社區,從社區開始一步一步發揮影響力。時至今日,我敢說鳳甲不大,但鳳甲在台灣藝術圈卻占有一席之地。
很多人認為,當代藝術是專屬藝術菁英的小圈圈題材,在我眼裡,藝術沒有什麼菁英不菁英的問題,只有夠不夠好的差異。鳳甲美術館有常態性的兒童美術推廣課程,也常有親子共同參與的藝術活動。藝術要走入人群、走入社會,才會是活的,才能反應當代的生活狀態。
以近期的展覽為例,我們不僅關注兒童美學的培養,甚至把觸角伸到各種不同的社群裡,例如視障者。我們設計讓視障者在義工輔助之下,引導他們作畫。他們一輩子看不到,畫出來的作品又將會是什麼樣子呢?大出我意外的是,這些視障者畫出的作品,色彩都相當瑰麗,充滿情感的脈動。
那陣子,有客人來館參觀時,我總愛特別介紹這些視障者作品,在他們的作品裡,我沒有看到絕望,而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也相信,當這些視障者畫完作品之際,一定會獲得更大的力量。而觀看者如我們,也從這些色彩的傳遞裡得到更大的正面力量。這些就是藝術帶來的改變。
不只例行性的展出,每兩年一次的錄像展也是本館的特色之一。今年我們錄像展的主題非常有意思,是「鬼魂的迴返」。
這大概是私營美術館的好處,因為不收政府的經費,所以我們的題材很大膽,我們請不同的藝術家拍錄一支關於鬼魂的電影或影片。
不僅如此,我們在活動前也多次開辦了相關活動,例如我們請了乩童到現場與觀眾面談。台北市這個都市化成熟的地方,很多年輕人甚至是小孩,已經沒有機會親睹乩童「風采」。
我們是以社會學分析、文化分析的角度去看鬼魂,我們請不同的人來座談,將不同的觀點傳達出去。
二○一四年,我一直以為我的投入沒有太多人知道,不起眼的援助支持,沒想到竟能獲頒台北文化獎。得知獲獎的同時,我人在外國,接到電話,因為不是預期內的獎,當然也是相當開心。
因為有了這個獎項的肯定,也間接說明了,我雖然一路在荒野之地,不斷點燃了各地之火,而這火終於一點一點的累積,在荒野裡燃起了一股光和熱,對於後進來說,這些光與熱逐漸匯集,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了。
在挫折裡看見生命的課題
早年,我的夢想是成立一家可以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大企業,就像現在很多年輕人謀職,會把知名企業當成首選的心態類似,但人生的變化很大,有時候不是事事都能盡如人意。
結束環宇之後,我從母公司拿到一百多萬,當時算是一筆錢,但要創業其實不夠。當時公司賣給ITT(這家公司一年的營業額比台灣的GDP還大),我簽合約要在公司待滿兩年,這兩年待遇很高,開始有點儲蓄。在外國人的公司再怎麼做也就是這樣,後來我還是出來自己創業。
剛開始沒什麼錢創業,我先成立一個貿易公司,登記資本額二十萬,我借朋友的一個辦公室,靠三張桌子併在一起,慢慢做。
貿易公司比較不需要資本額,簡單的打字機就可以。貿易公司不需要本錢,但觸角可以非常廣,我不光只做高科技的東西,其中最大的客戶是拍立得,他們剛發明自動對焦,我就在台灣幫他們代工。我應該要自己開工廠來做,但錢不夠,就找工廠做,然後再將貨組裝好運回美國,這有點像仲介的角色。後來拍立得在台灣有很大的裝配線,也是我幫他們安排的。
美國後來找我做省電開關,一般電燈都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