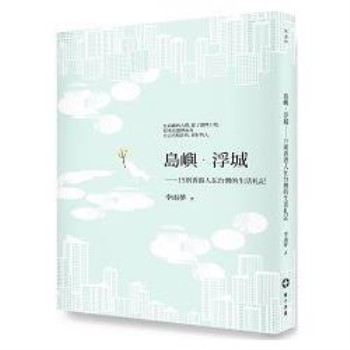Story 1 遠在他方的香港小食:士林夜市裡的十三座牛雜
台北的冬季多雨,陰陰細細,帶給人一種黏膩的感覺。來台灣生活之前,早有朋友提醒過我,台北比香港多雨、潮濕,但真正面臨雨季時,才知道衣服永遠曬不乾的苦惱。劉以鬯在《酒徒》曾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若是如此,記憶如潮水,我在台北的雨季裡便留下了滿滿的回憶。
台灣人總覺得香港的都會氣息濃厚,具有國際觀,連距離天空也比較近一點。在香港生活就像在世界的中心,能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世界。相反的,香港人也熱愛台灣,總覺得少了一股銅臭味,可換來更多生活品質與水準。兩地人民對於他者的浪漫化,呈現出自身位置的困境,不安現狀既是一種欲望的投射,也是為了追求理想生活的冀盼。在光影的交錯之間,造就了兩地觀光發展的蓬勃以及移民熱潮的吹捧。
「牛雜」,庶民小吃的代表
那個陰暗的下雨天,我走到了香港人最為熟悉的士林夜市,不為觀光,只為採訪十三座牛雜店的老闆湯建業。在香港,湯老闆是個名人,除了他的牛雜在香港首屈一指之外,同時他也上遍了大大小小的電視節目與平面媒體,在許多的旅遊美食書裡,都會提及他的牛雜店。「十三座」可以稱得上是香港牛雜的代名詞,是家喻戶曉的小食代表,一點也沒有誇張。
「十三座」一詞,來自於湯老闆父親早年在柴灣第十三座公屋下的小販生意,為了傳承或紀念逝去的老時光,故以此為牛雜店的名字。十三座牛雜並非數十年的老店,他在父親身上承接過來的,不是實體的店鋪,而是一種容易失傳的手藝。湯生的父親賣過粥,也賣過飲品,沒料到,最受食客歡迎的是滷牛雜,一道便宜的小食,讓光顧過的客人念念不忘。然而,他的父親滷牛雜雖是一絕,但他卻拒絕自己的小孩接手牛雜的生意,更警告千萬不能開牛雜店。他自己說到這段時,不免感慨:「父親曾告誡我,什麼行業都可以做,就是不要賣牛雜。」
湯爸爸的憂慮不是沒有原因的,牛雜的製作流程繁複又耗工費時,往往需要花上兩三天的時間做準備,一百斤的牛雜,經過清潔、處理、汆燙、滷製的過程,最後剩下的只有三十斤,成本相當高昂。賣牛雜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前置工作時間非常漫長,不像咖哩魚蛋、雞蛋仔、煎釀三寶般,既容易準備,也較容易被市場所接受。或許有人會問:市場對於咖哩魚蛋與牛雜的接受度有分別嗎?明顯是有的。華人在過去為農耕型社會,擁有一定比例的民眾至今仍不吃牛肉。如今的現代人在口味上與西方頗為接近,較少吃內臟類的食物,包括大腸、肝、肚等。基於以上的原因,牛雜的銷售客群相較於咖哩魚蛋少得多,也使牛雜生意備受挑戰。
早在從事牛雜店之前,老闆經營的是美容美髮的生意,並且在台灣擁有好幾家分店。那是一九八七年前後的事情,台灣解嚴前後,社會最有活力,也是經濟正值蓬勃發展的年代。台灣俗諺說道:「台灣錢淹腳目」,指的就是那時候。不過,錢財若不懂如何守成,便來得快也去得快。當時,湯老闆不能在美髮產業留下,主要都是因為經營不善的問題,在適應不了大環境生態的變化下,他最終還是將公司頂讓出來。在這次經驗中,他開始意識到一家公司的營運不能僅靠技術就能生存下來,其他部分如廣告宣傳、人員管理、財務規畫等都是環環相扣,會影響到一家公司的成敗。
彼時年紀尚輕的湯老闆當然不會理解那麼多,原本以為學習父親努力工作的態度就能改變一切,孰不知技術與經營終究是兩碼子的事。當分店逐漸增多的時候,他一人無法分飾多角,此時,手上的企業體宛如泡沫般快速膨脹,又極速地破滅。
要讓好強的他承認失敗,比登天更難。正當失易落魄的他走到淡水河前時,那莫名湧現的孤寂與徬徨,令他對自己的美容美髮技術感到懷疑。他奮力的將謀生工具的剪刀擲入河中,噗通的拋擲著失敗。他將過去埋葬於深河之中,也告訴自己,該是時候從美髮業中退場了。那時,他仍相當好勝,不相信美髮業是唯一能夠讓他立足社會的行業,抱持著這樣的想法,任何行業他都願意嘗試去闖蕩。退場以後,他毅然走進了台灣的工地,當起苦力背水泥爬上爬下,靠雙手養活自己,堅信努力一定會有回報。當時在工地的湯老闆,對於過去雖然失意,但對於未來仍然充滿希望。
那一年,他還不到三十歲,年輕卻滄桑。經營上的轉向
二○○五年,湯老闆從父親手上承接了那家牛雜店,把它換上一個嶄新的面貌,花了九年時間,在全香港擴張了七家分店,建立起雄霸一方的牛雜食肆王國。十三座牛雜之所以能在香港崛起,因為口味簡單,容易被大眾接受,也在適當的宣傳與行銷策略下,創下了良好的口碑,更使北角的一隅成為壯觀的風景線,隨時都有綿延的排隊人潮。因為經營有道,湯老闆的牛雜王國在短短十年間拓展迅速,並以中央廚房的形式,統一控制食材的味道,讓地方小吃也能營運的擲地有聲。只是,誰料到香港的變化竟然來得這麼快。二○○三年,一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導致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陷入空前的低潮,隨後與中國簽訂的CEPA讓香港「起死回生」,但同時,也使香港的生活更為依賴中國。每年不斷成長的中國觀光客人數、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的人數、在香港買樓的數量,這些都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使得香港成為全球人均所得名列前茅的地區。
然而,隨著中國近年來的高速發展與崛起,人民幣在近幾年內大幅升值,這讓完全依靠中國供應食物來源的香港人愈來愈能感受得到生活的壓力,也使十三座牛雜的成本增加不少。不僅如此,不斷上漲的店租,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動輒數十萬港幣的店租,使小本經營的商店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叢林中只能苦撐下去。但是,壓垮十三座牛雜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實是人力問題。
香港的餐飲業可以興盛來形容,相對而言,這一塊市場的勞動力卻嚴重不足。這導致供不應求的出現,缺工情況尤為嚴重,即使有錢也請不到有經驗的餐飲從業員。如此情形,使十三座牛雜的員工長期處於超時工作的狀態,人才留不住,流動頻繁的狀態下,牛雜的品質受到最為直接的衝擊。為了讓滷製牛雜保持一定的水準,湯老闆決定結束香港的營運,將重心轉往台灣,在「台灣第一夜市」的士林夜市裡,開闢他新的戰場。
猶記得在二○一四年的三月,我在報紙上赫然讀到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消息,當時全港的媒體都在同時報導這事情,正在沉淪的香港,彷彿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牛雜店的結業,對香港人來說,這是重重的一擊,產生一種無以名狀的疼痛。事實上,湯老闆認為,他的品牌以及香港並沒有那麼悲觀。他不禁慨嘆許多媒體的斷章取義,過於凸顯他的部分談話,讓他到來台灣開業的小小夢想,無緣無故地被形塑成為了逃離香港的版本,這實非他本意。「逃離」這個指控,對於湯老闆和香港,都太過沉重。他來台開店其實有著更為深沉而複雜的原因,並非單純歸究香港社會的現存問題。很多時候,他希望把事情慢慢說清楚,卻往往與電視及報導上有所出入,久而久之,他也習慣了媒體有其意識形態的需要,把他的創業夢放置在三菱鏡下,折射出七彩的浪漫光芒。雖然,事實並非如此。台灣是第二個家
來台灣開業是原有的規畫,湯老闆早在一九九○年代就已經在台灣結婚生子,並取得台灣的國籍。他的老婆和小孩沒有跟隨湯老闆回香港生活,十三座牛雜的經營都是靠著他在台港兩地奔波,與香港的合夥朋友和家人撐起來的。我問他:「為何不讓孩子跟著你回香港呢?」他回答道:「台灣的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比香港好。」這著實令人有點意外,激起我的追問。他繼續解釋兩地教學的不同︰「台灣的幼稚園與中小學教育裡,會要求小朋友們去勞動,包括掃地、洗碗、擦桌子,即便不夠乾淨也不要緊,老師和學校希望培養學生自己親力親為的習慣。反觀香港,小朋友只要一有時間,就會被家長安排學習不同語言及才藝。兩地的教育有著極大的差異,我寧可我的孩子更早學會自主與獨立。」
台灣早已是湯建業的家了,為了妻子和小孩,回台灣開店不過是遲早的事。香港媒體與民眾對於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惋惜與難過,似乎忘記了他既是香港人,也是臺灣女婿,回台灣開業也可算是回鄉而已。如果把十三座牛雜的結業,解釋成香港社會通貨膨脹、租金過高、連鎖店林立等已存的社會問題,似乎太過簡單,也太過一廂情願。
面對這些片面的解釋,湯老闆已經看得很淡然。在香港的生意做不下去,那就來台灣或者到其他地方創業,這並沒有對他造成太大的限制與障礙。從這種全球一體的觀念可看出他視野的宏觀,但同時間卻也可能忽略,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公民中,「移動」本身就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本,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要移民或移居到外地討生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湯建業所代表的是一種獅子山下的精神,縱然所謂的努力與收穫不一定是成正比的關係,但付出了努力必然會有一定收穫和回報。然而,到了今天,新自由主義肆虐全球,香港無法獨善其身,勞力與回報呈現反比的趨向,我們很多人只成為了被財團剝削的工具而已。窮忙族的生活就像陀螺一樣日以繼夜地轉動,卻無法讓自己所處的社會階級有向上流動的可能,這樣的癥結已然成為新世代年輕人共同面對的問題。
湯建業雖然早已歸化台灣國籍十數年,但牛雜這道香港小食卻仍然無法融入台灣的小吃文化中。有別於﹁添好運﹂這類港式飲茶餐廳,甫進軍台灣便獲得大量的好評,也不像早已成為台灣飲食文化一部分的街頭燒味便當店,還有出沒於夜市裡頭的雞蛋仔和凍檸茶。牛雜是近幾年才進入台灣的美食系譜,是否能真正獲得廣泛的接受,還得考驗台灣民眾的口味。滷味想像大不同
細數之下,在台灣與牛雜類似的料理,以牛作為小吃美食的,似乎只有滷牛腱和牛肉湯這兩樣,關於內臟部分則有滷牛肚,其他像是牛腸、牛舌、牛肝等很少出現在台灣的料理。牛的臟器之所以較為不被台灣人接受,或許跟台灣過去處於農業社會有關係,在不吃牛的習俗下,對於臟器的接受度也沒有豬來得高。另一方面,對於﹁滷味﹂這項小吃,台港兩地呈現了十分不同的想像。台灣的滷製食品多半偏甜,從滷肉飯到滷雞爪都是如此,香港的滷牛雜則帶有濃郁的中藥材,偏鹹。口感上的差異,也在挑戰著台灣顧客對於牛雜的接受程度。
湯老闆是商場老手,對市場有著一番獨到的見解。當我問他可否給未來希望到台灣生活或創業的香港朋友一些建議時,他突然嚴肅起來。「千萬不要對於台灣抱持著過分浪漫的想像,以為開一間咖啡店,或者做小吃非常容易。在台灣,市場是很現實的。一個產品的好壞,顧客的感受和嘴巴是最真實的。」他的嚴正忠告,當場震懾了我,幾個小時的訪問,大多是以輕鬆的方式來度過,然而,此刻坐我對面的他卻一本正經地解釋他的看法。
他認為,台灣料理的工序往往很簡單,然而,部分香港人總會小看台灣的料理,總是以為台灣不像中國大陸能發展出滿漢全席的磅礡氣勢,或是如同粵菜般蘊含深厚的飲食文化。但湯老闆認為,正因為如此「簡單」,更能看出製作者的用心,愈簡單的東西愈難做得好,台灣的飲食就是在庶民文化中帶著家常的味道。
就湯老闆的牛雜來說,為了來台開業,他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更改滷汁配方,以及整個製作的S O P流程。除了是為了配合台灣人的味蕾和飲食方式外,也是為了適應台灣本土的食材。他說:「台灣人很著重滷味的湯汁味道,但在香港吃牛雜卻沒有那麼強調滷汁。」他的說法,令我想到高雄著名的岡山羊肉爐,之所以能夠聲名遠播的並非羊肉本身,亦非製作羊肉爐的方法,而是岡山的特產豆瓣醬。因為這個看起來並不亮眼的豆瓣醬,讓岡山羊肉爐紅遍全台,成為南部的特色美食。
湯老闆如此的用心,背後反映出他對待饕客及食材的態度,並沒有因為自己是香港美食的代表的緣故,來到台灣後就隨便製作小吃來呼攏台灣人。相反,他更為戰戰兢兢的烹製出符合台灣口味的牛雜小吃,這種符合放棄了原有的港式味道,而是在台灣顧客能夠接受的範圍內,製作出具有香港特色的牛雜料理。畢竟來到他店裡光顧的客人,要的不一定是台灣口味,更多是因為他的港式風味而慕名前來。除了在口感上下功夫外,湯建業更將十坪大的店鋪布置得港味十足,除了沒有椅子的吧檯吃法「很香港」外,裡頭的叮叮車和公共房屋的設計,一併散發出濃濃的香港風情。
十三座牛雜,顧名思義以牛雜為招牌,但在招牌以外,這裡也販賣許多具有香港特式的飲品,包括絲襪奶茶、冰沙椰奶、凍檸茶、凍奶茶。在珍珠奶茶發源地的台灣,湯老闆大膽切入飲料的市場,嘗試與本地飲品作出市場區隔,成功獲得了一定數目的忠實顧客群。他的積極與努力,使在台深根的計畫尚算順利,在士林夜市的一級戰場中也站穩了腳步,聲名逐漸遠播。總是要再回香港
二○一四年層出不窮的食安風暴,也許是在台灣開業遇到的最大阻力。士林夜市的小吃店整體業績下滑了兩到三成,十三座牛雜也受到了直接的衝擊。慶幸的是,他們的資金尚算充足,店鋪也沒有太大,租金壓力相對小許多,這讓湯生的店在寒冬下得以躲過倒閉的風潮,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當我問他有否在台灣其他地方開設分店的計畫或準備時,他搖搖手說道:「目前牛雜飲食文化在台灣尚未普及與成熟,因此我暫時沒有開分店的想法,只希望能夠先守住這一塊陣地,等未來的情況穩定下來後,再作進一步的打算。」我繼續追問他:「那你是否真的放棄了香港市場,未來不會再回香港了?」湯生聽完後哄然大笑,並說:「離開香港只是暫時的啦!怎麼可能不回去香港呢?」語畢又接著一本正經的說:「其實現在與香港敘福樓飲食集團在討論合作的事宜,我出技術、他們出人力與店鋪,透過彼此互補合作的方式,在香港的商場裡販賣牛雜。」湯建業對敘福樓集團的老闆黃傑龍,也就是新的合作夥伴讚譽有加,也深信這敘福樓可以將十三座牛雜的品牌重整並發揚。
對於湯建業與十三座牛雜來說,二○一五年的最大事件,莫過於重新回到香港開業,將原本屬於香港的特色美食,迎回自己的城市。或許這趟的出走與返家時間沒有太久,不過香港人所引頸期盼的,屬於香港人的小吃,也終將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我連聲說道恭喜,為他的未來藍圖感到開心。在香港這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單打獨鬥的小食商鋪實在太辛苦,若沒有大企業的協助、扶植,策略性的結盟,不大可能長久立足。但同時間我也不免在心中泛起一絲絲的不安,擔心假若十三座牛雜有一天被收編,或者成了大量的連鎖食鋪時,那牛雜的味道是否還能夠一直維持?當然這味道不只是食物的,也包括香港小吃文化中濃厚的人情味。
採訪結束離開時,湯建業與我握手再三。那厚實的手掌所傳來的溫度,讓我對我城與香港美食有更深的體會,以及無以言語的牽掛。
台北的冬季多雨,陰陰細細,帶給人一種黏膩的感覺。來台灣生活之前,早有朋友提醒過我,台北比香港多雨、潮濕,但真正面臨雨季時,才知道衣服永遠曬不乾的苦惱。劉以鬯在《酒徒》曾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若是如此,記憶如潮水,我在台北的雨季裡便留下了滿滿的回憶。
台灣人總覺得香港的都會氣息濃厚,具有國際觀,連距離天空也比較近一點。在香港生活就像在世界的中心,能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世界。相反的,香港人也熱愛台灣,總覺得少了一股銅臭味,可換來更多生活品質與水準。兩地人民對於他者的浪漫化,呈現出自身位置的困境,不安現狀既是一種欲望的投射,也是為了追求理想生活的冀盼。在光影的交錯之間,造就了兩地觀光發展的蓬勃以及移民熱潮的吹捧。
「牛雜」,庶民小吃的代表
那個陰暗的下雨天,我走到了香港人最為熟悉的士林夜市,不為觀光,只為採訪十三座牛雜店的老闆湯建業。在香港,湯老闆是個名人,除了他的牛雜在香港首屈一指之外,同時他也上遍了大大小小的電視節目與平面媒體,在許多的旅遊美食書裡,都會提及他的牛雜店。「十三座」可以稱得上是香港牛雜的代名詞,是家喻戶曉的小食代表,一點也沒有誇張。
「十三座」一詞,來自於湯老闆父親早年在柴灣第十三座公屋下的小販生意,為了傳承或紀念逝去的老時光,故以此為牛雜店的名字。十三座牛雜並非數十年的老店,他在父親身上承接過來的,不是實體的店鋪,而是一種容易失傳的手藝。湯生的父親賣過粥,也賣過飲品,沒料到,最受食客歡迎的是滷牛雜,一道便宜的小食,讓光顧過的客人念念不忘。然而,他的父親滷牛雜雖是一絕,但他卻拒絕自己的小孩接手牛雜的生意,更警告千萬不能開牛雜店。他自己說到這段時,不免感慨:「父親曾告誡我,什麼行業都可以做,就是不要賣牛雜。」
湯爸爸的憂慮不是沒有原因的,牛雜的製作流程繁複又耗工費時,往往需要花上兩三天的時間做準備,一百斤的牛雜,經過清潔、處理、汆燙、滷製的過程,最後剩下的只有三十斤,成本相當高昂。賣牛雜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前置工作時間非常漫長,不像咖哩魚蛋、雞蛋仔、煎釀三寶般,既容易準備,也較容易被市場所接受。或許有人會問:市場對於咖哩魚蛋與牛雜的接受度有分別嗎?明顯是有的。華人在過去為農耕型社會,擁有一定比例的民眾至今仍不吃牛肉。如今的現代人在口味上與西方頗為接近,較少吃內臟類的食物,包括大腸、肝、肚等。基於以上的原因,牛雜的銷售客群相較於咖哩魚蛋少得多,也使牛雜生意備受挑戰。
早在從事牛雜店之前,老闆經營的是美容美髮的生意,並且在台灣擁有好幾家分店。那是一九八七年前後的事情,台灣解嚴前後,社會最有活力,也是經濟正值蓬勃發展的年代。台灣俗諺說道:「台灣錢淹腳目」,指的就是那時候。不過,錢財若不懂如何守成,便來得快也去得快。當時,湯老闆不能在美髮產業留下,主要都是因為經營不善的問題,在適應不了大環境生態的變化下,他最終還是將公司頂讓出來。在這次經驗中,他開始意識到一家公司的營運不能僅靠技術就能生存下來,其他部分如廣告宣傳、人員管理、財務規畫等都是環環相扣,會影響到一家公司的成敗。
彼時年紀尚輕的湯老闆當然不會理解那麼多,原本以為學習父親努力工作的態度就能改變一切,孰不知技術與經營終究是兩碼子的事。當分店逐漸增多的時候,他一人無法分飾多角,此時,手上的企業體宛如泡沫般快速膨脹,又極速地破滅。
要讓好強的他承認失敗,比登天更難。正當失易落魄的他走到淡水河前時,那莫名湧現的孤寂與徬徨,令他對自己的美容美髮技術感到懷疑。他奮力的將謀生工具的剪刀擲入河中,噗通的拋擲著失敗。他將過去埋葬於深河之中,也告訴自己,該是時候從美髮業中退場了。那時,他仍相當好勝,不相信美髮業是唯一能夠讓他立足社會的行業,抱持著這樣的想法,任何行業他都願意嘗試去闖蕩。退場以後,他毅然走進了台灣的工地,當起苦力背水泥爬上爬下,靠雙手養活自己,堅信努力一定會有回報。當時在工地的湯老闆,對於過去雖然失意,但對於未來仍然充滿希望。
那一年,他還不到三十歲,年輕卻滄桑。經營上的轉向
二○○五年,湯老闆從父親手上承接了那家牛雜店,把它換上一個嶄新的面貌,花了九年時間,在全香港擴張了七家分店,建立起雄霸一方的牛雜食肆王國。十三座牛雜之所以能在香港崛起,因為口味簡單,容易被大眾接受,也在適當的宣傳與行銷策略下,創下了良好的口碑,更使北角的一隅成為壯觀的風景線,隨時都有綿延的排隊人潮。因為經營有道,湯老闆的牛雜王國在短短十年間拓展迅速,並以中央廚房的形式,統一控制食材的味道,讓地方小吃也能營運的擲地有聲。只是,誰料到香港的變化竟然來得這麼快。二○○三年,一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導致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陷入空前的低潮,隨後與中國簽訂的CEPA讓香港「起死回生」,但同時,也使香港的生活更為依賴中國。每年不斷成長的中國觀光客人數、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的人數、在香港買樓的數量,這些都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使得香港成為全球人均所得名列前茅的地區。
然而,隨著中國近年來的高速發展與崛起,人民幣在近幾年內大幅升值,這讓完全依靠中國供應食物來源的香港人愈來愈能感受得到生活的壓力,也使十三座牛雜的成本增加不少。不僅如此,不斷上漲的店租,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動輒數十萬港幣的店租,使小本經營的商店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叢林中只能苦撐下去。但是,壓垮十三座牛雜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實是人力問題。
香港的餐飲業可以興盛來形容,相對而言,這一塊市場的勞動力卻嚴重不足。這導致供不應求的出現,缺工情況尤為嚴重,即使有錢也請不到有經驗的餐飲從業員。如此情形,使十三座牛雜的員工長期處於超時工作的狀態,人才留不住,流動頻繁的狀態下,牛雜的品質受到最為直接的衝擊。為了讓滷製牛雜保持一定的水準,湯老闆決定結束香港的營運,將重心轉往台灣,在「台灣第一夜市」的士林夜市裡,開闢他新的戰場。
猶記得在二○一四年的三月,我在報紙上赫然讀到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消息,當時全港的媒體都在同時報導這事情,正在沉淪的香港,彷彿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牛雜店的結業,對香港人來說,這是重重的一擊,產生一種無以名狀的疼痛。事實上,湯老闆認為,他的品牌以及香港並沒有那麼悲觀。他不禁慨嘆許多媒體的斷章取義,過於凸顯他的部分談話,讓他到來台灣開業的小小夢想,無緣無故地被形塑成為了逃離香港的版本,這實非他本意。「逃離」這個指控,對於湯老闆和香港,都太過沉重。他來台開店其實有著更為深沉而複雜的原因,並非單純歸究香港社會的現存問題。很多時候,他希望把事情慢慢說清楚,卻往往與電視及報導上有所出入,久而久之,他也習慣了媒體有其意識形態的需要,把他的創業夢放置在三菱鏡下,折射出七彩的浪漫光芒。雖然,事實並非如此。台灣是第二個家
來台灣開業是原有的規畫,湯老闆早在一九九○年代就已經在台灣結婚生子,並取得台灣的國籍。他的老婆和小孩沒有跟隨湯老闆回香港生活,十三座牛雜的經營都是靠著他在台港兩地奔波,與香港的合夥朋友和家人撐起來的。我問他:「為何不讓孩子跟著你回香港呢?」他回答道:「台灣的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比香港好。」這著實令人有點意外,激起我的追問。他繼續解釋兩地教學的不同︰「台灣的幼稚園與中小學教育裡,會要求小朋友們去勞動,包括掃地、洗碗、擦桌子,即便不夠乾淨也不要緊,老師和學校希望培養學生自己親力親為的習慣。反觀香港,小朋友只要一有時間,就會被家長安排學習不同語言及才藝。兩地的教育有著極大的差異,我寧可我的孩子更早學會自主與獨立。」
台灣早已是湯建業的家了,為了妻子和小孩,回台灣開店不過是遲早的事。香港媒體與民眾對於十三座牛雜結業的惋惜與難過,似乎忘記了他既是香港人,也是臺灣女婿,回台灣開業也可算是回鄉而已。如果把十三座牛雜的結業,解釋成香港社會通貨膨脹、租金過高、連鎖店林立等已存的社會問題,似乎太過簡單,也太過一廂情願。
面對這些片面的解釋,湯老闆已經看得很淡然。在香港的生意做不下去,那就來台灣或者到其他地方創業,這並沒有對他造成太大的限制與障礙。從這種全球一體的觀念可看出他視野的宏觀,但同時間卻也可能忽略,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公民中,「移動」本身就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本,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要移民或移居到外地討生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湯建業所代表的是一種獅子山下的精神,縱然所謂的努力與收穫不一定是成正比的關係,但付出了努力必然會有一定收穫和回報。然而,到了今天,新自由主義肆虐全球,香港無法獨善其身,勞力與回報呈現反比的趨向,我們很多人只成為了被財團剝削的工具而已。窮忙族的生活就像陀螺一樣日以繼夜地轉動,卻無法讓自己所處的社會階級有向上流動的可能,這樣的癥結已然成為新世代年輕人共同面對的問題。
湯建業雖然早已歸化台灣國籍十數年,但牛雜這道香港小食卻仍然無法融入台灣的小吃文化中。有別於﹁添好運﹂這類港式飲茶餐廳,甫進軍台灣便獲得大量的好評,也不像早已成為台灣飲食文化一部分的街頭燒味便當店,還有出沒於夜市裡頭的雞蛋仔和凍檸茶。牛雜是近幾年才進入台灣的美食系譜,是否能真正獲得廣泛的接受,還得考驗台灣民眾的口味。滷味想像大不同
細數之下,在台灣與牛雜類似的料理,以牛作為小吃美食的,似乎只有滷牛腱和牛肉湯這兩樣,關於內臟部分則有滷牛肚,其他像是牛腸、牛舌、牛肝等很少出現在台灣的料理。牛的臟器之所以較為不被台灣人接受,或許跟台灣過去處於農業社會有關係,在不吃牛的習俗下,對於臟器的接受度也沒有豬來得高。另一方面,對於﹁滷味﹂這項小吃,台港兩地呈現了十分不同的想像。台灣的滷製食品多半偏甜,從滷肉飯到滷雞爪都是如此,香港的滷牛雜則帶有濃郁的中藥材,偏鹹。口感上的差異,也在挑戰著台灣顧客對於牛雜的接受程度。
湯老闆是商場老手,對市場有著一番獨到的見解。當我問他可否給未來希望到台灣生活或創業的香港朋友一些建議時,他突然嚴肅起來。「千萬不要對於台灣抱持著過分浪漫的想像,以為開一間咖啡店,或者做小吃非常容易。在台灣,市場是很現實的。一個產品的好壞,顧客的感受和嘴巴是最真實的。」他的嚴正忠告,當場震懾了我,幾個小時的訪問,大多是以輕鬆的方式來度過,然而,此刻坐我對面的他卻一本正經地解釋他的看法。
他認為,台灣料理的工序往往很簡單,然而,部分香港人總會小看台灣的料理,總是以為台灣不像中國大陸能發展出滿漢全席的磅礡氣勢,或是如同粵菜般蘊含深厚的飲食文化。但湯老闆認為,正因為如此「簡單」,更能看出製作者的用心,愈簡單的東西愈難做得好,台灣的飲食就是在庶民文化中帶著家常的味道。
就湯老闆的牛雜來說,為了來台開業,他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更改滷汁配方,以及整個製作的S O P流程。除了是為了配合台灣人的味蕾和飲食方式外,也是為了適應台灣本土的食材。他說:「台灣人很著重滷味的湯汁味道,但在香港吃牛雜卻沒有那麼強調滷汁。」他的說法,令我想到高雄著名的岡山羊肉爐,之所以能夠聲名遠播的並非羊肉本身,亦非製作羊肉爐的方法,而是岡山的特產豆瓣醬。因為這個看起來並不亮眼的豆瓣醬,讓岡山羊肉爐紅遍全台,成為南部的特色美食。
湯老闆如此的用心,背後反映出他對待饕客及食材的態度,並沒有因為自己是香港美食的代表的緣故,來到台灣後就隨便製作小吃來呼攏台灣人。相反,他更為戰戰兢兢的烹製出符合台灣口味的牛雜小吃,這種符合放棄了原有的港式味道,而是在台灣顧客能夠接受的範圍內,製作出具有香港特色的牛雜料理。畢竟來到他店裡光顧的客人,要的不一定是台灣口味,更多是因為他的港式風味而慕名前來。除了在口感上下功夫外,湯建業更將十坪大的店鋪布置得港味十足,除了沒有椅子的吧檯吃法「很香港」外,裡頭的叮叮車和公共房屋的設計,一併散發出濃濃的香港風情。
十三座牛雜,顧名思義以牛雜為招牌,但在招牌以外,這裡也販賣許多具有香港特式的飲品,包括絲襪奶茶、冰沙椰奶、凍檸茶、凍奶茶。在珍珠奶茶發源地的台灣,湯老闆大膽切入飲料的市場,嘗試與本地飲品作出市場區隔,成功獲得了一定數目的忠實顧客群。他的積極與努力,使在台深根的計畫尚算順利,在士林夜市的一級戰場中也站穩了腳步,聲名逐漸遠播。總是要再回香港
二○一四年層出不窮的食安風暴,也許是在台灣開業遇到的最大阻力。士林夜市的小吃店整體業績下滑了兩到三成,十三座牛雜也受到了直接的衝擊。慶幸的是,他們的資金尚算充足,店鋪也沒有太大,租金壓力相對小許多,這讓湯生的店在寒冬下得以躲過倒閉的風潮,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當我問他有否在台灣其他地方開設分店的計畫或準備時,他搖搖手說道:「目前牛雜飲食文化在台灣尚未普及與成熟,因此我暫時沒有開分店的想法,只希望能夠先守住這一塊陣地,等未來的情況穩定下來後,再作進一步的打算。」我繼續追問他:「那你是否真的放棄了香港市場,未來不會再回香港了?」湯生聽完後哄然大笑,並說:「離開香港只是暫時的啦!怎麼可能不回去香港呢?」語畢又接著一本正經的說:「其實現在與香港敘福樓飲食集團在討論合作的事宜,我出技術、他們出人力與店鋪,透過彼此互補合作的方式,在香港的商場裡販賣牛雜。」湯建業對敘福樓集團的老闆黃傑龍,也就是新的合作夥伴讚譽有加,也深信這敘福樓可以將十三座牛雜的品牌重整並發揚。
對於湯建業與十三座牛雜來說,二○一五年的最大事件,莫過於重新回到香港開業,將原本屬於香港的特色美食,迎回自己的城市。或許這趟的出走與返家時間沒有太久,不過香港人所引頸期盼的,屬於香港人的小吃,也終將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我連聲說道恭喜,為他的未來藍圖感到開心。在香港這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單打獨鬥的小食商鋪實在太辛苦,若沒有大企業的協助、扶植,策略性的結盟,不大可能長久立足。但同時間我也不免在心中泛起一絲絲的不安,擔心假若十三座牛雜有一天被收編,或者成了大量的連鎖食鋪時,那牛雜的味道是否還能夠一直維持?當然這味道不只是食物的,也包括香港小吃文化中濃厚的人情味。
採訪結束離開時,湯建業與我握手再三。那厚實的手掌所傳來的溫度,讓我對我城與香港美食有更深的體會,以及無以言語的牽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