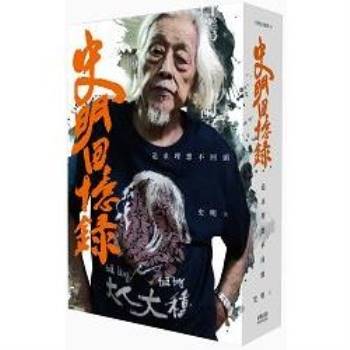第十七章 回到台灣
「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說沒有入境證怎麼上岸(在青島上船時,想說到台灣再說),於是問一個湖南軍人能不能幫忙,他馬上回答:「你跳吧!跳就解決了吧!」(這點就是中國人
靈巧的「敏感性」,笨拙的台灣人幾乎是不能馬上想到的)我們一看,船正在卸貨,岸邊的麻袋、布袋一層層往上堆,把船沿和地面的落差縮短了一大半,說時遲那時快,平賀膽子不小,說跳她馬上跳,我也跟著跳下去,果然沒事,袋子是軟的。腳一著地,我就馬上拉著平賀逃離現場,往火車站一直跑。
在基隆岸上,我記得看到一個中國警察拖拉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旁邊的人替孩子求情:「你原諒他吧!你原諒他小孩兒吧!」很多人都注意到那邊,那個穿著台灣日治時代黑色警察制服的一、青島坐船到基隆從青島到基隆,我記得船走了四、五天,船上坐了滿滿的國民黨軍人與難民,那些難民都穿著軍
服,帶著大包小包。我和平賀睡在甲板上,但即使是甲板上,貨物也堆積如山,很多布袋裡裝著麥子和小米。他們問我:「你哪裡啊?」我回答台灣,大家一聽到就親切起來,圍著我問東問西,譬如台灣最大的都市在哪裡?住在哪裡最好?等等,我當然就和他們吹噓台灣有多便利、多好多好。但遊子歸鄉,心情總是起伏不定。
等船到了基隆港,直接靠在岸壁上一看,碼頭四處皆由憲警站立監督。我們正在猶豫不定,想人卻說:「你們不知道,他跟共產黨有關……」台灣已經與中國一樣,我聽了感到非常可悲,接著我們就坐上火車,回到士林的家了。
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總歸是回到台灣了。到家裡已是下午三、四點,家人看到我們,都嚇了一
跳。我一進門就馬上爬上樓,那是阿嬤在拜佛祖的所在,當時阿嬤在後面,她因為是綁腳後流腳,穿著皮鞋腳步很重,踏踏踏地走過來。她說:「回來就好,
阿暉仔,回來就好了。」我忽然用雙手擁抱著阿嬤的腰,淚如泉湧,無所適從。老祖母還拍拍平賀的肩膀表示慰問。
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家裡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向,現在沒處去,你又回來幹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回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出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回家,看見我們,他連聲說:「回來了,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了。」並且以日語向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了)!」
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回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家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制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裡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裡或鎮公所裡,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裡,平賀才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困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才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系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制服的特務在站衛兵。
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家裡,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只好跟著去了,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裡,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裡整整待了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家裡送來,梳洗、如廁都有困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才可以回家。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家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致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舍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了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出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家知道我是從共產黨解放區回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別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了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回頭就給了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回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都是孫中山培養出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
另外,我從家裡的磚坪仔頂,常常看到貨車載著犯人遊街,通常是年輕人,被打得臉腫腫、面青青,手綁在背後,胳臂中插著一支告示牌,說他什麼罪刑重大、將押去槍斃,貨車開得很慢,要路人都看個清楚,俗語所說的「殺雞儆猴」,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怎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又壞?過了一個多月,阿嬤才對我說:「阿暉仔,二二八時節,阿山這些死人,從台灣頭殺到台灣尾,台北的圓山運動場,殺了好幾百的台灣少年人,都被丟到糞埽車(pùn-sò-chhia卡車),一車又一車,經過士林車頭前的道路,都送到淡水海棄入海底。士林河(基隆河)都是裝著死人的布袋(pòo-tē麻布袋),浮來浮去,海水都變成紅色了。士林草山的溪溝,滿布被阿山仔打死的一大堆屍體,屍體腐爛,看咱的病的施江南醫生也被打死,你老父的朋友被殺了很多人,士林大西街的某人、某人等也被打死,也有許多青年人都被抓去沒回家。看你的性格,如果在台灣也會打死吧,咱的祖公仔也是有保庇(pó-pì)的。」
我在蘇州認識的朋友陳寶川,在我回台灣不久,就跑來找我,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麼回來的?」他當時在做彰化銀行的襄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和特務有關係。我把在中共解放區的經歷告訴他,結論是中國這樣下去會有問題的,他便幫我介紹高理文(高素明),高理文也很驚訝我能夠從中共解放區逃出來,問了我很多細節。從談話中我聽得出來,當年他和蔣經國離開蘇聯時,也曾看出一些蘇聯的問題,譬如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等等,所以對於我的出逃,他連說「幸好!幸好!」高理文是中央信託局的最高顧問,他常請我吃飯,問我有關於中共的事情。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和中共的一些高幹都是同學,而他和蔣經國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
五、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我母親過世後,有一個叫做周慶安的人來找我。二二八事件以後,他曾參加過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在香港有三、四十個台灣青年,原打算和廖文毅做一番工作,但是看廖文毅的生活日趨變化,周慶安就回到台灣,透過林呈祿的兒子林益謙,才找到我這裡來。他住在大正街五條通,我常去找他聊天,總會有些青年人在他那裡,他也沒跟我多做介紹,只是告訴我:「這些人都是會拚命的。」(後來我有給他們講習地下戰)我這裡也有些親戚朋友等等二十來人,雙方常商議:「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指蔣介石)搞掉再說!」
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就是這樣創立的。我已和學生時期不一樣,不必多說什麼,就自然而然走上這條革命的路線。大家做地下工作,分成他跟我的兩條線,分別帶開,各自行動。
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槍很多,尤其是三八槍,我們各自蒐集了三、四十支槍,由我做頭,帶他們去草山的菁礐,我阿嬤在那裡有塊六十甲的共有地,平常的農戶不會注意,我們把槍埋藏在一個山上的雨寮裡頭。同時,由於我阿舅的朋友以前在草山公學校教書,我自小對那裡的環境很熟,和學校的老師們也認識,就向他們租了一間宿舍,在那裡住兩個同志,就近觀察蔣介石搭乘座車出入的情況。
當時蔣介石住在草山的貴賓樓,這是日治時代招待日本皇族的宅邸,從貴賓樓有一條柏油路可以直通台北總統府,這條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就有了,是日本官員為了到草山洗溫泉鋪設的。日治時代,從榮町的街道起站,一天有五、六班次叫做「巴士(トモエバス)」去到草山的公共浴池,有一家公共的「聚樂園」,普通人也能去洗溫泉及遊玩等,一人二角五分,可以泡湯一整天。我以前常和朋友一起從士林爬上草山,到公共浴池玩,沿路有吃不完的多尼仔(一種小果子),可以採來吃,還有我家的祖墳也在草山附近的菁礐,每年都得去掃墓。
我們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發覺蔣介石的七、八部座車隊實在開得太快了,用步槍沒辦法刺殺他,決定另想辦法。
這時候,剛好周慶安弄來一張地圖,說是日治時代日軍的參謀本部流出來的,上面畫著苗栗大湖與南庄之間,藏著很多重機槍。但是那地方屬於深山地區,入山要辦入山證,於是我去拜託高理文,弄到一張文件,說是我在幫中央信託局蒐集香茅油;當時,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香茅油是從台灣出口的,用來做肥皂、薄荷油,高理文還很好意地問我:「你大學畢業,做這種工作,適合得來嗎?」,我答:「不一定做得來,但為了台灣一定要做。」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我阿嬤弟弟的女兒阿彩姨仔嫁到苗栗,所以我去苗栗時,就住這個黃家。在苗栗也得到三個親戚朋友,協助參加我搜山。從苗栗市坐巴士到大湖,再從大湖走到南庄,那一帶就都是雜樹繁茂的深山了。地圖上雖然有目標和地名,但我找起來像在大海裡撈針。我的親戚還找來兩個客家人,我們從一九五○年年尾開始找,很耐心的一直找到一九五一年年尾,機關槍還是沒找到。然而那時,藏在菁礐的槍卻不幸被發現,才放棄找尋。這段期間,我帶苗栗的親戚及朋友去山裡蒐集香茅油,每個月有三個禮拜會住在苗栗,從山中用方型的汽油桶把香茅油以手提方式運下山,交給中央信託局的苗栗集油站,還賺了點錢。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去苗栗也將近一年。
大湖、南庄那一帶的山,原來都是有非常高大的樟樹,以前我們親戚來士林家裡,常帶樟腦油來。其實,製煉樟腦油的方法,和製煉香茅油的方式差不多;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把日本時代禁止開採的樟腦樹,當做木材賣到國外賺大錢,所以,那一帶的人沒辦法生活,才開始種起香茅油草。
一九五一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從苗栗回到士林,天氣很冷,正想回到家裡避避寒,還沒進家門,就看見亭仔腳的磚柱旁,有一個中國人的老婆仔在賣花生,她和顧客講話時,用的話不是北京話,也不是閩南話,我就感覺怪怪的,進門爬到磚坪仔上去看,沒想到對面也搬來一個中國年輕人,問了家人,說是這幾天才搬來的。由於我過去做過地下工作,所以警惕心比較高,馬上到阿嬤的眠床邊,抓起一把金條與美金,就跑出來了。然後我走到士林圓環鎮公所,還沒進門,就被熟識的公所職員何仔義推出來,他說:「你!幹嘛你?憲兵正在圍你的厝,你不知道?」我一聽,趕忙坐巴士往台北跑。
那時是下午三、四點,我遵守「危險時要大進大退」的原則,到台北後馬上坐火車下台中,第二天去高雄,第三天回到新竹,第四天又往屏東跑……,這樣反覆來去。因為警察局是早上九點上班,上班後會到旅館拿前一晚的住宿名單,所以我通常都是近午夜十二點進旅館開房間,四、五點就退房,趕第一班車到另一個地方。
高雄有個鹽埕區,我當時常常去那裡一間便宜旅館開房間。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剛好有個機會,在基隆港做了「海蟑螂」(都是港口的貧窮人的職業)。所謂「海蟑螂」(hái-ka-tsua﹣h),就是拿著日常用品,上船賣給那些沒有辦法上岸的船員,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從那些船上的人手上接一點貨,上陸之後再轉賣出去。後來,我轉做卸香蕉的工人,花了五兩金子,換到那頂卸貨的紅帽子,再找機會混上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船,逃離了台灣。
第十八章 政治亡命日本
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一、偷坐香蕉船,逃亡日本
一九五一年年底,我遭蔣家殖民政權特務警察,以叛亂罪名追查,既激憤也很緊張。但我就像在中國衝破凶險、過五關斬六將回到台灣那樣,精神冷靜,不驚慌,也不害怕,愈遭殃心志反倒愈堅強,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天天都是躲躲藏藏的東奔西走。
到翌年一九五二年二月,我前往基隆,在朋友(𨑨迌人)的介紹下,做「海蟑螂」,到停泊在基隆的外國船裡賣日用品或是台灣的特產品。不過幾天,很幸運的與基隆港的卸貨工頭做朋友,他叫做「打手的」(phah-chhiú-ê),經過一些日子的喝酒聊天或𨑨迌之後,等到互相熟悉了,見機拿出五兩重的金條送他,希望他借給我能夠自由上下船的一頂紅帽子(監視船隻的蔣家特務,都以這頂紅帽子為記號,才讓人出入香蕉船)。工頭接過金條,頓時吃了一驚,這五兩重的金條對他來說是頂大的一筆錢,當下馬上就對我千謝萬謝,隨即去拿一頂紅帽子來給我(他心裡當然知道我是要做什麼的)。
在基隆港口每次裝香蕉,都是從下午一直作業到隔天透早,由香蕉工人扛香蕉簍,從陸地裝卸到船艙裡。香蕉都用竹篾交叉編織而成的簍子裝著,一簍大約三十餘公斤,那時我年紀尚輕,還扛得起香蕉簍,一簍一簍扛上船,卸到船艙裡。通常是卸到夜半二、三點,工作才告一段落。
於是,我選在五月初,天氣不冷(當時還沒有暖氣設備),扛香蕉簍上船後,就把紅帽子托其他同伴的工人夥伴交回去給工頭交差,因為特務警察是以點紅帽子算人頭,只要帽子數量足夠,就算是工人都有上岸,他們就不會看人。
香蕉船艙底的上方有出入口,香蕉裝完後,出入口都以厚木板壓著,再以帆布蓋上去,所以我躲在船艙底,就好像躲在黑漆漆的棺材裡頭一樣。
無論如何,我要逃亡日本的計劃已付諸實行了,內心很澎湃,也很清楚,我要為革命、為獨立、為自由打拚的一生,已走到不可回頭的這一步了。
我在船艙底選擇了一個位置,是出入口對角的角落,我把三、四個香蕉簍子堆疊三層,擺放在我的四周,人就藏在簍子所圍成的高牆裡面,稍微可以伸腳躺下的狹隘空間裡。我在裡頭昏昏欲睡時,也感慨萬千的想到:「為何我一世人都在逃亡跑路!?」但只要船早點開動,我就會再次離開台灣了。
然而過一會兒,在黑暗中,忽然一絲光線穿過竹簍子照進來,偶然抬頭一看,很驚惶的發現,有個穿著藍布衣服的船員,從打開的出入口樓梯下到船艙裡,更奇怪的是,他一直朝我所躲藏的這角落緩緩的爬過來。他在爬到離我僅有一公尺左右的地方,忽然推一推我周圍所疊好的香蕉簍,簍子稍微晃動一下,他說了一句:「可危險啊!」同時在甲板上又有另一個人大聲喊:「好了!」我在一旁是拚命閉氣,忍耐著必死的一瞬間。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在我頭上有個通風口,從甲板上穿過通風口放下一條線,上頭綁著一隻溫度表,就是要測量艙底的溫度,那個溫度表卻卡在我疊好的香蕉簍子邊而不能上下,他是要下來撿溫度表的,也因為下艙的這個人搖動了香蕉簍子,使得溫度表往上動,所以甲板上的船員才喊好了。那時,在艙裡的船員也立即回頭就爬回去,同時將厚木板蓋回原位,艙內又恢復如同棺材裡的黑暗。天啊!!如果簍子被他震動得倒向我的角落來,那一瞬間我就會被發現,到時,就什麼都完了。此時,我始終都閉著氣且不敢隨意亂動的等待著,實在是很危險。人生事就是那麼危機四伏,多一分少一秒,事情就會有很大的變化。三點鐘後,船終於開動了,此時我心想著:很好的出發,這次一定會跑成功!!
這天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二、天山輪晚到神戶,被日警扣押
事後,很多人都在說,既然周圍都是香蕉,那麼吃香蕉就可以活了麼!他們不知道香蕉都是生的,根本不能吃。所以我在船艙底都沒吃沒喝,也沒有屎尿,一直到第三天,腦筋裡開始出現幻覺,睡覺時一直做夢,夢到了神戶,一定要大吃神戶牛肉、牛排,喝蘇打水的大夢。
通常台北到神戶的船,是繞過下關(門司),再通過瀨戶內海,三天二夜就會到達神戶。當時,我搭的這艘「天山輪」,是在戰時運送蔣家國府的物資船,是中國招商局的五千噸美國貨船(LST),坐到第四天還沒到下關,我就開始煩惱這艘船說不定會開到中國去(當時有不少國民黨的船,會開到中國去投降中國共產黨),如果是這樣,就真的完了。後來才知道,船為了躲避戰時留下來的魚雷,繞道四國的外海(太平洋),所以行程才會多花兩天。
五月十一日,船終於到達神戶港,靠岸後,日本的起貨工人就下艙來準備卸貨。他們有六個人,分成兩排坐著,其中一個工人就坐在我前面,根本沒想到我在他後面,我立刻採取行動,迅速舉起左手摀住他的嘴巴,不讓他出聲,再以右手塞一兩金子到他的手裡,然後在他的耳朵邊輕聲的以日語說:「我是從台灣來的,我很愛住日本,拜託你幫我一下。」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物資相當缺乏,老百姓都很苦,一兩金子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價值,他立刻說:「オ‧ゴクロウサマ!」(啊!辛苦了!)我要求他與我換穿衣服,他也隨即答應。換穿衣服後,他先爬到艙口看沒有警察後,才帶我出船艙。在戰後,大概這種類似的偷渡案例不少,所以他的同伴工人看到我,也當成沒看見一樣。
上岸後,我拜託這個工人帶我到神戶市的東亞道路,他隨即幫我僱了部計程車,還熱心的說:「我跟你去!」說著就馬上跟著坐進計程車內。東亞道路原來是神戶市一條有名的大馬路,當時街道被美軍轟炸得近乎面目全非,我要找的地點已經認不出來了。
此時我在心裡想著:「這個人雖是我的恩人,但是跟著我一起這麼長的時間,對我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豈不麻煩?」於是,我突然叫司機把計程車繞到一條車子無法進入的小巷弄前,車一停,我馬上再拿出一兩金子丟給工人,說聲:「ありがとう!さよなら!」(感謝!再見!)轉瞬間,我急忙跳下計程車,同時將車門關上,轉身拔腿就往巷弄裡跑,如此就把他甩掉(事後回想起來,真是過意不去)。
三、以不法入國,遭神戶警察逮捕
之後,我在小巷弄附近東繞西繞,越繞越不對勁,剛好走到一戶人家的庭園門口,大門正好開著,於是我就走進去問路,裡面的女人一聽,就回答說:「你要找的公寓離這裡只有二十來公尺。」我一聽,就安心下來,給她回個禮就走出庭園,沒想到一出門就碰到兩個日本警察在巡邏。那天是五月十一日,兩個禮拜前的四月二十八日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生效日,日本人獲得政治獨立,聯軍總司令麥帥將統治權還給日本,所以日本警察從二十八日起就恢復日本的治安權(聯軍佔領日本以來,日本警察一點權力都沒有),所以能出來巡察。
當時我滿臉鬍髭,渾身髒髒的,又穿著破爛的工人服,在這住宅區很突兀,警察一看就走近來,其中一個對我查問說:「你來你來,你在幹嘛?」我回說在找朋友,他又問:「你從哪裡來?」我一時愣住,只好說是從下關來(因為從台灣來日本時,船都會停靠在下關),沒想到這個警察又說:「我也是下關人,你是下關哪裡?」因我有去過下關很有名的円山公園,所以我脫口而出,說是從円山那裡來的,那個很意外的警察又說:「那麼巧,我也是円山公園那兒的人,你這樣不行,趕快去整理一下儀容,換換服裝,不然會被別的警察捉去。」
兩個警察話說完就走了。然而,沒想到他們倆走沒幾步,其中一個警察又突然轉過頭來問我:「喂,你從下關怎麼來的?」我答說是坐火車來的,他接著問:「火車票多少錢?」當時,我剛到日本,並不知道什麼價格,內心想日本通貨膨脹厲害,就回答千餘円,這樣就壞了事,其實只要幾百円,警察一聽到我這麼說,兩人馬上走回來,開始搜索我的口袋,發現裡面又有金條又有美金,在這最後關頭我無法自圓其說,不得不向他們坦白說出:「對不起,我是台灣人,從台灣來的。」
他們馬上把我帶到神戶的「生田警察署」,以非法入國的罪名,將我拘留起來。我說我是因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蔣家國府追捕才非法入國,警察方面對我還算不錯,馬上通知我在神戶的朋友(平賀的哥哥,以及許炎亭、施隆一),施氏等隨即買衣服來看我。我在拘留所裡被關了二個多禮拜,七、八個人關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監獄主」,他在監獄裡相當凶惡,但他聽說我是台灣人政治犯,卻對我很好,一下子買這買那要我吃,但是我很謹慎,因為六、七天沒吃東西,所以剛開始兩天光喝水,不吃東西,後來,慢慢的把一個便當吃五分之一,漸漸增加,後來才恢復正常。拘留十幾天後,受檢事官審問時,我向他說在台灣因為受到政治迫害,不得已才偷渡到日本。檢事官卻說:「這樣我們可以同情,但是你沒有任何證據可考,法律上我們無法知道你是不是因為殺人放火,才跑到日本來。﹂被拘留了二十幾天後,日本法院決定起訴我,就先讓我假釋,把我沒收的一些金條、美鈔也都還給我,這對我是相當好意的。
我出了拘留所,看到朋友們來接我。一直到十月,法院開庭審理,一庭結審,判四個月徒刑,三年緩刑。我非常開心,以為這樣就可以在日本住下來。但是我還是太天真,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料想不到,以上是司法判決,然後還有行政管轄的問題,必須要經過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處理,所以我一踏出法庭,「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官員,就等著將我送到神戶管理局收容所,繼續扣留,我才明瞭有可能從日本被送回台灣。
當初,在我要走出基隆時,就有做最壞的決死的覺悟,萬一事跡敗露時,就必須自盡身亡。不然,若被送回台灣,會遭蔣家國民黨的殘酷刑求,這是人所不能忍耐的,結果會吐出許多實情,獨立運動及同志們定受連累。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當時美軍將校所穿的軍衣給染成黑色),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在十一月的某天,出入國管理處處長差管理員來叫著:「施朝暉,出來,處長叫你去參見!」我一聽到,覺得事情終於來了,要被送回台灣了,精神有些緊張,把衣服一捆帶著,默默的跟他出去。但是,真沒想到,我一進入處長室,處長一見到我反而站起來,很溫和的伸出手來握我的手,對我說:「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一時之間我被搞得一頭霧水,聽處長說明後才知道:「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警備總司令部,經過外交途徑蔣家大阪領事館,向日本政府提出施朝暉逮捕令狀,說是叛亂反國民黨政府第一司令,要求日本政府把施朝暉政治犯遣送回台灣。」這卻證明我真的是政治犯,因此我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這種天堂地獄似的大變化救了我,終於可以住在日本了,真使我感慨萬千。其後,出入國神戶管理局把我送到橫濱出入國管理所,一個禮拜後辦理手續,遂釋放我於東京。
我在人生強壯佼好、春秋正富的時代,歷盡種種險惡,多次險遭不測,如此的磨練,終使我所抱的抽象革命意識,一步步成長為具體的革命行動
「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說沒有入境證怎麼上岸(在青島上船時,想說到台灣再說),於是問一個湖南軍人能不能幫忙,他馬上回答:「你跳吧!跳就解決了吧!」(這點就是中國人
靈巧的「敏感性」,笨拙的台灣人幾乎是不能馬上想到的)我們一看,船正在卸貨,岸邊的麻袋、布袋一層層往上堆,把船沿和地面的落差縮短了一大半,說時遲那時快,平賀膽子不小,說跳她馬上跳,我也跟著跳下去,果然沒事,袋子是軟的。腳一著地,我就馬上拉著平賀逃離現場,往火車站一直跑。
在基隆岸上,我記得看到一個中國警察拖拉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旁邊的人替孩子求情:「你原諒他吧!你原諒他小孩兒吧!」很多人都注意到那邊,那個穿著台灣日治時代黑色警察制服的一、青島坐船到基隆從青島到基隆,我記得船走了四、五天,船上坐了滿滿的國民黨軍人與難民,那些難民都穿著軍
服,帶著大包小包。我和平賀睡在甲板上,但即使是甲板上,貨物也堆積如山,很多布袋裡裝著麥子和小米。他們問我:「你哪裡啊?」我回答台灣,大家一聽到就親切起來,圍著我問東問西,譬如台灣最大的都市在哪裡?住在哪裡最好?等等,我當然就和他們吹噓台灣有多便利、多好多好。但遊子歸鄉,心情總是起伏不定。
等船到了基隆港,直接靠在岸壁上一看,碼頭四處皆由憲警站立監督。我們正在猶豫不定,想人卻說:「你們不知道,他跟共產黨有關……」台灣已經與中國一樣,我聽了感到非常可悲,接著我們就坐上火車,回到士林的家了。
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總歸是回到台灣了。到家裡已是下午三、四點,家人看到我們,都嚇了一
跳。我一進門就馬上爬上樓,那是阿嬤在拜佛祖的所在,當時阿嬤在後面,她因為是綁腳後流腳,穿著皮鞋腳步很重,踏踏踏地走過來。她說:「回來就好,
阿暉仔,回來就好了。」我忽然用雙手擁抱著阿嬤的腰,淚如泉湧,無所適從。老祖母還拍拍平賀的肩膀表示慰問。
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家裡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向,現在沒處去,你又回來幹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回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出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回家,看見我們,他連聲說:「回來了,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了。」並且以日語向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了)!」
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回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家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制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裡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裡或鎮公所裡,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裡,平賀才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困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才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系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制服的特務在站衛兵。
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家裡,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只好跟著去了,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裡,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裡整整待了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家裡送來,梳洗、如廁都有困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才可以回家。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家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致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舍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了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出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家知道我是從共產黨解放區回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別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了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回頭就給了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回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都是孫中山培養出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
另外,我從家裡的磚坪仔頂,常常看到貨車載著犯人遊街,通常是年輕人,被打得臉腫腫、面青青,手綁在背後,胳臂中插著一支告示牌,說他什麼罪刑重大、將押去槍斃,貨車開得很慢,要路人都看個清楚,俗語所說的「殺雞儆猴」,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怎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又壞?過了一個多月,阿嬤才對我說:「阿暉仔,二二八時節,阿山這些死人,從台灣頭殺到台灣尾,台北的圓山運動場,殺了好幾百的台灣少年人,都被丟到糞埽車(pùn-sò-chhia卡車),一車又一車,經過士林車頭前的道路,都送到淡水海棄入海底。士林河(基隆河)都是裝著死人的布袋(pòo-tē麻布袋),浮來浮去,海水都變成紅色了。士林草山的溪溝,滿布被阿山仔打死的一大堆屍體,屍體腐爛,看咱的病的施江南醫生也被打死,你老父的朋友被殺了很多人,士林大西街的某人、某人等也被打死,也有許多青年人都被抓去沒回家。看你的性格,如果在台灣也會打死吧,咱的祖公仔也是有保庇(pó-pì)的。」
我在蘇州認識的朋友陳寶川,在我回台灣不久,就跑來找我,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麼回來的?」他當時在做彰化銀行的襄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和特務有關係。我把在中共解放區的經歷告訴他,結論是中國這樣下去會有問題的,他便幫我介紹高理文(高素明),高理文也很驚訝我能夠從中共解放區逃出來,問了我很多細節。從談話中我聽得出來,當年他和蔣經國離開蘇聯時,也曾看出一些蘇聯的問題,譬如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等等,所以對於我的出逃,他連說「幸好!幸好!」高理文是中央信託局的最高顧問,他常請我吃飯,問我有關於中共的事情。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和中共的一些高幹都是同學,而他和蔣經國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
五、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我母親過世後,有一個叫做周慶安的人來找我。二二八事件以後,他曾參加過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在香港有三、四十個台灣青年,原打算和廖文毅做一番工作,但是看廖文毅的生活日趨變化,周慶安就回到台灣,透過林呈祿的兒子林益謙,才找到我這裡來。他住在大正街五條通,我常去找他聊天,總會有些青年人在他那裡,他也沒跟我多做介紹,只是告訴我:「這些人都是會拚命的。」(後來我有給他們講習地下戰)我這裡也有些親戚朋友等等二十來人,雙方常商議:「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指蔣介石)搞掉再說!」
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就是這樣創立的。我已和學生時期不一樣,不必多說什麼,就自然而然走上這條革命的路線。大家做地下工作,分成他跟我的兩條線,分別帶開,各自行動。
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槍很多,尤其是三八槍,我們各自蒐集了三、四十支槍,由我做頭,帶他們去草山的菁礐,我阿嬤在那裡有塊六十甲的共有地,平常的農戶不會注意,我們把槍埋藏在一個山上的雨寮裡頭。同時,由於我阿舅的朋友以前在草山公學校教書,我自小對那裡的環境很熟,和學校的老師們也認識,就向他們租了一間宿舍,在那裡住兩個同志,就近觀察蔣介石搭乘座車出入的情況。
當時蔣介石住在草山的貴賓樓,這是日治時代招待日本皇族的宅邸,從貴賓樓有一條柏油路可以直通台北總統府,這條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就有了,是日本官員為了到草山洗溫泉鋪設的。日治時代,從榮町的街道起站,一天有五、六班次叫做「巴士(トモエバス)」去到草山的公共浴池,有一家公共的「聚樂園」,普通人也能去洗溫泉及遊玩等,一人二角五分,可以泡湯一整天。我以前常和朋友一起從士林爬上草山,到公共浴池玩,沿路有吃不完的多尼仔(一種小果子),可以採來吃,還有我家的祖墳也在草山附近的菁礐,每年都得去掃墓。
我們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發覺蔣介石的七、八部座車隊實在開得太快了,用步槍沒辦法刺殺他,決定另想辦法。
這時候,剛好周慶安弄來一張地圖,說是日治時代日軍的參謀本部流出來的,上面畫著苗栗大湖與南庄之間,藏著很多重機槍。但是那地方屬於深山地區,入山要辦入山證,於是我去拜託高理文,弄到一張文件,說是我在幫中央信託局蒐集香茅油;當時,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香茅油是從台灣出口的,用來做肥皂、薄荷油,高理文還很好意地問我:「你大學畢業,做這種工作,適合得來嗎?」,我答:「不一定做得來,但為了台灣一定要做。」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我阿嬤弟弟的女兒阿彩姨仔嫁到苗栗,所以我去苗栗時,就住這個黃家。在苗栗也得到三個親戚朋友,協助參加我搜山。從苗栗市坐巴士到大湖,再從大湖走到南庄,那一帶就都是雜樹繁茂的深山了。地圖上雖然有目標和地名,但我找起來像在大海裡撈針。我的親戚還找來兩個客家人,我們從一九五○年年尾開始找,很耐心的一直找到一九五一年年尾,機關槍還是沒找到。然而那時,藏在菁礐的槍卻不幸被發現,才放棄找尋。這段期間,我帶苗栗的親戚及朋友去山裡蒐集香茅油,每個月有三個禮拜會住在苗栗,從山中用方型的汽油桶把香茅油以手提方式運下山,交給中央信託局的苗栗集油站,還賺了點錢。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去苗栗也將近一年。
大湖、南庄那一帶的山,原來都是有非常高大的樟樹,以前我們親戚來士林家裡,常帶樟腦油來。其實,製煉樟腦油的方法,和製煉香茅油的方式差不多;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把日本時代禁止開採的樟腦樹,當做木材賣到國外賺大錢,所以,那一帶的人沒辦法生活,才開始種起香茅油草。
一九五一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從苗栗回到士林,天氣很冷,正想回到家裡避避寒,還沒進家門,就看見亭仔腳的磚柱旁,有一個中國人的老婆仔在賣花生,她和顧客講話時,用的話不是北京話,也不是閩南話,我就感覺怪怪的,進門爬到磚坪仔上去看,沒想到對面也搬來一個中國年輕人,問了家人,說是這幾天才搬來的。由於我過去做過地下工作,所以警惕心比較高,馬上到阿嬤的眠床邊,抓起一把金條與美金,就跑出來了。然後我走到士林圓環鎮公所,還沒進門,就被熟識的公所職員何仔義推出來,他說:「你!幹嘛你?憲兵正在圍你的厝,你不知道?」我一聽,趕忙坐巴士往台北跑。
那時是下午三、四點,我遵守「危險時要大進大退」的原則,到台北後馬上坐火車下台中,第二天去高雄,第三天回到新竹,第四天又往屏東跑……,這樣反覆來去。因為警察局是早上九點上班,上班後會到旅館拿前一晚的住宿名單,所以我通常都是近午夜十二點進旅館開房間,四、五點就退房,趕第一班車到另一個地方。
高雄有個鹽埕區,我當時常常去那裡一間便宜旅館開房間。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剛好有個機會,在基隆港做了「海蟑螂」(都是港口的貧窮人的職業)。所謂「海蟑螂」(hái-ka-tsua﹣h),就是拿著日常用品,上船賣給那些沒有辦法上岸的船員,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從那些船上的人手上接一點貨,上陸之後再轉賣出去。後來,我轉做卸香蕉的工人,花了五兩金子,換到那頂卸貨的紅帽子,再找機會混上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船,逃離了台灣。
第十八章 政治亡命日本
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一、偷坐香蕉船,逃亡日本
一九五一年年底,我遭蔣家殖民政權特務警察,以叛亂罪名追查,既激憤也很緊張。但我就像在中國衝破凶險、過五關斬六將回到台灣那樣,精神冷靜,不驚慌,也不害怕,愈遭殃心志反倒愈堅強,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天天都是躲躲藏藏的東奔西走。
到翌年一九五二年二月,我前往基隆,在朋友(𨑨迌人)的介紹下,做「海蟑螂」,到停泊在基隆的外國船裡賣日用品或是台灣的特產品。不過幾天,很幸運的與基隆港的卸貨工頭做朋友,他叫做「打手的」(phah-chhiú-ê),經過一些日子的喝酒聊天或𨑨迌之後,等到互相熟悉了,見機拿出五兩重的金條送他,希望他借給我能夠自由上下船的一頂紅帽子(監視船隻的蔣家特務,都以這頂紅帽子為記號,才讓人出入香蕉船)。工頭接過金條,頓時吃了一驚,這五兩重的金條對他來說是頂大的一筆錢,當下馬上就對我千謝萬謝,隨即去拿一頂紅帽子來給我(他心裡當然知道我是要做什麼的)。
在基隆港口每次裝香蕉,都是從下午一直作業到隔天透早,由香蕉工人扛香蕉簍,從陸地裝卸到船艙裡。香蕉都用竹篾交叉編織而成的簍子裝著,一簍大約三十餘公斤,那時我年紀尚輕,還扛得起香蕉簍,一簍一簍扛上船,卸到船艙裡。通常是卸到夜半二、三點,工作才告一段落。
於是,我選在五月初,天氣不冷(當時還沒有暖氣設備),扛香蕉簍上船後,就把紅帽子托其他同伴的工人夥伴交回去給工頭交差,因為特務警察是以點紅帽子算人頭,只要帽子數量足夠,就算是工人都有上岸,他們就不會看人。
香蕉船艙底的上方有出入口,香蕉裝完後,出入口都以厚木板壓著,再以帆布蓋上去,所以我躲在船艙底,就好像躲在黑漆漆的棺材裡頭一樣。
無論如何,我要逃亡日本的計劃已付諸實行了,內心很澎湃,也很清楚,我要為革命、為獨立、為自由打拚的一生,已走到不可回頭的這一步了。
我在船艙底選擇了一個位置,是出入口對角的角落,我把三、四個香蕉簍子堆疊三層,擺放在我的四周,人就藏在簍子所圍成的高牆裡面,稍微可以伸腳躺下的狹隘空間裡。我在裡頭昏昏欲睡時,也感慨萬千的想到:「為何我一世人都在逃亡跑路!?」但只要船早點開動,我就會再次離開台灣了。
然而過一會兒,在黑暗中,忽然一絲光線穿過竹簍子照進來,偶然抬頭一看,很驚惶的發現,有個穿著藍布衣服的船員,從打開的出入口樓梯下到船艙裡,更奇怪的是,他一直朝我所躲藏的這角落緩緩的爬過來。他在爬到離我僅有一公尺左右的地方,忽然推一推我周圍所疊好的香蕉簍,簍子稍微晃動一下,他說了一句:「可危險啊!」同時在甲板上又有另一個人大聲喊:「好了!」我在一旁是拚命閉氣,忍耐著必死的一瞬間。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在我頭上有個通風口,從甲板上穿過通風口放下一條線,上頭綁著一隻溫度表,就是要測量艙底的溫度,那個溫度表卻卡在我疊好的香蕉簍子邊而不能上下,他是要下來撿溫度表的,也因為下艙的這個人搖動了香蕉簍子,使得溫度表往上動,所以甲板上的船員才喊好了。那時,在艙裡的船員也立即回頭就爬回去,同時將厚木板蓋回原位,艙內又恢復如同棺材裡的黑暗。天啊!!如果簍子被他震動得倒向我的角落來,那一瞬間我就會被發現,到時,就什麼都完了。此時,我始終都閉著氣且不敢隨意亂動的等待著,實在是很危險。人生事就是那麼危機四伏,多一分少一秒,事情就會有很大的變化。三點鐘後,船終於開動了,此時我心想著:很好的出發,這次一定會跑成功!!
這天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二、天山輪晚到神戶,被日警扣押
事後,很多人都在說,既然周圍都是香蕉,那麼吃香蕉就可以活了麼!他們不知道香蕉都是生的,根本不能吃。所以我在船艙底都沒吃沒喝,也沒有屎尿,一直到第三天,腦筋裡開始出現幻覺,睡覺時一直做夢,夢到了神戶,一定要大吃神戶牛肉、牛排,喝蘇打水的大夢。
通常台北到神戶的船,是繞過下關(門司),再通過瀨戶內海,三天二夜就會到達神戶。當時,我搭的這艘「天山輪」,是在戰時運送蔣家國府的物資船,是中國招商局的五千噸美國貨船(LST),坐到第四天還沒到下關,我就開始煩惱這艘船說不定會開到中國去(當時有不少國民黨的船,會開到中國去投降中國共產黨),如果是這樣,就真的完了。後來才知道,船為了躲避戰時留下來的魚雷,繞道四國的外海(太平洋),所以行程才會多花兩天。
五月十一日,船終於到達神戶港,靠岸後,日本的起貨工人就下艙來準備卸貨。他們有六個人,分成兩排坐著,其中一個工人就坐在我前面,根本沒想到我在他後面,我立刻採取行動,迅速舉起左手摀住他的嘴巴,不讓他出聲,再以右手塞一兩金子到他的手裡,然後在他的耳朵邊輕聲的以日語說:「我是從台灣來的,我很愛住日本,拜託你幫我一下。」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物資相當缺乏,老百姓都很苦,一兩金子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價值,他立刻說:「オ‧ゴクロウサマ!」(啊!辛苦了!)我要求他與我換穿衣服,他也隨即答應。換穿衣服後,他先爬到艙口看沒有警察後,才帶我出船艙。在戰後,大概這種類似的偷渡案例不少,所以他的同伴工人看到我,也當成沒看見一樣。
上岸後,我拜託這個工人帶我到神戶市的東亞道路,他隨即幫我僱了部計程車,還熱心的說:「我跟你去!」說著就馬上跟著坐進計程車內。東亞道路原來是神戶市一條有名的大馬路,當時街道被美軍轟炸得近乎面目全非,我要找的地點已經認不出來了。
此時我在心裡想著:「這個人雖是我的恩人,但是跟著我一起這麼長的時間,對我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豈不麻煩?」於是,我突然叫司機把計程車繞到一條車子無法進入的小巷弄前,車一停,我馬上再拿出一兩金子丟給工人,說聲:「ありがとう!さよなら!」(感謝!再見!)轉瞬間,我急忙跳下計程車,同時將車門關上,轉身拔腿就往巷弄裡跑,如此就把他甩掉(事後回想起來,真是過意不去)。
三、以不法入國,遭神戶警察逮捕
之後,我在小巷弄附近東繞西繞,越繞越不對勁,剛好走到一戶人家的庭園門口,大門正好開著,於是我就走進去問路,裡面的女人一聽,就回答說:「你要找的公寓離這裡只有二十來公尺。」我一聽,就安心下來,給她回個禮就走出庭園,沒想到一出門就碰到兩個日本警察在巡邏。那天是五月十一日,兩個禮拜前的四月二十八日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生效日,日本人獲得政治獨立,聯軍總司令麥帥將統治權還給日本,所以日本警察從二十八日起就恢復日本的治安權(聯軍佔領日本以來,日本警察一點權力都沒有),所以能出來巡察。
當時我滿臉鬍髭,渾身髒髒的,又穿著破爛的工人服,在這住宅區很突兀,警察一看就走近來,其中一個對我查問說:「你來你來,你在幹嘛?」我回說在找朋友,他又問:「你從哪裡來?」我一時愣住,只好說是從下關來(因為從台灣來日本時,船都會停靠在下關),沒想到這個警察又說:「我也是下關人,你是下關哪裡?」因我有去過下關很有名的円山公園,所以我脫口而出,說是從円山那裡來的,那個很意外的警察又說:「那麼巧,我也是円山公園那兒的人,你這樣不行,趕快去整理一下儀容,換換服裝,不然會被別的警察捉去。」
兩個警察話說完就走了。然而,沒想到他們倆走沒幾步,其中一個警察又突然轉過頭來問我:「喂,你從下關怎麼來的?」我答說是坐火車來的,他接著問:「火車票多少錢?」當時,我剛到日本,並不知道什麼價格,內心想日本通貨膨脹厲害,就回答千餘円,這樣就壞了事,其實只要幾百円,警察一聽到我這麼說,兩人馬上走回來,開始搜索我的口袋,發現裡面又有金條又有美金,在這最後關頭我無法自圓其說,不得不向他們坦白說出:「對不起,我是台灣人,從台灣來的。」
他們馬上把我帶到神戶的「生田警察署」,以非法入國的罪名,將我拘留起來。我說我是因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蔣家國府追捕才非法入國,警察方面對我還算不錯,馬上通知我在神戶的朋友(平賀的哥哥,以及許炎亭、施隆一),施氏等隨即買衣服來看我。我在拘留所裡被關了二個多禮拜,七、八個人關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監獄主」,他在監獄裡相當凶惡,但他聽說我是台灣人政治犯,卻對我很好,一下子買這買那要我吃,但是我很謹慎,因為六、七天沒吃東西,所以剛開始兩天光喝水,不吃東西,後來,慢慢的把一個便當吃五分之一,漸漸增加,後來才恢復正常。拘留十幾天後,受檢事官審問時,我向他說在台灣因為受到政治迫害,不得已才偷渡到日本。檢事官卻說:「這樣我們可以同情,但是你沒有任何證據可考,法律上我們無法知道你是不是因為殺人放火,才跑到日本來。﹂被拘留了二十幾天後,日本法院決定起訴我,就先讓我假釋,把我沒收的一些金條、美鈔也都還給我,這對我是相當好意的。
我出了拘留所,看到朋友們來接我。一直到十月,法院開庭審理,一庭結審,判四個月徒刑,三年緩刑。我非常開心,以為這樣就可以在日本住下來。但是我還是太天真,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料想不到,以上是司法判決,然後還有行政管轄的問題,必須要經過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處理,所以我一踏出法庭,「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的官員,就等著將我送到神戶管理局收容所,繼續扣留,我才明瞭有可能從日本被送回台灣。
當初,在我要走出基隆時,就有做最壞的決死的覺悟,萬一事跡敗露時,就必須自盡身亡。不然,若被送回台灣,會遭蔣家國民黨的殘酷刑求,這是人所不能忍耐的,結果會吐出許多實情,獨立運動及同志們定受連累。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把身上所穿的衣服(當時美軍將校所穿的軍衣給染成黑色),在上衣的衣角內裡,縫上兩片刮鬍刀片,以防萬一。可是我覺得會到這種最後的情況,是很不可思議的,心裡一點也不悲觀,也不覺得失望,只是天天都摸摸那兩片刀片,時時刻刻在等著事件的結果。
在十一月的某天,出入國管理處處長差管理員來叫著:「施朝暉,出來,處長叫你去參見!」我一聽到,覺得事情終於來了,要被送回台灣了,精神有些緊張,把衣服一捆帶著,默默的跟他出去。但是,真沒想到,我一進入處長室,處長一見到我反而站起來,很溫和的伸出手來握我的手,對我說:「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一時之間我被搞得一頭霧水,聽處長說明後才知道:「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警備總司令部,經過外交途徑蔣家大阪領事館,向日本政府提出施朝暉逮捕令狀,說是叛亂反國民黨政府第一司令,要求日本政府把施朝暉政治犯遣送回台灣。」這卻證明我真的是政治犯,因此我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這種天堂地獄似的大變化救了我,終於可以住在日本了,真使我感慨萬千。其後,出入國神戶管理局把我送到橫濱出入國管理所,一個禮拜後辦理手續,遂釋放我於東京。
我在人生強壯佼好、春秋正富的時代,歷盡種種險惡,多次險遭不測,如此的磨練,終使我所抱的抽象革命意識,一步步成長為具體的革命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