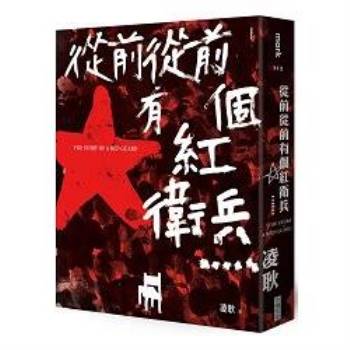回到廈門
王光美被鬥爭後不久,清華大學舉行了一次大掃除。大字報欄上厚厚的一層紙都被刮了下來,洗刷乾淨,好再貼上新的大字報。象徵王光美末日的標語紙一直都在各大樓的牆壁上隨著寒風飄搖,現在也被清除了。元旦將近,校園各處都洋溢著萬象更新的氣息。
我們幾乎是最後一批離開北京的串連代表。三姐早在十幾天前就回家了,只有二姐含淚在清華園送我。她說她太想念母親了,不久一定會設法回家一次。載我們往火車站的專車,應大家的要求在天安門前停下來。
「請讓我們多拍幾張照片吧!」我說:「我們也許一輩子都不會再來了。」我站在白石橋上,手扶欄杆,心裡想著元旦就要到了,北京的家家戶戶一定都在忙著大掃除和剁豬肉、包餃子。家裡,母親也一定在忙著。
這裡沒有值得我們留連忘返的東西,只有風、沙和商店裡或公共汽車上的人們投來的冷漠眼光。不過,我們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依依不捨。
在聞名的天壇附近的永定門車站上,成千的人在竹棚下等火車。有人等了一天,有人等了好幾天。
我們的火車要到傍晚才來,於是我們決定再進城一次,來一趟告別之遊。我請梅梅一起到一家館子吃烤鴨,她卻急著要回天壇。因此,我們買了一隻烤鴨帶出來,走過天安門前,我面向天安門,手舉烤鴨作道別狀,由梅梅替我拍了一張照(後來,這件事傳到廈門,說我揮烤鴨向北京道別,戰友們都笑我,敵人則藉此攻擊我)。正要上火車之前,我問同伴們敢不敢轉道沿路多看幾個城市,反正已經趕不上回家過元旦了。他們怯怯地回答了一個「好」字。其實,我是要他們陪著我實現自己的願望,因為我想到山西去看大哥。從北京到太原的火車幸好沒有誤點。在火車上的一天一夜裡,我們拚命趕寫串連報告,想在年前把它趕完。我很驕傲地告訴同伴,我們圓滿地完成了五大任務:一、我們在北京完成了革命串連,和北京各校的紅衛兵交換了革命心得、材料和袖章,並且建立了聯繫,一本厚厚的通訊錄就是證據;二、我們見到了毛澤東,雖然沒能拍下照片,每人都在日誌裡記載了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印象和描述;三、我們瞻仰了祖國山河,有許多照片為證;四、我們得到了許多內幕消息,帶回大批材料,同志們看到這些材料,一定會以為是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五、我們接觸過外國人,並且參加了一次國際行動─也就是鬥爭過外國人,更改過路名(這最後一項工作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不過總部可能不覺得有趣)。
我沒有把自己的私人任務─會見家人列入其內。
結帳時,我發現我們差不多花光了整整人民幣一千元的公款,剩下的只有兩百元左右;而核對所有的發票以後,發現比原數又少了十塊錢,梅梅、搥胸和我分攤了這個差額。
然後我們拿出所有購買的東西來看,其中有給同學、朋友的禮物,給母親的枕頭套、高跟鞋、絲襪和化妝品,給二哥買的地圖。我自己帶出來的一百二十元已花掉將近一百元,大姐和二姐為我花的錢還沒算在內,何況來往的車費和在清華的吃住都不是自己負擔的。
到了太原後,看到街上有許多人在辦年貨,像我們這樣身背行囊的紅衛兵不多。我們又像叫化子一樣,心裡難免窘怕。接待站人員發現我們故意繞道回家時,幾乎不肯負責我們的吃住。
我實在不忍心把同伴們丟在嚴寒的太原,可是又捨不得錯過見大哥的機會,只好託搥胸代為照顧其他同伴,自己一人到了大哥家。
大哥有個溫暖的小家庭─一個賢妻和兩個寶寶,一男一女。他們遠在北方安家,真叫人惋惜(我趕緊寫信給母親,叫她千萬不要來了,這地方的寒冷不是她受得了的)。
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把兩個小孩送到南方去由母親扶養。只要家庭環境過得去,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都設法把孩子送回南方家中去撫養。按照規定,已婚的外地工作人員不能請假返鄉探望父母,大哥沒有辦法親自送孩子回去。他一直在打聽鐵路局能不能把一個四歲和一個兩歲的孩子代送回去。他說曾經看過一部叫作《蘭蘭和冬冬》的電影,片中兩個小孩單獨從上海旅行到北京去找爸爸、媽媽,一路上受到了鐵路員工的熱心照顧。顯然,大哥還不知道現在的火車交通亂成什麼樣子。其實,大哥、大嫂並不願意和孩子分離。可是兩個人都要上班,北方的教育、育兒設備和衛生都很差,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女長得像北方小孩一樣愚蠢又粗魯。
母親也早就想含飴弄孫了。她計劃在退休後到全國各地走走,順便把大哥的孩子和大姐、二姐將來的孩子帶回來,在家裡開起自己的托兒所。可是,這場破壞她計劃的文化大革命到現在都還沒有收場的意思。
我哀求大哥、大嫂讓我負責把兩個娃娃帶回去,相信梅梅和其他同伴一定會喜歡這兩個小東西。
大哥苦笑道:「你連自己都照顧不來呢,自己都還是孩子,怎麼能帶兩個小小孩?媽寫過信來說你愛哭,沒有責任感,她還得成天跟在你的後面呢。」
「那些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我長大了,又是紅衛兵頭頭。我什麼大事都做過,可以獨當一面了!」
儘管我說得舌敝唇焦,也勸不動大哥。
我來訪的最大目的既然失敗,便決定不再逗留,匆匆趕回太原和同伴會面。同伴們離鄉背井,過了個最淒涼的元旦。我從大哥家帶去了許多吃的,總算讓大家享受了一頓遲來的盛宴。
我們繼續向南走,到了西安。這是一個大而不熱鬧的城市,在這裡停留了一天多一點。西安市的市民隨地吐痰的習慣實在可怕,弄得到處是痰。我們嘗了當地的名食─羊肉泡饃,吃過後卻是好久都還覺得不舒服。我們本來想參觀全國最大的飛機場,臨時改變了主意,昏昏沉沉地上了火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這列火車走的方向不對!
最後,我們在中國的石油中心蘭州市下了火車。這列火車是一直開往新疆的,寒冷的天氣使我們卻步了。我們在蘭州市過了一天,唯一的收穫是買到了每公斤人民幣五角六分的牛肉乾,這個價錢是我們家鄉的十分之一。我們買了一大包,夾在饅頭裡吃,真是痛快極了。可是,同車的乘客對我們說,脫水牛肉沒有什麼營養。
在河南省鄭州換上京廣線的火車後,我們的心情都安定了不少。河南的食品便宜得驚人,蒸雞一斤五角錢,還有五香豆腐乾、蘋果和梨等,我們便大享了口福。
火車一點也不擠,一路上很少遇見串連的紅衛兵。這一次,途中也沒有乞丐搗亂。串連已經過去,火車站的軍人又可以有效地維持秩序了。
我們請隨車服務人員來分享食物,和我們聊天,除了火車司機和司爐外,幾乎人人都來吃我們的牛肉乾,看看我們的東西,聽聽我們的故事。到了漢口,聽接待人員說接待站過兩天就要關閉了,關閉以後,我們就得自己負責吃住。一驚之下,我們匆匆在全國最長的長江大橋上拍了幾張照,就登上了宜昌號汽船順流而下,前往南京,全程費時三天。
這三天裡,梅梅每天都起個絕早,跑到船頭去唱西藏民謠和各地的民謠。有一天,她以為四下無人,脫下了軍用大衣,握著拳頭,引吭高歌起來,似乎渾然忘卻了腳下的滔滔江水。
我想從背後給她偷拍一張照片。「小心別翻下去,不要受涼了。」我拾起甲板上的大衣,抖抖灰,給她披上。我說:「妳唱得真好,三山五嶽都要向妳俯首稱臣,長流的江水也要向妳致敬了!」她羞得直要掐我的手。後面有人大叫:「跳進長江游泳吧!你們真是天生的一對。」
船上約有三百多個乘客,大家對我們都很客氣。遇到淺灘,我們幫船夫撐篙,在廚房裡,我們幫伙夫切菜,我們幫不識字的人寫家書,還為娛樂大家而歌唱。有時,我身披厚厚的大衣佇立船頭,
任由思潮澎湃。我想到了千古豪傑。在我看來,他們的生命財富直如「一江春水向東流」。我也想到了自己,敢問蒼天,少年心志知多少?
我知道自己是生長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肩頭的擔子是多麼重大!過去兩個月的所見所聞,在我的心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有時,梅梅悄悄地溜到我的身旁,我驕傲地向她傾訴心頭的宏願。她靜靜地聽著,從不插言反對。
「靠緊一點!靠緊一點!」搥胸總愛拿著照相機偷偷地走過來,跟我們開玩笑。他從背後為我們拍了不少照片,像是有意參加攝影比賽似的。我懶得追他,只要求他不要拿這些照片給別人看。
後來,他還是分給大家看了,每張照片上都加了標題,如「他們是誰!」、「船首雙鶴」等等。
梅梅和我特別喜歡在船頭散步,一面作詩吟對。後來,我們還把這些詩合起來,在總部油印出來,題名為《大江東去》。
在南京上岸後,我們立刻坐火車到上海。到處的接待站都關閉了,幸虧二姐有個同學在上海醫學院,我們可以住在男生宿舍。學院在文革期間都停課,醫學院的學生多半回家去了。上海市大街小巷的大字報都在報導發生在上海市的一條大新聞:「工人奪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已經控制了所有的工廠,從廠長和黨書記手裡奪到了大權。在上海逗留的兩天,我們有幾個人到各工廠的工人接待站蒐集資料,並且和工人交談,這才真正相信了有所謂奪權的事。世上每一個鬥爭的目的不是都在於爭奪政治大權嗎?
這時,我們開始擔心家鄉的情況。強大無比的工人組織在上海市聯合力量完成了奪權大業,這次行動被稱為「一月風暴」,受到了官方刊物的一致讚揚。現在,報紙上的社論公開號召紅衛兵聯合起來,肩負起奪權的重大任務。我們在回福州的旅途中,整整兩天兩夜都在討論這個新的發展。在我們看來,這似乎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們只在福州市做了短暫的停留,可是對八-二九總部的改變卻非常驚訝。頭頭們已經鬆懈了戰鬥精神,變得散漫而又沉溺於物質享受,有許多人已經不再自己出馬指揮鬥爭了,不是坐在辦公室裡,就是開車到軍營去打乒乓球、籃球,或看免費電影。自從把葉飛日記的摘要交給韓先楚後,八-二九和軍方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八-二九的頭頭們似乎只有興趣和軍區司令部的重要官員打交道,對下級人員毫不買帳。阿豬更是能自由地出入軍營。
後來證明八-二九總部這時的鬆懈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前福州市紅衛兵總部的分子(不論是否已經倒戈到八-二九)和前工人赤衛隊一同趁此良機,重新爭取到福州群眾的支持,很快地就變成了我們不共戴天的勁敵。
總部的人竟對我們的串連成果絲毫不感興趣,這使我十分生氣。他們才當了半年的紅衛兵,就已經變成了老官僚!
阿豬也很不滿現狀,要求我留下來幫助她整頓組織,把它變成一支新的生力軍。
我說:「我太想家了,也太累,無論如何都得回去。」
福州市的一位忠實戰友悄悄遞給我幾封由廈門來的信件和電報,都是打聽我們的消息的,並表示廈門極需要我們回去。這些信大都是大塊頭和廈大紅衛兵獨立團的頭頭們寫的。
阿豬很失望,我們兩人第二次大吵了一頓。我對她說,我如果留下,會把蝨子傳遍交際處。一路上,我已經不知不覺地沾到了這些小害蟲。
阿豬抓來一瓶噴霧殺蟲劑,假裝要替我消毒。「你非留在福州不可!福州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
「福州會要我的命!要我的命!要我的命!」
她沒有辦法,只好開吉普車把我送到火車站(為了表示不再腐化,所以這次沒開轎車)。
在火車上,我像個大痲瘋似的,命令所有的同伴離我遠一點,不要和我同坐一張座位,也不要碰我,免得被我傳染到。
梅梅覺得我有神經病,即使有了蝨子,也不值得這麼大驚小怪。下了火車,我命令大家坐公共汽車回家,自己穿小巷徒步回去。我最大的恐懼是怕碰見熟人。天氣並不冷,我還是用圍巾把臉圍住,只露出兩隻眼睛。
母親來開門,她向我衝過來。我連忙轉開:「不要碰我!我有蝨子!大概已經很多了!有五六天了!」
天呀,真是滑稽!我把纏上我的小腿的貓兒一腳踢開,衝進院子,剝下了軍用大衣、制服、毛衣、內衣和棉褲,叫喊母親:「快拿熱水來!把這些可惡的蝨子燙死!」說著就抓起肥皂和杓子,舀了冰冷的井水往身上澆,洗將起來,沖洗了好幾次才罷手。我居然也會有蝨子!
母親、正在午睡的二哥、三姐和小貓統統跑來瞪著我看。
「我沒怎麼樣,也不是發了神經!等我打開箱子給你們看,我給每個人都帶了禮物。」
洗完澡後,我回到房裡,穿上幾件衣服,就打開了行李,亮出禮物。
母親摸摸我的頭說:「傻孩子,為什麼買這麼多東西?媽什麼也不要,只要你回來,答應媽再也不出門了,好不好?」
「我保證再也不出門了。」
「瘦了這麼多!」
「也許是蝨子吸了我太多的血。」
母親跳了起來:「想吃什麼?媽馬上去買。真是巧,你走的那天我正好休假,今天你回來了,我又休假!」
「我只想睡一覺,」我說:「蝨子咬得我好幾夜沒睡好。」
「那就睡在我的床上吧。枕頭套和被單都是新換的,而且比較暖和。」
我鑽進被窩裡,真是舒服極了!我環住母親的脖子,在她的額上輕輕一吻。她拉下我細瘦的臂膀,蓋好被,用面頰摩摩我的臉說:「乖兒子,快睡吧。」
二哥進來說了聲再見,他要上班去了。我告訴他,晚上要和他長談一次,然後翻了個身沉沉地睡著了。
晚飯後,二哥把我帶進他的書房。我拿出了地圖和照片,鋪了一屋子,連床上都擺滿了。他把炭爐拿進書房說:「你睡了一下午,現在不睏了,談個通宵吧。」突然間,我發覺自己長得好高。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輕鬆自若地和二哥暢談宇宙萬物!
王光美被鬥爭後不久,清華大學舉行了一次大掃除。大字報欄上厚厚的一層紙都被刮了下來,洗刷乾淨,好再貼上新的大字報。象徵王光美末日的標語紙一直都在各大樓的牆壁上隨著寒風飄搖,現在也被清除了。元旦將近,校園各處都洋溢著萬象更新的氣息。
我們幾乎是最後一批離開北京的串連代表。三姐早在十幾天前就回家了,只有二姐含淚在清華園送我。她說她太想念母親了,不久一定會設法回家一次。載我們往火車站的專車,應大家的要求在天安門前停下來。
「請讓我們多拍幾張照片吧!」我說:「我們也許一輩子都不會再來了。」我站在白石橋上,手扶欄杆,心裡想著元旦就要到了,北京的家家戶戶一定都在忙著大掃除和剁豬肉、包餃子。家裡,母親也一定在忙著。
這裡沒有值得我們留連忘返的東西,只有風、沙和商店裡或公共汽車上的人們投來的冷漠眼光。不過,我們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依依不捨。
在聞名的天壇附近的永定門車站上,成千的人在竹棚下等火車。有人等了一天,有人等了好幾天。
我們的火車要到傍晚才來,於是我們決定再進城一次,來一趟告別之遊。我請梅梅一起到一家館子吃烤鴨,她卻急著要回天壇。因此,我們買了一隻烤鴨帶出來,走過天安門前,我面向天安門,手舉烤鴨作道別狀,由梅梅替我拍了一張照(後來,這件事傳到廈門,說我揮烤鴨向北京道別,戰友們都笑我,敵人則藉此攻擊我)。正要上火車之前,我問同伴們敢不敢轉道沿路多看幾個城市,反正已經趕不上回家過元旦了。他們怯怯地回答了一個「好」字。其實,我是要他們陪著我實現自己的願望,因為我想到山西去看大哥。從北京到太原的火車幸好沒有誤點。在火車上的一天一夜裡,我們拚命趕寫串連報告,想在年前把它趕完。我很驕傲地告訴同伴,我們圓滿地完成了五大任務:一、我們在北京完成了革命串連,和北京各校的紅衛兵交換了革命心得、材料和袖章,並且建立了聯繫,一本厚厚的通訊錄就是證據;二、我們見到了毛澤東,雖然沒能拍下照片,每人都在日誌裡記載了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印象和描述;三、我們瞻仰了祖國山河,有許多照片為證;四、我們得到了許多內幕消息,帶回大批材料,同志們看到這些材料,一定會以為是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五、我們接觸過外國人,並且參加了一次國際行動─也就是鬥爭過外國人,更改過路名(這最後一項工作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不過總部可能不覺得有趣)。
我沒有把自己的私人任務─會見家人列入其內。
結帳時,我發現我們差不多花光了整整人民幣一千元的公款,剩下的只有兩百元左右;而核對所有的發票以後,發現比原數又少了十塊錢,梅梅、搥胸和我分攤了這個差額。
然後我們拿出所有購買的東西來看,其中有給同學、朋友的禮物,給母親的枕頭套、高跟鞋、絲襪和化妝品,給二哥買的地圖。我自己帶出來的一百二十元已花掉將近一百元,大姐和二姐為我花的錢還沒算在內,何況來往的車費和在清華的吃住都不是自己負擔的。
到了太原後,看到街上有許多人在辦年貨,像我們這樣身背行囊的紅衛兵不多。我們又像叫化子一樣,心裡難免窘怕。接待站人員發現我們故意繞道回家時,幾乎不肯負責我們的吃住。
我實在不忍心把同伴們丟在嚴寒的太原,可是又捨不得錯過見大哥的機會,只好託搥胸代為照顧其他同伴,自己一人到了大哥家。
大哥有個溫暖的小家庭─一個賢妻和兩個寶寶,一男一女。他們遠在北方安家,真叫人惋惜(我趕緊寫信給母親,叫她千萬不要來了,這地方的寒冷不是她受得了的)。
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把兩個小孩送到南方去由母親扶養。只要家庭環境過得去,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都設法把孩子送回南方家中去撫養。按照規定,已婚的外地工作人員不能請假返鄉探望父母,大哥沒有辦法親自送孩子回去。他一直在打聽鐵路局能不能把一個四歲和一個兩歲的孩子代送回去。他說曾經看過一部叫作《蘭蘭和冬冬》的電影,片中兩個小孩單獨從上海旅行到北京去找爸爸、媽媽,一路上受到了鐵路員工的熱心照顧。顯然,大哥還不知道現在的火車交通亂成什麼樣子。其實,大哥、大嫂並不願意和孩子分離。可是兩個人都要上班,北方的教育、育兒設備和衛生都很差,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女長得像北方小孩一樣愚蠢又粗魯。
母親也早就想含飴弄孫了。她計劃在退休後到全國各地走走,順便把大哥的孩子和大姐、二姐將來的孩子帶回來,在家裡開起自己的托兒所。可是,這場破壞她計劃的文化大革命到現在都還沒有收場的意思。
我哀求大哥、大嫂讓我負責把兩個娃娃帶回去,相信梅梅和其他同伴一定會喜歡這兩個小東西。
大哥苦笑道:「你連自己都照顧不來呢,自己都還是孩子,怎麼能帶兩個小小孩?媽寫過信來說你愛哭,沒有責任感,她還得成天跟在你的後面呢。」
「那些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我長大了,又是紅衛兵頭頭。我什麼大事都做過,可以獨當一面了!」
儘管我說得舌敝唇焦,也勸不動大哥。
我來訪的最大目的既然失敗,便決定不再逗留,匆匆趕回太原和同伴會面。同伴們離鄉背井,過了個最淒涼的元旦。我從大哥家帶去了許多吃的,總算讓大家享受了一頓遲來的盛宴。
我們繼續向南走,到了西安。這是一個大而不熱鬧的城市,在這裡停留了一天多一點。西安市的市民隨地吐痰的習慣實在可怕,弄得到處是痰。我們嘗了當地的名食─羊肉泡饃,吃過後卻是好久都還覺得不舒服。我們本來想參觀全國最大的飛機場,臨時改變了主意,昏昏沉沉地上了火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這列火車走的方向不對!
最後,我們在中國的石油中心蘭州市下了火車。這列火車是一直開往新疆的,寒冷的天氣使我們卻步了。我們在蘭州市過了一天,唯一的收穫是買到了每公斤人民幣五角六分的牛肉乾,這個價錢是我們家鄉的十分之一。我們買了一大包,夾在饅頭裡吃,真是痛快極了。可是,同車的乘客對我們說,脫水牛肉沒有什麼營養。
在河南省鄭州換上京廣線的火車後,我們的心情都安定了不少。河南的食品便宜得驚人,蒸雞一斤五角錢,還有五香豆腐乾、蘋果和梨等,我們便大享了口福。
火車一點也不擠,一路上很少遇見串連的紅衛兵。這一次,途中也沒有乞丐搗亂。串連已經過去,火車站的軍人又可以有效地維持秩序了。
我們請隨車服務人員來分享食物,和我們聊天,除了火車司機和司爐外,幾乎人人都來吃我們的牛肉乾,看看我們的東西,聽聽我們的故事。到了漢口,聽接待人員說接待站過兩天就要關閉了,關閉以後,我們就得自己負責吃住。一驚之下,我們匆匆在全國最長的長江大橋上拍了幾張照,就登上了宜昌號汽船順流而下,前往南京,全程費時三天。
這三天裡,梅梅每天都起個絕早,跑到船頭去唱西藏民謠和各地的民謠。有一天,她以為四下無人,脫下了軍用大衣,握著拳頭,引吭高歌起來,似乎渾然忘卻了腳下的滔滔江水。
我想從背後給她偷拍一張照片。「小心別翻下去,不要受涼了。」我拾起甲板上的大衣,抖抖灰,給她披上。我說:「妳唱得真好,三山五嶽都要向妳俯首稱臣,長流的江水也要向妳致敬了!」她羞得直要掐我的手。後面有人大叫:「跳進長江游泳吧!你們真是天生的一對。」
船上約有三百多個乘客,大家對我們都很客氣。遇到淺灘,我們幫船夫撐篙,在廚房裡,我們幫伙夫切菜,我們幫不識字的人寫家書,還為娛樂大家而歌唱。有時,我身披厚厚的大衣佇立船頭,
任由思潮澎湃。我想到了千古豪傑。在我看來,他們的生命財富直如「一江春水向東流」。我也想到了自己,敢問蒼天,少年心志知多少?
我知道自己是生長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肩頭的擔子是多麼重大!過去兩個月的所見所聞,在我的心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有時,梅梅悄悄地溜到我的身旁,我驕傲地向她傾訴心頭的宏願。她靜靜地聽著,從不插言反對。
「靠緊一點!靠緊一點!」搥胸總愛拿著照相機偷偷地走過來,跟我們開玩笑。他從背後為我們拍了不少照片,像是有意參加攝影比賽似的。我懶得追他,只要求他不要拿這些照片給別人看。
後來,他還是分給大家看了,每張照片上都加了標題,如「他們是誰!」、「船首雙鶴」等等。
梅梅和我特別喜歡在船頭散步,一面作詩吟對。後來,我們還把這些詩合起來,在總部油印出來,題名為《大江東去》。
在南京上岸後,我們立刻坐火車到上海。到處的接待站都關閉了,幸虧二姐有個同學在上海醫學院,我們可以住在男生宿舍。學院在文革期間都停課,醫學院的學生多半回家去了。上海市大街小巷的大字報都在報導發生在上海市的一條大新聞:「工人奪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已經控制了所有的工廠,從廠長和黨書記手裡奪到了大權。在上海逗留的兩天,我們有幾個人到各工廠的工人接待站蒐集資料,並且和工人交談,這才真正相信了有所謂奪權的事。世上每一個鬥爭的目的不是都在於爭奪政治大權嗎?
這時,我們開始擔心家鄉的情況。強大無比的工人組織在上海市聯合力量完成了奪權大業,這次行動被稱為「一月風暴」,受到了官方刊物的一致讚揚。現在,報紙上的社論公開號召紅衛兵聯合起來,肩負起奪權的重大任務。我們在回福州的旅途中,整整兩天兩夜都在討論這個新的發展。在我們看來,這似乎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們只在福州市做了短暫的停留,可是對八-二九總部的改變卻非常驚訝。頭頭們已經鬆懈了戰鬥精神,變得散漫而又沉溺於物質享受,有許多人已經不再自己出馬指揮鬥爭了,不是坐在辦公室裡,就是開車到軍營去打乒乓球、籃球,或看免費電影。自從把葉飛日記的摘要交給韓先楚後,八-二九和軍方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八-二九的頭頭們似乎只有興趣和軍區司令部的重要官員打交道,對下級人員毫不買帳。阿豬更是能自由地出入軍營。
後來證明八-二九總部這時的鬆懈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前福州市紅衛兵總部的分子(不論是否已經倒戈到八-二九)和前工人赤衛隊一同趁此良機,重新爭取到福州群眾的支持,很快地就變成了我們不共戴天的勁敵。
總部的人竟對我們的串連成果絲毫不感興趣,這使我十分生氣。他們才當了半年的紅衛兵,就已經變成了老官僚!
阿豬也很不滿現狀,要求我留下來幫助她整頓組織,把它變成一支新的生力軍。
我說:「我太想家了,也太累,無論如何都得回去。」
福州市的一位忠實戰友悄悄遞給我幾封由廈門來的信件和電報,都是打聽我們的消息的,並表示廈門極需要我們回去。這些信大都是大塊頭和廈大紅衛兵獨立團的頭頭們寫的。
阿豬很失望,我們兩人第二次大吵了一頓。我對她說,我如果留下,會把蝨子傳遍交際處。一路上,我已經不知不覺地沾到了這些小害蟲。
阿豬抓來一瓶噴霧殺蟲劑,假裝要替我消毒。「你非留在福州不可!福州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
「福州會要我的命!要我的命!要我的命!」
她沒有辦法,只好開吉普車把我送到火車站(為了表示不再腐化,所以這次沒開轎車)。
在火車上,我像個大痲瘋似的,命令所有的同伴離我遠一點,不要和我同坐一張座位,也不要碰我,免得被我傳染到。
梅梅覺得我有神經病,即使有了蝨子,也不值得這麼大驚小怪。下了火車,我命令大家坐公共汽車回家,自己穿小巷徒步回去。我最大的恐懼是怕碰見熟人。天氣並不冷,我還是用圍巾把臉圍住,只露出兩隻眼睛。
母親來開門,她向我衝過來。我連忙轉開:「不要碰我!我有蝨子!大概已經很多了!有五六天了!」
天呀,真是滑稽!我把纏上我的小腿的貓兒一腳踢開,衝進院子,剝下了軍用大衣、制服、毛衣、內衣和棉褲,叫喊母親:「快拿熱水來!把這些可惡的蝨子燙死!」說著就抓起肥皂和杓子,舀了冰冷的井水往身上澆,洗將起來,沖洗了好幾次才罷手。我居然也會有蝨子!
母親、正在午睡的二哥、三姐和小貓統統跑來瞪著我看。
「我沒怎麼樣,也不是發了神經!等我打開箱子給你們看,我給每個人都帶了禮物。」
洗完澡後,我回到房裡,穿上幾件衣服,就打開了行李,亮出禮物。
母親摸摸我的頭說:「傻孩子,為什麼買這麼多東西?媽什麼也不要,只要你回來,答應媽再也不出門了,好不好?」
「我保證再也不出門了。」
「瘦了這麼多!」
「也許是蝨子吸了我太多的血。」
母親跳了起來:「想吃什麼?媽馬上去買。真是巧,你走的那天我正好休假,今天你回來了,我又休假!」
「我只想睡一覺,」我說:「蝨子咬得我好幾夜沒睡好。」
「那就睡在我的床上吧。枕頭套和被單都是新換的,而且比較暖和。」
我鑽進被窩裡,真是舒服極了!我環住母親的脖子,在她的額上輕輕一吻。她拉下我細瘦的臂膀,蓋好被,用面頰摩摩我的臉說:「乖兒子,快睡吧。」
二哥進來說了聲再見,他要上班去了。我告訴他,晚上要和他長談一次,然後翻了個身沉沉地睡著了。
晚飯後,二哥把我帶進他的書房。我拿出了地圖和照片,鋪了一屋子,連床上都擺滿了。他把炭爐拿進書房說:「你睡了一下午,現在不睏了,談個通宵吧。」突然間,我發覺自己長得好高。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輕鬆自若地和二哥暢談宇宙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