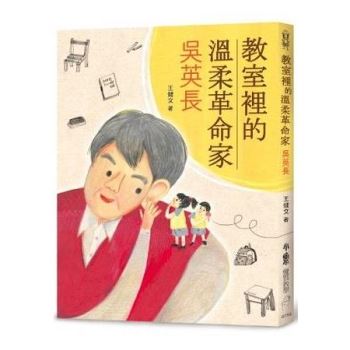第四章 教室裡的森林小學
從人權的意義中,我們曾導出個人有無上的價值。人就是人,應被當作人看待。由此我們強調「自尊尊人」的道德信條,所謂「自尊尊人」,就是尊重自己是個「人」,也尊重他人是個「人」。此信條之奉行,只有表現在日常行動上,才最為徹底,最為貼切。
吳英長,〈教育與人權〉,《杏壇》,1970年5月20日
教學是說服
比巫美韻晚了四年,72級的楊怡靜、范信賢曾經質疑吳老師的一句話:
老師以前常會說:「教學是一種說服的藝術。」有一陣子,我們會跟老師說:「『說服』太具有壓迫性了,我們比較喜歡把教學當做是一種『分享』的過程,就是在教學過程中開創更多孩子可以教我們的機會,和孩子們相互學習、溫馨陪伴。」老師聽了,他總是沈思一下,又無言的再露出微笑。
吳老師在1997年發表的一篇〈感性理性話實習〉的最後一段,後來在他所留下的檔案中,又以「教學是說服?!」為題獨立徵引,他說:
「小子難纏」影片第一集,空手道師傅宮城在教男主角丹尼爾空手道之前,先約法三章的說:「你想學,我負責把你教會,但是我要你做什麼,你不要問。」然後就提了兩桶水和抹布,要他先洗車子。丹尼爾一臉錯愕和狐疑,正要開口問為什麼,就被宮城「你不是答應了嗎?」給擋了回去。
我帶實習喜歡用這個故事做開場白,因為我碰到最大的致命傷就是懷疑。懷疑表示不信任師傅的安排,不信任就不會盡力去學習。這幾屆剛開始上課時,學生都會戴著懷疑的眼鏡:「我的小學老師不是這樣教的,小朋友可能這樣學嗎?」「以前沒有人這樣教我,我還不是活得好好的!」我知道這是長期以來,從來就沒有被人好好的以精緻教學服務過,而產生的不信任。如果他們再被要求而難以適應時,原先的懷疑就變成憤怒,然後躲進烏龜殼內生悶氣,碰到有人掀起怨氣,就跟著起舞!很多時候,我也無法倖免捲入怨氣中,跟著一起生氣!
我知道說服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相信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以感性接納他們不滿的情緒,以浪漫撤除他們防衛的藩籬之外,還要以理性肯定他們的經驗,以意志要求他們細部施工,並給予充份的信任。73級的邱耀平說:「老師的堅持本身就是成功的最大保證,讓我們打從心底說出:『我願意』!」「教學是說服?!」的標題很有趣,一個問號、一個感嘆號。問號是對學生的尊重,保留自己見解可修正的彈性;感嘆號是反思之後的堅持,吳老師依然認為「教學是說服」。
「教學」若只是「分享」,當然如朗朗乾坤,一切分明;「教學」若只需「分享」,自然如推門見月,花好月圓。吳老師的微笑不語,一方面肯定學生說的當然是對的,教學當然是「分享」;另方面是證道之言,教學的實踐常常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分享」。
就好像「收服」,「建立關係」之後相得於心,但「建立關係」的過程卻可能百折千迴。
溫美玉很直率地說,並不是每個學生都喜歡吳老師:
他就沒有辦法達到每個人都喜歡他,比如說學生第一個就不喜歡他了,很多學生是會不喜歡他的,因為他的要求太嚴格了。「你為什麼不要像別的老師就跟我做朋友,讓我覺得很快樂?」到最後就像你說的,當初我好喜歡的老師,為什麼當我回頭去看他的時候,他怎麼不像我想像中的那個樣子?可是有些老師就像美酒一樣,越陳越香,吳老師就是這種人。
81級的李俊泰回憶大二上「教育心理學」一開始的感覺:
當時我實在不喜歡上老師的課,因為覺得吳老師跟其它老師相比較,作業多、要求多、此外又不會說笑話,再加上吳老師平常都不茍言笑,很多同學都蠻排斥。……
但是久而久之,李俊泰漸漸能夠聽得懂吳老師在說些什麼。之後又還修了吳老師的「創造力與特殊才能」、「課程與教學」、「認知心理學」。他自承,尤其是「後設認知」對自己影響很大,從吳老師那裏學到:
人的思考不要只有水平思考,不只要「向前看」,更要「向後看、向左看、向右看、向上看、向下看……」,鼓勵我們要「眼看四方、耳聽八方」,使我知道書本的知識是死的、能靈活運用才是真學問。
92級的楊弼涵,記得大四那年的實習課,「老師第一堂課就宣示了,要給我們別的地方學不到的、別人不會教的。」楊弼涵接著回顧那一門實習課:老師帶給我們的觀念,讓我們對一個小學老師的專業有了極深的認識。他讓我們見樹又見林,所以我們沒有迷失在教案設計、試教的花俏道具和教師甄試的紛紛擾擾裡。這一年的時光,老師給了我們最好的薰陶,每週五的早上,我們總是帶著整整兩堂課的充足下課。老師一再告訴我們這些知識的重要,這些觀念的可貴,因此當時的我,每次離開課堂,遇到另外一班的同學,心裡總是帶了幾份驕傲。當有人著急別班做了什麼什麼,而我們班卻都沒有時,老師也會安撫我們的情緒,並帶著一絲優越感的說:「不必急,我們要先做重要的事」。
楊弼涵被吳老師收服了,「別的地方學不到的、別人不會教的」,學生若接受了,對「別的地方學的我們卻學不到,別人覺得不必教的,我們卻在學。」這樣的「不從眾」,便不致感到焦慮,反倒對自己所做的事,帶著一種「我們要先做重要的事」的自豪。
但是,這麼多的學生,是被收服的多?還是未收服的多?是認知正在做「重要的事情」的多?還是為了總是做「別人不做的事」、或是沒做「別人都做的事」而感到焦慮的多?
也許每個人的觀察不同吧?我總覺得美玉的觀察可能比較接近真實。唐忠義也告訴我:「上他的課,很多人不喜歡他。」因為「他口語表達不佳,加上課業的要求觸角很廣,如果你沒辦法接納他時,會覺的他給的是一份寫不完的功課。」
在一篇1980初期東師學生訪談吳老師的文章中,作者詹淑惠有著生動的描述與對話:
上過吳老師教育史的學,大部分都會覺得壓力很大,怎麼會有這麼與眾不同的教法呢?曾有一位學妹告訴我:「上了吳老師兩節的教育史,睡了三四天覺也補不回來。」……
「學生這麼害怕教育史,老師您有什麼感想?」
「平常上課學生都能接受,但一到考試就會怕。……現在很多學生畢業出去,連基本能力都沒有,這樣如何能教給小朋友東西呢?……所以我在不得已之下採取強硬手段。我這麼做的原因,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也知道該怎麼來做;因此,在要求上,我有理由說,學生須經過這樣的訓練。」……
「從六十八年第一次教教育史開始,發現學生讀文章有點問題,學生也覺得不對勁;但雙方又不知道問題出於那裡,總覺得沒有辦法突破,搞得雙方都很痛苦。直到第二年的第二學期,才發現癥結出在讀書方法。」……「第三年上課,則開始講述讀書的方法。可是同學不能了解我的用意,認為怎麼不是在講教育史。後來我先撥一部分時間講讀書方法,在講教育史的內容。雖然學生的壓力很大,但基本能力我必須教給學生。」
接著淑惠大膽地問:
「如果將來證明教法失敗,則應如何呢?」
吳老師瞪大眼睛看我,似乎我的問題很突然。當然,這是由於吳老師對這方面有信心。老師笑著說:
「果真有這麼一天……」
似乎很難回答,讓我不忍心問此問題,沒想到老師幽默的說句:「但願沒有這麼一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害我剛才好緊張。
「我會詳細探討教材,並從理論中尋找實際,避免自己流於獨斷,在衡量學生的程度來做決定。」(詹淑惠,〈一位堅定教育信念的老師:訪吳英長老師〉)
閱讀淑惠的訪談,吳老師在臺東教學生涯初期的困思衡慮,以及與學生之間的磨合,頓時出現了鮮活的畫面。我也才想起,1979年吳老師給我的一封短簡上說的是什麼:
這幾天計畫怎樣,有無興趣來臺東聊聊。學期將結束之前,才發現有跟學生強調基本的思考訓練之必要。
記得在臺北借了您一本何秀煌的「思想的方法」,不知您放在那兒,如放在學校,寒假過後回臺北才寄來。(吳老師書信1979年1月27日)
對於如何「說服」學生?吳老師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焦慮吧!
教學即輔導
吳老師就讀政大教育所博士班時的同學林清財,曾經在帶領一班數學教育系四年級學生的教育實習課,外埠參觀,路經臺東時,吳老師利用晚上時間,特別為這班外校的學生上了一堂「成為教師」的課程。雖然是博士班老同學,林清財卻只是第一次見識吳老師的教學現場。一開始不免擔心:
當時,我們全體師生白天玩累了,剛用過晚餐,正是肚皮飽眼皮鬆時刻,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下可慘了,學生們一定會向英長老師行周公禮。學生們漫不經心地走進圖書館,只見英長老師不慌不忙地為學生們泡茶、泡咖啡……,然後發下一份東師學生的〈我的教育信念〉讓學生們閱讀,接著彼此分享、討論,最後英長老師以英文歌曲“Let it be”,來詮釋生命的傳承。兩個多小時下來,學生們不但沒睡著,相反的,他們的眼睛亮了,學生們熱烈討論……,欲罷不能,要不是夜已深了,他們是不想回旅館休息。此後,在車上,回學校後,學生們持續討論著、思考著如何成為一位教師,是英長老師點燃了他們的生命力。
2003年,林清財在主持嘉義大學輔導學系系務時,吳老師已退休,力邀吳老師遠道嘉義兼課,擔任一班大四的「教學即輔導」和一班大一的「教育心理學」兩門課程。其中教育心理學本是吳老師的拿手課程,大四的「教學即輔導」卻讓林清財也開了眼界。在教學構想中,吳老師明白闡釋「教學即輔導」的意涵:
教學與輔導在實務中被視為無交集。本課程基於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理論,思考教師如何將輔導落實於教學情境中,即在教室當下(Now and Here)完成輔導的功能。因為教學現場有兩大主軸線:教材開展與人際互動,所以在實際教學情境中,教師會先建立教材開展的主軸線,做為另一主軸線人際互動的基礎,然後由活絡的人際網路,將教室塑造為師生共同成長的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
本課程講授的具體作法,是透過文學作品,抽出教學即輔導的重要概念,使學生在教學現場中,除了認識個人的教學信念和教師思考歷程以外,還能觸發個人生命中的內在體驗,做為將來如何展現教學生命力的準備。
吳老師的學生朗朗上口他的一句名言:「好的教學,沒有教室管理的問題」。77級的陳雅鈴更完整地轉述吳老師的話:
教學即輔導。在教學當下,同時完成教學與輔導的功能,也就是好的教學,就沒有教室管理的問題,因為透過教學,同時可以達成行為和心理的輔導。學生忙於學習,問題行為自然減少,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常規管理,進而形成新的優質班級文化。
陳雅鈴也自我剖白,「在修習老師的課程中,讓我內心潛藏的那個脆弱受傷的小孩,感受到被了解、尊重和肯定,漸漸地學會勇敢和獨立,學會轉化負面的情緒成為成長的力量,建立正向積極的自我形象。」88級的柯慧儀深深記得當年的感動:
還記得第一次上你的課,你說︰「一個老師的成績,要由學生眼睛發亮的程度而定。」那是上大學後,第一次在課堂上,我的眼睛被點亮了。外埠教育參觀時,你說︰「開放教育是讓孩子對自己的經驗開放……,使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在受教過程,常常無法肯定自己的我,頓時落淚。
93級的李衿綺則說:「父母給了我生命,然而是您讓我覺得自己重要。」
吳老師最能打動人的地方,是他讓每個學生找到那條通往自己的道路,因而建立的自己的尊嚴。
「教學即輔導」既然要「將教室塑造為師生共同成長的學習社群」,那麼,除了引領學生反思自己的生命經驗,得到昇華的力量外,教師也可能走在與學生同樣的路上。
吳老師曾經在評論一個教學案例時,對於教師對著學生告白自己成長中存在的陰暗記憶時,教師與學生共同得到成長。他說:
在讀書治療的過程中,師生攜手進入作品所描繪的世界,一起解讀自己生命經驗的陰暗面。整個過程師生的人格交互輝映,雙方彼此扶持,不必擔心自我袒露會帶來任何不愉快的壓力。在教室裡,進行著「生命力的激盪」,師生因而得以共同成長,原來教學是可以達到這般的境界!……這讓我想到「教學即輔導」這個概念,透過教學進行輔導,期對象不只限於學生,也應包括教師在內。
吳老師進一步闡釋「為己教學」的深刻意義,因為教學者不只是引導學生找到那條「通往自己的道路」,同時教師自己也在尋找「成為自己」的道路: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兩個對比的概念可以進一步延伸成:「為人教學」和「為己教學」。我們認為教學不只要「為人」,點化別人,更要「為己」,造就自己。「為己」是「為人」的前提,所謂己立而後可以立人,己達而後可以達人。「為人教學」是指教師在傳授知識和解除困惑時,提攜和啟迪後進。學生後來的成就或可榮耀教師,但那終究是「為人作嫁衣裳」。對教師「成為一個人」來說,還是難免有些遺憾!「為己教學」是透過教學去探討個人內在的生命體驗,也就是教師要不斷地從教學現場進行自覺反省,為自己樹立內在的楷模,成就自己的專業能力和道德人格。(吳英長,〈燃起教室的生命力〉,收入:《深入教學現場》)
老少擺渡人的寓言,說的不正是這樣的故事嗎?
從人權的意義中,我們曾導出個人有無上的價值。人就是人,應被當作人看待。由此我們強調「自尊尊人」的道德信條,所謂「自尊尊人」,就是尊重自己是個「人」,也尊重他人是個「人」。此信條之奉行,只有表現在日常行動上,才最為徹底,最為貼切。
吳英長,〈教育與人權〉,《杏壇》,1970年5月20日
教學是說服
比巫美韻晚了四年,72級的楊怡靜、范信賢曾經質疑吳老師的一句話:
老師以前常會說:「教學是一種說服的藝術。」有一陣子,我們會跟老師說:「『說服』太具有壓迫性了,我們比較喜歡把教學當做是一種『分享』的過程,就是在教學過程中開創更多孩子可以教我們的機會,和孩子們相互學習、溫馨陪伴。」老師聽了,他總是沈思一下,又無言的再露出微笑。
吳老師在1997年發表的一篇〈感性理性話實習〉的最後一段,後來在他所留下的檔案中,又以「教學是說服?!」為題獨立徵引,他說:
「小子難纏」影片第一集,空手道師傅宮城在教男主角丹尼爾空手道之前,先約法三章的說:「你想學,我負責把你教會,但是我要你做什麼,你不要問。」然後就提了兩桶水和抹布,要他先洗車子。丹尼爾一臉錯愕和狐疑,正要開口問為什麼,就被宮城「你不是答應了嗎?」給擋了回去。
我帶實習喜歡用這個故事做開場白,因為我碰到最大的致命傷就是懷疑。懷疑表示不信任師傅的安排,不信任就不會盡力去學習。這幾屆剛開始上課時,學生都會戴著懷疑的眼鏡:「我的小學老師不是這樣教的,小朋友可能這樣學嗎?」「以前沒有人這樣教我,我還不是活得好好的!」我知道這是長期以來,從來就沒有被人好好的以精緻教學服務過,而產生的不信任。如果他們再被要求而難以適應時,原先的懷疑就變成憤怒,然後躲進烏龜殼內生悶氣,碰到有人掀起怨氣,就跟著起舞!很多時候,我也無法倖免捲入怨氣中,跟著一起生氣!
我知道說服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相信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以感性接納他們不滿的情緒,以浪漫撤除他們防衛的藩籬之外,還要以理性肯定他們的經驗,以意志要求他們細部施工,並給予充份的信任。73級的邱耀平說:「老師的堅持本身就是成功的最大保證,讓我們打從心底說出:『我願意』!」「教學是說服?!」的標題很有趣,一個問號、一個感嘆號。問號是對學生的尊重,保留自己見解可修正的彈性;感嘆號是反思之後的堅持,吳老師依然認為「教學是說服」。
「教學」若只是「分享」,當然如朗朗乾坤,一切分明;「教學」若只需「分享」,自然如推門見月,花好月圓。吳老師的微笑不語,一方面肯定學生說的當然是對的,教學當然是「分享」;另方面是證道之言,教學的實踐常常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分享」。
就好像「收服」,「建立關係」之後相得於心,但「建立關係」的過程卻可能百折千迴。
溫美玉很直率地說,並不是每個學生都喜歡吳老師:
他就沒有辦法達到每個人都喜歡他,比如說學生第一個就不喜歡他了,很多學生是會不喜歡他的,因為他的要求太嚴格了。「你為什麼不要像別的老師就跟我做朋友,讓我覺得很快樂?」到最後就像你說的,當初我好喜歡的老師,為什麼當我回頭去看他的時候,他怎麼不像我想像中的那個樣子?可是有些老師就像美酒一樣,越陳越香,吳老師就是這種人。
81級的李俊泰回憶大二上「教育心理學」一開始的感覺:
當時我實在不喜歡上老師的課,因為覺得吳老師跟其它老師相比較,作業多、要求多、此外又不會說笑話,再加上吳老師平常都不茍言笑,很多同學都蠻排斥。……
但是久而久之,李俊泰漸漸能夠聽得懂吳老師在說些什麼。之後又還修了吳老師的「創造力與特殊才能」、「課程與教學」、「認知心理學」。他自承,尤其是「後設認知」對自己影響很大,從吳老師那裏學到:
人的思考不要只有水平思考,不只要「向前看」,更要「向後看、向左看、向右看、向上看、向下看……」,鼓勵我們要「眼看四方、耳聽八方」,使我知道書本的知識是死的、能靈活運用才是真學問。
92級的楊弼涵,記得大四那年的實習課,「老師第一堂課就宣示了,要給我們別的地方學不到的、別人不會教的。」楊弼涵接著回顧那一門實習課:老師帶給我們的觀念,讓我們對一個小學老師的專業有了極深的認識。他讓我們見樹又見林,所以我們沒有迷失在教案設計、試教的花俏道具和教師甄試的紛紛擾擾裡。這一年的時光,老師給了我們最好的薰陶,每週五的早上,我們總是帶著整整兩堂課的充足下課。老師一再告訴我們這些知識的重要,這些觀念的可貴,因此當時的我,每次離開課堂,遇到另外一班的同學,心裡總是帶了幾份驕傲。當有人著急別班做了什麼什麼,而我們班卻都沒有時,老師也會安撫我們的情緒,並帶著一絲優越感的說:「不必急,我們要先做重要的事」。
楊弼涵被吳老師收服了,「別的地方學不到的、別人不會教的」,學生若接受了,對「別的地方學的我們卻學不到,別人覺得不必教的,我們卻在學。」這樣的「不從眾」,便不致感到焦慮,反倒對自己所做的事,帶著一種「我們要先做重要的事」的自豪。
但是,這麼多的學生,是被收服的多?還是未收服的多?是認知正在做「重要的事情」的多?還是為了總是做「別人不做的事」、或是沒做「別人都做的事」而感到焦慮的多?
也許每個人的觀察不同吧?我總覺得美玉的觀察可能比較接近真實。唐忠義也告訴我:「上他的課,很多人不喜歡他。」因為「他口語表達不佳,加上課業的要求觸角很廣,如果你沒辦法接納他時,會覺的他給的是一份寫不完的功課。」
在一篇1980初期東師學生訪談吳老師的文章中,作者詹淑惠有著生動的描述與對話:
上過吳老師教育史的學,大部分都會覺得壓力很大,怎麼會有這麼與眾不同的教法呢?曾有一位學妹告訴我:「上了吳老師兩節的教育史,睡了三四天覺也補不回來。」……
「學生這麼害怕教育史,老師您有什麼感想?」
「平常上課學生都能接受,但一到考試就會怕。……現在很多學生畢業出去,連基本能力都沒有,這樣如何能教給小朋友東西呢?……所以我在不得已之下採取強硬手段。我這麼做的原因,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也知道該怎麼來做;因此,在要求上,我有理由說,學生須經過這樣的訓練。」……
「從六十八年第一次教教育史開始,發現學生讀文章有點問題,學生也覺得不對勁;但雙方又不知道問題出於那裡,總覺得沒有辦法突破,搞得雙方都很痛苦。直到第二年的第二學期,才發現癥結出在讀書方法。」……「第三年上課,則開始講述讀書的方法。可是同學不能了解我的用意,認為怎麼不是在講教育史。後來我先撥一部分時間講讀書方法,在講教育史的內容。雖然學生的壓力很大,但基本能力我必須教給學生。」
接著淑惠大膽地問:
「如果將來證明教法失敗,則應如何呢?」
吳老師瞪大眼睛看我,似乎我的問題很突然。當然,這是由於吳老師對這方面有信心。老師笑著說:
「果真有這麼一天……」
似乎很難回答,讓我不忍心問此問題,沒想到老師幽默的說句:「但願沒有這麼一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害我剛才好緊張。
「我會詳細探討教材,並從理論中尋找實際,避免自己流於獨斷,在衡量學生的程度來做決定。」(詹淑惠,〈一位堅定教育信念的老師:訪吳英長老師〉)
閱讀淑惠的訪談,吳老師在臺東教學生涯初期的困思衡慮,以及與學生之間的磨合,頓時出現了鮮活的畫面。我也才想起,1979年吳老師給我的一封短簡上說的是什麼:
這幾天計畫怎樣,有無興趣來臺東聊聊。學期將結束之前,才發現有跟學生強調基本的思考訓練之必要。
記得在臺北借了您一本何秀煌的「思想的方法」,不知您放在那兒,如放在學校,寒假過後回臺北才寄來。(吳老師書信1979年1月27日)
對於如何「說服」學生?吳老師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焦慮吧!
教學即輔導
吳老師就讀政大教育所博士班時的同學林清財,曾經在帶領一班數學教育系四年級學生的教育實習課,外埠參觀,路經臺東時,吳老師利用晚上時間,特別為這班外校的學生上了一堂「成為教師」的課程。雖然是博士班老同學,林清財卻只是第一次見識吳老師的教學現場。一開始不免擔心:
當時,我們全體師生白天玩累了,剛用過晚餐,正是肚皮飽眼皮鬆時刻,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下可慘了,學生們一定會向英長老師行周公禮。學生們漫不經心地走進圖書館,只見英長老師不慌不忙地為學生們泡茶、泡咖啡……,然後發下一份東師學生的〈我的教育信念〉讓學生們閱讀,接著彼此分享、討論,最後英長老師以英文歌曲“Let it be”,來詮釋生命的傳承。兩個多小時下來,學生們不但沒睡著,相反的,他們的眼睛亮了,學生們熱烈討論……,欲罷不能,要不是夜已深了,他們是不想回旅館休息。此後,在車上,回學校後,學生們持續討論著、思考著如何成為一位教師,是英長老師點燃了他們的生命力。
2003年,林清財在主持嘉義大學輔導學系系務時,吳老師已退休,力邀吳老師遠道嘉義兼課,擔任一班大四的「教學即輔導」和一班大一的「教育心理學」兩門課程。其中教育心理學本是吳老師的拿手課程,大四的「教學即輔導」卻讓林清財也開了眼界。在教學構想中,吳老師明白闡釋「教學即輔導」的意涵:
教學與輔導在實務中被視為無交集。本課程基於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理論,思考教師如何將輔導落實於教學情境中,即在教室當下(Now and Here)完成輔導的功能。因為教學現場有兩大主軸線:教材開展與人際互動,所以在實際教學情境中,教師會先建立教材開展的主軸線,做為另一主軸線人際互動的基礎,然後由活絡的人際網路,將教室塑造為師生共同成長的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
本課程講授的具體作法,是透過文學作品,抽出教學即輔導的重要概念,使學生在教學現場中,除了認識個人的教學信念和教師思考歷程以外,還能觸發個人生命中的內在體驗,做為將來如何展現教學生命力的準備。
吳老師的學生朗朗上口他的一句名言:「好的教學,沒有教室管理的問題」。77級的陳雅鈴更完整地轉述吳老師的話:
教學即輔導。在教學當下,同時完成教學與輔導的功能,也就是好的教學,就沒有教室管理的問題,因為透過教學,同時可以達成行為和心理的輔導。學生忙於學習,問題行為自然減少,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常規管理,進而形成新的優質班級文化。
陳雅鈴也自我剖白,「在修習老師的課程中,讓我內心潛藏的那個脆弱受傷的小孩,感受到被了解、尊重和肯定,漸漸地學會勇敢和獨立,學會轉化負面的情緒成為成長的力量,建立正向積極的自我形象。」88級的柯慧儀深深記得當年的感動:
還記得第一次上你的課,你說︰「一個老師的成績,要由學生眼睛發亮的程度而定。」那是上大學後,第一次在課堂上,我的眼睛被點亮了。外埠教育參觀時,你說︰「開放教育是讓孩子對自己的經驗開放……,使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在受教過程,常常無法肯定自己的我,頓時落淚。
93級的李衿綺則說:「父母給了我生命,然而是您讓我覺得自己重要。」
吳老師最能打動人的地方,是他讓每個學生找到那條通往自己的道路,因而建立的自己的尊嚴。
「教學即輔導」既然要「將教室塑造為師生共同成長的學習社群」,那麼,除了引領學生反思自己的生命經驗,得到昇華的力量外,教師也可能走在與學生同樣的路上。
吳老師曾經在評論一個教學案例時,對於教師對著學生告白自己成長中存在的陰暗記憶時,教師與學生共同得到成長。他說:
在讀書治療的過程中,師生攜手進入作品所描繪的世界,一起解讀自己生命經驗的陰暗面。整個過程師生的人格交互輝映,雙方彼此扶持,不必擔心自我袒露會帶來任何不愉快的壓力。在教室裡,進行著「生命力的激盪」,師生因而得以共同成長,原來教學是可以達到這般的境界!……這讓我想到「教學即輔導」這個概念,透過教學進行輔導,期對象不只限於學生,也應包括教師在內。
吳老師進一步闡釋「為己教學」的深刻意義,因為教學者不只是引導學生找到那條「通往自己的道路」,同時教師自己也在尋找「成為自己」的道路: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兩個對比的概念可以進一步延伸成:「為人教學」和「為己教學」。我們認為教學不只要「為人」,點化別人,更要「為己」,造就自己。「為己」是「為人」的前提,所謂己立而後可以立人,己達而後可以達人。「為人教學」是指教師在傳授知識和解除困惑時,提攜和啟迪後進。學生後來的成就或可榮耀教師,但那終究是「為人作嫁衣裳」。對教師「成為一個人」來說,還是難免有些遺憾!「為己教學」是透過教學去探討個人內在的生命體驗,也就是教師要不斷地從教學現場進行自覺反省,為自己樹立內在的楷模,成就自己的專業能力和道德人格。(吳英長,〈燃起教室的生命力〉,收入:《深入教學現場》)
老少擺渡人的寓言,說的不正是這樣的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