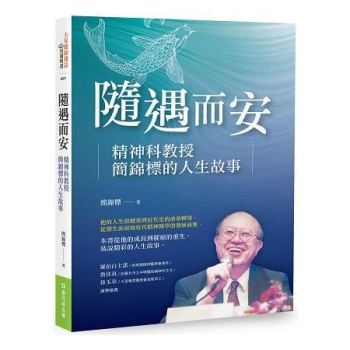端午鯉魚,簡家大孫
日治時期,每年到了5月5日端午節,經常會下雨,而鯉魚有魚躍龍門的典故,這時掛起鯉魚的旗子,便能期望家裡的男孩子可以魚躍成龍,還未有男孩的家庭,也有祈求上天保佑家裡誕生男孩的寓意。因此,端午節也稱為男孩節。
就在這樣一個專屬於男孩的節日,我出生在桃園簡家,當時,男孩節的習俗在臺灣已邁入第三十八個年頭,有男孩的家庭會在屋頂上懸掛鯉魚旗,期許家中的男孩能順利長大、身強體壯。
身為家裡的長孫,祖父對我的期許極高,因為生日在「端午節」,他更加盼望長孫是一個像樣的孩子,能成為男人中的男人,於是便取了「錦標」這個名字,希望我能永遠第一名,拿到競賽中只有冠軍才能擁有的「錦標」。
如果問我,這樣別有深意的名字,到底是壓力,還是一種鼓勵?我想是各有各的好處吧!畢竟從小就背負著家中長輩深深的期望,漸漸地也養成了我不畏懼、勇往直前、努力不懈的個性。
幾乎打從骨子裡,我就是個競爭心很強烈的人,不只怕違背家人的期待,也害怕失敗,這樣的人格特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也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壓力。舉例來說,每當考試成績不在前三名,自己就會覺得心情很差,得失心重,但話說回來,誰又能一輩子,無時無刻都維持在第一名呢?
桃園的老家,位在景福宮旁,景福宮在現在桃園市桃園區,地方習稱大廟,是當地的信仰中心,非常熱鬧。小時候,祖父經常帶我到附近走動散步,這一帶也是童年記憶最深刻的地方。
簡家的興盛從曾祖父一輩開始,曾祖父是清朝時期的秀才,當時為了到臺南參加科舉考試,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用雙腳走了整整一個星期的路。好不容易放榜後,順利當上縣長,分配到一部分的土地,後來租借給佃農,成為地主,但真正的繁華與滄桑卻從祖父開始。
祖父是名教育家,很受當地人敬重。他從當時總督府(現總統府)國語學校畢業後,被分發到桃園國小教書。印象中,他總是穿著一身帥氣的黑色西裝和黑色皮鞋,帶上高高的紳士帽,鄰居的長輩常形容他是一個彬彬有禮的紳士。
讀幼稚園時,他常牽著我的手到大廟附近散步,從景福宮一直走到附近的菜市場,看到他的人,總會微笑和他打招呼:「簡老師,又來散步啦?」小時候的記憶裡,祖父是一位相當受人尊敬的好好先生。當地有人說,桃園簡家不僅算是書香世家,而且還是桃園第一大地主,或許不少人會好奇,一輩子都在教書的祖父,怎麼會成為桃園最大的地主?背後的原因很曲折,可以說,祖父的土地一部分繼承祖產,一部分則是因為一場為友人擔保的意外!
簡家的繁華到祖父的時間,好日子並未過太久,祖父在年輕時,太容易相信人,替朋友作了擔保,結果借錢的朋友落跑了,祖父因此被日本銀行追討,欠了大筆的債務。
在無力償還下,照理說,祖父應該會被宣告破產才對,家裡的土地也會被銀行沒收,拿去抵押還債。但或許是祖父平常為人有品格,受鄉里人敬重,在祖父徬徨、手足無措的時候,銀行經理便向祖父提議,把債務和抵押品由擔保人完全承擔,祖父因此搖身一變,成了坐擁百甲土地的大地主,但同時卻也得扛上這筆龐大的債務。
家中經濟無預警遭逢巨變,祖父不得不省吃儉用,記憶中,家裡的腳踏車永遠都是破破舊舊的。還記得,有一次我洗完手,水龍頭沒鎖緊,祖父就叫我拿一個臉盆,放在滴著水的水龍頭下方接水,接著跟我說,這些水都是要付錢的。甚至有時候忘了關電燈,他也會把我叫回來,提醒我,電也是要錢的。
儘管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幼稚園的孩子,祖父也一再訓誡與提醒。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知道原來東西不是無中生有,是要花錢買的,就像電有電費、水有水費,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理所當然地使用,而是得付出些什麼。
祖父的節省,讓當地不少人感到好奇,有些不是很清楚簡家狀況的人,開始有了閒言閒語,形容祖父是「皇帝命,乞丐身」,現在想想,或許是這種評價,祖父才不想讓外人看輕,刻意注重打扮,總是以一副紳士的模樣見人吧!
一直到祖父過世前,這筆龐大的債務仍未還清,父親繼承祖父的債務,繼續還債給銀行,過著像祖父一樣無比節省的日子。
小時候,母親曾半開玩笑、有點委屈地說,「大家都說你們簡家是桃園第一大地主,誰知道竟然欠了這麼多錢,生活要這麼節儉。」母親的埋怨不是沒有理由,畢竟她出生在富裕人家,父親是臺中前三大地主之一,過去從事建築建設工作,常在日本小社區蓋日式房屋,供日本人居住,現在臺中的大全街,就是以外公的名字命名的。正因如此,從小生長在大戶人家的母親嫁來簡家後,不但無法買新衣服、看電影,還得處處精打細算,心中的委屈和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來我不是日本人?!
我的求學階段,歷經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來臺的轉變。在國小五年級以前,我始終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如果能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會出現如此的認知差距,並不意外。
父親和母親都受過正統的日本教育,父親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念書,不過沒念到畢業就回臺灣相親,與母親結婚。母親雖未像父親留學日本,卻也在臺灣接受日本的高等教育,臺中女中畢業的她,會說一口流利日文,也因此,我一出生,就被父母用日文養大,日語幾乎就是我的母語。
父母非常重視我的教育,深受日本文化洗禮的他們,選了一所幾乎全是日本人的學校。那是一間有幼稚園的國小,國小的校長就是幼稚園的園長,當時臺灣人要進去讀書,很不容易,幾乎是要有家庭背景的人才能進去就讀,其他像警察、老師、醫師的小孩即使有機會進得去,也只能算是有資格拿到入場券,能不能進去就讀,還得通過校長的面試。
記得幼稚園面試那天,母親把我打扮得很規距,看起來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當走進面試的房間時,校長便拿了一顆橘子在我面前晃了兩下,問我這是什麼?也許是要測試我日文好不好?會不會說日文?當時我沒意會過來,只是呆著一張臉、滿臉困惑的看著他,直到校長用臺語說:「柑仔!」,我才豁然開朗的用日語回答:「蜜柑(みかん/發音為mi kann)!」。就這樣因為「蜜柑」,我順利通過面試,開始接受日本教育,與日本人一起念書。
從幼稚園到小學五年級,同學和老師幾乎全是日本人,因為我是少數的臺灣人,難免有點受到歧視,會有感到被歧視的心理反射是當時別的班級,班長都是由成績第一名的同學擔任,但我在班上總是拿第一名,卻沒做過一次班長,就連國小朝會的升旗手,我也沒做過。對從小被祖父灌輸要有榮譽心,好勝心極強的我,一直認為能在朝會時,站在升旗台上升旗,是一種無比榮耀,這個機會通常是各班的班長輪流擔當。有一次班上的班長因為生病臨時請假,無法參加朝會,當時我心裡暗自竊喜,心想終於可以輪到我去代表升旗了。結果,老師卻選了另一個日本同學當升旗手,雖然當時我憤憤不平,但仍無法理解自己與日本人的差別。其實老師當時的動作,都在提醒我是一個被殖民的日本臺灣人,但因為從小的生長環境和教育背景,我當時始終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日本人。
1945年,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小五年級的我,眼看著同學和老師紛紛回日本,心裡莫名惆悵,回家後很認真地問母親:「我們什麼時候也要回日本?」,結果母親正經地告訴我,「你是臺灣人,不用回日本。」當時,我的心中滿是疑問,用美國人最常講的話來形容當時的心情就是:「What happen to me?」這是什麼情況,為何會如此?為何我不用回日本?為此我還悶悶不樂了好一陣子。現在回想當時確實很天真,但在我的認知裡,被教育做為一個日本人是光榮的,會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的觀念竟是如此根深蒂固。
(摘自《隨遇而安》第一部成長)
日治時期,每年到了5月5日端午節,經常會下雨,而鯉魚有魚躍龍門的典故,這時掛起鯉魚的旗子,便能期望家裡的男孩子可以魚躍成龍,還未有男孩的家庭,也有祈求上天保佑家裡誕生男孩的寓意。因此,端午節也稱為男孩節。
就在這樣一個專屬於男孩的節日,我出生在桃園簡家,當時,男孩節的習俗在臺灣已邁入第三十八個年頭,有男孩的家庭會在屋頂上懸掛鯉魚旗,期許家中的男孩能順利長大、身強體壯。
身為家裡的長孫,祖父對我的期許極高,因為生日在「端午節」,他更加盼望長孫是一個像樣的孩子,能成為男人中的男人,於是便取了「錦標」這個名字,希望我能永遠第一名,拿到競賽中只有冠軍才能擁有的「錦標」。
如果問我,這樣別有深意的名字,到底是壓力,還是一種鼓勵?我想是各有各的好處吧!畢竟從小就背負著家中長輩深深的期望,漸漸地也養成了我不畏懼、勇往直前、努力不懈的個性。
幾乎打從骨子裡,我就是個競爭心很強烈的人,不只怕違背家人的期待,也害怕失敗,這樣的人格特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也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壓力。舉例來說,每當考試成績不在前三名,自己就會覺得心情很差,得失心重,但話說回來,誰又能一輩子,無時無刻都維持在第一名呢?
桃園的老家,位在景福宮旁,景福宮在現在桃園市桃園區,地方習稱大廟,是當地的信仰中心,非常熱鬧。小時候,祖父經常帶我到附近走動散步,這一帶也是童年記憶最深刻的地方。
簡家的興盛從曾祖父一輩開始,曾祖父是清朝時期的秀才,當時為了到臺南參加科舉考試,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用雙腳走了整整一個星期的路。好不容易放榜後,順利當上縣長,分配到一部分的土地,後來租借給佃農,成為地主,但真正的繁華與滄桑卻從祖父開始。
祖父是名教育家,很受當地人敬重。他從當時總督府(現總統府)國語學校畢業後,被分發到桃園國小教書。印象中,他總是穿著一身帥氣的黑色西裝和黑色皮鞋,帶上高高的紳士帽,鄰居的長輩常形容他是一個彬彬有禮的紳士。
讀幼稚園時,他常牽著我的手到大廟附近散步,從景福宮一直走到附近的菜市場,看到他的人,總會微笑和他打招呼:「簡老師,又來散步啦?」小時候的記憶裡,祖父是一位相當受人尊敬的好好先生。當地有人說,桃園簡家不僅算是書香世家,而且還是桃園第一大地主,或許不少人會好奇,一輩子都在教書的祖父,怎麼會成為桃園最大的地主?背後的原因很曲折,可以說,祖父的土地一部分繼承祖產,一部分則是因為一場為友人擔保的意外!
簡家的繁華到祖父的時間,好日子並未過太久,祖父在年輕時,太容易相信人,替朋友作了擔保,結果借錢的朋友落跑了,祖父因此被日本銀行追討,欠了大筆的債務。
在無力償還下,照理說,祖父應該會被宣告破產才對,家裡的土地也會被銀行沒收,拿去抵押還債。但或許是祖父平常為人有品格,受鄉里人敬重,在祖父徬徨、手足無措的時候,銀行經理便向祖父提議,把債務和抵押品由擔保人完全承擔,祖父因此搖身一變,成了坐擁百甲土地的大地主,但同時卻也得扛上這筆龐大的債務。
家中經濟無預警遭逢巨變,祖父不得不省吃儉用,記憶中,家裡的腳踏車永遠都是破破舊舊的。還記得,有一次我洗完手,水龍頭沒鎖緊,祖父就叫我拿一個臉盆,放在滴著水的水龍頭下方接水,接著跟我說,這些水都是要付錢的。甚至有時候忘了關電燈,他也會把我叫回來,提醒我,電也是要錢的。
儘管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幼稚園的孩子,祖父也一再訓誡與提醒。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知道原來東西不是無中生有,是要花錢買的,就像電有電費、水有水費,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理所當然地使用,而是得付出些什麼。
祖父的節省,讓當地不少人感到好奇,有些不是很清楚簡家狀況的人,開始有了閒言閒語,形容祖父是「皇帝命,乞丐身」,現在想想,或許是這種評價,祖父才不想讓外人看輕,刻意注重打扮,總是以一副紳士的模樣見人吧!
一直到祖父過世前,這筆龐大的債務仍未還清,父親繼承祖父的債務,繼續還債給銀行,過著像祖父一樣無比節省的日子。
小時候,母親曾半開玩笑、有點委屈地說,「大家都說你們簡家是桃園第一大地主,誰知道竟然欠了這麼多錢,生活要這麼節儉。」母親的埋怨不是沒有理由,畢竟她出生在富裕人家,父親是臺中前三大地主之一,過去從事建築建設工作,常在日本小社區蓋日式房屋,供日本人居住,現在臺中的大全街,就是以外公的名字命名的。正因如此,從小生長在大戶人家的母親嫁來簡家後,不但無法買新衣服、看電影,還得處處精打細算,心中的委屈和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來我不是日本人?!
我的求學階段,歷經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來臺的轉變。在國小五年級以前,我始終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如果能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會出現如此的認知差距,並不意外。
父親和母親都受過正統的日本教育,父親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念書,不過沒念到畢業就回臺灣相親,與母親結婚。母親雖未像父親留學日本,卻也在臺灣接受日本的高等教育,臺中女中畢業的她,會說一口流利日文,也因此,我一出生,就被父母用日文養大,日語幾乎就是我的母語。
父母非常重視我的教育,深受日本文化洗禮的他們,選了一所幾乎全是日本人的學校。那是一間有幼稚園的國小,國小的校長就是幼稚園的園長,當時臺灣人要進去讀書,很不容易,幾乎是要有家庭背景的人才能進去就讀,其他像警察、老師、醫師的小孩即使有機會進得去,也只能算是有資格拿到入場券,能不能進去就讀,還得通過校長的面試。
記得幼稚園面試那天,母親把我打扮得很規距,看起來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當走進面試的房間時,校長便拿了一顆橘子在我面前晃了兩下,問我這是什麼?也許是要測試我日文好不好?會不會說日文?當時我沒意會過來,只是呆著一張臉、滿臉困惑的看著他,直到校長用臺語說:「柑仔!」,我才豁然開朗的用日語回答:「蜜柑(みかん/發音為mi kann)!」。就這樣因為「蜜柑」,我順利通過面試,開始接受日本教育,與日本人一起念書。
從幼稚園到小學五年級,同學和老師幾乎全是日本人,因為我是少數的臺灣人,難免有點受到歧視,會有感到被歧視的心理反射是當時別的班級,班長都是由成績第一名的同學擔任,但我在班上總是拿第一名,卻沒做過一次班長,就連國小朝會的升旗手,我也沒做過。對從小被祖父灌輸要有榮譽心,好勝心極強的我,一直認為能在朝會時,站在升旗台上升旗,是一種無比榮耀,這個機會通常是各班的班長輪流擔當。有一次班上的班長因為生病臨時請假,無法參加朝會,當時我心裡暗自竊喜,心想終於可以輪到我去代表升旗了。結果,老師卻選了另一個日本同學當升旗手,雖然當時我憤憤不平,但仍無法理解自己與日本人的差別。其實老師當時的動作,都在提醒我是一個被殖民的日本臺灣人,但因為從小的生長環境和教育背景,我當時始終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日本人。
1945年,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小五年級的我,眼看著同學和老師紛紛回日本,心裡莫名惆悵,回家後很認真地問母親:「我們什麼時候也要回日本?」,結果母親正經地告訴我,「你是臺灣人,不用回日本。」當時,我的心中滿是疑問,用美國人最常講的話來形容當時的心情就是:「What happen to me?」這是什麼情況,為何會如此?為何我不用回日本?為此我還悶悶不樂了好一陣子。現在回想當時確實很天真,但在我的認知裡,被教育做為一個日本人是光榮的,會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的觀念竟是如此根深蒂固。
(摘自《隨遇而安》第一部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