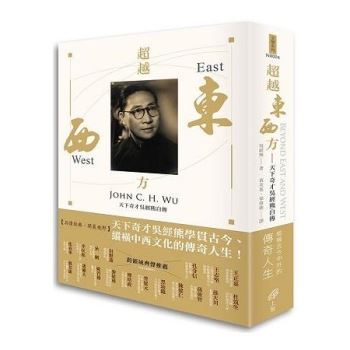第一章 生命恩賜
我的生辰是按照陰曆,己亥年(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七日生於江蘇寧波。那時春光明媚、曙光乍現。二月即俗稱的「花月」,傳說在這個月分裡「滿山蒼翠,宛如碧玉」。嫩葉和花蕾都在迎接太陽;柳梢漸漸轉綠,蘭花吐露芬芳,果園中的花朵都含苞待放。總之,歲月已穿過冬天陰暗的隧道,迎向璀璨的春光。這正是《雅歌》中新娘聽到愛人呼喚的季節:
我的愛人招呼我說:「起來,我的愛卿!快來,我的佳麗!看,嚴冬已過,時雨止息,且已過去;田間的花卉已露,歌唱的時期已近。在我們的地方已聽到斑鳩聲;無花果樹已發出初果,葡萄樹已開花放香;起來,我的愛卿!快來,我的佳麗!」(歌二10~13)
天主選擇了我的生辰,把我從母胎中呼喚出來。家人後來告訴我,我急著看到光明,助產婆來到之前我已呱呱墜地。
二月十七日和其他任何一天一樣,是出生的吉日。這一天正好在兩個民間節日之間。相傳道家之祖老子的生日是二月十五日,佛教觀世音菩薩的生日是二月十九日,我則稱心如意地夾在道教和佛教兩大宗教之間。此外,二月也是紀念孔子忌日的時節。因此可以看到,中國三大宗教似乎聚集一起,來作我的靈性保母。這三個宗教使我獲益良多,雖然我最終看到的「光」,是那普照每一個人的「道」(Logos)。
我現在對這三大宗教或思想派別所持的態度,可借用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句來形容:
直到我衷心信服你們留下的一切,我才敢繼續前進。
我已細讀過那些,真的十分值得讚美。(我在其間徘徊片刻)
沒有什麼比它更偉大,沒有什麼比它更值得讚賞!
我專注地凝視它好一會兒,然後將之摒棄,
如今,我在我的時代,佇立在屬於我自己的地方。
是的,凡屬人的一切,沒有比這三大派思想更偉大的。但基督宗教是屬神的,把基督信仰當成西方宗教是一大誤解。西方也許屬於基督宗教(我但願更加如此),但基督信仰並不屬於西方。它超越東方與西方,超越古老與新的。它比古老的更古老,比新的更新。對我來說,它比我從小耳濡目染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更本土。我感謝這三大派思想,因為是它們領我走向基督。基督使我的生命整合貫通,由於這整合,我很慶幸自己生為黃種人卻能接受白種人的教育。
根據某些迷信的說法,我的生辰八字非常吉利。雖然因著基督的聖寵,我已經拋開迷信,可是我從小就深信我的命很好,多少是受到這些迷信的影響。自少年時代,我就覺得自己有朝一日能在政壇上大有作為;我的國家,甚至全世界,都會因我的存在而更美好。因此,我一開始就抱著很大的期望,可是後來我的生活卻證明這些期待完全沒根據;每當我將理想和現實兩相比較,都會因為對比太強烈而啞然失笑。也許這正是我變得如此幽默又如此謙虛的原因吧!所謂幽默,不外乎自娛,取笑自我的惡行,同時謙虛地承認絕對的真理。的確,天主確實有本事從壞事中找出美善來。
我的陰曆生日相當於西元一八九九年三月廿八日。我很欣慰地得知,我特別崇敬的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是在一五一五年同一天、同一時辰出生;而律師聖人聖若望.賈必昌(St. John of Capistrano),在一四六五年同一天回到天國。這一切並不保證我也會成為聖人,但是對我的靈修生活確實是極大的鼓舞。如果我出生在聖誕節、復活節,或聖母的任一慶日,我一定會更快樂。但我是何許人,竟敢懷疑天主的智慧?祂不是比羅馬總督比拉多更有權說:「我寫了,就寫了」(若十九22)?至於我,我衷心喜樂地善用自由意志,接受天主自亙古就為我寫下的一切。
有些朋友注意到,自從我成了天主教徒後,似乎失去一些雄心壯志。其實我現在的野心比過去更大。我曾經享有世俗的榮耀,卻令我感到十分空虛。滿足於會腐朽的事物,根本不能算是雄心。對我來說,整個世界不再有任何值得垂涎的事物。我唯一的「野心」,是作天主的乖兒子,這是全心順從天主的人都能有的雄心。如果這個野心不是最崇高的,我的心絕不會憩息其中;如果它不是對所有人開放,我的心片刻也不會接受它。既然作天主子女的至高特恩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那麼除此以外去享受其他特恩又有什麼好處呢?
天主不單賜給我出生的吉日,更給我一個出生的好地方。我出生在寧波市一個叫做「二十四院」的地方。「寧波」的意思是「寧靜的波浪」。我不大知道這地名的來歷,大概是因為它建於甬江河岸,甬江使寧波與大海相連,且潮汐定時漲落,我們那時的人習慣以潮汐來判斷時間。
寧波人並不特別高尚文雅,但是熱情、誠實,充滿活力和冒險精神。大多數人從事工商業,較少投身於文學及藝術。寧波人都很聰明,且子女眾多,也許與愛吃海鮮有關。
就我所了解的,寧波人最大的長處是能全心享受生活。天主創造了寧波人,而寧波人認為活著真好(參創一26~31)。他們固然屬於塵世,泥土味十足;但從未忘記大地屬於上主,且把大地的產物當作上主的恩賜。換句話說,他們很享受生命的盛宴,認為那是上主提供給他們享受的。我相信天主喜愛這樣的人,甚於那些過分講究品味的人──他們彷彿是受邀來品評天主所準備的宴席。寧波人享受生命的恩賜,就像飢腸轆轆的美國男孩享用熱狗一樣。
寧波人的性格有些粗獷不馴,卻不怯懦多疑。他們享受生活,具有豐富的常識,也很有幽默感,只是這些幽默來自日常的玩笑,而不是文雅的風趣。他們熱愛肥美的大地及泥土的氣息,在宇宙間怡然自得。寧波的日月星辰、風雨、貓狗和花鳥,似乎比他處更富有人性,而且彷彿是每個家庭最親近的成員。童年時,我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看!日上三竿,該做午飯了。」或「小雞已回籠子,你爹就要回家了。」或者「看那彤雲!明天會比今天熱。」又或者「聽!喜鵲在你頭上叫了三聲,明天會有好事降臨。」如果是烏鴉叫,表示會走霉運,而消除霉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邊往地上吐痰,一邊說「呸!」你的身體就像是一根占卜杖,要是你打噴嚏,表示遠方的朋友在說你的好話;如果耳朵癢,一定是有人在背後說你壞話。早在西方人有收音機之前,我們寧波人已發明了心靈溝通法。
就是這樣,我的童年生活有如在仙境中度過。還記得第一次參觀紡織廠時,我是多麼驚奇。我自作聰明地說:「裡面一定有巫婆。」而且,我覺得自己非常勇敢,在這鬼屋裡還能保持鎮靜。
有一次,鄰居讓我聽他們新買的留聲機。我心想:「真可憐!這個死人的靈魂竟被惡毒的魔術師關在盒子裡,魔術師一念符咒,這可憐人就得重複說一遍!」單純的東方想像力初次接觸到西方的科學發明,那是我一生中最興奮、刺激的日子。對我、對寧波或中國各地的孩子來說,那段日子再也無法重現了。科學發現了許多宇宙奇異現象,但同時也扼殺了驚奇感。
十四年前,我寫過一段話,忠實地表達了當時對西方物質文明與中國接觸的感想。在某種程度上,這段文字仍可代表我目前的感受。
古老中國可愛的靈魂,仍舊在我心中縈繞,就像童年時令我著迷、幾乎已遺忘的旋律。我多麼希望能重回年老母親的懷抱!當我回首,總會令我怦然心動,因為
她是大地上的柔美風景,處處充滿和諧、平靜、寧謐、璀燦、萌芽,喜悅而無歡鬧,這若非幸福,也比你巨大的熱情更接近幸福。
如今,中國已變了,她被捲入世界狂潮的漩渦中。宛如西風中的樹葉、悠悠長江中的落花,她不再是她自己,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不可知的未來。我知道她能在大風大浪下生存,戰勝一切困厄和考驗。可是,她已無法重回過去甜美靈魂的本質。她的音樂不再像笛聲般行雲流水地迴盪,而是變為金屬般粗糙的音色,猶如華格納的傑作。對於她的孩子,她不再是昔日溫柔的母親,而是如夏日般酷烈的嚴厲父親。中國,我的祖國已死,新中國萬歲。
如今,中國的靈魂正經歷歷史上最痛苦的時期。旋律已經結束,和聲卻尚未譜成。她正處於四分五裂的混亂之中。至於我,天主已經消除了我的不協調,將和諧注入我的靈魂。可是我的祖國、我的同胞呢?只要他們沒有得到和諧,只要這世界仍舊不和諧,我的和諧也無法完成。
不管怎樣,我想到寧波的時候,總是不免帶著濃濃的鄉愁,部分是因為思鄉,部分是對童年歲月的懷念。我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是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特意去尋找出生時的房子(我孩提時代已搬離那裡,沒有再回去過)。大哥陪著我敲門詢問,好心的房客開門讓我們進去看看。大哥指出我出生的房問、母親去世時停放遺體的大廳,以及屬於鄰居的區域,而那些鄰居也都過世了。這一切恍如一場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