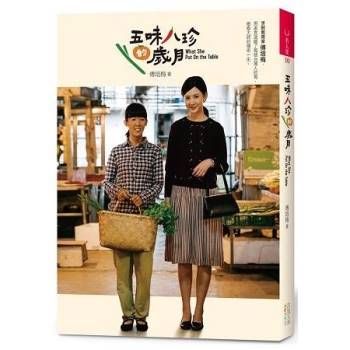連水餃都煮不好
曾經有很多人,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詢問過我,怎麼那麼會做菜?「怎麼」學的?這個「怎麼」,我想是雙重意思,也就是妳為什麼想學做菜,又怎麼(跟誰)學到的。
其實,我當年暗下決心,要學好做菜,都是為了要在先生面前爭回一口氣!
外子程紹慶的祖籍跟我一樣是山東大連,也是當時少數在台灣的大連同鄉之一。紹慶是標準的北方人胃口,尤其愛吃水餃,當然對餃子的要求也格外挑剔,不但要皮薄餡多,要帶汁,還得小巧。他最中意的是用明蝦(大蝦)包的大蝦水餃,或是用黃魚肉包的黃魚水餃。
結縭之初我們定居在高雄他公司的宿舍裡,只有一房一廳各六疊榻榻米大小。這個「廳」兼做客廳與飯廳兩用,晚上就變成麻將間了。宿舍內五家合用的廚房在長廊後頭,我為了討好外子,常常包水餃,但是每次吃了他都不高興。
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問他:「好吃嗎?」
他生氣的說:「這種餃子怎麼能吃,每個裡面都是一包水。」
我仔細一看,真的每一個餃子都有開個口,水大概從那裏跑進去的,但是怎麼會開口呢?我每一個都是用力捏邊的啊。
從那以後煮餃子的過程中,我便一直注視鍋中,一個一個來檢查,開口的就夾出留著我自己吃,即使如此小心,仍有滲水進去,經常煮得淡而無味。我看著他吃一口就丟一個,氣得筷子一摔拂手而去時,更是眼淚汪汪,無地自容。
在苦思不解其因之下,第二天我帶著餡料、皮子,去拜訪了年長的同鄉劉老太太,請她指教,怎樣才能讓餃子煮不破。
她一見我就笑說:「閨女啊!你怎麼長這麼大,還不會包個餃子?」於是我包給她看,先放餡在皮中間,用筷子抹一下皮邊,再對合起來用力捏緊,不對嗎?
「不對,不對,妳怎麼用筷子去抹邊呢?!筷子上有油,那不一煮就開口了嗎?」頓時,我清醒了,是啊!有油的筷子(因餡料中有拌油)去抹一下,濕濕的看似捏合了,但煮時遇到熱氣一定會開口(縫)的,這麼簡單的事,我當年都不懂,飽受怨氣,每次都對著煮熟的一鍋餃子「相面」,挑那看似未裂口的,一直擔心這次會被丟幾個。
外子吃水餃很講究,除了外形要完整,不滲水,蝦肉餡兒還必須要明蝦才行,從前在高雄不易買到明蝦,我有時專程跑到七賢三路的大市場找也找不到,就改買小蝦代替,他一吃就知道了味道不對,我雖強辯蝦的營養成分是一樣,但他要的卻是那鮮味和口感的不同。
大連人喜好吃魚餡餃子,黃魚餡是來台灣後才在高級專賣店賣出(當時一個十元),我為了滿足他的嗜好,不管黃魚在市價上賣得有多貴,也捨得買來包給他吃,以滿足他的口腹之慾。
虛心學菜,不恥下問
我學做菜,隨時都抱著研究的精神,不恥下問。
早年一位學員(林秋江夫人)問起她所吃的一道菜,上菜時油還在盤裡翻滾,上面還有很多大蒜。
這是個啥?我也沒吃過,於是找到復興園,照她形容的講給跑堂的聽,要點這樣的菜,跑堂操著蘇北口音告訴我說:「哦,那是炒鱔糊!」
上菜後我就邊吃邊研究,人家是怎麼做的。第二天就立刻買了鱔魚回來如法炮製。做出來覺得不夠道地,就再去吃一次,回來再實習,終於摸清楚了做法,可以告訴她了。
像這樣子「虛心偷學」所研究出的菜式實屬不少,記得一家有名的楓林小館,某學員說那店有一道甜甜酸酸的,一大片豬肉連著細骨的菜,叫「京都排骨」,我就按址找去,點那京都排骨,但怎麼也想不透為什麼骨頭會那麼細,肉卻又長又嫩?
實驗了多次,實在做不出來。於是找關係,出高酬,請那家餐廳的師傅來家裡教我,原來他們將豬小排自每一骨頭的中間,用刀劈開來成兩半,骨頭只有原來的一半粗,當然細得很啦。難怪這種醃過又炸,再配上甜酸醬汁的特殊排骨,人人愛吃。
我為學做菜,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和金錢,我一向愛惜羽毛,做法不正宗不願教,尤其後來上電視教做菜,更是不敢馬虎,生怕做得不道地讓人看笑話。
我一向認為只要有恆心和毅力,天底下沒有什麼是學不成的。我的個性很急,有什麼事想要做,就一定要馬上去做,不論多苦多難,也要試試,哪怕後來做不成,至少已經試過了。若是不試,心裡老是不平,想起就後悔不已,也許會難過一輩子。
桃李滿天下
教授烹飪三十多年來,我從未登報做招生廣告,口碑都是由學員口傳或新聞採訪報導而來。我對自己教菜的內容與態度向來有自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個性,使我毫無保留甘心施教。每道完成的菜餚一定親自嚐過,先自我批評優劣,再分給學員吃,並告訴他們應注意的事項。
味覺因人而異,對菜餚的接受度也不盡相同,但每道菜總有一定的標準尺度,淡而不能薄、甜而不可濃、辣而不能烈、肥而不要膩,都是基本信條。
我也一再強調,中華料理可舉一反三,比如學會了宮保雞丁,就可變化出宮保魷魚、宮保蝦仁,甚至宮保雙脆等。
有時學員們也會笑稱傅老師總是買一送一,有時還買一送三呢?做菜只要學會調味和烹飪技法之後,再活用智慧去發揮創意,就能運用巧思發揮自如了。
為了核發結業證書,我設計了術科考試,初、中級與高級班的題目不同,但絕對可以看得出高低。學員要自購材料現場製做,考驗他們的刀工、火候、調味等,雖然學員們多半都能過關,卻很少有人獲得滿分。調味料的下鍋,會因先後順序不同而直接影響風味,最重要的還是要掌握住過油的油溫,時間長短和鏟動的速度快慢,都能影響成品的好壞。
中國烹飪班的畢業證書,在國外相當具有權威性,憑著證書就可以開業或就職,因此常有熟人前來說項,情商為其子女、親人不上課而領取證書,或付錢想買證書,我都一概婉拒。畢竟是多年維護的金字招牌,可不能因為人情或金錢而傷及清譽。
中國烹飪班在一九九○年,因為我萌生退休之意而寫下了休止符。
當時外子的身體每況愈下,我想利用時間在他有生之年多陪陪他,另外當時的「新新人類」及職業婦女型態的生活轉變,大都不愛下廚房,新式的廚房設計都是與客廳相通的開放空間,怕油煙,又懶於打掃,使得現代婦女紛紛遠庖廚,為此,學菜的盛況不再。
我這整整三十年,多彩多姿的烹飪補習班、教學相長的生活於焉告一段落。
第一次上電視就出糗
一九六一年我開始在自家院子裡設班教菜,很快就求教者眾多。隔年台灣經日本技術協助開創電視事業,台灣電視公司在一九六二年的十月十日正式開播。初初開播一天只有中午和晚間播出數小時的黑白畫面。台視開播不久,我經由一位學生推薦,與「幸福家庭」的節目製作人孫步菲女士見面,很快就談成了我的電視處女秀。
當年的烹飪節目屬於婦女節目的一部分,另有插花、服裝、美容、兒童保育,共分為五個單元,各播出一天。當時會去上電視純粹出於好奇,加上學生們一致鼓勵打氣,因此就打鴨子上架。
我被安排在十二月的第三週(禮拜三)上節目,母親為我連夜趕製了一條圍裙,當天陪著我去,幫忙拿東西,孩子們更是自告奮勇端爐子、提材料、抱碗盤,差一點連計程車都坐不下去。
現場播出的節目需要配合時間,我在走廊外邊,早早把炭火生好,等攝影棚大門開啟,進去擺妥炭爐、材料,這才發現不得了,竟然忘記帶菜刀來,真是百密一疏。
當天要做的菜是「松鼠黃魚」,不但要剔下魚骨、取肉,還要在肉面上切一排排的尖粒花刀,這許多動作沒有菜刀怎麼做?弄得我心急如焚。AD(現場導播)路長華小姐建議我快去公司員工餐廳借一把。
當時的搭景十分簡陋,那天灰色的佈景板上,畫著線條簡單的一尾魚,爐台、工作台都是木板釘的、空心不牢還晃動著、像隨時會倒塌。待爐子的火已不旺了,才叫我開始,那把借來的刀鈍得魚頭都切不下,急得我滿頭大汗,切花也像鋸東西,來回拉上好多下,等我把魚沾上麵糊炸熟時,已見導播在用手指畫圈圈(叫我快結束),心想那怎麼可以?我做事向來有始有終的,就不管她怎麼畫,還是匆匆炒料、煮汁、勾了芡,淋到魚上,當時急得連一聲再見也來不及說,就結束了生平第一次的電視教學。
守在家裡收看的外子,一見我回來就說:「妳慌慌張張的,做得可真差啊!」
其實我心裡早在懊悔著不該去的,丟人現眼的全被人家看到了(幸好當時中南部收視不到,台北的普及率也並不高)。
沒想到一星期後,製作人孫小姐又來請我,並告知上次播出過後,接到不少觀眾對我的好評,她拜託我再去一次,於是又挑起了我的好強心。
第二次我示範了另一道高難度的菜「紅燒海參」,從如何發泡到出水、煨、燴、爆、燒全部過程都交代和示範完整。
溫暖了每個台灣人的胃
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得到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的社教節目金鐘獎,這是對我節目的一大肯定,令我萬分高興。一九八三年節目二十週年時,公司特別製作了一個「中華美味處處香」的特別節目,來紀念這個自開播以來與公司一同成長,廣受歡迎的長青節目。
一九九三年台視三十週年,我提出了辭職信,想為自己的電視教學生涯打上休止符,圓滿的結束這屬於表演性的生活。持續了六年多的五分鐘教一道菜的「傅培梅時間」,算是做到另一種的自我挑戰,我雖辛苦,總算走過了,內心已十分知足滿意。但是台視方面不肯放人,再三的慰留,節目部熊經裡還說,他擔當不起這麼元老的好節目,在他任上停播。經過多次的溝通,公司決定將一週五天的帶狀節目,調回以前的方式每週一次,為時三十分鐘。
從一九九四年起,我開始在節目中採用時令的材料,一次示範兩道菜,一繁一簡,當然調味與烹調法是迥然不同的。播出一年後,我深感市面上的中國菜在急驟的轉變,中餐廚師不斷轉型,菜色也推陳出新,為了提供一個廣為人知、展顯好手藝得機會,我在節目中開闢了「名廚名菜」的單元,讓各大飯店的主廚以及美食競賽中獲獎的師傅,都有機會亮亮相,向觀眾介紹他的拿手菜。
由於國外進口的材料日多,只要經名廚使用,觀眾不但學會了做法,也獲得許多對食材的新知識,當然我仍舊每次都會慣例的在開場時,先自己教一道菜,來滿足觀眾的期待。
天下雜誌在第二○○期有一特別企劃的報導,大題目為「影響二○○,起飛二○○」,刊登著近四百年來對台灣有貢獻、有影響,為台灣搭過希望之橋的各行各業的二○○人,其中分類有七個部分,即世界、開拓、啟蒙、行動、自重、豐富與共生,我很榮幸的也被收錄在其中,「豐富」篇內,記得同篇裡尚有梁實秋、瓊瑤、許文龍、紀政、高清愿、成舍我、林海音…等共二十七位,雖屬不同領域的工作,但對台灣社會的豐富性均有著貢獻,也是宣揚和保存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功勞者。
那篇頭的引言中對我的介紹寫到:
「…『傅培梅』三個字,在那艱苦打拚的歲月,讓人解饞解愁,也讓大家開始懂得注重美食,享受生活…。在那個粗茶淡飯的年代,傅培梅溫暖了每個台灣人的胃。」
由此可見我的電視烹飪教學對台灣民主的影響力確實是深遠而宏大無比。在那個年代(民國五十年代)大家的生活單調,總期盼著一點紓解和一些想望,美食顯然就是最好安慰劑。
曾經有很多人,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詢問過我,怎麼那麼會做菜?「怎麼」學的?這個「怎麼」,我想是雙重意思,也就是妳為什麼想學做菜,又怎麼(跟誰)學到的。
其實,我當年暗下決心,要學好做菜,都是為了要在先生面前爭回一口氣!
外子程紹慶的祖籍跟我一樣是山東大連,也是當時少數在台灣的大連同鄉之一。紹慶是標準的北方人胃口,尤其愛吃水餃,當然對餃子的要求也格外挑剔,不但要皮薄餡多,要帶汁,還得小巧。他最中意的是用明蝦(大蝦)包的大蝦水餃,或是用黃魚肉包的黃魚水餃。
結縭之初我們定居在高雄他公司的宿舍裡,只有一房一廳各六疊榻榻米大小。這個「廳」兼做客廳與飯廳兩用,晚上就變成麻將間了。宿舍內五家合用的廚房在長廊後頭,我為了討好外子,常常包水餃,但是每次吃了他都不高興。
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問他:「好吃嗎?」
他生氣的說:「這種餃子怎麼能吃,每個裡面都是一包水。」
我仔細一看,真的每一個餃子都有開個口,水大概從那裏跑進去的,但是怎麼會開口呢?我每一個都是用力捏邊的啊。
從那以後煮餃子的過程中,我便一直注視鍋中,一個一個來檢查,開口的就夾出留著我自己吃,即使如此小心,仍有滲水進去,經常煮得淡而無味。我看著他吃一口就丟一個,氣得筷子一摔拂手而去時,更是眼淚汪汪,無地自容。
在苦思不解其因之下,第二天我帶著餡料、皮子,去拜訪了年長的同鄉劉老太太,請她指教,怎樣才能讓餃子煮不破。
她一見我就笑說:「閨女啊!你怎麼長這麼大,還不會包個餃子?」於是我包給她看,先放餡在皮中間,用筷子抹一下皮邊,再對合起來用力捏緊,不對嗎?
「不對,不對,妳怎麼用筷子去抹邊呢?!筷子上有油,那不一煮就開口了嗎?」頓時,我清醒了,是啊!有油的筷子(因餡料中有拌油)去抹一下,濕濕的看似捏合了,但煮時遇到熱氣一定會開口(縫)的,這麼簡單的事,我當年都不懂,飽受怨氣,每次都對著煮熟的一鍋餃子「相面」,挑那看似未裂口的,一直擔心這次會被丟幾個。
外子吃水餃很講究,除了外形要完整,不滲水,蝦肉餡兒還必須要明蝦才行,從前在高雄不易買到明蝦,我有時專程跑到七賢三路的大市場找也找不到,就改買小蝦代替,他一吃就知道了味道不對,我雖強辯蝦的營養成分是一樣,但他要的卻是那鮮味和口感的不同。
大連人喜好吃魚餡餃子,黃魚餡是來台灣後才在高級專賣店賣出(當時一個十元),我為了滿足他的嗜好,不管黃魚在市價上賣得有多貴,也捨得買來包給他吃,以滿足他的口腹之慾。
虛心學菜,不恥下問
我學做菜,隨時都抱著研究的精神,不恥下問。
早年一位學員(林秋江夫人)問起她所吃的一道菜,上菜時油還在盤裡翻滾,上面還有很多大蒜。
這是個啥?我也沒吃過,於是找到復興園,照她形容的講給跑堂的聽,要點這樣的菜,跑堂操著蘇北口音告訴我說:「哦,那是炒鱔糊!」
上菜後我就邊吃邊研究,人家是怎麼做的。第二天就立刻買了鱔魚回來如法炮製。做出來覺得不夠道地,就再去吃一次,回來再實習,終於摸清楚了做法,可以告訴她了。
像這樣子「虛心偷學」所研究出的菜式實屬不少,記得一家有名的楓林小館,某學員說那店有一道甜甜酸酸的,一大片豬肉連著細骨的菜,叫「京都排骨」,我就按址找去,點那京都排骨,但怎麼也想不透為什麼骨頭會那麼細,肉卻又長又嫩?
實驗了多次,實在做不出來。於是找關係,出高酬,請那家餐廳的師傅來家裡教我,原來他們將豬小排自每一骨頭的中間,用刀劈開來成兩半,骨頭只有原來的一半粗,當然細得很啦。難怪這種醃過又炸,再配上甜酸醬汁的特殊排骨,人人愛吃。
我為學做菜,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和金錢,我一向愛惜羽毛,做法不正宗不願教,尤其後來上電視教做菜,更是不敢馬虎,生怕做得不道地讓人看笑話。
我一向認為只要有恆心和毅力,天底下沒有什麼是學不成的。我的個性很急,有什麼事想要做,就一定要馬上去做,不論多苦多難,也要試試,哪怕後來做不成,至少已經試過了。若是不試,心裡老是不平,想起就後悔不已,也許會難過一輩子。
桃李滿天下
教授烹飪三十多年來,我從未登報做招生廣告,口碑都是由學員口傳或新聞採訪報導而來。我對自己教菜的內容與態度向來有自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個性,使我毫無保留甘心施教。每道完成的菜餚一定親自嚐過,先自我批評優劣,再分給學員吃,並告訴他們應注意的事項。
味覺因人而異,對菜餚的接受度也不盡相同,但每道菜總有一定的標準尺度,淡而不能薄、甜而不可濃、辣而不能烈、肥而不要膩,都是基本信條。
我也一再強調,中華料理可舉一反三,比如學會了宮保雞丁,就可變化出宮保魷魚、宮保蝦仁,甚至宮保雙脆等。
有時學員們也會笑稱傅老師總是買一送一,有時還買一送三呢?做菜只要學會調味和烹飪技法之後,再活用智慧去發揮創意,就能運用巧思發揮自如了。
為了核發結業證書,我設計了術科考試,初、中級與高級班的題目不同,但絕對可以看得出高低。學員要自購材料現場製做,考驗他們的刀工、火候、調味等,雖然學員們多半都能過關,卻很少有人獲得滿分。調味料的下鍋,會因先後順序不同而直接影響風味,最重要的還是要掌握住過油的油溫,時間長短和鏟動的速度快慢,都能影響成品的好壞。
中國烹飪班的畢業證書,在國外相當具有權威性,憑著證書就可以開業或就職,因此常有熟人前來說項,情商為其子女、親人不上課而領取證書,或付錢想買證書,我都一概婉拒。畢竟是多年維護的金字招牌,可不能因為人情或金錢而傷及清譽。
中國烹飪班在一九九○年,因為我萌生退休之意而寫下了休止符。
當時外子的身體每況愈下,我想利用時間在他有生之年多陪陪他,另外當時的「新新人類」及職業婦女型態的生活轉變,大都不愛下廚房,新式的廚房設計都是與客廳相通的開放空間,怕油煙,又懶於打掃,使得現代婦女紛紛遠庖廚,為此,學菜的盛況不再。
我這整整三十年,多彩多姿的烹飪補習班、教學相長的生活於焉告一段落。
第一次上電視就出糗
一九六一年我開始在自家院子裡設班教菜,很快就求教者眾多。隔年台灣經日本技術協助開創電視事業,台灣電視公司在一九六二年的十月十日正式開播。初初開播一天只有中午和晚間播出數小時的黑白畫面。台視開播不久,我經由一位學生推薦,與「幸福家庭」的節目製作人孫步菲女士見面,很快就談成了我的電視處女秀。
當年的烹飪節目屬於婦女節目的一部分,另有插花、服裝、美容、兒童保育,共分為五個單元,各播出一天。當時會去上電視純粹出於好奇,加上學生們一致鼓勵打氣,因此就打鴨子上架。
我被安排在十二月的第三週(禮拜三)上節目,母親為我連夜趕製了一條圍裙,當天陪著我去,幫忙拿東西,孩子們更是自告奮勇端爐子、提材料、抱碗盤,差一點連計程車都坐不下去。
現場播出的節目需要配合時間,我在走廊外邊,早早把炭火生好,等攝影棚大門開啟,進去擺妥炭爐、材料,這才發現不得了,竟然忘記帶菜刀來,真是百密一疏。
當天要做的菜是「松鼠黃魚」,不但要剔下魚骨、取肉,還要在肉面上切一排排的尖粒花刀,這許多動作沒有菜刀怎麼做?弄得我心急如焚。AD(現場導播)路長華小姐建議我快去公司員工餐廳借一把。
當時的搭景十分簡陋,那天灰色的佈景板上,畫著線條簡單的一尾魚,爐台、工作台都是木板釘的、空心不牢還晃動著、像隨時會倒塌。待爐子的火已不旺了,才叫我開始,那把借來的刀鈍得魚頭都切不下,急得我滿頭大汗,切花也像鋸東西,來回拉上好多下,等我把魚沾上麵糊炸熟時,已見導播在用手指畫圈圈(叫我快結束),心想那怎麼可以?我做事向來有始有終的,就不管她怎麼畫,還是匆匆炒料、煮汁、勾了芡,淋到魚上,當時急得連一聲再見也來不及說,就結束了生平第一次的電視教學。
守在家裡收看的外子,一見我回來就說:「妳慌慌張張的,做得可真差啊!」
其實我心裡早在懊悔著不該去的,丟人現眼的全被人家看到了(幸好當時中南部收視不到,台北的普及率也並不高)。
沒想到一星期後,製作人孫小姐又來請我,並告知上次播出過後,接到不少觀眾對我的好評,她拜託我再去一次,於是又挑起了我的好強心。
第二次我示範了另一道高難度的菜「紅燒海參」,從如何發泡到出水、煨、燴、爆、燒全部過程都交代和示範完整。
溫暖了每個台灣人的胃
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得到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的社教節目金鐘獎,這是對我節目的一大肯定,令我萬分高興。一九八三年節目二十週年時,公司特別製作了一個「中華美味處處香」的特別節目,來紀念這個自開播以來與公司一同成長,廣受歡迎的長青節目。
一九九三年台視三十週年,我提出了辭職信,想為自己的電視教學生涯打上休止符,圓滿的結束這屬於表演性的生活。持續了六年多的五分鐘教一道菜的「傅培梅時間」,算是做到另一種的自我挑戰,我雖辛苦,總算走過了,內心已十分知足滿意。但是台視方面不肯放人,再三的慰留,節目部熊經裡還說,他擔當不起這麼元老的好節目,在他任上停播。經過多次的溝通,公司決定將一週五天的帶狀節目,調回以前的方式每週一次,為時三十分鐘。
從一九九四年起,我開始在節目中採用時令的材料,一次示範兩道菜,一繁一簡,當然調味與烹調法是迥然不同的。播出一年後,我深感市面上的中國菜在急驟的轉變,中餐廚師不斷轉型,菜色也推陳出新,為了提供一個廣為人知、展顯好手藝得機會,我在節目中開闢了「名廚名菜」的單元,讓各大飯店的主廚以及美食競賽中獲獎的師傅,都有機會亮亮相,向觀眾介紹他的拿手菜。
由於國外進口的材料日多,只要經名廚使用,觀眾不但學會了做法,也獲得許多對食材的新知識,當然我仍舊每次都會慣例的在開場時,先自己教一道菜,來滿足觀眾的期待。
天下雜誌在第二○○期有一特別企劃的報導,大題目為「影響二○○,起飛二○○」,刊登著近四百年來對台灣有貢獻、有影響,為台灣搭過希望之橋的各行各業的二○○人,其中分類有七個部分,即世界、開拓、啟蒙、行動、自重、豐富與共生,我很榮幸的也被收錄在其中,「豐富」篇內,記得同篇裡尚有梁實秋、瓊瑤、許文龍、紀政、高清愿、成舍我、林海音…等共二十七位,雖屬不同領域的工作,但對台灣社會的豐富性均有著貢獻,也是宣揚和保存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功勞者。
那篇頭的引言中對我的介紹寫到:
「…『傅培梅』三個字,在那艱苦打拚的歲月,讓人解饞解愁,也讓大家開始懂得注重美食,享受生活…。在那個粗茶淡飯的年代,傅培梅溫暖了每個台灣人的胃。」
由此可見我的電視烹飪教學對台灣民主的影響力確實是深遠而宏大無比。在那個年代(民國五十年代)大家的生活單調,總期盼著一點紓解和一些想望,美食顯然就是最好安慰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