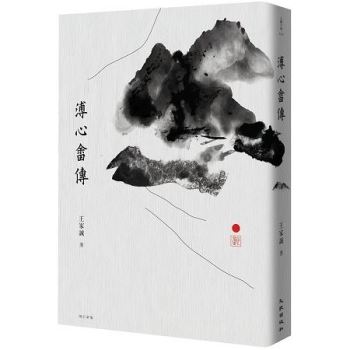龍的傳人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貝勒愛新覺羅載瀅的次子誕生。由於這天是咸豐皇帝的忌辰,所以把他的生日改為七月二十四日。從咸豐即位後便在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恭親王奕訢,是他的祖父。他的誕生,對此際政壇失意,奉旨「養病」的恭親王,是一件大喜之事。出生第三日,光緒皇帝賜名為「溥儒」。「心畬」是他後來所取的字(因心畬較為人知,故本傳以溥心畬稱之)。
清室姓氏之說,相當複雜。有些說法是,本姓「愛新覺羅」,後人除實質上保有此姓之外,受漢人影響,簡化姓名。就以譜系中所排輩分為姓。如溥心畬的祖父輩,輩分為「奕」,名有「言」字邊,奕 (咸豐)、奕訢、奕 ……是道光皇帝諸子的姓名。
他父親輩,以輩分姓載,名以「水」為偏旁,載淳(同治)、載湉、載瀅……是道光皇帝孫子輩的姓名。再下一輩姓「溥」,名字有「人」字偏旁,溥儀(宣統)、溥儒、溥傑、溥佑即是。溥儒子侄輩姓「毓」,名有「山」字偏旁。溥儒之子名「溥毓岦」,義子名「溥毓岐」,「毓」上冠以溥姓,是個例外。溥儒的獨女,名「韜華」未冠父姓。
在溥心畬的詩文中,很少提到他父親載瀅,但津津樂道他祖父恭親王的兩件軼事:
咸豐十年秋,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況失利,英法聯軍漸漸逼近北京。咸豐皇帝不顧群臣諫阻,倉皇出奔熱河。行前,恭親王臨危授命,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負責與英法兩國議和,安定民心。咸豐並以硃筆上諭一道授予恭親王:
「如有意外事件發生,你即可自登大位,諸事當以社稷為重。」
溥心畬說這道聖諭,一直保存在恭親王手中,其後傳給長孫小恭親王溥偉,溥偉則呈獻給宣統皇帝溥儀。此事儘管有學者提出懷疑,但溥心畬似乎深信不疑。巧的是,次年,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咸豐皇帝就以三十幾歲的壯年,病逝熱河;如真有此一硃諭,可謂一語成讖了。
另一則他愛說的恭親王軼事是:
沖齡的同治皇帝即位後,為了國事,恭親王常與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激烈爭辯。一次慈禧怒極,責問他:「汝係何人!」
恭親王當即不甘示弱地回敬一句:「宣宗之子,仁宗之孫,今上之叔也!」
慈禧太后為之氣沮,乃改容致歉。
在外患頻仍,內爭不斷的政壇中,屢起屢伏的恭親王,除留給子孫輝煌的家世外,尚有三寶:
第一寶是金桃皮鞘的「白虹刀」。此刀傳到溥偉手中後,壯志凌雲地想內誅權臣,外抗推翻愛新覺羅王朝的革命黨,怎奈時代在變,雖然寶刀在手,不過如蚍蜉之撼大樹,徒增舊王孫的悲涼之感。
清宣宗道光皇帝生有九子,有的早殤,有的生母地位低微,兒子也不為道光喜愛。最得寵的是四子奕 和六子奕訢。兩位少年皇子在上書房讀書之外,也尊祖制勤習馬、步功夫,以便培植成文武兼備的統治者。
兩兄弟共同創出槍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道光皇帝看到他們演練後十分欣慰。槍法賜名為「棣華協力」,刀法名「寶鍔宣威」。並以宮廷寶刀「銳捷刀」賜奕 ,「白虹刀」賜奕訢。
道光二十六年夏天,六五高齡的皇帝,經過多年的考慮,決定立奕 為皇太子(四年後即位為咸豐皇帝),封奕訢為親王;餘子為郡王。立儲君的上諭,採康熙皇帝留下的方式,密藏於金匱中,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的匾後;另一密旨則交內務府收存。在選擇儲君的過程,兩位皇子的生母和師傅,少不了明爭暗鬥,出謀劃策,但總算大勢已定,親王之封,也足見道光皇帝對六皇子的恩寵,僅次於四皇太子而已。
咸豐即位後,遵照大行皇帝遺詔,封奕訢為「恭親王」,封其他諸弟為郡王。咸豐元年恭親王分府,分到的是乾隆年間大學士和珅的宅第;此為恭親王遺留子孫的第二寶。
由於和珅恃寵而驕,獨攬大權,賄賂公行,極盡豪奢之能事,因而也就成了新君嘉慶皇帝整肅的對象。嘉慶指斥和珅罪狀共二十款,第十三款為:「昨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隔斷式樣,皆倣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不知是何肺腸!」賜令和珅自盡。
由此可見府第的宏偉瑰麗。
當年不滿二十歲的恭親王得此名冠京城,僅次於皇家園林的巨宅,諸王無不稱羨。他更將此歷史勝蹟大加整修,分為王府和花園前後兩大部分,前部為辦公居家之處。花園名「萃錦園」,取集眾芳精英,成一代名園之意。尤其當恭親王失勢閒居之際,多在園中吟詠嘯傲。所集唐詩,名「萃錦吟」,用以寄寓懷抱,傳誦一時。此外,他又在萃錦園北,另闢一座「鑑園」,規模自不能與萃錦園相比。
萃錦園中景觀,可分廿景,載瀅一一詠之於詩,收於《雲林書屋詩集》中。
民國十幾年,恭親王爵位繼承人溥偉,將王府抵押給天主教會。其後輔仁大學代償鉅債,取得產權,王府就此易手。但溥心畬兄弟依然租賃萃錦園多年,埋首著作,對客揮毫,奠定在藝術界的地位。暇時,常在大戲樓中粉墨登場,自娛娛客,寄託舊王孫和遺老們的幽懷。
溥心畬出生前十年左右,一再被慈禧太后排擠的恭親王,多半避居在西山戒壇寺牡丹院中,他捐款修廟,虔信佛教之外,也廣蓄詩書和古代字畫以銷磨歲月。再加上王府收藏,數量更為可觀,如陸機「平復帖」、易元吉「聚猿圖」等名蹟,比內府所藏書畫珍品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文化遺產,日後溥心畬兄弟避居戒壇寺時,成為心靈的滋養。清朝亡後,溥心畬雖淪為一介平民,卻不失為精神貴族,卒成名揚國際的經學家、詩人和書畫大師。由此看來,恭親王收藏的古籍書畫,可稱第三寶。
五個月大的溥心畬,蒙恩賜以頭品頂戴,恭親王抱他入朝謝恩。這是他首蒙光緒皇帝召見。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入夜後,恭親王離開了擾攘的人世,享年六十七歲。病重時,光緒皇帝奉慈禧太后命三度蒞臨探視。想到三十餘年間,朝廷每遇艱難危險。慈禧便請這位勇於任事的親王出山,攜手共事。一旦意見相左,利益衝突,則藉帝旨加以罷黜,恐怕兩人心中都不勝感慨吧。而當日母以子貴的西宮太后慈禧,已是六十四、五歲的老婦,真是歲月不饒人。恭親王逝世後,光緒與太后親臨致奠,光緒輟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諡為「恭忠親王」,配享太廟。並諭:
「王忠誠匡弼,悉協機宜,諸臣當以王為法。」這也是他憂勤半生的一種哀榮。恭親王有四子,長、三、四子均早卒,以次子載瀅的長子溥偉過繼為長子載澂之後,也承襲了恭親王的爵位。被恭親王視為掌珠的獨女,為慈禧收養於宮中,封榮壽公主,很少與家人團聚。公主婚後不久即孀居,但依舊隨侍慈禧左右,加封為「固倫」公主。
恭親王喪事完畢之後,三歲的溥心畬隨父兄到頤和園的排雲殿謝恩,光緒皇帝賜以金帛,他後來在〈感興〉詩中寫:「我生之初蒙召見,拜舞曾上排雲殿。」指的便是出生五個月和三歲時的兩次晉見。看著方面大耳聰明伶俐的溥心畬,光緒皇帝想起為他命名之事說:「汝名儒;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光緒皇帝語出《論語》〈雍也第六〉章,是孔子對子夏所說的一段話。朱熹註為:
「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注得似乎比原文更為費解。論語課本中別有一注是:
「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
看來是指儒者器識與擔當大小的分別。
《三國演義》雖屬小說者流,但「諸葛亮舌戰群儒」時,論君子儒小人儒的分別,更為透徹:
「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
不僅光緒皇帝以君子儒期盼這位恭忠親王的裔孫,溥心畬生平也以經學家和碩儒自許。若以小說中諸葛亮的尺度來衡量溥心畬一生的行誼和事業成就,恐怕也是見仁見智,難有定論。
光緒二十五年,四歲的溥心畬開始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經,並習書法。依自傳的說法,先學篆書和隸書,次為北碑和右軍楷法,十二歲之前,連行書草書,也有相當的基礎。
四歲這年,他的弟弟溥佑誕生。但新生嬰兒帶給家庭的不是喜悅,而是困擾。國殤或守父母喪期間妊娠所生的子女,為禮所不容。溥佑誕生,正值恭忠親王的喪期,依法不得報宗人府享受皇族封賜和一切應享的權利,遂成了恭王府的「黑人」。變通的辦法,是過繼給孤零無後的族人,為其宗祧。這事一直拖延到溥佑十歲左右,才過繼給清太祖後裔饒余敏親王為後。家中僅有一位孤零的老婦,因之,溥佑少年時代,可能並無幸福可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生母項夫人過世時,他才認祖歸宗。
貝勒載瀅,除嫡福晉(元配夫人)外,有六房側室。據說嫡福晉脾氣不好,又好妒,使側室感到壓力,對於未來地位和生活也缺乏保障,紛紛向載瀅爭取名分。其時清室已經不行側福晉之封。在嫡、庶交攻下左右為難的載瀅,只好請慈禧太后定奪;結果把六位側室,一律封為「太太」。
過繼給伯父載澂,襲恭親王爵位的溥偉,為嫡福晉所生,無論在恭親王府或朝廷中,他都有相當的權勢。溥心畬和溥佑的生母項夫人,為第一側室,人稱「大太太」,餘者依次稱「二太太」、「三太太」……幾位側室分居各自的公館內,並不時常見面,也許這就是溥心畬和父親、五位庶母比較生疏的原因之一。
項夫人是廣東南海人,為書香世家,屬廣東駐防旗。父親在北京太醫院,作一名小官。項夫人自幼飽讀經書,對家中僕婦慈和,對溥心畬則督教甚嚴,在爾後避難和隱居生活中,更親自教導讀經。溥心畬認為其一生造詣與節操,得之於母教;即使晚年,在友人和學生面前,言必稱「先母」,孺慕之情,見於顏色。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起事,導致八國聯軍之役。七月二十日北京城陷,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倉皇西行。八月至太原,九月到達西安。命李鴻章、慶親王奕劻與各國公使議和。聯軍所提的先決條件是加重懲治罪魁。但,真正慫恿義和團,導致八國聯軍之役的禍首是慈禧太后,太后不得已,只有找些親王、大臣作為代罪羔羊。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下詔將端郡王載漪等革職、監禁或充軍、降調不一而足。貝勒載瀅也在其中,判交宗人府圈禁。至此,載瀅更加消沉,以酒澆愁、寄情於園林、輸銀建廟;這也許是幼年溥心畬對父親比較生疏的另一原因。
光緒二十七年,六歲的溥心畬,開始在私塾讀書,塾師為宛平名士陳應榮。所讀《論語》、《孟子》等,以背誦為主,每日由兩三行漸能背到十餘行,同時也要能夠默寫。據他說,當時無論貴冑子弟和一般讀書人,十六七歲前,必須把十三經讀畢。以後他時常勉勵子侄和後進,幼年背誦之書,終生不忘,受益無窮。
他記得,作詩是由七歲開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律詩,至五七言古詩;再往後就開始學策論、經史一類的作文了。他始終認為圈點句讀,是讀書的要領,使人深入咀嚼,不致粗心浮氣。江西永新的龍子恕,宜春的歐陽鏡溪,也陸續成為他的嚴師。私塾中只有年節、父母壽誕和本人生日才得放假。雖然母親和蒙師督教嚴格,但童年的溥心畬,依然活潑好動,有一次便淘氣得幾乎失掉性命。
萃錦園中的「流杯亭」,又稱「沁秋亭」,是一個八角形的小亭,在假山的北側,奇形怪石,環繞在亭的四周,極為幽雅。假山與亭,暗通水道,流過亭內時,蜿蜒曲折,非常別致。流杯亭的設計是受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所描寫曲水流觴的影響。王府主人春秋宴客於亭中,假山古井中汲出涼沁心肺的泉水,從水道中流出,客人只見涓涓清流,浮觴其中,一觴一詠,十分優雅。
溥心畬在亭畔石上,攀登騎坐,大概是練習騎馬動作,搖搖撼撼,一塊巨碑似的湖石,突然壓在身上,使他動彈不得。十幾個太監僕夫,跑來救援,卻無法把石頭挪開,據說後來項夫人跪地默禱,才得抬開大石。出人意外的,除了嘴角右上方留下一點疤痕外,其餘竟毫髮無傷,童年軼事,雖說是破了龍相,不能不說是奇蹟。
八歲那一年,正在學作七言絕句詩的溥心畬晉見慈禧太后。
當天,是慈禧太后壽誕之日,頤和園中,滿是祝嘏的王親貴冑。她的興致很好。竟把這聰明俊秀的王孫抱在膝上問:「聽說你會作對聯?」
溥心畬好像未加思索似的,順口作出一副五言聯祝壽。聯句文雅得體,典也用得妥貼,太后稱之為「本朝神童」,賞給他文房四寶。溥心畬神童之名不脛而走。
曹子建七步成詩,但溥心畬生平,詩思敏捷,成詩似乎不需七步。有些弟子請他題畫,三十幾幅,每張畫剛舖平,他已經落墨紙上,頃刻之間,全數題完。有的弟子在一旁筆錄,竟然跟不上他作詩的速度。因此每當有學畫者臨門,他開頭便問「你有沒有作詩?」他認為只要詩好、字好、人品好,再加上飽讀經書,畫不學也能畫好。
光緒三十一年,他已十歲。由於學習騎射和太極拳,使他的面容,俊秀中透著幾分精壯。七月二十四日他生日那天,由嫡母赫舍里氏帶領前往頤和園晉見慈禧太后。年逾古稀的太后,依然很有威儀。她所統治的中國雖然備遭屈辱,國土幾被列強瓜分;據溥心畬說,許多外國使臣在初次晉見時,依然會怕得發抖。有的朝臣、命婦,在她面前更不知所措。但這一天慈禧太后所顯露的卻是慈祥的一面。
頤和園萬壽山的樂壽堂中,榮壽長公主和幾位溥心畬的姑姑姊姊侍立在側。榮壽公主是溥心畬的親姑姑,五十左右年紀。有她在旁使溥心畬心裡安定不少。太后親切地拉著心畬的手,問他在讀什麼書?他說在讀《詩經》。
太后命他賦萬壽山詩,他想到殿外碧波蕩漾的昆明湖,很快地便吟出:
「彩雲生鳳闕,佳氣滿龍池。」詩句中對仗工整,氣象寬宏,使太后大為讚賞。勉勵他好好讀書,將來作一番事業。除了賜他福壽字外,並叫宮女捧出四盤生日禮物:一柄玲瓏的玉如意、十錠一兩重的金元寶、十錠一兩重的銀元寶,此外,還有珍珠瑪瑙各若干。這些賞賜,溥心畬一直珍藏著,可惜民國三十六年南遊之際未能攜在身邊,就此永別故都。
當時他更意想不到的是,三十餘年後,他失去了成長、嬉戲、讀書的恭王府花園,卻賃住在萬壽山樂壽堂緊鄰的介壽堂,可以隨意到清澈廣闊的「龍池」中,獵野鴨和垂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