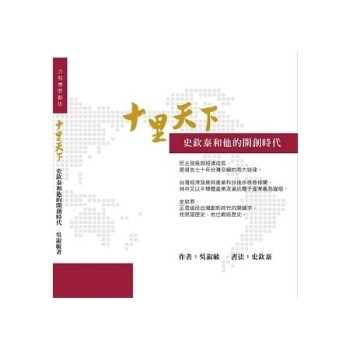1946年,史欽泰出生在高雄茄萣鄉,一個尋常家庭。
茄萣鄉,位在台南與高雄的交界。它是一個小漁村,茄萣外海是絕佳魚場,小小的漁村,曾經有80% 的人是漁夫。地名的源起,一說是平埔族語「多魚之地」的音譯,另一說是海邊紅樹林樹種之一的茄萣仔,荷蘭人則在地圖上標示為「漁夫角」。
史欽泰的祖父有小學畢業學歷,在鄉下已經算是很有學問的人,國民政府來台後實施地方自治,找人當議員,他的祖父曾因此當過地方上的議員。在史欽泰的印象中,當時並不了解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很多人來找祖父,好像他是地方上比較公正的人。祖父60幾歲就過世了,從政也未曾是這個家庭的志向。
他的回憶裡:
茄萣是窮得不得了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是住茅屋,地面是泥土,只要一下雨都是滑滑的。 那時候晚上非常暗,沒有電,不太有人會在晚上做什麼重要的事,多半悠閒在外面乘涼、看星星⋯。
那時代物資少,沒有鞋子上學,鄉下都是這樣。一方面是窮,一方面鄉下也就是這樣。我記得第一年小學的書包是我媽媽縫的,因為她去學裁縫,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母親自己做的。
茄萣小狀元
因著父親工作關係,小學階段,史欽泰整整唸過三所不同的學校。
史欽泰的父親學農,在台糖工作,被派駐到偏僻的農場種甘蔗,因為必須巡看蔗田,就和蔗田、蔗農生活在一起。農場通常只有三四戶人家,對外交通只有倚賴載送甘蔗的小火車,而且,也只有在運送甘蔗的時候,小火車才會開進農場。
如此一來,上學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由於茄萣的老家離小學比較近,父親自顧不暇,史欽泰在小學一、二年級階段,就跟著阿嬤生活、上學。童年回憶裡,陪阿嬤回娘家的路如此清晰:
我阿嬤的娘家在湖內,茄萣到湖內之間有公墓,遇節慶陪我阿嬤回去,走路要走將近一個鐘頭才回得到家裡。湖內那邊是使用井水。
後來有人幫農場那幾戶人家做零星的工作,每天運用台車(一塊木板加四個輪子的交通工具)出入,也順便買菜帶回來給太太們。雖然交通仍舊很不方便,小孩子總算可以跟著去上學。
因此,到了三、四年級,他回到家裡,跟著兩個弟弟一起坐台車去唸書。五、六年級時,因為父親又調職,比較接近麻豆糖廠,他轉學到麻豆鎮念文正小學。幾乎每個學校念兩年,很難交朋友,對小學同學也都沒什麼印象。多年後,他參加小學同學會,大家記得的,就是:「那個來一下就走掉的,很厲害!」出生在這個都是漁夫、魚塭的窮漁村,想升學、攻取美國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事,也完全不在史家的規畫當中。史欽泰說:
父親已經算是那個時代比較好的職業,所以我也沒什麼理由不唸書。三兄弟中我唸書比較好,我是念書很順,並不是父母有特別的計畫。
在鄉下,升學不易。史欽泰就讀文正國小時,每一個年級最多兩班,讀升學班,就到城裡考試,另一班則是不升學的。升學班裡,看起來更有能力的送到台南考試,其他同學就參加縣或鄉鎮的中學、農專、技職學校⋯⋯等的入學考試。
當時老師挑了12個學生到台南去考聯招(當時是初中),12個人都上榜!但是在鄉下唸書,程度其實跟不上,第一年大部份同學都留級,最後只剩下三個人能夠初中準時畢業。
初中三年以後再考高中,史欽泰順利考入台南一中。高中畢業之際,台灣還有保送大學的制度,他正是符合保送大學資格的學生之一。他選擇進入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大學的選擇,鍾情半導體
他記得當時台南一中前幾位同學都選擇台大醫學系。傳統上,台灣人多半最希望孩子念醫,特別是中南部。史欽泰卻不想:
我基本上不願意當醫生,因為我覺得時間不自由,好像被關在醫院, 覺得蠻無聊的。再者,我想,醫生每天都面對痛苦的事,痛苦的臉。我喜歡到處去看東西,我認為醫生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排斥,選擇保送到台大電機。
當時他完全不理解這個選擇將帶來的影響,電機系做什麼?他只知道是理工、是科學:
當時我只知道發電機、馬達啊,這些傳統的東西,根本不知道電機將來是什麼樣子,資訊很有限。我的爸媽完全讓我自己選擇。
那個年代,讀書的人,尤其受高教育的人很少。
史欽泰進入大學是1964年,世界局勢仍然十分動盪,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已打了好幾年(1960年開始),而前一年──1963年11月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進入台大,知識領域豁然開朗,除了從老教授學習,最重要的新知識來源是來自海外的訪問學者、客座教授。
1960年代,台灣大學電機系裡,沒有教半導體的專任師資。當時偶而有海外學人願意回國短期講學,每一年台大電機大約會邀請兩、三位訪問學者回來,講授他們正在進行的新領域,可以說,都是當年台灣教授開不出來的課。史欽泰因此有機會聽到積體電路,進而下定決心要走這個領域。他回憶道:大四那一年,我們班基本上是兩個出路,一邊是半導體,一邊是電腦,這兩個方向都有國外回來的客座專家;我雖然兩邊的課都有選,但後來慢慢偏半導體。當時半導體的客座專家就是回台灣的IBM研究員方復先生-他現在是中研院院士,也是工研院早期前瞻科技指導委員會(ARAC,Advanced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 ) 顧問。我們班上有一半同學後來走半導體,都是因為修了他開的課,像台積電的研發領導:蔣尚義、胡正明,當年和我同班念這門課。
當時大學生,尤其台大電機系,畢業後幾乎沒有人留在國內。但是,想要出國留學,絕大部分人都需要獎學金,很少人能自費留學的,因為幾乎不可能,除非家境真的很好。
那時台大電機系畢業的學生在國內,可以做研究工作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方賢齊(時任電信總局局長)在電信總局以下、剛剛設立不久的電信研究所。這是模仿美國Bell Lab(貝爾實驗室)設立的研究單位。其他比較好的工作機會就是到外商公司,或是到加工出口區。當時李國鼎先生(時任經濟部長)已經在推加工出口區,來台投資的外商都是在那裡做組裝(assembly)。再有,就是留在學校當助教。
史欽泰想要學半導體,出國留學更是必要的選項。
「當時沒有什麼資訊,也不知道如何選擇學校,總是多少是看先前學長的經驗,很幸運的,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錄取了我,同時提供獎學金,因此,我就到美國去了。」史欽泰回想當年的經濟條件,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這筆獎學金,他不可能出國留學。
我大學修了課,覺得半導體蠻好的,也知道了普林斯敦大學有半導體。普林斯敦給我獎學金,一個月大約100多塊美金(大約是180 美金,那時候1美元約是40塊台幣),再包括免學費,那時候只知道生活沒有問題。到了美國,覺得每樣東西都貴,買不下手,我是窮慣的人,不成問題。後來考過試,奬學金增加,有200多塊,日子就過得比較好。
很多同學必須要先借錢。像我先出去,我就把錢存下來寄給同學當作保證金,要有保證金才能出國,所以我們的錢是彼此在周轉;留學生在美國打工也蠻多的。
回想起來,我去普林斯敦也是很奇妙的緣份。第一,我不認識這個學校,只是有三個台大電機學長在那裡念書。第二,居然有獎學金,學校名字聽起來也不錯。那時候資訊很少,都靠前人的線索。打造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第一批先鋒當中:楊丁元、史欽泰、章青駒,這三位台大電機系前後期學長弟,也是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前後期學長弟。他們正是當年回國短期教學的方復先生,播下的種子!
茄萣鄉,位在台南與高雄的交界。它是一個小漁村,茄萣外海是絕佳魚場,小小的漁村,曾經有80% 的人是漁夫。地名的源起,一說是平埔族語「多魚之地」的音譯,另一說是海邊紅樹林樹種之一的茄萣仔,荷蘭人則在地圖上標示為「漁夫角」。
史欽泰的祖父有小學畢業學歷,在鄉下已經算是很有學問的人,國民政府來台後實施地方自治,找人當議員,他的祖父曾因此當過地方上的議員。在史欽泰的印象中,當時並不了解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很多人來找祖父,好像他是地方上比較公正的人。祖父60幾歲就過世了,從政也未曾是這個家庭的志向。
他的回憶裡:
茄萣是窮得不得了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是住茅屋,地面是泥土,只要一下雨都是滑滑的。 那時候晚上非常暗,沒有電,不太有人會在晚上做什麼重要的事,多半悠閒在外面乘涼、看星星⋯。
那時代物資少,沒有鞋子上學,鄉下都是這樣。一方面是窮,一方面鄉下也就是這樣。我記得第一年小學的書包是我媽媽縫的,因為她去學裁縫,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母親自己做的。
茄萣小狀元
因著父親工作關係,小學階段,史欽泰整整唸過三所不同的學校。
史欽泰的父親學農,在台糖工作,被派駐到偏僻的農場種甘蔗,因為必須巡看蔗田,就和蔗田、蔗農生活在一起。農場通常只有三四戶人家,對外交通只有倚賴載送甘蔗的小火車,而且,也只有在運送甘蔗的時候,小火車才會開進農場。
如此一來,上學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由於茄萣的老家離小學比較近,父親自顧不暇,史欽泰在小學一、二年級階段,就跟著阿嬤生活、上學。童年回憶裡,陪阿嬤回娘家的路如此清晰:
我阿嬤的娘家在湖內,茄萣到湖內之間有公墓,遇節慶陪我阿嬤回去,走路要走將近一個鐘頭才回得到家裡。湖內那邊是使用井水。
後來有人幫農場那幾戶人家做零星的工作,每天運用台車(一塊木板加四個輪子的交通工具)出入,也順便買菜帶回來給太太們。雖然交通仍舊很不方便,小孩子總算可以跟著去上學。
因此,到了三、四年級,他回到家裡,跟著兩個弟弟一起坐台車去唸書。五、六年級時,因為父親又調職,比較接近麻豆糖廠,他轉學到麻豆鎮念文正小學。幾乎每個學校念兩年,很難交朋友,對小學同學也都沒什麼印象。多年後,他參加小學同學會,大家記得的,就是:「那個來一下就走掉的,很厲害!」出生在這個都是漁夫、魚塭的窮漁村,想升學、攻取美國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事,也完全不在史家的規畫當中。史欽泰說:
父親已經算是那個時代比較好的職業,所以我也沒什麼理由不唸書。三兄弟中我唸書比較好,我是念書很順,並不是父母有特別的計畫。
在鄉下,升學不易。史欽泰就讀文正國小時,每一個年級最多兩班,讀升學班,就到城裡考試,另一班則是不升學的。升學班裡,看起來更有能力的送到台南考試,其他同學就參加縣或鄉鎮的中學、農專、技職學校⋯⋯等的入學考試。
當時老師挑了12個學生到台南去考聯招(當時是初中),12個人都上榜!但是在鄉下唸書,程度其實跟不上,第一年大部份同學都留級,最後只剩下三個人能夠初中準時畢業。
初中三年以後再考高中,史欽泰順利考入台南一中。高中畢業之際,台灣還有保送大學的制度,他正是符合保送大學資格的學生之一。他選擇進入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大學的選擇,鍾情半導體
他記得當時台南一中前幾位同學都選擇台大醫學系。傳統上,台灣人多半最希望孩子念醫,特別是中南部。史欽泰卻不想:
我基本上不願意當醫生,因為我覺得時間不自由,好像被關在醫院, 覺得蠻無聊的。再者,我想,醫生每天都面對痛苦的事,痛苦的臉。我喜歡到處去看東西,我認為醫生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排斥,選擇保送到台大電機。
當時他完全不理解這個選擇將帶來的影響,電機系做什麼?他只知道是理工、是科學:
當時我只知道發電機、馬達啊,這些傳統的東西,根本不知道電機將來是什麼樣子,資訊很有限。我的爸媽完全讓我自己選擇。
那個年代,讀書的人,尤其受高教育的人很少。
史欽泰進入大學是1964年,世界局勢仍然十分動盪,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已打了好幾年(1960年開始),而前一年──1963年11月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進入台大,知識領域豁然開朗,除了從老教授學習,最重要的新知識來源是來自海外的訪問學者、客座教授。
1960年代,台灣大學電機系裡,沒有教半導體的專任師資。當時偶而有海外學人願意回國短期講學,每一年台大電機大約會邀請兩、三位訪問學者回來,講授他們正在進行的新領域,可以說,都是當年台灣教授開不出來的課。史欽泰因此有機會聽到積體電路,進而下定決心要走這個領域。他回憶道:大四那一年,我們班基本上是兩個出路,一邊是半導體,一邊是電腦,這兩個方向都有國外回來的客座專家;我雖然兩邊的課都有選,但後來慢慢偏半導體。當時半導體的客座專家就是回台灣的IBM研究員方復先生-他現在是中研院院士,也是工研院早期前瞻科技指導委員會(ARAC,Advanced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 ) 顧問。我們班上有一半同學後來走半導體,都是因為修了他開的課,像台積電的研發領導:蔣尚義、胡正明,當年和我同班念這門課。
當時大學生,尤其台大電機系,畢業後幾乎沒有人留在國內。但是,想要出國留學,絕大部分人都需要獎學金,很少人能自費留學的,因為幾乎不可能,除非家境真的很好。
那時台大電機系畢業的學生在國內,可以做研究工作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方賢齊(時任電信總局局長)在電信總局以下、剛剛設立不久的電信研究所。這是模仿美國Bell Lab(貝爾實驗室)設立的研究單位。其他比較好的工作機會就是到外商公司,或是到加工出口區。當時李國鼎先生(時任經濟部長)已經在推加工出口區,來台投資的外商都是在那裡做組裝(assembly)。再有,就是留在學校當助教。
史欽泰想要學半導體,出國留學更是必要的選項。
「當時沒有什麼資訊,也不知道如何選擇學校,總是多少是看先前學長的經驗,很幸運的,普林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錄取了我,同時提供獎學金,因此,我就到美國去了。」史欽泰回想當年的經濟條件,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這筆獎學金,他不可能出國留學。
我大學修了課,覺得半導體蠻好的,也知道了普林斯敦大學有半導體。普林斯敦給我獎學金,一個月大約100多塊美金(大約是180 美金,那時候1美元約是40塊台幣),再包括免學費,那時候只知道生活沒有問題。到了美國,覺得每樣東西都貴,買不下手,我是窮慣的人,不成問題。後來考過試,奬學金增加,有200多塊,日子就過得比較好。
很多同學必須要先借錢。像我先出去,我就把錢存下來寄給同學當作保證金,要有保證金才能出國,所以我們的錢是彼此在周轉;留學生在美國打工也蠻多的。
回想起來,我去普林斯敦也是很奇妙的緣份。第一,我不認識這個學校,只是有三個台大電機學長在那裡念書。第二,居然有獎學金,學校名字聽起來也不錯。那時候資訊很少,都靠前人的線索。打造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第一批先鋒當中:楊丁元、史欽泰、章青駒,這三位台大電機系前後期學長弟,也是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前後期學長弟。他們正是當年回國短期教學的方復先生,播下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