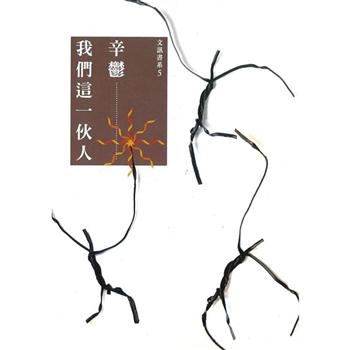他為自己點起一盞長明燈——簡述向明
那年,與向明遊浙東,有一個晚上我們借宿新安江旁的一家小旅店。屋外水聲潺潺,有月光斜射進窗,我們聊著各自家鄉的小吃。話題不知怎麼突然一轉,轉到民國三十八年國家最危急的那段日子,我說:很想把那段日子忘掉。向明說:我也想忘,但是忘不了。我說:那麼你把它寫下來。向明說:我遲早會寫。
時隔十年,向明終於噙著淚水,寫下〈滄桑我的一九四九〉。我讀著讀著,也不禁為之淚沾衣襟;他的遭遇比我更慘。同時,我也明白了他走路雙腳稍有失衡的原因。
以詩消除人間苦痛
與向明認識在詩人夏菁家裡,但記不起日期。那天,秦松拉我去夏菁先生家,說是夏府有好吃的,而且,覃子豪先生也在座。我因嘴饞所以膽壯,跟了秦松去。在夏府認識了多位年長於我的詩人,其中之一是向明。我記得他穿著空軍官服,英挺灑脫的靜立在子豪先生身後,向我點頭招呼。
飽餐後告辭出門,才想到自己冒失,想回身向夏菁先生道歉,迎面的卻是向明,他笑一笑,然後說:
「我們才見一次面,就又要告別。」
我來不及問何故,向明說:「過幾天我就要去馬祖。」
向明那時在空軍通信單位服役,調遷頻繁,身不由己。
我們沒有說再見。第二次見面,是一年之後,在台大醫院覃子豪先生的病榻旁。
向明那時已婚,家在台北市公館後側的山丘上,屬違建,所以十分簡陋,我去過兩次,一次還吃了董大嫂包的餃子,道地的北方口味。
〈滄桑我的一九四九〉一文末段,向明寫到學習與自省,除了上補習班讀英文之外,也開始接觸文學,特別是詩。他念念不忘斷腿之痛,因而雖身在軍中,卻興起「反戰」之思。並且,從那時起確立了詩人應強烈反戰,反一切非公義的與不人道的作為;詩人,認識了痛苦,更應為消除人間痛苦服役。
向明早期的詩作中,確有些作品明白的表達反戰——如〈靶場那邊〉一詩,與反人性傷害(亦即白色恐怖)的意念——如〈今天的故事〉一詩。
不斷拓寬文學視野
在軍中,向明從上等兵一直幹到上校,要不是憑著一股「不斷向前」的意念,絕難辦到。他曾多次被派往外島,設立通訊網。在外島沉悶的生活環境中苦讀,終於獲得升遷,擺脫苦役,調回本部。並且,由於多年勤學扎下的英文功夫,曾多次獲得遠赴美國、以色列等地觀摩與進修的機會。不但增加見聞、知識,更結交多位異國朋友。
寫作方面,也因接觸面的拓寬,由詩擴及雜感隨想與論述。同時為增加收入貼補家用,由翻譯一般文件而書籍,有一段時間,外接工作幾難應付。
說到雜感隨想,向明曾與羊令野、商禽、大荒、辛鬱在現已停刊的《民族晚報》副刊,開闢「三人行」專欄。每日一篇 (七百字左右),為時七年。其間商禽只寫了一個短時期,大荒也因身體不好,斷斷續續的寫,羊令野只在專欄初設時寫了一年多,大多由向明與辛鬱供稿。如今檢視當年所寫的「三人行」七百字專欄,真是不勝感慨。因為「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們當初開此專欄,旨在給讀者一點啟發,所以特別偏重教育與青年問題。卻忽略了,晚報的讀者,幾乎以較年長者為主,而且,大多是下了班的職場人士,他們喜歡的,應該是談天說地、海闊天空的消閒文字。這常令我回想而自問是不是多此一寫?不知向明兄作何感想,但我知道他很珍惜那些短文。
卸脱軍裝,一度曾有向明要去《聯合報》副刊之說,後來卻去了《中華日報》副刊,幫蔡文甫主編的忙。多年下來,經由《中華日報》副刊而認識並結交多位文友,並且,更多的閱讀與更多的思考,也為日後做一個專職寫作人,積儲了不少能量。
其間,主編《藍星詩刊》,也讓他體會從忙中品味人生的苦樂,藉此而窺視人性的不同層面與內外表裡。
照亮了崎嶇的詩路
文學圈中,向明有「儒雅」之形,有人喜呼為「老帥哥」,所以也常與異性文友共研詩藝,極被她們看重。在這方面,我是自嘆不如的。
向明自《中華日報》退休後,《藍星詩刊》因後援撤手而宣告停刊,個人時間較多,經我邀約而參與我們一年一次的大陸行,幾年下來,我們的足跡遍及名山勝川,各佛家勝地,多個文化遺址。有一次,我們二人行,以杭州為中心,遍遊寧波、紹興、嘉興、瑞安等地,一路上,有幾位青年詩人陪伴,不但得到極大的尊重,也真正體會到江南風物人情的美善。向明回台後,曾有詩、文紀行。
這樣的旅遊,後因某事件的發生而中止,如今想來,有多處規劃的行程尚未完成,不免有遺憾之感。偶爾興念重組這一小團體,卻因同好均已白髮蒼蒼,不勝腳力,只好打消此念。
一九九二年三月,向明與多位中生代詩人共組《台灣詩學季刊》並任首屆社長,他曾有文記述:「....是我詩生命的第二度挑戰,因為我大膽的誤入由學院為班底的詩人及詩評家陣營,他們個個都是國內外文學博士,惟我一人行伍丘八出身,且年歲虚長,我真是有點自不量力。」
其實,向明說得太過謙虛。以他的創作實力、辦刊經驗,足可為其他人的範式。何況,所謂「寶刀未老」,他多年積儲的創作能量,必有推波助瀾作用。果然,直到當今,向明的詩與文,幾乎未曾在任何一期中缺席。
近年來,向明更為「七絃」這一詩人組合的主力。「七絃」者,七位詩人也。這一組合,純粹為了寫詩、愛詩的共同興趣。組成之後,每個月集會一次。或品茗或飲酒,由一詩人作東,七人輪流。就像七根琴絃,平日各自發聲,每月合奏妙音,條件是,聚會中必須提出新作。如今「七絃」詩人組合,已出版第二冊詩集,名為《七絃——食餘飲後集(二)》。七位詩人為向明、曹介直、朵思、艾農、鍾雲如、張國治、須文蔚。
勤於創作,是向明這些年被公認的特色,同時,他也勤於四處奔波,為聯繫詩的情誼。他為自己點起一盞長燃的燈,照亮了崎嶇的詩路,邁向康莊!
那年,與向明遊浙東,有一個晚上我們借宿新安江旁的一家小旅店。屋外水聲潺潺,有月光斜射進窗,我們聊著各自家鄉的小吃。話題不知怎麼突然一轉,轉到民國三十八年國家最危急的那段日子,我說:很想把那段日子忘掉。向明說:我也想忘,但是忘不了。我說:那麼你把它寫下來。向明說:我遲早會寫。
時隔十年,向明終於噙著淚水,寫下〈滄桑我的一九四九〉。我讀著讀著,也不禁為之淚沾衣襟;他的遭遇比我更慘。同時,我也明白了他走路雙腳稍有失衡的原因。
以詩消除人間苦痛
與向明認識在詩人夏菁家裡,但記不起日期。那天,秦松拉我去夏菁先生家,說是夏府有好吃的,而且,覃子豪先生也在座。我因嘴饞所以膽壯,跟了秦松去。在夏府認識了多位年長於我的詩人,其中之一是向明。我記得他穿著空軍官服,英挺灑脫的靜立在子豪先生身後,向我點頭招呼。
飽餐後告辭出門,才想到自己冒失,想回身向夏菁先生道歉,迎面的卻是向明,他笑一笑,然後說:
「我們才見一次面,就又要告別。」
我來不及問何故,向明說:「過幾天我就要去馬祖。」
向明那時在空軍通信單位服役,調遷頻繁,身不由己。
我們沒有說再見。第二次見面,是一年之後,在台大醫院覃子豪先生的病榻旁。
向明那時已婚,家在台北市公館後側的山丘上,屬違建,所以十分簡陋,我去過兩次,一次還吃了董大嫂包的餃子,道地的北方口味。
〈滄桑我的一九四九〉一文末段,向明寫到學習與自省,除了上補習班讀英文之外,也開始接觸文學,特別是詩。他念念不忘斷腿之痛,因而雖身在軍中,卻興起「反戰」之思。並且,從那時起確立了詩人應強烈反戰,反一切非公義的與不人道的作為;詩人,認識了痛苦,更應為消除人間痛苦服役。
向明早期的詩作中,確有些作品明白的表達反戰——如〈靶場那邊〉一詩,與反人性傷害(亦即白色恐怖)的意念——如〈今天的故事〉一詩。
不斷拓寬文學視野
在軍中,向明從上等兵一直幹到上校,要不是憑著一股「不斷向前」的意念,絕難辦到。他曾多次被派往外島,設立通訊網。在外島沉悶的生活環境中苦讀,終於獲得升遷,擺脫苦役,調回本部。並且,由於多年勤學扎下的英文功夫,曾多次獲得遠赴美國、以色列等地觀摩與進修的機會。不但增加見聞、知識,更結交多位異國朋友。
寫作方面,也因接觸面的拓寬,由詩擴及雜感隨想與論述。同時為增加收入貼補家用,由翻譯一般文件而書籍,有一段時間,外接工作幾難應付。
說到雜感隨想,向明曾與羊令野、商禽、大荒、辛鬱在現已停刊的《民族晚報》副刊,開闢「三人行」專欄。每日一篇 (七百字左右),為時七年。其間商禽只寫了一個短時期,大荒也因身體不好,斷斷續續的寫,羊令野只在專欄初設時寫了一年多,大多由向明與辛鬱供稿。如今檢視當年所寫的「三人行」七百字專欄,真是不勝感慨。因為「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們當初開此專欄,旨在給讀者一點啟發,所以特別偏重教育與青年問題。卻忽略了,晚報的讀者,幾乎以較年長者為主,而且,大多是下了班的職場人士,他們喜歡的,應該是談天說地、海闊天空的消閒文字。這常令我回想而自問是不是多此一寫?不知向明兄作何感想,但我知道他很珍惜那些短文。
卸脱軍裝,一度曾有向明要去《聯合報》副刊之說,後來卻去了《中華日報》副刊,幫蔡文甫主編的忙。多年下來,經由《中華日報》副刊而認識並結交多位文友,並且,更多的閱讀與更多的思考,也為日後做一個專職寫作人,積儲了不少能量。
其間,主編《藍星詩刊》,也讓他體會從忙中品味人生的苦樂,藉此而窺視人性的不同層面與內外表裡。
照亮了崎嶇的詩路
文學圈中,向明有「儒雅」之形,有人喜呼為「老帥哥」,所以也常與異性文友共研詩藝,極被她們看重。在這方面,我是自嘆不如的。
向明自《中華日報》退休後,《藍星詩刊》因後援撤手而宣告停刊,個人時間較多,經我邀約而參與我們一年一次的大陸行,幾年下來,我們的足跡遍及名山勝川,各佛家勝地,多個文化遺址。有一次,我們二人行,以杭州為中心,遍遊寧波、紹興、嘉興、瑞安等地,一路上,有幾位青年詩人陪伴,不但得到極大的尊重,也真正體會到江南風物人情的美善。向明回台後,曾有詩、文紀行。
這樣的旅遊,後因某事件的發生而中止,如今想來,有多處規劃的行程尚未完成,不免有遺憾之感。偶爾興念重組這一小團體,卻因同好均已白髮蒼蒼,不勝腳力,只好打消此念。
一九九二年三月,向明與多位中生代詩人共組《台灣詩學季刊》並任首屆社長,他曾有文記述:「....是我詩生命的第二度挑戰,因為我大膽的誤入由學院為班底的詩人及詩評家陣營,他們個個都是國內外文學博士,惟我一人行伍丘八出身,且年歲虚長,我真是有點自不量力。」
其實,向明說得太過謙虛。以他的創作實力、辦刊經驗,足可為其他人的範式。何況,所謂「寶刀未老」,他多年積儲的創作能量,必有推波助瀾作用。果然,直到當今,向明的詩與文,幾乎未曾在任何一期中缺席。
近年來,向明更為「七絃」這一詩人組合的主力。「七絃」者,七位詩人也。這一組合,純粹為了寫詩、愛詩的共同興趣。組成之後,每個月集會一次。或品茗或飲酒,由一詩人作東,七人輪流。就像七根琴絃,平日各自發聲,每月合奏妙音,條件是,聚會中必須提出新作。如今「七絃」詩人組合,已出版第二冊詩集,名為《七絃——食餘飲後集(二)》。七位詩人為向明、曹介直、朵思、艾農、鍾雲如、張國治、須文蔚。
勤於創作,是向明這些年被公認的特色,同時,他也勤於四處奔波,為聯繫詩的情誼。他為自己點起一盞長燃的燈,照亮了崎嶇的詩路,邁向康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