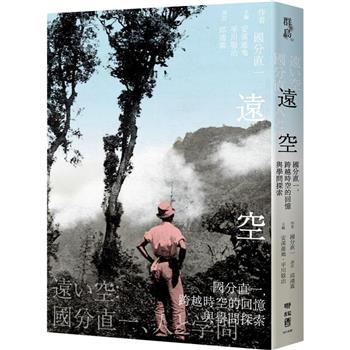嘉南平原的正中央有一個叫做大莆林的小村莊。東邊越過一望無際的甘蔗田後,可以遠望蜿蜒的新高連峰。這裡到山腳地帶為止距離三里,到海岸距離有十里多,北邊跟南邊接續著無限的平原。
父親是這個村子的三等郵局長。我在昭和八年九月,大約四年後睽違已久地從京都回來。「大哥幾年不見,還是一樣瘦巴巴的,」弟弟們笑著迎接我,「很對不起送過去的東西沒辦法滿足你,但我很開心看到你回來氣色很好。」母親高興得手足無措。父親還是父親,他不懂思想運動但還是很擔心我。
「你去女子學校教書,女生很難理解的,要是你姊姊還在就好了,可惜很早就死了。」他還是把我當作小孩子一樣。
那天晚上,父親很感慨地說:「你也長大了,我想有一天我們就回去內地吧。」
曾經聽說過家裡的兒子只要有一個從學校畢業了,大多不久就會傳給後面的新人,但是卻發生了「不足為外人道的問題」。
中學三年級的多可司抓著頭說:「是我的事情。」四年級的四方司憤慨地說:「多可司那個傢伙只會打架鬧事而已。」
我問父親不足為外人道的問題是怎麼回事,才知道多可司揍了某位有權勢官吏的兒子(父親是這麼說的)。因為這位兒子寫情書給多可司朋友的姊姊,所以就說他軟弱然後揍了他。被害人的父親到學校進行了很強勢的談判,結果是多可司受到無限期停學的處分,然而校長似乎沒有想要息事寧人的意思,甚至說孩子不好是因為父母也不好。父親用著平靜的語調說起這件事,並沒有很激動的情緒,母親則熱淚盈眶。
我出發去臺南赴任之前,想要與說這個話的人談談,隔天就去了嘉義中學。校長渡邊節治先生上半身前傾,稍微四方形的臉且臉色鐵青,看起來有點神經質。
「啊你就是大哥嗎?國分是問題學生,不管怎麼說像他這種體格,每次一說到打群架都有他的份。上面的哥哥是很沉穩,但三年級的國分很令人困擾。他在我的修身課上發出怪聲音,還公然的叫我螃蟹。一定是三年級的國分對著我就讀嘉義高等女學校的女兒說他是『螃蟹的孩子O型腿』,這種學生會妨礙教育的,雖然是無限期停學,但就算要轉學也沒地方要收吧。」
校長連讓我說句打招呼話的空隙都不給,一口氣說完這些話。
把學生教成這樣,學校方面也有一些責任吧,我雖然無意間變得反抗,但也不得不感到慚愧,只能隱藏起悲哀就此罷休。
校長突然把靜靜地要離開的我叫住,問我「你在做什麼工作啊?」我回答:「我最近從京都回來,接著要去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赴任。」之後校長帶點輕視的眼神看著我說:「是那個京大事件的京都大學吧。」接著又說:「大學畢業不能太馬虎呢,外地有外地的特別情況。你啊,不能沒有考慮到你還穿著這一身服裝。」校長不帶一點感情,穿著那身白色,在這個土地被叫做官服的制服。
穿著這個服裝行走的人們,每個人都意識到了什麼?應該沒有公僕的自覺,而是覺得自己是在民眾之上的官員,具有這樣的外地官僚意識吧?這比配著槍劍喀嚓喀嚓作響走在路上的時代還要奇怪,我離開時心裡抱持著這種想法。
後來父母帶著弟弟們回到母親的故鄉靜岡,因為這是自從父親在明治四十一年來臺以來第一次回內地,多可司一個人開心的說:「爸爸像浦島太郎一樣。」我也突然想要跟大家一起再回去內地,但因為父親說:「自己想要葬身於這片土地,但卻無法實現真的很可惜。雖然我是貧窮的官吏,但完全想不起來自己做了什麼事情值得回憶而感到空虛。所以哪怕只有你,留在臺灣工作好嗎?」雖然沒有自信可以留下來工作,但也就不再想了。
多可司一本正經的說:「大哥加油喔。」臉上帶著止不住感傷的表情,然後跟四方司兩個人得意的拉著大行李箱走在父母親前面,父母親也在這種氣氛下笑著出發了。
雖然已經到九月底了,頭上還是頂著大太陽,但正因為父母的笑容還有弟弟們意氣風發的樣子,可說是幫我在這片土地上開拓了一條生存之道。
後來,多可司的同年級同學,渡邊校長的長男春一君,把校長私藏的春宮圖帶到學校給同學們看而引起問題。這個人好像也追隨多可司的腳步,回去了內地。
二
臺南來到了各個大街小巷都無法避免沙塵滿天的季節。
在大約可以容納一個師團軍隊的站前廣場,其中的一個角落,矗立著一棵巨大有如森林中的木棉樹一般、彷彿知道這條街道所有歷史的榕樹。西邊是一條筆直朝下的人力輕便車道,顯示出這裡是向西邊傾斜著,榕樹底下有一條種植美麗鳳凰木的道路朝著南邊。從這條路走沒多久,會有一個圓環,圓環的緬甸合歡樹影下立著白色兒玉先生像從那邊經過古色古香的州廳舍洋樓和具有廣東風格美感的兩廣會館,再走幾步路就到了官舍街。在南邊角落有一棵大柳樹的房子左轉之後,走到盡頭是供奉鄭成功的開山神社的紅色圍牆,在走到紅色圍牆盡頭的南邊山丘上座落著一間寧靜安定的學校。
進了大門後,在玄關的前面有一棵白色樹皮的木棉樹,像是學校的象徵一般,矗直地朝著天空生長木棉樹。
到職第一天,我面對著一群可愛少女,她們的聲音年輕、稚嫩,總帶著像是要捉弄你的視線,讓人想摸摸她們妹妹頭;站在讓人感到已經成長為女性的少女當中,我開始後悔千里迢迢地為了工作來到這裡,因為對於深住曼殊院僧房的我來說,這裡像是會讓人心力交瘁的世界。
校長是松平治郎吉老師,這裡一半的教師,或許超過一半以上都是女性。
松平校長是我中學時代的恩師。他自由的思考方式讓我感到新鮮,是最吸引我的老師。
但當在我站在好久不見的老師面前,因為太懷念而說不出話來的時候,老師突然說:「你的履歷表的字很糟糕欸。」接著問:「你有先去見過臺北的督學再過來吧?」我回答沒有去過,結果老師開始叱責:「你應該要帶著伴手禮,殷勤地去拜訪督學才對!」「在這所學校,不管是學務主任還是總務主任,都一定要帶點東西去打招呼,你怎麼這麼粗心,以後不能這樣。」
「你怎麼剪了一頭披散的短髮,都沒有留長過嗎?」
接著又像是訓誡我一般地說著:「高年級學生的精神年齡都超過你。」「老師在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教我做人處世的道理,不,他是看到我還是像個中學生一樣而感到不滿吧。」我感到越來越渺小了。
「老師已經變了。」雖然我這麼想,但那個晚上我還是像被趕走一樣的搭上急行列車,到臺北新起町的市場,買了好幾箱內地產的二十世紀梨準備出門。
我帶著二十世紀梨去拜訪主任督學大浦精一老師,老師是我高等學校時代的恩師,所以感覺不僅僅是督學而已。他是以寡言嚴謹著名的人,所以我想如果送了二十世紀梨的話,一定會被他喝斥的,在我惶恐的敲了老師家玄關的大門時,「啊,終於回來了。」老師燦爛得笑著來歡迎我。
老師跟我說了很多話,最後說:「我很愛喝酒,也會請藝伎,舞蹈也變好了。」「老師做這些通俗的事情也是在展示累積社會經驗的方法,是督學官這樣的地位讓老師變成這樣的人嗎?會讓老師接近酒和女人,都是怎麼樣的人呢?」在我想到出神的時候,「你啊,在女子學校可不能整天嘻嘻哈哈的。」老師突然又變回很正經的樣子,話題也轉到時代的思想了。
「松岡洋右和中野正剛等都提出了正確的主張,權藤的理論也應該要關注,就是回歸日本精神。但是臺灣這個地方,你太悠哉了,每次到一些研究會的時候還是會擁戴裴斯泰洛齊的思想。」
「上任後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做好授課的細項。」
恩師大浦老師消失了,主任督學官大浦老師時不時強壓的樣子映在我的眼中。
後來我去拜訪了庄司萬太郎老師,以前有聽過他的西洋史的課,膚色黝黑,身材高大的老師和嬌小的太太一起接待了我,用親切溫暖的話語告訴我,從現在起要努力精進,發掘出臺灣的歷史。
在談話的當中,老師問到月薪多少,完全不知情的我回答:「我還沒有詢問。」老師就說:「你太隨性了,應該有五等,是在四月任官沒錯吧。」
什麼是五等?我不知道什麼是任官。
多虧了二十世紀梨,讓松平校長的心情變得好多了。「老師的確是變了,但是什麼讓老師變成這樣的呢?」
「從內地佛教學校來的善良老師,之後,也許是數年來在這塊土地的官僚氣息中學到了很多事情,漸漸地改變了處世之道以及對事情的看法吧?」
老師對我很不滿,但我在心中感到很難過。
我在一個地名很有趣、叫做桶盤淺的臺地上租房子,吃飯都是去附近的公寓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