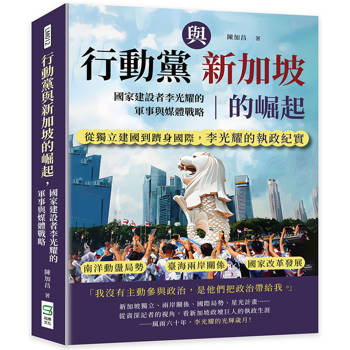日本把李光耀帶上政治之路
新加坡共和國開國總理李光耀是在1954年組織人民行動黨直接參加政治的,但是,在這之前,他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一般人並不是很清楚。
李光耀曾說,第一次使他傾向問政的,是在日軍占領新加坡的三年半期間(1942-1945)的一場經歷。當時是新加坡淪陷時期,日本人把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李光耀十八九歲的某一天,經歷了一場可能改變他一生命運,也可能改變新加坡歷史的「大檢證」。
李光耀回憶說:「日軍占領新加坡初期,有一天,我像其他數以千計的青年,在集中營受『檢證』。有一部分青年被送到另一邊,那是死路。我本能地覺得情形不對,於是要求看守的日本憲兵准許我回家拿一些個人的物件,非常幸運獲准。我從此一去不再回頭,『檢證』的事也就逃過去。」由此刻起,日軍開始統治新加坡三年六個月!
脫險之後,李光耀作了很多思考,這段期間,他打定主意要擺脫外國人的奴役與統治。這也是他後來在新加坡光復後決心打倒英國殖民地主義者,爭取獨立自主的原因。
用李光耀自己的話說:「日本人從來不會知道他們對象我這樣一代人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他們卻確實造成我及和我同一代人的決心,致力於爭取自由,擺脫外國人的奴役與統治。」
他在回憶錄中說:「日本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經歷最重要的階段,讓我有機會把握觀察人們的行為,把人類社會及人們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這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還多。」
李光耀說:「我沒有主動參與政治,是他們(日本)把政治帶給我。」
但是李光耀的實際政治傾向應該是戰後他去英國留學,進入劍橋大學後才嶄露。
和許多其他來自殖民地的學生一樣,李光耀參加了後來馬來亞聯合邦政府第一任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創立的「馬來亞論壇」,這是一個讓來自馬來亞及新加坡留學生討論政治的平臺。
李光耀這時已經擺出「學長」樣子,經常不厭倦地勸告其他留學生說,你們像我這樣有非常難得的機會出國深造,因此,回國後就得對國家肩負起更重大的責任。
論壇的成員中,突出人物有新加坡的開國元勛正副總理李光耀及吳慶瑞,有馬來亞(後來馬來西亞)的東姑首相和副首相敦拉薩克。也有幾十年來自始至終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不願屈服於當權派的左翼知識分子。
當時(1948年),馬來亞半島已經發生共產黨(馬共)發動的武裝叛亂,英國殖民地政府跟著宣布新馬兩地進入「緊急狀態」。李光耀這名年輕人公開表明不贊成他的國家由一個共產黨政權統治。但是,他也公開表明服膺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其實這也是許多留學生的時尚思想。他口才好、學識豐富,被「馬來亞論壇」選派代表馬來亞出席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社會主義青年會議。馬來亞共產黨駐歐洲代表林鴻美(林豐美)當然也出席了。在倫敦留學的幾位同學包括李光耀的弟弟李金耀及吳慶瑞等人也去觀光。
大會通過的議案中,包括一項爭取新加坡及馬來半島在內的馬來亞獨立,正如所預期的,李光耀和新馬的留學生們都支持這項議案。
在當時,共產黨及大部分國家都視馬來亞和新加坡是一體,他們不了解英國在戰後已將新馬兩地行政系統分開。
當布達佩斯的共產黨報紙刊登這則支持馬共為爭取國家獨立而抗爭的議決案的新聞時,把李光耀和其他出席人士的照片擺在一起。關注學生課外可能涉及「顛覆」殖民地政府活動的駐布達佩斯的英國大使館,即刻把有關剪報寄回倫敦。1950年8月,李光耀完成學業回來新加坡時,即刻被警方召喚到羅敏申路隸屬刑事調查局的「政治部」接受盤問,解釋為何他的照片會登在共產黨的黨報上。
新加坡治安當局如此緊張是很自然的事。當時的新加坡已進入緊急狀態,馬共製造社會混亂,另一面中共建政伊始,衝擊著當地的華人(僑)社會,朝鮮戰爭也已爆發,是燃燒歲月的開始。
李光耀此時福星高照,遇到了貴人,負責盤問他的是一位英籍政治部警官柯里頓。柯經過冷靜鄭重評估李光耀後,「網開一面」不逮捕他(在另一章節會有敘述)。
進入「昭南日本學園」
日軍完成全島島民「檢證」之後,開始以軍政統治新加坡。
社會治安逐漸恢復,市面交通如公共巴士及有線電車還受到川行路線和時間的限制,仍有不便,大部分市民和學生用腳踏車代步。
4月29日慶祝「天長節」日皇裕仁生日的第三天——5月1日,由軍政監部宣傳班創辦的第一所日本語文學校便正式開課,那是日軍占領新加坡兩個半月後的事。
據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考慮到「如果在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不得不去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2日(開課第二天)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分三個月一學期,於7月參加畢業典禮。」
李光耀的回憶錄說學校是在奎因街,校長是神保(光太郎),但沒有提到校名。這裡我想補充一些學校的背景來協助理解征服者的教育政策。很巧的,我也是第一期的學生,那年,我未滿11歲。
小坡三馬路奎因街只有一所日本學校,叫「昭南日本學園」,位於舊公教中學及天主教堂隔鄰一棟兩層的白色洋樓。樓上樓下教室分別為「富士班」、「櫻花」、「南」及「日之丸」上下午班。1945年日本投降後,這棟洋樓被馬來亞共產黨星洲市委會使用,隨著當局1948年6月頒布緊急法令,馬共隨即轉入地下,空樓便改為史丹卜民眾聯絡所。現在已擴建為商用大樓。
幾十年來我不敢「冒昧」透露我曾經是李光耀戰時(1942年)「昭南日本學園」第一期同校不同班同學。我是樓下「櫻花」班學生,老師是矢崎浩。李光耀是在樓上的教室上課,我不清楚是哪一班,也不認識他,只記得樓上的教室掛有天皇的「神像」,樓下則沒有,也不可以掛,因為「神像」之上不能讓任何物件壓頂,更不允許任何人的腳底「踩踏」。書本第一章便已告訴我們:天皇是「神」,不是人。
1950年,李光耀從英國留學回來,多年後成了行動黨的立法議員,也擔任從事學潮與工潮者的法律顧問,直到就任總理。這時,我們都出來社會工作了。有一天,我的姐夫(我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都在同一間日語學校念兩三年書)和我談起政壇上活躍的李光耀時,突然問起我知不知道他也曾在「昭南日本學園」唸過書。那時我還很小,單純得很,當然不知道。我不相信,以為姐夫認錯人,因為李光耀問政以來,只聽他說過日治時期曾在日本軍宣傳班工作一段短時期,從來沒有聽說他曾經在日本學校讀過書。
姐夫說,李光耀在班上給他深刻印象是因為李的英文講得很棒,口才很好,常在班上高談闊論,沒人能贏他。很明顯看出他鋒芒初露,超群出眾,也讓同學以為他是在炫耀自己的才華。多年後,我在李光耀出版的回憶錄(1923-1965)讀到他曾在奎因街的一所日本學校讀過日文的事,我才相信姐夫沒有張冠李戴。
我記得還有一個也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學吳信達。戰後他在一家華文中學教英文,後轉教育部,再受聘於華僑銀行任高職。他是著名(英文)小說家,國家圖書館還存有他的著作。
在回憶「昭南日本學園」時,李光耀提到「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有不同。其中有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李同學」這段話也許記錯了,那時20歲左右的工人應該是很少有機會上學。
據「昭南日本學園」校長神保光太郎在他一年任滿回國後著寫的《昭南日本學園》書中記載,學校開學時報名的各籍各階層人士甚多,第一期有320人(過後逐期增加到二、三千人),年齡由12歲到52歲(男女同學中,年長和年少的混在一班),其中16歲到20歲的青少年以華族學生最多,占三分之一,華族女生也有32人,占全校女生半數以上,其次是印度籍、再來是馬來籍、歐亞籍及其他國籍學生。
因年齡差別,功課上年紀小的同學必定比不上學長姐,但是念起日本文來,在同一班上不分年齡大小,大家是初次接觸到日文,第一次觸及日文50音。我有小學的中文底,淺的文字可以看懂讀懂,也不一定比原讀英校的大同學吃虧。幸好學校一視同仁,大小混在一個班。入學之初,花了一些日子,先學會唱日本歌。
入學前,我的年齡只有11歲,比規定入學年齡少一歲,不能報名,但已經報名入學的大姐向校長求情(另有一兄一姐也入學),我也獲准入學,這樣一來,我家裡兄姐四人便進了「昭南日本學園」。還有一位吳卓英同學也是11歲,也由已入學的哥哥吳漢英向校長說情而獲得名額。戰後,日本海運發展至世界各個港口,漢英在新加坡日本海員協會工作,又創辦日文夜校數十年,學以致用,直到退休為止。
我的兄姐都是適齡學生,大姐在萊佛士女校剛考完年底的劍橋高級文憑會考,太平洋戰爭即告爆發,當時擔心的是考卷由郵船運往英國途中,會被日機轟炸沉入海底。
新加坡共和國開國總理李光耀是在1954年組織人民行動黨直接參加政治的,但是,在這之前,他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一般人並不是很清楚。
李光耀曾說,第一次使他傾向問政的,是在日軍占領新加坡的三年半期間(1942-1945)的一場經歷。當時是新加坡淪陷時期,日本人把新加坡改名為「昭南島」。李光耀十八九歲的某一天,經歷了一場可能改變他一生命運,也可能改變新加坡歷史的「大檢證」。
李光耀回憶說:「日軍占領新加坡初期,有一天,我像其他數以千計的青年,在集中營受『檢證』。有一部分青年被送到另一邊,那是死路。我本能地覺得情形不對,於是要求看守的日本憲兵准許我回家拿一些個人的物件,非常幸運獲准。我從此一去不再回頭,『檢證』的事也就逃過去。」由此刻起,日軍開始統治新加坡三年六個月!
脫險之後,李光耀作了很多思考,這段期間,他打定主意要擺脫外國人的奴役與統治。這也是他後來在新加坡光復後決心打倒英國殖民地主義者,爭取獨立自主的原因。
用李光耀自己的話說:「日本人從來不會知道他們對象我這樣一代人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他們卻確實造成我及和我同一代人的決心,致力於爭取自由,擺脫外國人的奴役與統治。」
他在回憶錄中說:「日本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經歷最重要的階段,讓我有機會把握觀察人們的行為,把人類社會及人們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這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還多。」
李光耀說:「我沒有主動參與政治,是他們(日本)把政治帶給我。」
但是李光耀的實際政治傾向應該是戰後他去英國留學,進入劍橋大學後才嶄露。
和許多其他來自殖民地的學生一樣,李光耀參加了後來馬來亞聯合邦政府第一任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創立的「馬來亞論壇」,這是一個讓來自馬來亞及新加坡留學生討論政治的平臺。
李光耀這時已經擺出「學長」樣子,經常不厭倦地勸告其他留學生說,你們像我這樣有非常難得的機會出國深造,因此,回國後就得對國家肩負起更重大的責任。
論壇的成員中,突出人物有新加坡的開國元勛正副總理李光耀及吳慶瑞,有馬來亞(後來馬來西亞)的東姑首相和副首相敦拉薩克。也有幾十年來自始至終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不願屈服於當權派的左翼知識分子。
當時(1948年),馬來亞半島已經發生共產黨(馬共)發動的武裝叛亂,英國殖民地政府跟著宣布新馬兩地進入「緊急狀態」。李光耀這名年輕人公開表明不贊成他的國家由一個共產黨政權統治。但是,他也公開表明服膺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其實這也是許多留學生的時尚思想。他口才好、學識豐富,被「馬來亞論壇」選派代表馬來亞出席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社會主義青年會議。馬來亞共產黨駐歐洲代表林鴻美(林豐美)當然也出席了。在倫敦留學的幾位同學包括李光耀的弟弟李金耀及吳慶瑞等人也去觀光。
大會通過的議案中,包括一項爭取新加坡及馬來半島在內的馬來亞獨立,正如所預期的,李光耀和新馬的留學生們都支持這項議案。
在當時,共產黨及大部分國家都視馬來亞和新加坡是一體,他們不了解英國在戰後已將新馬兩地行政系統分開。
當布達佩斯的共產黨報紙刊登這則支持馬共為爭取國家獨立而抗爭的議決案的新聞時,把李光耀和其他出席人士的照片擺在一起。關注學生課外可能涉及「顛覆」殖民地政府活動的駐布達佩斯的英國大使館,即刻把有關剪報寄回倫敦。1950年8月,李光耀完成學業回來新加坡時,即刻被警方召喚到羅敏申路隸屬刑事調查局的「政治部」接受盤問,解釋為何他的照片會登在共產黨的黨報上。
新加坡治安當局如此緊張是很自然的事。當時的新加坡已進入緊急狀態,馬共製造社會混亂,另一面中共建政伊始,衝擊著當地的華人(僑)社會,朝鮮戰爭也已爆發,是燃燒歲月的開始。
李光耀此時福星高照,遇到了貴人,負責盤問他的是一位英籍政治部警官柯里頓。柯經過冷靜鄭重評估李光耀後,「網開一面」不逮捕他(在另一章節會有敘述)。
進入「昭南日本學園」
日軍完成全島島民「檢證」之後,開始以軍政統治新加坡。
社會治安逐漸恢復,市面交通如公共巴士及有線電車還受到川行路線和時間的限制,仍有不便,大部分市民和學生用腳踏車代步。
4月29日慶祝「天長節」日皇裕仁生日的第三天——5月1日,由軍政監部宣傳班創辦的第一所日本語文學校便正式開課,那是日軍占領新加坡兩個半月後的事。
據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考慮到「如果在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為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不得不去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2日(開課第二天)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分三個月一學期,於7月參加畢業典禮。」
李光耀的回憶錄說學校是在奎因街,校長是神保(光太郎),但沒有提到校名。這裡我想補充一些學校的背景來協助理解征服者的教育政策。很巧的,我也是第一期的學生,那年,我未滿11歲。
小坡三馬路奎因街只有一所日本學校,叫「昭南日本學園」,位於舊公教中學及天主教堂隔鄰一棟兩層的白色洋樓。樓上樓下教室分別為「富士班」、「櫻花」、「南」及「日之丸」上下午班。1945年日本投降後,這棟洋樓被馬來亞共產黨星洲市委會使用,隨著當局1948年6月頒布緊急法令,馬共隨即轉入地下,空樓便改為史丹卜民眾聯絡所。現在已擴建為商用大樓。
幾十年來我不敢「冒昧」透露我曾經是李光耀戰時(1942年)「昭南日本學園」第一期同校不同班同學。我是樓下「櫻花」班學生,老師是矢崎浩。李光耀是在樓上的教室上課,我不清楚是哪一班,也不認識他,只記得樓上的教室掛有天皇的「神像」,樓下則沒有,也不可以掛,因為「神像」之上不能讓任何物件壓頂,更不允許任何人的腳底「踩踏」。書本第一章便已告訴我們:天皇是「神」,不是人。
1950年,李光耀從英國留學回來,多年後成了行動黨的立法議員,也擔任從事學潮與工潮者的法律顧問,直到就任總理。這時,我們都出來社會工作了。有一天,我的姐夫(我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都在同一間日語學校念兩三年書)和我談起政壇上活躍的李光耀時,突然問起我知不知道他也曾在「昭南日本學園」唸過書。那時我還很小,單純得很,當然不知道。我不相信,以為姐夫認錯人,因為李光耀問政以來,只聽他說過日治時期曾在日本軍宣傳班工作一段短時期,從來沒有聽說他曾經在日本學校讀過書。
姐夫說,李光耀在班上給他深刻印象是因為李的英文講得很棒,口才很好,常在班上高談闊論,沒人能贏他。很明顯看出他鋒芒初露,超群出眾,也讓同學以為他是在炫耀自己的才華。多年後,我在李光耀出版的回憶錄(1923-1965)讀到他曾在奎因街的一所日本學校讀過日文的事,我才相信姐夫沒有張冠李戴。
我記得還有一個也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學吳信達。戰後他在一家華文中學教英文,後轉教育部,再受聘於華僑銀行任高職。他是著名(英文)小說家,國家圖書館還存有他的著作。
在回憶「昭南日本學園」時,李光耀提到「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有不同。其中有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李同學」這段話也許記錯了,那時20歲左右的工人應該是很少有機會上學。
據「昭南日本學園」校長神保光太郎在他一年任滿回國後著寫的《昭南日本學園》書中記載,學校開學時報名的各籍各階層人士甚多,第一期有320人(過後逐期增加到二、三千人),年齡由12歲到52歲(男女同學中,年長和年少的混在一班),其中16歲到20歲的青少年以華族學生最多,占三分之一,華族女生也有32人,占全校女生半數以上,其次是印度籍、再來是馬來籍、歐亞籍及其他國籍學生。
因年齡差別,功課上年紀小的同學必定比不上學長姐,但是念起日本文來,在同一班上不分年齡大小,大家是初次接觸到日文,第一次觸及日文50音。我有小學的中文底,淺的文字可以看懂讀懂,也不一定比原讀英校的大同學吃虧。幸好學校一視同仁,大小混在一個班。入學之初,花了一些日子,先學會唱日本歌。
入學前,我的年齡只有11歲,比規定入學年齡少一歲,不能報名,但已經報名入學的大姐向校長求情(另有一兄一姐也入學),我也獲准入學,這樣一來,我家裡兄姐四人便進了「昭南日本學園」。還有一位吳卓英同學也是11歲,也由已入學的哥哥吳漢英向校長說情而獲得名額。戰後,日本海運發展至世界各個港口,漢英在新加坡日本海員協會工作,又創辦日文夜校數十年,學以致用,直到退休為止。
我的兄姐都是適齡學生,大姐在萊佛士女校剛考完年底的劍橋高級文憑會考,太平洋戰爭即告爆發,當時擔心的是考卷由郵船運往英國途中,會被日機轟炸沉入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