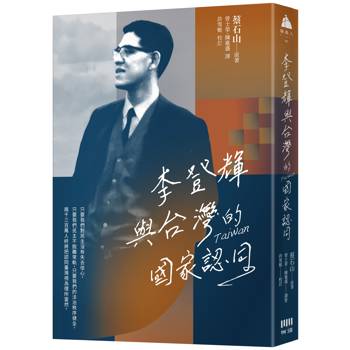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的平面媒體機關《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誹謗年已七十三歲的李登輝,視他為一個藐視祖國的「分離主義份子」、一個勾結美國的「騙子」、一個以政策「將台灣推向大災難深淵」的人。同一天,台灣的一千四百萬合格選民,無懼於中國長達一週的軍事演習與飛彈試射的威脅,在全國一萬兩千五百九十七個投票所自由投下他們的選票,壓倒性選出李登輝為總統。擁有壓倒性的選舉勝利與人民的授權,這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不斷且直率駁斥中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事實上,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宣告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誓言要使台灣完全獨立於外國的控制(這個宣告根本背離了其前任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明確政策。一九四九年因逃避共產黨遷到台灣之後,蔣介石與蔣經國僅打算,將台灣視為國民政府未來光復中國大陸的堡壘)。李登輝隨後解散台灣省政府,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國之音」的訪問中,進一步要求一個「特殊國與國」的外交機制,欲透過此一機制進行未來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協商。
藉著宣告台灣是「主權國家」,李登輝很清楚想要提倡一種「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的形式。蘇聯瓦解以後,國家民族主義開始因新的主權國家的擴增而在整個一九九〇年代期間支配著歐洲。李登輝了解,中國人長期以來適應了太平盛世的帝國權力架構,二十世紀之後,又受到近代民族主義情感的刺激。然而,他並不將中國文化視為一個整體,也不接受單一的中國史觀。因此,李登輝要應用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概念,將中國視為「可媲美於西方基督教的一個完整的文明。而在西方基督教內部,像法國與英國等民族國家成為具有共同文化的政治次單位(subunits)」。在李登輝自己的歷史演變架構之中,「國家民族主義」是一種相當受到認可的民族主義,正如最近在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烏克蘭所建立的主權國家,它不應該被解釋成為純粹的「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國家民族主義」不是立基於哲學、藝術、文學與宗教等文化上的差異,而是立基於政治的架構,與台灣島的地理和社會習俗的不變事實之上。也就是說,台灣的海洋型傾向的憲政民主,並不類同於大陸型的中國,以及其共產極權無所不包的權力結構。
儘管北京可能並不完全了解李登輝關於民族主義的新說法,李登輝關於中國與台灣關係的構想(「特殊國與國」)所產生的影響,則是立即的、長期的與情感的。李登輝最大的優點在於,他能夠敏銳解讀並塑造國內的公共意見,同時能夠激起民眾追隨他自己的目標。儘管大部分的台灣人原為漢族,一般來說,他們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並不一致,而且從一八九五年起,在政治、社會、經濟,甚至語言上,即和他們的中國大陸遠親分隔開來(除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年內戰期間之外)。其實,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從清朝政府接收台灣以前,台灣島民早已建立台灣民主國,希望尋求歐洲人與美國人的支持。儘管該台灣民主國十分短命,這一段歷史卻「代表一個虛擬的台灣國族認同概念的歷史起點」,因為它「在象徵上與法律上標示著台灣從中國最初的分離」。過去幾十年間,台灣分裂的國族認同變得更明顯且更容易分辨。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台灣更民主化、更多自由與經濟更成功,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共產中國令人遺憾的違反人權記錄,以及它持續威脅以武力「解放」台灣。二〇〇四年,中國沿著大陸南部海岸部署了大約六百枚飛彈,對準台灣。
李登輝努力喚起的「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似乎已經贏得台灣島上多數福佬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支持。但是,仍有頗高比例的「外省人」(一九四九年隨中華民國政府由大陸逃難到台灣),繼續維持與中國深切的個人關係與情感聯繫,而且他們一般來說並不信賴李登輝,也不奉行李登輝的政治議程。為了舒緩台灣內部矛盾衝突的多重認同(本省人對外省人,或獨立對統一),李登輝尋找一個簡稱為「新台灣人」的新認同方案的可能性。李登輝多族群、多文化的提議,在他所稱的「國家民族主義」與傳統的「族群民族主義」之間明確做出區別。這個無所不包的「新台灣人」概念,將所有台灣住民給包括進去,無論其族群背景和來到台灣的時間先後。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時,香港出生的馬英九宣告自己是「新台灣人」,並擊敗台灣本土出生且頗受歡迎的陳水扁的時候,這個新的認同遂於一九九〇年代後期蔚為風行。
然而,李登輝的「新台灣人」概念長久以來仍處於孕育階段,而且胎盤不穩。李登輝剛繼任台灣的總統一職時,就像其前任一樣,似乎熱切支持中國統一。但是,退休之後,他經歷了心理學家所稱的「政治的贖罪」(political atonement)。這表現在他無情地指控國民黨是個「外來政權」,並且積極地提倡台灣獨立等事實之上。二〇〇三年一月,李登輝在一次演說中指出:「台灣人出賣他們的身體與靈魂給外來政權的時間太久了,現在正是將之取回來的時刻。因為台灣是屬於台灣人的。」這類說詞反映出李登輝正在解構他自己的「中國性」,另一方面卻受到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同聲譴責。再者,李登輝承認年輕時,自己對日本的感受多過對中國的感受,這是因為他是在日本人辦的學校與其他日本人同學競爭中長大,後來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也在日本的陸軍擔任過尉官。簡言之,文化上混血的李登輝一直是個具有多重認同的人,因此體現出些許矛盾衝突。他早先認同自己是個日本人,然後是個中國人,最後則是個台灣人。他的生命史是近代台灣社會的縮影和真實的寫照,本書也是一本關於台灣認同的塑造、解構與再造的陳述。
藉著宣告台灣是「主權國家」,李登輝很清楚想要提倡一種「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的形式。蘇聯瓦解以後,國家民族主義開始因新的主權國家的擴增而在整個一九九〇年代期間支配著歐洲。李登輝了解,中國人長期以來適應了太平盛世的帝國權力架構,二十世紀之後,又受到近代民族主義情感的刺激。然而,他並不將中國文化視為一個整體,也不接受單一的中國史觀。因此,李登輝要應用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概念,將中國視為「可媲美於西方基督教的一個完整的文明。而在西方基督教內部,像法國與英國等民族國家成為具有共同文化的政治次單位(subunits)」。在李登輝自己的歷史演變架構之中,「國家民族主義」是一種相當受到認可的民族主義,正如最近在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烏克蘭所建立的主權國家,它不應該被解釋成為純粹的「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國家民族主義」不是立基於哲學、藝術、文學與宗教等文化上的差異,而是立基於政治的架構,與台灣島的地理和社會習俗的不變事實之上。也就是說,台灣的海洋型傾向的憲政民主,並不類同於大陸型的中國,以及其共產極權無所不包的權力結構。
儘管北京可能並不完全了解李登輝關於民族主義的新說法,李登輝關於中國與台灣關係的構想(「特殊國與國」)所產生的影響,則是立即的、長期的與情感的。李登輝最大的優點在於,他能夠敏銳解讀並塑造國內的公共意見,同時能夠激起民眾追隨他自己的目標。儘管大部分的台灣人原為漢族,一般來說,他們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並不一致,而且從一八九五年起,在政治、社會、經濟,甚至語言上,即和他們的中國大陸遠親分隔開來(除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年內戰期間之外)。其實,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從清朝政府接收台灣以前,台灣島民早已建立台灣民主國,希望尋求歐洲人與美國人的支持。儘管該台灣民主國十分短命,這一段歷史卻「代表一個虛擬的台灣國族認同概念的歷史起點」,因為它「在象徵上與法律上標示著台灣從中國最初的分離」。過去幾十年間,台灣分裂的國族認同變得更明顯且更容易分辨。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台灣更民主化、更多自由與經濟更成功,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共產中國令人遺憾的違反人權記錄,以及它持續威脅以武力「解放」台灣。二〇〇四年,中國沿著大陸南部海岸部署了大約六百枚飛彈,對準台灣。
李登輝努力喚起的「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似乎已經贏得台灣島上多數福佬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支持。但是,仍有頗高比例的「外省人」(一九四九年隨中華民國政府由大陸逃難到台灣),繼續維持與中國深切的個人關係與情感聯繫,而且他們一般來說並不信賴李登輝,也不奉行李登輝的政治議程。為了舒緩台灣內部矛盾衝突的多重認同(本省人對外省人,或獨立對統一),李登輝尋找一個簡稱為「新台灣人」的新認同方案的可能性。李登輝多族群、多文化的提議,在他所稱的「國家民族主義」與傳統的「族群民族主義」之間明確做出區別。這個無所不包的「新台灣人」概念,將所有台灣住民給包括進去,無論其族群背景和來到台灣的時間先後。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時,香港出生的馬英九宣告自己是「新台灣人」,並擊敗台灣本土出生且頗受歡迎的陳水扁的時候,這個新的認同遂於一九九〇年代後期蔚為風行。
然而,李登輝的「新台灣人」概念長久以來仍處於孕育階段,而且胎盤不穩。李登輝剛繼任台灣的總統一職時,就像其前任一樣,似乎熱切支持中國統一。但是,退休之後,他經歷了心理學家所稱的「政治的贖罪」(political atonement)。這表現在他無情地指控國民黨是個「外來政權」,並且積極地提倡台灣獨立等事實之上。二〇〇三年一月,李登輝在一次演說中指出:「台灣人出賣他們的身體與靈魂給外來政權的時間太久了,現在正是將之取回來的時刻。因為台灣是屬於台灣人的。」這類說詞反映出李登輝正在解構他自己的「中國性」,另一方面卻受到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同聲譴責。再者,李登輝承認年輕時,自己對日本的感受多過對中國的感受,這是因為他是在日本人辦的學校與其他日本人同學競爭中長大,後來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也在日本的陸軍擔任過尉官。簡言之,文化上混血的李登輝一直是個具有多重認同的人,因此體現出些許矛盾衝突。他早先認同自己是個日本人,然後是個中國人,最後則是個台灣人。他的生命史是近代台灣社會的縮影和真實的寫照,本書也是一本關於台灣認同的塑造、解構與再造的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