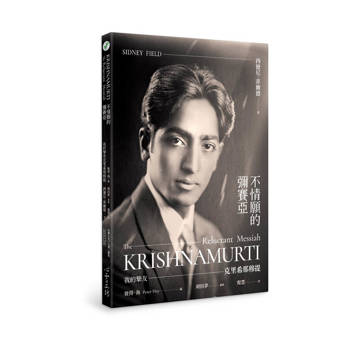第四章
1928年的6月份,克里希那吉即將前往歐洲,參加在荷蘭歐門舉辦的營地聚會,因此我們邀請他、拉嘉戈帕爾和羅莎琳.威廉姆斯離開之前來家裡坐坐。這是我們全家第一次見到羅莎琳。她是一位金髮碧眼的漂亮姑娘,身上有種樸實的氣質,非常有吸引力。我們都很喜歡她。
那天晚上大家相談甚歡,有個場景我記得非常清晰:克里希那吉詢問我的父親,既然我已經從好萊塢高中畢業,他是否同意我和他一道去參加歐門的露營聚會,以及為此在埃爾德古堡舉辦的熱身活動。聽到這個邀請家人顯然都非常高興,我更是欣喜若狂。
克里希那吉幾天後就要動身離開,但我沒辦法那麼快做好準備,所以決定拿到護照安排好汽船之後獨自前往。那時夏季赴歐旅遊的高峰期碰巧剛剛開始,因此等待的時間比預期要長。其實我挺喜歡推遲幾天再過去,這樣我就有機會參加好幾場由小夥伴同學們為我舉辦的開心告別派對了。
一切都令人興奮極了。我從未離開過家人,也從沒去過歐洲。這會是一場偉大的冒險,不過我還是有點害怕。
出發的日子終於來到。家人和幾個朋友送我到洛杉磯的南太平洋車站與我告別,我將從這裡乘坐著名的日落號列車前往芝加哥。(為了創下長途飛行新紀錄,當時是有橫越美國的航班的,不過只負責運送郵件,偶爾也有勇敢的單人旅者搭機。)抵達芝加哥後,接應的友人把我送上駛往紐約的世紀特快列車。三年前我去過紐約,當時我們正離開哥斯大黎加準備前往好萊塢,途中在那裡曾經短暫停留。我很喜歡紐約,但父母不停地嘮叨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回可沒人再指點我該做什麼、該去哪裡、晚上何時該回旅館了。我逍遙自在地玩了兩天,沒想到竟然會對這個大都市生出困惑迷惘的感覺。帶著一絲焦慮我踏上了荷美航線旗下的鹿特丹號豪華旗艦遊輪,準備出發前往荷蘭。
旅程非常順利,四周的乘客也都一副歡天喜地的模樣。五天之後我抵達鹿特丹,一個極其繁忙的港口城市,每條街道上都能看到很多人在騎自行車。我直接坐上計程車前往火車站,在那裡搭上了往阿姆斯特丹的列車。途中經過一大片美麗平坦的田野罌粟園,色彩真是無比絢爛──緋紅、白色、黃色、粉色。幾個小時之後抵達了目的地,然後和旅途中結識的幾位朋友一同乘船遊覽這個城市的一條風景如畫的運河。我瞬間就愛上了阿姆斯特丹,希望能在那裡多玩幾天,但是我已經答應克里希那吉直接去歐門,所以打電話給埃爾德古堡(Castle Eerde),告訴他們我將搭乘五點整出發的火車。來歐門小火車站接我的是克里希那吉的司機,他身穿制服、開著主辦方的賓士敞篷車。我們繼續朝著埃爾德古堡駛去。
到達埃爾德城堡時天色已暗,薄霧漸起,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傍晚。我們緩緩駛入一條寬敞的林蔭道,路旁是高大壯美的山毛櫸,濃密的樹冠隨風輕柔地擺動於薄霧中,開心地彼此玩耍著,就像是在我們頭頂上方竊竊私語似的。天鵝絨般華美的綠色隧道盡頭,你可以隱約看見這座十八世紀古堡的輪廓。這一幕令人聯想起迪士尼童話中通往白馬王子傳奇居所的魔法隧道。
精雕細琢的鐵門被緩緩打開,我們正準備開進去時司機停了下來,等著一隻閒逛的野鹿慢慢悠悠穿過馬路,那隻鹿好奇地看了看我們然後快步跑開。司機解釋說,克里希那吉已經下令要讓路給森林中的野鹿。這個意外插曲使得我第一次有機會觀察一下這座古堡,而且就在距離它不遠不近的位置。寧靜地它佇立在那裡,散發著莊嚴華貴的風彩,前面是精心修剪的草坪和花園。古堡周圍環繞著廣闊的護城河,一座寬敞的橋梁優雅地橫跨兩岸,通向宏偉的入口處。這座城堡連同周圍五千英畝的樹林與草地,是菲力浦.凡.帕蘭特男爵──克的一位富有的貴族好友──贈送給他的。
我想我的確是期待一進入古堡就能看見克里希那吉的,至少應該有人帶著笑容迎接我、說上幾句令人開心的話,可是一個人都沒見著。司機把我送到附屬樓內的一個房間,這是為了接待客人而新建的側樓。有位克莉斯蒂夫人過來見我,而且帶來了不好的消息,我是第一批抵達的客人,我要求去見克里希那吉,出現的卻是艾米莉.勒琴斯夫人,她似乎是此地的負責人。雖然她的態度冷漠,看上去像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管家,但身上散發的舊式氣息卻相當迷人。她告訴我克里希那吉得了重感冒,前一天才從倫敦趕過來,所以接下來幾天都要閉門修養。運氣真是不好,我心想應該按照自己的計劃在阿姆斯特丹多待幾天的,這樣就能夠和途中認識的朋友們一起到處逛逛了。不過我還是來到了這裡,這麼美的一個地方,還有克里希那吉,或許幾天後就能見著他了;由於他赤子般的純真和魅力,女人對他總是呵護有加。況且,此刻我還有書可讀、有唱片可聽。
在裝飾典雅、空間寬敞的正式餐廳裡安靜地吃完晚飯後,我四處轉了轉,欣賞著貴重的古董家具、油畫、祖先留下的掛毯和藝術品。這個地方既華麗又莊嚴,氣派堂皇卻不造作,的確符合主人的身分。
回到房間時外面已經開始下雨,想到一個人在離家幾千英里的地方,我突然感到特別孤單。接下來的幾天令人沮喪到了極點。雨不停地下著,甚至都不能出門去美麗的森林裡散步,因為路上四處都是泥坑,根本無法通行。隨後到達的幾位長者似乎一進來就躲進自己的房間「冥想」去了,以便「和高層存有進行交流感應」。前幾個星期我還在開派對作樂,此時情況突然急轉直下。我猜這段時間的「反觀默照」—有人這麼告訴過我—是接下來屬靈體驗的必要前奏,因此除了忍耐似乎別無它法。
某天晚餐之後我逼問艾米莉女士克里希那的健康情況,到底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他呢?「他準備好了就可以,」她嚴肅地回答。「順便說一下,」她繼續說道,「既然克里希那已經完全與世界導師合一了,所以大家決定人人都該稱呼他克里希那吉而不是克里希那。」接著她解釋了在克里希那這個名字後面加上「吉」的意思──表示摯愛和敬重的尊稱。我卻認為這種做法是把人拱上了神壇,而且知道克里希那吉一定會感到厭惡的。為什麼室利.克里希那沒有被稱為室利.克里希那吉呢?
反正克里希那吉仍然需要閉門獨處。天氣變得更加惡劣了。古堡裡我本可閱讀的書被鎖了起來,想要使用唱機也必須得到拉嘉戈帕爾的同意,但那時他人還沒到。
一些年輕的營地來賓開始陸續抵達營地,大部分都是女生。遺憾的是這並沒有讓我感到歡欣雀躍,因為她們身上散發出一股難以穿透的靈性傲慢。她們過去曾經一同參加過活動,傾向於對陌生人抱持居高臨下的排拒態度。
我下定決心走人,至少要離開幾天的時間。我可以悄悄走開不告訴任何人,然後快速去巴黎轉一圈,在那邊找點樂子再回來,甚至沒人會留意我在不在,這個想法令我感到興奮不已。我給歐門的一個旅行社打電話,他們為我安排好火車票,替我訂了巴黎的一家小酒店的房間。第二天我會從歐門出發,我知道只要給點好處,就可以讓那位年長友善的司機送我去車站,而且對此事保持緘默。
當天下午天空放晴,出現了十天以來的第一道陽光,但這並不是那天具有特殊意義的唯一理由。我坐在可以俯瞰城堡入口的房間裡、看著迎面而來的陽光穿透樹梢,突然間注意到一名身材高挑穿著一襲鋪滿了大紅玫瑰圖案黑色貼身長袍的年輕女孩,正穿過草坪朝著古堡走來。她邁著大步輕快地走著,整個人充滿了自信,就好像她是派對女主人一樣。她漆黑的長髮和髮間別著的紅玫瑰及長袍相映成趣。她算是我抵達後這十天以來見到的最明亮最活力四射的景象了;而且看起來年齡與我相仿。我立刻被她吸引,決定必須馬上和她碰面。迅速梳理好頭髮之後我衝了出去,興奮地坐在跨橋的護欄上,等待她從古堡裡走出來。突然間她已經來到了我的面前。我們都面帶微笑和對方打招呼,然後我說了一些下雨後天晴了之類無關緊要的話,便開始自我介紹。
「我叫露絲.羅伯茨,」她的英國口音很好聽,「你就是那個美國男孩吧?」
「是的,你怎麼知道的?你有眼通嗎?」她笑了起來,笑容溫暖有力,立即擄獲了我的心。
「我看過來賓名單,」她補充道,「可是你聽上去不像美國人。」
我解釋說我是在哥斯大黎加出生的,她立即回應說很喜歡我自認為已擺脫掉的口音。她在我身邊坐下,我們聊了一會兒。她有一種高傲的美,明亮的黑眼珠裡閃爍著調皮的火花、流露出獨立自主的神態,鼓舞著我說出心裡話。我沒提到第二天要去巴黎,但她已經察覺我是因為見不著克里希那吉而感到失望。
「你把希望寄託在克里希那吉身上是很傻的,」她就事論事地說。
她是對的。克里希那吉本人也曾警告過我這一點,但事情還是發生了,其實我並不喜歡這種感覺。她帶著一抹嘲弄的微笑走開了,我看著她邁著感性又輕盈的貓步,逐漸消失於附屬樓的女性專區。
雖然我感覺被她立即吸引,但從未幻想過以後的生活會跟她聯結在一起。她很有魅力,不過顯然是把我當成孩子一樣在看待。第二天要去巴黎的決心已經動搖,可我同時也擔心自己展現出的模樣不夠成熟。或許去趟巴黎哪怕只有幾天的時間,回來之後她就可能覺得我見過世面老練了一些。我一直記得好萊塢高中的那位教法語的男老師的話,「巴黎會使你成為真正的男人。」當我沉浸在這些想法中的時候艾米莉女士出現了,她告訴我說克里希那吉將會在明天下午三點見我。這下好了,巴黎已經被我暫時拋諸腦後,不過露絲可沒有。
一想到要見克里希那吉我就激動不已,那晚幾乎沒闔眼。不過他這麼久沒理我,心裡還是覺得有點受傷,於是決定要表現得鎮靜、冷漠而疏離,讓他知道我這十天來的感受是什麼。
他住在古堡的二樓,第二天我準時敲響他的房門。聽到他讓我進去的聲音時,我的心臟跳得飛快。按照艾米莉女士先前關於他健康情況的描述,我以為克里希那吉會看上去蒼白、消瘦又憔悴。但是當我推開房門時,看見的卻是眼前的這位盤腿坐在矮台子上的男子,他白色的腰布外面罩著一件金黃色長袍。這真是我所見過的最光彩奪目最美的人類。我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地凝視著,他是真的讓我屏住了呼吸。那一刻可以說是終生難忘。接著他微笑地說,「進來吧,進來吧,西德尼,」並且示意我和他一起坐到講台上。出於禮貌我想問候一下他身體的情況,儘管看上去他從未顯得這麼健康過,而我卻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沉默了許久之後他說他知道我不太開心,我點點頭。接著他說我前幾個星期一直忙於社交活動,眼下感到失望是在所難免的。我很想知道他是怎麼得知的,因為我們已經兩個多月沒見面或交流了。我猜想這是出於理性推測。他盯著我看的時候眼神顯得特別明亮,然後他說,「我很高興你取消了去巴黎的旅程。」這可真是令我大吃一驚,因為此計畫我沒告訴過任何人。「巴黎是個美麗的城市,可也是個腐爛的黑洞。」他又加上了這麼一句話。我說我打算在露營活動結束後再過去遊玩。接著話題轉到了古堡和莊園的美景上面,他答應幾天後親自帶我四處走走,到時候我們會去樹林和牧場裡做個遠程散步。接下來又是一陣長時間的沉默,感覺像是在邀約我討論我的問題,但是那一刻我什麼問題也沒了,心裡感到平靜而滿足。探訪來到了尾聲,當我起身準備離開時,他告訴我幾乎所有的客人都已抵達,明天上午會在圖書館發表簡短的歡迎辭。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我們在寬敞的圖書館裡集合,一起盤坐在漂亮的波斯地毯上,克里希那吉則盤腿坐在我們對面的沙發上。這是房間裡僅存的一件家具,後面的牆上還掛著一幅十七世紀專門為古堡訂製的華麗哥白林壁毯。他的開場白是我們過去多生多世都曾經和他在一起過,未來世也將會繼續同行。(最近我向他提到這句話,他非常驚訝地說,「我真的說過嗎?」)他發言的時間很短,簡單地介紹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想做的事:幫助人類獲得終極自由,協助他們靠自己擺脫一切權威束縛。在他演講過程中的某個時刻,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在我身上發生了。沒有任何理由地,我突然感到一陣狂喜從心輪區域爆發出來,一波接著一波越來越強烈,直到我覺得必須張開嘴為至樂大聲歡呼為止。這使我想起了《拉撒路笑了》一劇中歐文.皮切爾的狂笑──但這回可是真實不虛的體驗,祂不請自來且不期而遇,整個佔據了我的身心。在這個過程中我被超拔到幾乎要離開自己的身體。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也從沒想過自己能夠體驗到祂。
致辭結束之後多數的來賓都趁著陽光明媚在午餐前去樹林裡散步。我自己一個人待著,想盡可能地留住無法描述的那一刻所留下的芳香。我獨自一人坐在高大榆樹的綠蔭下,感受著那股至樂大能逐漸平息下來,融入到呼吸的韻律中,繼之而來的是浩瀚無邊的靜謐和不斷向上湧動的愛意,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感覺逐漸退居幕後。我期待著即將到來的和克里希那吉的散步,希望他能再度點燃幾天前為我帶來高峰經驗的內在火花。我渴望再度被那狂喜的火焰吞沒,它讓整個世界都變得純淨無邪,就好像那天清晨才剛剛被誕生出來似的。
我們的確出去散步了,克里希那吉和我,不過渴望的體悟並未出現。儘管如此,我還是領受到一種輕盈、明透和靜謐的奇妙之感。踩著人跡罕至的泥土小徑,在高高的樹下穿行,色彩鮮豔的蝴蝶於光影中飛來舞去,我們一路悠閒地散著步,幾乎沒什麼交流。克里希那吉似乎對自然界發生的每一個變化都了然於胸,甚至連腳下的蟲子他都十分小心不要踩到牠們。我告訴他我認為他的歡迎辭非常鼓舞人心,但是對我自身的屬靈經驗卻隻字未提。這層體悟才剛剛冒出頭且瞬間即逝,展開討論似乎為時尚早,它就像是一株嬌嫩的植物,你必須細心地加以照料,不讓它暴露在強風中。克里希那吉通常會在最不經意的時刻隨口說出一句話,勁道如同加勒比海的颶風一樣把你徹底摧毀。我以前經歷過,這次可不想再冒這個險了。
如同往常一樣我在這個話題上兜著圈子,迫切地想知道他對我甚為重視的議題有什麼看法。「在你達到你的解脫目標之前,」我問他,「你有過什麼特殊體驗嗎,例如巨大的狂喜和解放之感?」
「有過,」他答道。
「那你對它做了什麼?」
「什麼也沒做。我從不追求這種經驗。」
「如果你感覺這類經歷是前行路上的重要指標,你會鼓勵這種行為嗎?」
「我會帶著全然的覺知和愛去觀察,看看祂要把我引向何處。」
這是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我願意把這個議題先就這麼擱著。在古堡裡每天都有人前來探訪克里希那吉。有些人會待上幾個小時或者住上兩三天。在短暫的來訪中有兩名協助世界導師傳播教誨的「使徒」。一年前英國神智學會領軍人物,浮誇招搖的喬治.阿倫戴爾,突然宣佈成立使徒會,他自己也是成員之一。他指派妻子魯克米尼.戴維,一位年輕漂亮的婆羅門女性,和詹姆斯.衛奇伍德主教一同前來造訪。魯克米尼身穿五顏六色的印度紗麗,看上去很漂亮。她的態度開放友好,每個人都喜歡她。詹姆斯.衛奇伍德主教則穿著神父的法衣,身材高大、面色黝黑、長相英俊,胸前墜著一個很大的鑲寶石的十字架,手上戴著主教戒指。他冷漠淡然,渾身上下充斥著自我重要感,散發出靈性傲慢的腐朽氣息。一位熟知他的朋友為我寫了封介紹信,但我已經完全失去興趣,信都懶得交給他了。
克對喬治.阿倫戴爾和衛奇伍德主教發布的荒唐且具有煽動性的言論感到相當不安,他們的意思是某些人經由擇選成為了「克里希那吉的門徒」。阿倫戴爾宣稱這是彌勒菩薩傳遞下來的旨意。克憤怒地拒絕了他們的一切安排,聲稱自己絕不會接受任何門徒的。那些知道他私下對此事有多麼厭惡的人,非常驚訝於他在公開場合處理這個問題時表現出的溫和態度。他們有所不知的是,貝贊特博士因為信任阿倫戴爾而被捲入其中,基於對貝贊特夫人的愛,克不會做出任何可能令她尷尬或傷害到情感的激烈舉動。(但是多年之後他在歐亥強烈表達了自己在這個議題上的看法,他認為阿倫戴爾和衛奇伍德無情地試圖利用他來壯大自己。我曾經和克面對面地討論過這個話題,知道克對他們為達一己之目的而使出卑劣伎倆有多麼憤怒。)
一週接著一週,漫長盛夏在快樂中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我們在可愛的樹林裡散步,閒聊了幾回但沒說什麼具有啟發性或深刻的內容,因為除了享受他的陪伴之外似乎什麼都不需要了。
不過我和他的最後一次談話卻令我感到不安。在來埃爾德之前我剛從高中畢業,雖然一向對學習不是特別上心,但確實是打算繼續上大學的。我所需要的只是一點點鼓勵,克里希那吉卻沒有給我。當我問他是否應該繼續學業追求事業發展時,他帶著以往談話中流露出的相同心境回答說:生命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獲得內在自由,一種無條件的解放,以便達到真正的徹悟解脫。其它事情都是在浪費時間。「不要浪費你的時間,每一天都很重要。要設立目標,然後匯集所有能量去實現它。」他說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整個人格都由於他為自己設立的個人目標而燃燒:幫助所有人獲得自由解脫。
對一個容易受外境影響剛睜開眼睛準備看新世界的男孩來說,放下學業和事業發展去追求「解脫」並不是什麼上乘建議,但我認為這個忠告與克當時對世界的看法及感受是一致的。可是從他後來對教育的觀點來判斷,我很懷疑他是否會繼續給出這樣的建議。多年來克的溝通技巧和傳達教誨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概括地說,他晚年時的言論變得更加清晰銳利。或許多年前他早已洞見到一切,所以當早期的某次講座結束之後我告訴他說他的話語斷斷續續不夠連貫,因此我不明白他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沒錯,我今早的談話有點搞砸了。我想描繪的是一個嶄新的維度和意涵,但卻用了舊有的方式在詮釋,這就像一名畫家正在嘗試繪出不同的東西,而我也正在學習新的技巧,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停了一會兒然後說到,「或許到了六十歲時……」總之,我不想讓有關我未來的話題給埃爾德的美妙經歷蒙上陰影,所以就暫時將它置於腦後了。
接下來的幾天既有節奏緩慢的默觀冥想,也有令人興奮的歡樂時光。大家在古堡四周風景如畫的護城河上划船,還被允許可以玩遊戲—主要是打排球,有時克里希那吉也會參與進來。結識來自不同國家的有趣人士真是充滿著樂趣又帶來了自我探索上面的挑戰。我非常感激克給了我機會和他在一起,但是很難向他傳達這份情感,因為他拒絕接受任何人對他表達感恩。他在任何時刻都散發出一種令人變得警覺和敏銳的靈性品質。
在這段時間裡我沒怎麼看到那位令我激動的新朋友露絲.羅伯茨。她一般都忙著和比她年長的朋友們在一起,其中一位已經訂婚的富有荷蘭哲學家J. J.范德.列烏比她大了十歲。庫斯是人們送給他的暱稱,此君個子很高,臉上帶著一副哲人容易有的嚴肅表情,而且他的頭髮已經全禿,由此而傳出了一段小插典,讓這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厭其煩地講了一遍又一遍。某個陽光燦爛的下午他無預警地站在附屬樓二樓的一間臥室窗戶的正下方,突然感覺有一團黏稠的東西掉在他的光頭上。身為哲人的他力持鎮靜,心想應該是一隻飛過的大鳥拉屎掉到了他頭上。這是他自己的業力,得想開一點。為了不讓人發現,他緩慢而不動聲色地伸手去拿掉頭上的鳥屎,但真相卻令他恍然大悟──那團惱人的東西只不過是普通的牙膏罷了。他推測這一定是哪個幽默感扭曲的人搞的惡作劇。他義憤填膺地抬起頭,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看到的竟然是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爾躲在他正上方的窗戶後面笑得前仰後翻。庫斯撂下幾句精選的髒話之後,朝著最近的浴室走去。解脫這檔事兒有點過頭了!
後來我開玩笑地問克里希那吉,到底是他還是拉嘉戈帕爾如此精準地把牙膏擠到了庫斯的光頭上。克調皮地大笑不止,只是說拉嘉戈帕爾的幽默感相當古怪,然後補充了一句:庫斯對於這整件事過於拘謹當真了。
埃爾德古堡的快樂時光結束得太早了一點。訪客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搬到營區去,那裡也是莊園的領地,距離古堡大約一英里。
那天一大早就開始下雨,直到傍晚才放晴,當時克里希那吉和我正在樹林裡散步。天空中點綴著不同的色彩和夏日的光輝,腳下的土地則散發著褐色樹葉和潮濕泥土的芬芳。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段時間。想到以後可能再也見不著這麼非比尋常的地方,我的心開始被傷感的陰影所籠罩。在那兒逗留的日子令人難忘,我試著憶起某些比較有意義的時刻,但腦海裡如萬花筒般閃現的卻是一些無關聯也無關緊要的畫面:克里希那吉獨自一人穿過森林,新蓄的鬍子使他看起來酷似基督。艾米莉女士惱火地要我用西班牙語和某位客人溝通──他是來自波多黎各的知名人士──請求他外出散步時千萬不要隨地吐痰。(這名肇事者快速而連續地從嘴巴兩側使勁地吐痰,就像要創造某種記錄似的)「這是最違反美學最不衛生的行為,」艾米莉女士抱怨道。一名來自倫敦的年輕學生脫光衣服跳進古老的護城河裡,去撿我們先前在玩的那個排球,其他人則吃驚地看著他,緊張兮兮地發出咯咯笑聲。某位來自賴德拜特澳大利亞雪梨莊園的訪客,一臉激動地說自己聽不懂克里希那吉在說些什麼,因為他不是「信仰菩薩的人」。身材高挑愛玩的露絲和一名來自加利福尼亞風度翩翩的陸軍上尉大步走在林蔭小道上,而我這個「來自哥斯大黎加的美國男孩」—大家都這麼稱呼我—則了無希望地在一旁觀望著他們。
我知道在歐門營地的講座中是不可能和克里希那吉碰面了,所以趁著我們站在古堡正門口的時刻向他道別。我說了幾句感恩的話,但似乎完全不合時宜,然後給了他一個拉丁式的擁抱。他也同樣抱了抱我,告訴我他非常享受和我在一起的時光,並且說我們日後會有更多見面機會的。他的話就像是提示的暗號一樣,瞬間讓那美妙的狂喜再度爆發出來,並且立即把我送上樹梢頭,令我進入了無言之境。幸運的是我已經和他說過再見,於是便逕自走向樹林。等我回到附屬樓的房間時已經是黃昏,所有的人都離開了。
在外頭等候司機來接我時,心裡反思著那份狂喜之禮和埃爾德古堡之行帶給我的屬靈餽贈,然後決心這次一定不能再丟失祂,但也心知肚明這種體驗不是你決定要得到就能擁有的,因為祂降不降臨完全是自發的,不可能透過邀約、哄騙或誘導讓祂出現。不過就當時的營地聚會而言那是一個絕佳的開端,對我來說也是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經歷。
營地聚會的日子結束之後,我去了比利時和法國。巴黎很美,也很刺激。克里希那吉警告過我的,它的確有陰暗醜陋的一面,不過你可以親近它而不必然被灼傷。
1928年的6月份,克里希那吉即將前往歐洲,參加在荷蘭歐門舉辦的營地聚會,因此我們邀請他、拉嘉戈帕爾和羅莎琳.威廉姆斯離開之前來家裡坐坐。這是我們全家第一次見到羅莎琳。她是一位金髮碧眼的漂亮姑娘,身上有種樸實的氣質,非常有吸引力。我們都很喜歡她。
那天晚上大家相談甚歡,有個場景我記得非常清晰:克里希那吉詢問我的父親,既然我已經從好萊塢高中畢業,他是否同意我和他一道去參加歐門的露營聚會,以及為此在埃爾德古堡舉辦的熱身活動。聽到這個邀請家人顯然都非常高興,我更是欣喜若狂。
克里希那吉幾天後就要動身離開,但我沒辦法那麼快做好準備,所以決定拿到護照安排好汽船之後獨自前往。那時夏季赴歐旅遊的高峰期碰巧剛剛開始,因此等待的時間比預期要長。其實我挺喜歡推遲幾天再過去,這樣我就有機會參加好幾場由小夥伴同學們為我舉辦的開心告別派對了。
一切都令人興奮極了。我從未離開過家人,也從沒去過歐洲。這會是一場偉大的冒險,不過我還是有點害怕。
出發的日子終於來到。家人和幾個朋友送我到洛杉磯的南太平洋車站與我告別,我將從這裡乘坐著名的日落號列車前往芝加哥。(為了創下長途飛行新紀錄,當時是有橫越美國的航班的,不過只負責運送郵件,偶爾也有勇敢的單人旅者搭機。)抵達芝加哥後,接應的友人把我送上駛往紐約的世紀特快列車。三年前我去過紐約,當時我們正離開哥斯大黎加準備前往好萊塢,途中在那裡曾經短暫停留。我很喜歡紐約,但父母不停地嘮叨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回可沒人再指點我該做什麼、該去哪裡、晚上何時該回旅館了。我逍遙自在地玩了兩天,沒想到竟然會對這個大都市生出困惑迷惘的感覺。帶著一絲焦慮我踏上了荷美航線旗下的鹿特丹號豪華旗艦遊輪,準備出發前往荷蘭。
旅程非常順利,四周的乘客也都一副歡天喜地的模樣。五天之後我抵達鹿特丹,一個極其繁忙的港口城市,每條街道上都能看到很多人在騎自行車。我直接坐上計程車前往火車站,在那裡搭上了往阿姆斯特丹的列車。途中經過一大片美麗平坦的田野罌粟園,色彩真是無比絢爛──緋紅、白色、黃色、粉色。幾個小時之後抵達了目的地,然後和旅途中結識的幾位朋友一同乘船遊覽這個城市的一條風景如畫的運河。我瞬間就愛上了阿姆斯特丹,希望能在那裡多玩幾天,但是我已經答應克里希那吉直接去歐門,所以打電話給埃爾德古堡(Castle Eerde),告訴他們我將搭乘五點整出發的火車。來歐門小火車站接我的是克里希那吉的司機,他身穿制服、開著主辦方的賓士敞篷車。我們繼續朝著埃爾德古堡駛去。
到達埃爾德城堡時天色已暗,薄霧漸起,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傍晚。我們緩緩駛入一條寬敞的林蔭道,路旁是高大壯美的山毛櫸,濃密的樹冠隨風輕柔地擺動於薄霧中,開心地彼此玩耍著,就像是在我們頭頂上方竊竊私語似的。天鵝絨般華美的綠色隧道盡頭,你可以隱約看見這座十八世紀古堡的輪廓。這一幕令人聯想起迪士尼童話中通往白馬王子傳奇居所的魔法隧道。
精雕細琢的鐵門被緩緩打開,我們正準備開進去時司機停了下來,等著一隻閒逛的野鹿慢慢悠悠穿過馬路,那隻鹿好奇地看了看我們然後快步跑開。司機解釋說,克里希那吉已經下令要讓路給森林中的野鹿。這個意外插曲使得我第一次有機會觀察一下這座古堡,而且就在距離它不遠不近的位置。寧靜地它佇立在那裡,散發著莊嚴華貴的風彩,前面是精心修剪的草坪和花園。古堡周圍環繞著廣闊的護城河,一座寬敞的橋梁優雅地橫跨兩岸,通向宏偉的入口處。這座城堡連同周圍五千英畝的樹林與草地,是菲力浦.凡.帕蘭特男爵──克的一位富有的貴族好友──贈送給他的。
我想我的確是期待一進入古堡就能看見克里希那吉的,至少應該有人帶著笑容迎接我、說上幾句令人開心的話,可是一個人都沒見著。司機把我送到附屬樓內的一個房間,這是為了接待客人而新建的側樓。有位克莉斯蒂夫人過來見我,而且帶來了不好的消息,我是第一批抵達的客人,我要求去見克里希那吉,出現的卻是艾米莉.勒琴斯夫人,她似乎是此地的負責人。雖然她的態度冷漠,看上去像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管家,但身上散發的舊式氣息卻相當迷人。她告訴我克里希那吉得了重感冒,前一天才從倫敦趕過來,所以接下來幾天都要閉門修養。運氣真是不好,我心想應該按照自己的計劃在阿姆斯特丹多待幾天的,這樣就能夠和途中認識的朋友們一起到處逛逛了。不過我還是來到了這裡,這麼美的一個地方,還有克里希那吉,或許幾天後就能見著他了;由於他赤子般的純真和魅力,女人對他總是呵護有加。況且,此刻我還有書可讀、有唱片可聽。
在裝飾典雅、空間寬敞的正式餐廳裡安靜地吃完晚飯後,我四處轉了轉,欣賞著貴重的古董家具、油畫、祖先留下的掛毯和藝術品。這個地方既華麗又莊嚴,氣派堂皇卻不造作,的確符合主人的身分。
回到房間時外面已經開始下雨,想到一個人在離家幾千英里的地方,我突然感到特別孤單。接下來的幾天令人沮喪到了極點。雨不停地下著,甚至都不能出門去美麗的森林裡散步,因為路上四處都是泥坑,根本無法通行。隨後到達的幾位長者似乎一進來就躲進自己的房間「冥想」去了,以便「和高層存有進行交流感應」。前幾個星期我還在開派對作樂,此時情況突然急轉直下。我猜這段時間的「反觀默照」—有人這麼告訴過我—是接下來屬靈體驗的必要前奏,因此除了忍耐似乎別無它法。
某天晚餐之後我逼問艾米莉女士克里希那的健康情況,到底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他呢?「他準備好了就可以,」她嚴肅地回答。「順便說一下,」她繼續說道,「既然克里希那已經完全與世界導師合一了,所以大家決定人人都該稱呼他克里希那吉而不是克里希那。」接著她解釋了在克里希那這個名字後面加上「吉」的意思──表示摯愛和敬重的尊稱。我卻認為這種做法是把人拱上了神壇,而且知道克里希那吉一定會感到厭惡的。為什麼室利.克里希那沒有被稱為室利.克里希那吉呢?
反正克里希那吉仍然需要閉門獨處。天氣變得更加惡劣了。古堡裡我本可閱讀的書被鎖了起來,想要使用唱機也必須得到拉嘉戈帕爾的同意,但那時他人還沒到。
一些年輕的營地來賓開始陸續抵達營地,大部分都是女生。遺憾的是這並沒有讓我感到歡欣雀躍,因為她們身上散發出一股難以穿透的靈性傲慢。她們過去曾經一同參加過活動,傾向於對陌生人抱持居高臨下的排拒態度。
我下定決心走人,至少要離開幾天的時間。我可以悄悄走開不告訴任何人,然後快速去巴黎轉一圈,在那邊找點樂子再回來,甚至沒人會留意我在不在,這個想法令我感到興奮不已。我給歐門的一個旅行社打電話,他們為我安排好火車票,替我訂了巴黎的一家小酒店的房間。第二天我會從歐門出發,我知道只要給點好處,就可以讓那位年長友善的司機送我去車站,而且對此事保持緘默。
當天下午天空放晴,出現了十天以來的第一道陽光,但這並不是那天具有特殊意義的唯一理由。我坐在可以俯瞰城堡入口的房間裡、看著迎面而來的陽光穿透樹梢,突然間注意到一名身材高挑穿著一襲鋪滿了大紅玫瑰圖案黑色貼身長袍的年輕女孩,正穿過草坪朝著古堡走來。她邁著大步輕快地走著,整個人充滿了自信,就好像她是派對女主人一樣。她漆黑的長髮和髮間別著的紅玫瑰及長袍相映成趣。她算是我抵達後這十天以來見到的最明亮最活力四射的景象了;而且看起來年齡與我相仿。我立刻被她吸引,決定必須馬上和她碰面。迅速梳理好頭髮之後我衝了出去,興奮地坐在跨橋的護欄上,等待她從古堡裡走出來。突然間她已經來到了我的面前。我們都面帶微笑和對方打招呼,然後我說了一些下雨後天晴了之類無關緊要的話,便開始自我介紹。
「我叫露絲.羅伯茨,」她的英國口音很好聽,「你就是那個美國男孩吧?」
「是的,你怎麼知道的?你有眼通嗎?」她笑了起來,笑容溫暖有力,立即擄獲了我的心。
「我看過來賓名單,」她補充道,「可是你聽上去不像美國人。」
我解釋說我是在哥斯大黎加出生的,她立即回應說很喜歡我自認為已擺脫掉的口音。她在我身邊坐下,我們聊了一會兒。她有一種高傲的美,明亮的黑眼珠裡閃爍著調皮的火花、流露出獨立自主的神態,鼓舞著我說出心裡話。我沒提到第二天要去巴黎,但她已經察覺我是因為見不著克里希那吉而感到失望。
「你把希望寄託在克里希那吉身上是很傻的,」她就事論事地說。
她是對的。克里希那吉本人也曾警告過我這一點,但事情還是發生了,其實我並不喜歡這種感覺。她帶著一抹嘲弄的微笑走開了,我看著她邁著感性又輕盈的貓步,逐漸消失於附屬樓的女性專區。
雖然我感覺被她立即吸引,但從未幻想過以後的生活會跟她聯結在一起。她很有魅力,不過顯然是把我當成孩子一樣在看待。第二天要去巴黎的決心已經動搖,可我同時也擔心自己展現出的模樣不夠成熟。或許去趟巴黎哪怕只有幾天的時間,回來之後她就可能覺得我見過世面老練了一些。我一直記得好萊塢高中的那位教法語的男老師的話,「巴黎會使你成為真正的男人。」當我沉浸在這些想法中的時候艾米莉女士出現了,她告訴我說克里希那吉將會在明天下午三點見我。這下好了,巴黎已經被我暫時拋諸腦後,不過露絲可沒有。
一想到要見克里希那吉我就激動不已,那晚幾乎沒闔眼。不過他這麼久沒理我,心裡還是覺得有點受傷,於是決定要表現得鎮靜、冷漠而疏離,讓他知道我這十天來的感受是什麼。
他住在古堡的二樓,第二天我準時敲響他的房門。聽到他讓我進去的聲音時,我的心臟跳得飛快。按照艾米莉女士先前關於他健康情況的描述,我以為克里希那吉會看上去蒼白、消瘦又憔悴。但是當我推開房門時,看見的卻是眼前的這位盤腿坐在矮台子上的男子,他白色的腰布外面罩著一件金黃色長袍。這真是我所見過的最光彩奪目最美的人類。我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地凝視著,他是真的讓我屏住了呼吸。那一刻可以說是終生難忘。接著他微笑地說,「進來吧,進來吧,西德尼,」並且示意我和他一起坐到講台上。出於禮貌我想問候一下他身體的情況,儘管看上去他從未顯得這麼健康過,而我卻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沉默了許久之後他說他知道我不太開心,我點點頭。接著他說我前幾個星期一直忙於社交活動,眼下感到失望是在所難免的。我很想知道他是怎麼得知的,因為我們已經兩個多月沒見面或交流了。我猜想這是出於理性推測。他盯著我看的時候眼神顯得特別明亮,然後他說,「我很高興你取消了去巴黎的旅程。」這可真是令我大吃一驚,因為此計畫我沒告訴過任何人。「巴黎是個美麗的城市,可也是個腐爛的黑洞。」他又加上了這麼一句話。我說我打算在露營活動結束後再過去遊玩。接著話題轉到了古堡和莊園的美景上面,他答應幾天後親自帶我四處走走,到時候我們會去樹林和牧場裡做個遠程散步。接下來又是一陣長時間的沉默,感覺像是在邀約我討論我的問題,但是那一刻我什麼問題也沒了,心裡感到平靜而滿足。探訪來到了尾聲,當我起身準備離開時,他告訴我幾乎所有的客人都已抵達,明天上午會在圖書館發表簡短的歡迎辭。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我們在寬敞的圖書館裡集合,一起盤坐在漂亮的波斯地毯上,克里希那吉則盤腿坐在我們對面的沙發上。這是房間裡僅存的一件家具,後面的牆上還掛著一幅十七世紀專門為古堡訂製的華麗哥白林壁毯。他的開場白是我們過去多生多世都曾經和他在一起過,未來世也將會繼續同行。(最近我向他提到這句話,他非常驚訝地說,「我真的說過嗎?」)他發言的時間很短,簡單地介紹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想做的事:幫助人類獲得終極自由,協助他們靠自己擺脫一切權威束縛。在他演講過程中的某個時刻,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在我身上發生了。沒有任何理由地,我突然感到一陣狂喜從心輪區域爆發出來,一波接著一波越來越強烈,直到我覺得必須張開嘴為至樂大聲歡呼為止。這使我想起了《拉撒路笑了》一劇中歐文.皮切爾的狂笑──但這回可是真實不虛的體驗,祂不請自來且不期而遇,整個佔據了我的身心。在這個過程中我被超拔到幾乎要離開自己的身體。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也從沒想過自己能夠體驗到祂。
致辭結束之後多數的來賓都趁著陽光明媚在午餐前去樹林裡散步。我自己一個人待著,想盡可能地留住無法描述的那一刻所留下的芳香。我獨自一人坐在高大榆樹的綠蔭下,感受著那股至樂大能逐漸平息下來,融入到呼吸的韻律中,繼之而來的是浩瀚無邊的靜謐和不斷向上湧動的愛意,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感覺逐漸退居幕後。我期待著即將到來的和克里希那吉的散步,希望他能再度點燃幾天前為我帶來高峰經驗的內在火花。我渴望再度被那狂喜的火焰吞沒,它讓整個世界都變得純淨無邪,就好像那天清晨才剛剛被誕生出來似的。
我們的確出去散步了,克里希那吉和我,不過渴望的體悟並未出現。儘管如此,我還是領受到一種輕盈、明透和靜謐的奇妙之感。踩著人跡罕至的泥土小徑,在高高的樹下穿行,色彩鮮豔的蝴蝶於光影中飛來舞去,我們一路悠閒地散著步,幾乎沒什麼交流。克里希那吉似乎對自然界發生的每一個變化都了然於胸,甚至連腳下的蟲子他都十分小心不要踩到牠們。我告訴他我認為他的歡迎辭非常鼓舞人心,但是對我自身的屬靈經驗卻隻字未提。這層體悟才剛剛冒出頭且瞬間即逝,展開討論似乎為時尚早,它就像是一株嬌嫩的植物,你必須細心地加以照料,不讓它暴露在強風中。克里希那吉通常會在最不經意的時刻隨口說出一句話,勁道如同加勒比海的颶風一樣把你徹底摧毀。我以前經歷過,這次可不想再冒這個險了。
如同往常一樣我在這個話題上兜著圈子,迫切地想知道他對我甚為重視的議題有什麼看法。「在你達到你的解脫目標之前,」我問他,「你有過什麼特殊體驗嗎,例如巨大的狂喜和解放之感?」
「有過,」他答道。
「那你對它做了什麼?」
「什麼也沒做。我從不追求這種經驗。」
「如果你感覺這類經歷是前行路上的重要指標,你會鼓勵這種行為嗎?」
「我會帶著全然的覺知和愛去觀察,看看祂要把我引向何處。」
這是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我願意把這個議題先就這麼擱著。在古堡裡每天都有人前來探訪克里希那吉。有些人會待上幾個小時或者住上兩三天。在短暫的來訪中有兩名協助世界導師傳播教誨的「使徒」。一年前英國神智學會領軍人物,浮誇招搖的喬治.阿倫戴爾,突然宣佈成立使徒會,他自己也是成員之一。他指派妻子魯克米尼.戴維,一位年輕漂亮的婆羅門女性,和詹姆斯.衛奇伍德主教一同前來造訪。魯克米尼身穿五顏六色的印度紗麗,看上去很漂亮。她的態度開放友好,每個人都喜歡她。詹姆斯.衛奇伍德主教則穿著神父的法衣,身材高大、面色黝黑、長相英俊,胸前墜著一個很大的鑲寶石的十字架,手上戴著主教戒指。他冷漠淡然,渾身上下充斥著自我重要感,散發出靈性傲慢的腐朽氣息。一位熟知他的朋友為我寫了封介紹信,但我已經完全失去興趣,信都懶得交給他了。
克對喬治.阿倫戴爾和衛奇伍德主教發布的荒唐且具有煽動性的言論感到相當不安,他們的意思是某些人經由擇選成為了「克里希那吉的門徒」。阿倫戴爾宣稱這是彌勒菩薩傳遞下來的旨意。克憤怒地拒絕了他們的一切安排,聲稱自己絕不會接受任何門徒的。那些知道他私下對此事有多麼厭惡的人,非常驚訝於他在公開場合處理這個問題時表現出的溫和態度。他們有所不知的是,貝贊特博士因為信任阿倫戴爾而被捲入其中,基於對貝贊特夫人的愛,克不會做出任何可能令她尷尬或傷害到情感的激烈舉動。(但是多年之後他在歐亥強烈表達了自己在這個議題上的看法,他認為阿倫戴爾和衛奇伍德無情地試圖利用他來壯大自己。我曾經和克面對面地討論過這個話題,知道克對他們為達一己之目的而使出卑劣伎倆有多麼憤怒。)
一週接著一週,漫長盛夏在快樂中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我們在可愛的樹林裡散步,閒聊了幾回但沒說什麼具有啟發性或深刻的內容,因為除了享受他的陪伴之外似乎什麼都不需要了。
不過我和他的最後一次談話卻令我感到不安。在來埃爾德之前我剛從高中畢業,雖然一向對學習不是特別上心,但確實是打算繼續上大學的。我所需要的只是一點點鼓勵,克里希那吉卻沒有給我。當我問他是否應該繼續學業追求事業發展時,他帶著以往談話中流露出的相同心境回答說:生命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獲得內在自由,一種無條件的解放,以便達到真正的徹悟解脫。其它事情都是在浪費時間。「不要浪費你的時間,每一天都很重要。要設立目標,然後匯集所有能量去實現它。」他說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整個人格都由於他為自己設立的個人目標而燃燒:幫助所有人獲得自由解脫。
對一個容易受外境影響剛睜開眼睛準備看新世界的男孩來說,放下學業和事業發展去追求「解脫」並不是什麼上乘建議,但我認為這個忠告與克當時對世界的看法及感受是一致的。可是從他後來對教育的觀點來判斷,我很懷疑他是否會繼續給出這樣的建議。多年來克的溝通技巧和傳達教誨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概括地說,他晚年時的言論變得更加清晰銳利。或許多年前他早已洞見到一切,所以當早期的某次講座結束之後我告訴他說他的話語斷斷續續不夠連貫,因此我不明白他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沒錯,我今早的談話有點搞砸了。我想描繪的是一個嶄新的維度和意涵,但卻用了舊有的方式在詮釋,這就像一名畫家正在嘗試繪出不同的東西,而我也正在學習新的技巧,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停了一會兒然後說到,「或許到了六十歲時……」總之,我不想讓有關我未來的話題給埃爾德的美妙經歷蒙上陰影,所以就暫時將它置於腦後了。
接下來的幾天既有節奏緩慢的默觀冥想,也有令人興奮的歡樂時光。大家在古堡四周風景如畫的護城河上划船,還被允許可以玩遊戲—主要是打排球,有時克里希那吉也會參與進來。結識來自不同國家的有趣人士真是充滿著樂趣又帶來了自我探索上面的挑戰。我非常感激克給了我機會和他在一起,但是很難向他傳達這份情感,因為他拒絕接受任何人對他表達感恩。他在任何時刻都散發出一種令人變得警覺和敏銳的靈性品質。
在這段時間裡我沒怎麼看到那位令我激動的新朋友露絲.羅伯茨。她一般都忙著和比她年長的朋友們在一起,其中一位已經訂婚的富有荷蘭哲學家J. J.范德.列烏比她大了十歲。庫斯是人們送給他的暱稱,此君個子很高,臉上帶著一副哲人容易有的嚴肅表情,而且他的頭髮已經全禿,由此而傳出了一段小插典,讓這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厭其煩地講了一遍又一遍。某個陽光燦爛的下午他無預警地站在附屬樓二樓的一間臥室窗戶的正下方,突然感覺有一團黏稠的東西掉在他的光頭上。身為哲人的他力持鎮靜,心想應該是一隻飛過的大鳥拉屎掉到了他頭上。這是他自己的業力,得想開一點。為了不讓人發現,他緩慢而不動聲色地伸手去拿掉頭上的鳥屎,但真相卻令他恍然大悟──那團惱人的東西只不過是普通的牙膏罷了。他推測這一定是哪個幽默感扭曲的人搞的惡作劇。他義憤填膺地抬起頭,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看到的竟然是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爾躲在他正上方的窗戶後面笑得前仰後翻。庫斯撂下幾句精選的髒話之後,朝著最近的浴室走去。解脫這檔事兒有點過頭了!
後來我開玩笑地問克里希那吉,到底是他還是拉嘉戈帕爾如此精準地把牙膏擠到了庫斯的光頭上。克調皮地大笑不止,只是說拉嘉戈帕爾的幽默感相當古怪,然後補充了一句:庫斯對於這整件事過於拘謹當真了。
埃爾德古堡的快樂時光結束得太早了一點。訪客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搬到營區去,那裡也是莊園的領地,距離古堡大約一英里。
那天一大早就開始下雨,直到傍晚才放晴,當時克里希那吉和我正在樹林裡散步。天空中點綴著不同的色彩和夏日的光輝,腳下的土地則散發著褐色樹葉和潮濕泥土的芬芳。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段時間。想到以後可能再也見不著這麼非比尋常的地方,我的心開始被傷感的陰影所籠罩。在那兒逗留的日子令人難忘,我試著憶起某些比較有意義的時刻,但腦海裡如萬花筒般閃現的卻是一些無關聯也無關緊要的畫面:克里希那吉獨自一人穿過森林,新蓄的鬍子使他看起來酷似基督。艾米莉女士惱火地要我用西班牙語和某位客人溝通──他是來自波多黎各的知名人士──請求他外出散步時千萬不要隨地吐痰。(這名肇事者快速而連續地從嘴巴兩側使勁地吐痰,就像要創造某種記錄似的)「這是最違反美學最不衛生的行為,」艾米莉女士抱怨道。一名來自倫敦的年輕學生脫光衣服跳進古老的護城河裡,去撿我們先前在玩的那個排球,其他人則吃驚地看著他,緊張兮兮地發出咯咯笑聲。某位來自賴德拜特澳大利亞雪梨莊園的訪客,一臉激動地說自己聽不懂克里希那吉在說些什麼,因為他不是「信仰菩薩的人」。身材高挑愛玩的露絲和一名來自加利福尼亞風度翩翩的陸軍上尉大步走在林蔭小道上,而我這個「來自哥斯大黎加的美國男孩」—大家都這麼稱呼我—則了無希望地在一旁觀望著他們。
我知道在歐門營地的講座中是不可能和克里希那吉碰面了,所以趁著我們站在古堡正門口的時刻向他道別。我說了幾句感恩的話,但似乎完全不合時宜,然後給了他一個拉丁式的擁抱。他也同樣抱了抱我,告訴我他非常享受和我在一起的時光,並且說我們日後會有更多見面機會的。他的話就像是提示的暗號一樣,瞬間讓那美妙的狂喜再度爆發出來,並且立即把我送上樹梢頭,令我進入了無言之境。幸運的是我已經和他說過再見,於是便逕自走向樹林。等我回到附屬樓的房間時已經是黃昏,所有的人都離開了。
在外頭等候司機來接我時,心裡反思著那份狂喜之禮和埃爾德古堡之行帶給我的屬靈餽贈,然後決心這次一定不能再丟失祂,但也心知肚明這種體驗不是你決定要得到就能擁有的,因為祂降不降臨完全是自發的,不可能透過邀約、哄騙或誘導讓祂出現。不過就當時的營地聚會而言那是一個絕佳的開端,對我來說也是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經歷。
營地聚會的日子結束之後,我去了比利時和法國。巴黎很美,也很刺激。克里希那吉警告過我的,它的確有陰暗醜陋的一面,不過你可以親近它而不必然被灼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