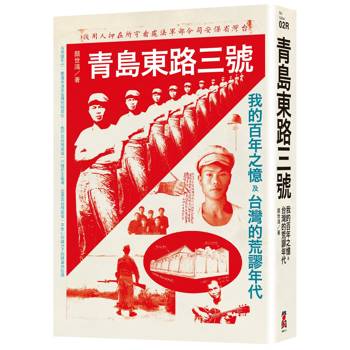【第六章】一九五○年六月,凌晨二時被捕(節錄)
就因為葉兄已被捕,「自新」不能考慮,怕跟他的口供不符。當年學期考試六月廿五日開始,參加考試可能被捕,所以決定考幾科算幾科。因《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連家也不能歸,怕連累家人。自五月三十日起,午前二點以前四處流浪。當時蚊子多,躲在病理教室前看書,實在被蚊子騷擾得有點煩、有點苦。
六月十五日中午石玉峰來,剛考完畢業考。以後才知他能到此無事,是王超倫擋下來的。他還沒有吃中飯,近下午二點,宿舍剩飯可以處理,我請廚房的師傅炒飯讓他吃。
「賣了《美術全集》和美樂達三.五相機得了四百元,準備今晚回家。」這時候石玉峰是如何我還不知道,一年難得幾次相遇,想不到這是他二、三年逃亡生活的開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與吳東烈、陳榮添被槍決;陳榮添兄是借他的身分證,四條起訴,法官可能判十年,一再駁回,硬要他走馬場町。《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使人要絕情;我不敢回家,也許受這條例的嚇脅。
六月二十日,班上朋友照例送粽子。以前一餐吃四、五粒粽子不算稀奇。吃罷晚飯,心內正思策這個晚上如何度過,先回寢室看一點書。十八日錢寄來二百元,一百五十元給大妹,連日記包裝起來託她帶回去。還了福利部的錢,身邊只剩四十元。
當時心內是覺得對父母、一家人有內疚。一些事有機會也做交代。基本上還了福利社的賒帳,金錢上不欠任何人;道義上也不欠任何人。雖然有負師長、傅斯年校長他們的期望,這種事在這時代也是很平常的事;讀一些抗戰,日本占領香港、新加坡,與華僑及災民的遭遇一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大巫見小巫;看各人的處遇及運氣。例如一九四五年大轟炸,三月一日炸台南,有一位想跑到小公園東南那一鋼筋水泥半地上型的防空壕,人已擠滿了,他是硬被人推出去,沒有辦法他逃到約二十公尺東方的亭仔腳的柱子邊;結果防空壕中了五百公斤炸彈,全壕的人近一百人都死了,他毫髮無傷。
偶而我會想起一九四四年冬那盲卜者的一句如斬鐵一般:「庚寅官符」,父親自己替我算是如此,以後家人在民雄去問卜結果更肯定,雙重官符十三年。父親過世以前在家人前,對朋友也都無奈說一聲:「命也。」他似乎很少說我的過失。這是很簡單,他自己也坐牢拖累了一家人。甚至我想不考中學,買了《早稻田講義錄》開始準備;么妹出生後,父親運轉,經濟好轉,反而是父親迫我考中學。
六月二十日夜,我正剛要由房子出去,有人敲門,我心內怔了一下,不過腳步聲似乎是熟悉的,結果是老柯(柯賢清)。他自去日本歸來,走路好像跟以前不同,可能學人家走路;軍官左側帶刀,跨出右腳以後,左腳的走法有各人不同的微妙差異。老柯是有一點拖的氣味,不注意看不出來。
「出去走走吧!」他一進來就說。
看他的表情似乎有很多的事情要說,而我正有一個問題要請他幫忙。這就換上了長褲、襯衫,還穿上去年去台北監獄時買的皮靴。出了校門,兩個人還一直沉默。我們出了新公園,老柯先開口:「這些日子,許多人被捕了,也聽說一些人逃了,一些人不見了,一團亂糟糟的……我心內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自危心態,好像去年的四六。」
柯兄與石玉峰一樣是中學同班以來的朋友,由導師指派去考過日本軍校;歸來一慢,就慢了一年,他在工學院電機系一直是最優秀的。他所謂自危,我也了解──只不過是由日本歸來帶了兩本河上肇的書。六月十五日那一天,石玉峰談過:「老柯是沒有問題了,太傑出、太銳利,人家反而不敢去碰他。」這些道理不一定在什麼時空都可以適用。郭琇琮就是他太出色,所以許多人都去爭取他。心內浮起那句:「塞翁失馬,禍福難知」。其實這句話也套不上。所以我似演舞台劇,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說。
「你不會有事的,老石就可能不同了。以後你回顧這幾年,會慢慢地找出其中道理。你了不起把那些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書燒掉;以後密告可能風行,可免惹些是非。目前你是不會有事。」我這麼說,他覺得太神奇,似話中有話。不過反正他知道我說話一向不會彎彎曲曲的。
「你自己呢?」他這麼一反問,就難交代了。我停下來在腦內稍做整理。
「我如能拖到這個月底沒有事,大概沒有事。」事實上拖不到半天,也不是對老朋友不老實。但事實如說出來了,萬一我出事,他反而會卡在那《肅清條例》的麻煩裡,那條例是要人絕情絕義的。而當時韓戰還沒有發生,中共是否渡海解放台灣還是未知數。六月十日吳石案判決,我知道的是內應之路已斷了一條。
當時已知道楊廷椅與葉兄被逮捕了,不馬上來抓我,可能是校長的好意;而且派人來暗示,要我自首。當時魏綸如兄與楊某同住,保密局去抓楊某,楊某不在,把他抓去保密局。後來傅校長保他出來,還考了六月十日的畢業考;而且來宿舍會我,告訴我葉兄已被捕。這就是傅校長叫他來的,不然以他的性格,不會攬上這種大的麻煩事,當時心內又感激也無奈。以後我們有賀年卡的往來,只是六十四年餘沒有見面了。
楊廷椅(老朱)可以說不知道我的現址,葉兄不能這麼說。而且國民黨的眼線四周埋伏,我沒有走,他們應該是知道的。我的呆望是考六月廿五日起到月底的期末考,這不過是對自己無策的一種妥協想法。以前日本特高、憲兵抓得那麼兇。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日本人歸去以前,把書排在路邊賣,馬克思、列寧、考茨基的書,全集之多,真是使我心中不解。我沒有經濟學的基礎,哲學對我不通,偶而也借來看看,沒有買。連《三民主義》、《北京好日》等一大堆。
我們再默默走入衡陽街的冰果室,又談了一些朋友的消息。那麼老實的李炎輝也被捕了。老柯還知道台南市也有一些人被捕,而後又談到時局的變化。
就因為葉兄已被捕,「自新」不能考慮,怕跟他的口供不符。當年學期考試六月廿五日開始,參加考試可能被捕,所以決定考幾科算幾科。因《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連家也不能歸,怕連累家人。自五月三十日起,午前二點以前四處流浪。當時蚊子多,躲在病理教室前看書,實在被蚊子騷擾得有點煩、有點苦。
六月十五日中午石玉峰來,剛考完畢業考。以後才知他能到此無事,是王超倫擋下來的。他還沒有吃中飯,近下午二點,宿舍剩飯可以處理,我請廚房的師傅炒飯讓他吃。
「賣了《美術全集》和美樂達三.五相機得了四百元,準備今晚回家。」這時候石玉峰是如何我還不知道,一年難得幾次相遇,想不到這是他二、三年逃亡生活的開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與吳東烈、陳榮添被槍決;陳榮添兄是借他的身分證,四條起訴,法官可能判十年,一再駁回,硬要他走馬場町。《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使人要絕情;我不敢回家,也許受這條例的嚇脅。
六月二十日,班上朋友照例送粽子。以前一餐吃四、五粒粽子不算稀奇。吃罷晚飯,心內正思策這個晚上如何度過,先回寢室看一點書。十八日錢寄來二百元,一百五十元給大妹,連日記包裝起來託她帶回去。還了福利部的錢,身邊只剩四十元。
當時心內是覺得對父母、一家人有內疚。一些事有機會也做交代。基本上還了福利社的賒帳,金錢上不欠任何人;道義上也不欠任何人。雖然有負師長、傅斯年校長他們的期望,這種事在這時代也是很平常的事;讀一些抗戰,日本占領香港、新加坡,與華僑及災民的遭遇一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大巫見小巫;看各人的處遇及運氣。例如一九四五年大轟炸,三月一日炸台南,有一位想跑到小公園東南那一鋼筋水泥半地上型的防空壕,人已擠滿了,他是硬被人推出去,沒有辦法他逃到約二十公尺東方的亭仔腳的柱子邊;結果防空壕中了五百公斤炸彈,全壕的人近一百人都死了,他毫髮無傷。
偶而我會想起一九四四年冬那盲卜者的一句如斬鐵一般:「庚寅官符」,父親自己替我算是如此,以後家人在民雄去問卜結果更肯定,雙重官符十三年。父親過世以前在家人前,對朋友也都無奈說一聲:「命也。」他似乎很少說我的過失。這是很簡單,他自己也坐牢拖累了一家人。甚至我想不考中學,買了《早稻田講義錄》開始準備;么妹出生後,父親運轉,經濟好轉,反而是父親迫我考中學。
六月二十日夜,我正剛要由房子出去,有人敲門,我心內怔了一下,不過腳步聲似乎是熟悉的,結果是老柯(柯賢清)。他自去日本歸來,走路好像跟以前不同,可能學人家走路;軍官左側帶刀,跨出右腳以後,左腳的走法有各人不同的微妙差異。老柯是有一點拖的氣味,不注意看不出來。
「出去走走吧!」他一進來就說。
看他的表情似乎有很多的事情要說,而我正有一個問題要請他幫忙。這就換上了長褲、襯衫,還穿上去年去台北監獄時買的皮靴。出了校門,兩個人還一直沉默。我們出了新公園,老柯先開口:「這些日子,許多人被捕了,也聽說一些人逃了,一些人不見了,一團亂糟糟的……我心內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自危心態,好像去年的四六。」
柯兄與石玉峰一樣是中學同班以來的朋友,由導師指派去考過日本軍校;歸來一慢,就慢了一年,他在工學院電機系一直是最優秀的。他所謂自危,我也了解──只不過是由日本歸來帶了兩本河上肇的書。六月十五日那一天,石玉峰談過:「老柯是沒有問題了,太傑出、太銳利,人家反而不敢去碰他。」這些道理不一定在什麼時空都可以適用。郭琇琮就是他太出色,所以許多人都去爭取他。心內浮起那句:「塞翁失馬,禍福難知」。其實這句話也套不上。所以我似演舞台劇,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說。
「你不會有事的,老石就可能不同了。以後你回顧這幾年,會慢慢地找出其中道理。你了不起把那些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書燒掉;以後密告可能風行,可免惹些是非。目前你是不會有事。」我這麼說,他覺得太神奇,似話中有話。不過反正他知道我說話一向不會彎彎曲曲的。
「你自己呢?」他這麼一反問,就難交代了。我停下來在腦內稍做整理。
「我如能拖到這個月底沒有事,大概沒有事。」事實上拖不到半天,也不是對老朋友不老實。但事實如說出來了,萬一我出事,他反而會卡在那《肅清條例》的麻煩裡,那條例是要人絕情絕義的。而當時韓戰還沒有發生,中共是否渡海解放台灣還是未知數。六月十日吳石案判決,我知道的是內應之路已斷了一條。
當時已知道楊廷椅與葉兄被逮捕了,不馬上來抓我,可能是校長的好意;而且派人來暗示,要我自首。當時魏綸如兄與楊某同住,保密局去抓楊某,楊某不在,把他抓去保密局。後來傅校長保他出來,還考了六月十日的畢業考;而且來宿舍會我,告訴我葉兄已被捕。這就是傅校長叫他來的,不然以他的性格,不會攬上這種大的麻煩事,當時心內又感激也無奈。以後我們有賀年卡的往來,只是六十四年餘沒有見面了。
楊廷椅(老朱)可以說不知道我的現址,葉兄不能這麼說。而且國民黨的眼線四周埋伏,我沒有走,他們應該是知道的。我的呆望是考六月廿五日起到月底的期末考,這不過是對自己無策的一種妥協想法。以前日本特高、憲兵抓得那麼兇。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日本人歸去以前,把書排在路邊賣,馬克思、列寧、考茨基的書,全集之多,真是使我心中不解。我沒有經濟學的基礎,哲學對我不通,偶而也借來看看,沒有買。連《三民主義》、《北京好日》等一大堆。
我們再默默走入衡陽街的冰果室,又談了一些朋友的消息。那麼老實的李炎輝也被捕了。老柯還知道台南市也有一些人被捕,而後又談到時局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