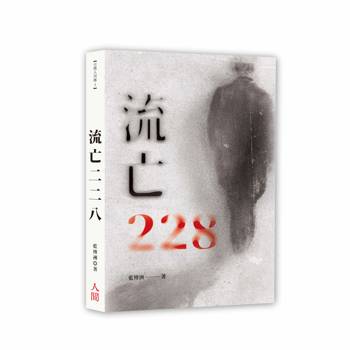從高雄苓雅寮出發――延平學院進步學生葉紀東(1927-2000)
他出生於日據下高雄苓雅寮。
他以第一名畢業公學校並考進高雄中學校。
他越級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卻因「政治審查」而被除名。
光復後,他北上就讀新成立的延平大學,
他對接收政權從期望、失望到絕望而參加地下黨,
他投入臺灣的學生運動,組織臺北學生的二二八武裝鬥爭。
事變後,他回到南部家鄉領導地下組織,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早晨,因身分暴露而出走大陸……
我的本名是葉崇培,日據時代出生於高雄市苓雅寮工人家庭。父親是台灣鐵道部高雄工廠車床工人。母親聰明能幹,但吃了一輩子苦。我小時候就常聽她說,她五歲開始,每天天未明就被叫起來幫外婆幹活,做飯,餵豬,餵牛;十四歲開始,天未亮就出門,走到她家在覆鼎金的田地幹農活,天黑了才收工,還得挑一擔柴火回家。母親嫁到我家後又遭受封建意識的祖母虐待,如果不是為了我們幾個兄弟,早就離婚了。母親省吃儉用,養雞養豬,用撿來的樹枝樹皮當柴火。她到一家裁縫店學針線活,幾天後就開始攬活回家做(連地主家高檔的細毛西服也敢接回來修),幾乎每天幹到半夜。這樣,一家人靠父親的工資和母親為人縫紉的收入維持生計,雖不富裕,尚能溫飽。我和兩個弟弟還能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上中學,母親功不可沒。光靠父親的薪水做不到的。
我讀的小學叫青葉公學校,同班同學五十幾人,包括曾任高雄市議會議長的陳田錨、三信高商校長蔡華山、東元電機總經理張火山等等。從二年級起,一直到畢業,我都保持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四、五、六年級連續三年的級任老師孫媽諒熱心桑梓教育,對我照顧有加,多次找勸父親,一定要讓我多受教育。父親也向我表示,他不會給我們兄弟留下什麼財產,但我們能考上什麼學校,他一定支持我們上學。
民族歧視與覺醒
一九四○年四月,我從小學畢業,慕名而報考臺灣南部當時最難考的名校――高雄中學校。當時高雄市人口三十萬,日本居民祇不過一兩萬,不到全市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而高雄中學每年招生的名額,日本人占四分之三,臺灣人只占四分之一。那年,招二百多人,包括我在內,考上的臺灣同學祇有五十五人。也就是說,日人子弟優劣混雜,很容易考上,而臺灣同學必須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少數人。孫老師和同學都慶賀我考上這個學校。父親還給我訂做了一雙皮鞋當做禮物。我每天從苓雅寮走到三塊厝上學,才知道十四歲的母親下田走的路比我還更遠更辛苦。
父親極富民族主義精神,學習勤奮,待人誠懇,雖然沒有上過日本學校,但讀了很多漢文書。日本發動「七七」侵華戰爭後,加強台灣的殖民統治,嚴厲取締漢文教育。父親怕我們祇受日本教育,而忘了民族文化,因此冒著風險,要求我每天必須安排一段時間接受他的漢文授課。我雖然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但老老實實,學會了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和「論語」。因為日軍常遭八路軍游擊戰的抗擊,在學校,校長訓話常把共產黨描繪成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壞人。回到家,我說給父親聽。父親卻說,共產黨是好還是壞,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然後沒有再說什麼。但他這句話一直記在我心頭。父親還喜愛民族樂曲,組織了一個民族樂器演奏隊,大部分是他工廠的工友和鄰里好友,常常在我們家門前的樹底下演奏南管,招來鄰里小孩圍觀。父親買來一把二胡給我,要我學奏。但我不爭氣,始終沒有學成。那把二胡在?上掛了好長時間以後,父親把它送給別人了。
高雄中學是民族歧視嚴重的學校。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懂得什叫「民族歧視」。開學後,我仍埋頭讀書,但很快就開始吃苦頭了。數理化、英文、日文,我的成績都不錯。還有勞動、體育、軍訓等課,我也認真地做。割草,積肥,明明做得比日本同學多,但老師給我打的分數常常是七十多分,故意拉低我學業成績的平均分數。在課堂?,老師問考卷,我常得九十多分或滿分,惹得日本同學妒嫉。有一次,考卷被搶去撕碎。我氣得當場回擊一拳。下課時,一群日本學生就攔住我,拉到操場一角痛揍,直到我鼻血橫流,躺倒草地,才揚長而去。苓雅寮同學找到我,帶我去洗鼻血,發覺鼻樑骨被打彎了。我怕母親看見會傷心,好些日子,等到天黑了才回家。好在年輕,鼻樑骨慢慢長直了。
最讓我刻骨記恨的是,高我一年級的臺灣同學顏再策(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平日為人剛強,敢於反抗日本同學的欺侮,保護臺灣同學,因此就被日本同學告密說上夜市吃宵夜,違犯校規,而被罰跪在操場司令臺上,讓夏日太陽暴曬。每當回憶此事,顏君遭此嚴厲懲罰而低頭哭泣的情形猶在眼前。
為了防備日本同學的欺侮,臺灣同學特別團結,我們苓雅寮同學上學時都要集合在一個地點,由高年級同學帶隊一起走,下課時也一樣,集合好了才一起走。我被攔住,拉去挨揍那一次,就是同學們等不到我,派人四處尋找,送我回家的。我們一起上下課的傳統一直保留下來。
我的抗日情緒,由於考臺北高等學校口試不及格而更加強烈。
一九四四年,唸完雄中四年級時,我就由學校推薦越級去參加臺灣最難考的台北高等學校升學考試。那年,考生五百多名,我成功地通過了筆試,成為一百零一名錄取者之一。與我同時考上的雄中學生還有三個人,但他們一個是五年級的應屆畢業生,另外兩個則是補習後的重考生。聽說,頭一年有五人留級,口試還要刷去六名,以保持一年級學生一百名。
所謂「口試」,其實就是「政治審查」,對台灣學生特別嚴格。由於我的筆試成績優異,開始時,考官對我十分親切友好。學校分文理兩科,理科又分甲班學英語,乙班學德語。日本當時的醫學屬德國系統,學醫必須懂德語。所以他問我為什麼要考理乙,是不是將來想學醫?我回答說想學火箭,因為我注意到德國用火箭越海轟炸英倫三島。而我正在學數學曲線,對各種曲線可以用不同的方程式表現,很有興趣。
考官一聽,應該是以為一個臺灣學生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研究火箭吧,於是就關心起我的對日「忠誠」了。他問我為什麼不改日本姓名,家?是否用日語等有關「皇民化」的問題。一聽到他們問起「皇民化」的問題,我就很反感。他以一種傲慢的語氣問我有沒有常常去參拜神社呀!我堵爛地答道我家離神社太遠所以不太常去。事實上,學校每個月都會安排我們集體武裝步行到位於壽山的神社參拜。可我總是藉故不去。主考官有點不高興,但還是接著問我家?有沒有神壇?有啊!我說,大家都有。他問那你拜不拜?照規定應該天天拜,可我卻從來沒有拜過,因為不好意思便敷衍說偶爾會拜一下。日本人主考官又問我都祈禱些什麼?我說保佑我身體健康。我明知應該祈禱諸如「武運長久」「皇軍勝利」之類的口號,但我卻偏不這樣說,因此惹惱了日本主考官。考官的臉色變了,用力擱下手上的筆,口試結束了。
幸好,我的筆試成績非常優異,學校還是允許先辦理報到手續。但一個星期後,他們就要我回高雄中學,一面繼續上五年級的課;一面等候通知。果然,榜上無名。我的級任老師野村急了,問我是否身體有病,叫我去查X光片。我心想是心?有「病」,但不敢跟他明講口試的情形。
這個事件雖然對我打擊很大,但也同時使我的民族意識覺醒,看透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有了認識。我因而覺悟到,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青年,如果還想靠唸日本書而往上爬的話,那麼,臺灣人民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因此,我就開始重新去思考臺灣人民將來的出路是什麼?如果靠日本人,有沒有光榮幸福的未來?
(未完……)
他出生於日據下高雄苓雅寮。
他以第一名畢業公學校並考進高雄中學校。
他越級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卻因「政治審查」而被除名。
光復後,他北上就讀新成立的延平大學,
他對接收政權從期望、失望到絕望而參加地下黨,
他投入臺灣的學生運動,組織臺北學生的二二八武裝鬥爭。
事變後,他回到南部家鄉領導地下組織,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早晨,因身分暴露而出走大陸……
我的本名是葉崇培,日據時代出生於高雄市苓雅寮工人家庭。父親是台灣鐵道部高雄工廠車床工人。母親聰明能幹,但吃了一輩子苦。我小時候就常聽她說,她五歲開始,每天天未明就被叫起來幫外婆幹活,做飯,餵豬,餵牛;十四歲開始,天未亮就出門,走到她家在覆鼎金的田地幹農活,天黑了才收工,還得挑一擔柴火回家。母親嫁到我家後又遭受封建意識的祖母虐待,如果不是為了我們幾個兄弟,早就離婚了。母親省吃儉用,養雞養豬,用撿來的樹枝樹皮當柴火。她到一家裁縫店學針線活,幾天後就開始攬活回家做(連地主家高檔的細毛西服也敢接回來修),幾乎每天幹到半夜。這樣,一家人靠父親的工資和母親為人縫紉的收入維持生計,雖不富裕,尚能溫飽。我和兩個弟弟還能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上中學,母親功不可沒。光靠父親的薪水做不到的。
我讀的小學叫青葉公學校,同班同學五十幾人,包括曾任高雄市議會議長的陳田錨、三信高商校長蔡華山、東元電機總經理張火山等等。從二年級起,一直到畢業,我都保持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四、五、六年級連續三年的級任老師孫媽諒熱心桑梓教育,對我照顧有加,多次找勸父親,一定要讓我多受教育。父親也向我表示,他不會給我們兄弟留下什麼財產,但我們能考上什麼學校,他一定支持我們上學。
民族歧視與覺醒
一九四○年四月,我從小學畢業,慕名而報考臺灣南部當時最難考的名校――高雄中學校。當時高雄市人口三十萬,日本居民祇不過一兩萬,不到全市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而高雄中學每年招生的名額,日本人占四分之三,臺灣人只占四分之一。那年,招二百多人,包括我在內,考上的臺灣同學祇有五十五人。也就是說,日人子弟優劣混雜,很容易考上,而臺灣同學必須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少數人。孫老師和同學都慶賀我考上這個學校。父親還給我訂做了一雙皮鞋當做禮物。我每天從苓雅寮走到三塊厝上學,才知道十四歲的母親下田走的路比我還更遠更辛苦。
父親極富民族主義精神,學習勤奮,待人誠懇,雖然沒有上過日本學校,但讀了很多漢文書。日本發動「七七」侵華戰爭後,加強台灣的殖民統治,嚴厲取締漢文教育。父親怕我們祇受日本教育,而忘了民族文化,因此冒著風險,要求我每天必須安排一段時間接受他的漢文授課。我雖然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但老老實實,學會了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和「論語」。因為日軍常遭八路軍游擊戰的抗擊,在學校,校長訓話常把共產黨描繪成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壞人。回到家,我說給父親聽。父親卻說,共產黨是好還是壞,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然後沒有再說什麼。但他這句話一直記在我心頭。父親還喜愛民族樂曲,組織了一個民族樂器演奏隊,大部分是他工廠的工友和鄰里好友,常常在我們家門前的樹底下演奏南管,招來鄰里小孩圍觀。父親買來一把二胡給我,要我學奏。但我不爭氣,始終沒有學成。那把二胡在?上掛了好長時間以後,父親把它送給別人了。
高雄中學是民族歧視嚴重的學校。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懂得什叫「民族歧視」。開學後,我仍埋頭讀書,但很快就開始吃苦頭了。數理化、英文、日文,我的成績都不錯。還有勞動、體育、軍訓等課,我也認真地做。割草,積肥,明明做得比日本同學多,但老師給我打的分數常常是七十多分,故意拉低我學業成績的平均分數。在課堂?,老師問考卷,我常得九十多分或滿分,惹得日本同學妒嫉。有一次,考卷被搶去撕碎。我氣得當場回擊一拳。下課時,一群日本學生就攔住我,拉到操場一角痛揍,直到我鼻血橫流,躺倒草地,才揚長而去。苓雅寮同學找到我,帶我去洗鼻血,發覺鼻樑骨被打彎了。我怕母親看見會傷心,好些日子,等到天黑了才回家。好在年輕,鼻樑骨慢慢長直了。
最讓我刻骨記恨的是,高我一年級的臺灣同學顏再策(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平日為人剛強,敢於反抗日本同學的欺侮,保護臺灣同學,因此就被日本同學告密說上夜市吃宵夜,違犯校規,而被罰跪在操場司令臺上,讓夏日太陽暴曬。每當回憶此事,顏君遭此嚴厲懲罰而低頭哭泣的情形猶在眼前。
為了防備日本同學的欺侮,臺灣同學特別團結,我們苓雅寮同學上學時都要集合在一個地點,由高年級同學帶隊一起走,下課時也一樣,集合好了才一起走。我被攔住,拉去挨揍那一次,就是同學們等不到我,派人四處尋找,送我回家的。我們一起上下課的傳統一直保留下來。
我的抗日情緒,由於考臺北高等學校口試不及格而更加強烈。
一九四四年,唸完雄中四年級時,我就由學校推薦越級去參加臺灣最難考的台北高等學校升學考試。那年,考生五百多名,我成功地通過了筆試,成為一百零一名錄取者之一。與我同時考上的雄中學生還有三個人,但他們一個是五年級的應屆畢業生,另外兩個則是補習後的重考生。聽說,頭一年有五人留級,口試還要刷去六名,以保持一年級學生一百名。
所謂「口試」,其實就是「政治審查」,對台灣學生特別嚴格。由於我的筆試成績優異,開始時,考官對我十分親切友好。學校分文理兩科,理科又分甲班學英語,乙班學德語。日本當時的醫學屬德國系統,學醫必須懂德語。所以他問我為什麼要考理乙,是不是將來想學醫?我回答說想學火箭,因為我注意到德國用火箭越海轟炸英倫三島。而我正在學數學曲線,對各種曲線可以用不同的方程式表現,很有興趣。
考官一聽,應該是以為一個臺灣學生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研究火箭吧,於是就關心起我的對日「忠誠」了。他問我為什麼不改日本姓名,家?是否用日語等有關「皇民化」的問題。一聽到他們問起「皇民化」的問題,我就很反感。他以一種傲慢的語氣問我有沒有常常去參拜神社呀!我堵爛地答道我家離神社太遠所以不太常去。事實上,學校每個月都會安排我們集體武裝步行到位於壽山的神社參拜。可我總是藉故不去。主考官有點不高興,但還是接著問我家?有沒有神壇?有啊!我說,大家都有。他問那你拜不拜?照規定應該天天拜,可我卻從來沒有拜過,因為不好意思便敷衍說偶爾會拜一下。日本人主考官又問我都祈禱些什麼?我說保佑我身體健康。我明知應該祈禱諸如「武運長久」「皇軍勝利」之類的口號,但我卻偏不這樣說,因此惹惱了日本主考官。考官的臉色變了,用力擱下手上的筆,口試結束了。
幸好,我的筆試成績非常優異,學校還是允許先辦理報到手續。但一個星期後,他們就要我回高雄中學,一面繼續上五年級的課;一面等候通知。果然,榜上無名。我的級任老師野村急了,問我是否身體有病,叫我去查X光片。我心想是心?有「病」,但不敢跟他明講口試的情形。
這個事件雖然對我打擊很大,但也同時使我的民族意識覺醒,看透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有了認識。我因而覺悟到,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青年,如果還想靠唸日本書而往上爬的話,那麼,臺灣人民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因此,我就開始重新去思考臺灣人民將來的出路是什麼?如果靠日本人,有沒有光榮幸福的未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