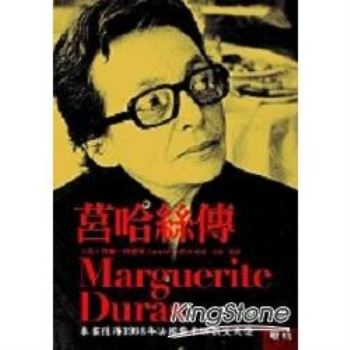序
勞爾‧阿德萊
我的遭遇是從一本書開始的——《太平洋防波堤》。我在租來的一幢房子裡發現了它,和其他的書在一道,疲憊的。那甚至還算不上是個書架。它也沒有逃脫其他火車站小說的命運,被海灘的陽光烤得焦黃,抑或是被美麗星空下的暴雨滌蕩得水跡斑斑。我幾乎沒有怎麼猶豫地選擇了它。但是我總有一種感覺,覺得它是在等我。在那個夏天,我遭受了個人情感上的一次重創,以為自己永遠恢復不過來了。我可以證明,是一本書幫我緩過勁來,讓我鼓足勇氣面對明天,它的時間替代了我的時間,它的敘事環境替代了我那一團亂麻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太平洋防波堤》裡年輕姑娘的那一份野性的執著,那一份滿含著愛的智慧。回到巴黎以後,我想要給瑪格麗特‧莒哈絲寫一封信。
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把信放在聖伯努瓦街的郵箱裡,兩天後,瑪格麗特給我來了電話。她想要見我。說說話,她說。我猶豫了,說實話,猶豫著要不要跨越這一步去見她。一本書能給的,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它的作者卻未必能給……再說,那時的瑪格麗特似乎屬於一個不受任何限制的小圈子,虔誠地宣揚那種洋洋自得的聖徒傳記式作品,宣揚作品的真不復存在,至少她自己是那麼做的。
對於莒哈絲的世界,和我的同齡人一樣,我也知之甚少。日漸腐朽的印度,混雜著印度支那小村莊黃昏日落時的場景。對我而言,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莒哈絲所意味著的:對一天將盡的這個時刻的追憶,世界的粗糙不平隱沒在黃昏的陰沉裡,恐懼和暴力似乎都繳械投降了,但是仍然在陰影中徘徊。在那樣的時刻,在那樣的黃昏時分,所有的襲擊都可能發生。殖民別墅的白熾燈光尚未點燃,而黑暗也尚未濃厚到令流浪者和災禍預言家駐足的地步。
在那個時刻,小女孩應該留在家中。也是在那個時刻,有一次,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有個從來沒有違背過母親命令的小女孩走出了家門,在她身後,黑暗中,一個乞丐大叫著突然跳了出來。小女孩跑啊,跑啊,她再也沒能緩過勁來。一直到生命遲暮,這尖叫聲仍然停留在她的記憶之中,揮之不去。
按響聖伯努瓦街的門鈴時,我有點惴惴不安。不,我沒有再去讀莒哈絲,但是她嚇著我了。她的聲音,她的風格,她的光芒在我心中建立了一個所謂的莒哈絲傳奇,我既有對傳奇人物的一種不正常的好奇心,又有一種對作家的讚賞。之後我卻發現全都搞錯了。瑪格麗特來開了門,把我領進廚房,為我準備咖啡。一雙活潑的眼睛:這是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充沛的精力,笑容滿面。後來我得以不斷地接近她,而這印象也一直沒有改變:她最親近的,分列在她不同人生各個不同階段的朋友(因為在她對待不同朋友時,在對比強烈的寫作的選擇中,在相去甚遠、經由她精心區別的各種理念前,她的確會展示不同的人生),在追憶她時幾乎都會說:瑪格麗特留下的,是她的笑。調皮的,孩子般的笑,傳達友情的笑,諷刺的笑,甚至是滿懷惡意的笑。瑪格麗特笑所有的東西,所有的人,男男女女,甚至她自己。那天,她也是一邊說一邊笑,一直在笑,談話是從鏡子邊釘的那些照片開始的,她的童年。我記得,她還談到了她的母親,談到了她和兒子的各種奇遇。
我們繼續不定時地見面。但更多的是電話交談。瑪格麗特專門愛在夜半時分給人打電話。每出一本書,她都會像個小女孩那般焦灼不安,急切地問你的看法,拙態百出卻又不容分說。她生病了,我們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往來。她把自己隔離起來,一個愛她的男人在照顧她,保護她。我從來不是她的朋友;可能算得上一個她「比較喜歡」的人,這是她的話,一個她喜歡隨便談談什麼的人,什麼都能談,又什麼都不談,從做菜到電影、文學、時裝、雜聞、政治,就這樣,事先也沒什麼意向,隨意,談到哪兒是哪兒的那種談話。她喜歡孩子,喜歡到幾近瘋狂。我的女兒蕾阿就是在她那本《藍眼睛黑頭髮》出版的第二天出生的,也是黑頭髮,藍眼睛。她覺得這是某種生命的符號。後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疏淡了來往,但是從來沒有完全中斷過聯繫。《情人》的成功讓她陷入了榮譽的陷阱。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和我說話了;她有點拿腔拿調,用第三人稱談論自己,她不知道自己這樣正是給誹謗者提供了絕好的證據。不過她也不在乎別人的冷笑,因為她覺得他們根本沒有真正讀懂她的作品。無所謂。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了類似俄國知識分子的悲愴形象,古怪、頹敗。聲名之後,莒哈絲遭到的是當眾被侮辱的命運。
生病又讓她再一次遠離他人,但她沒有遠離自己,沒有遠離自己的寫作慾。昏迷了九個月之後,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要求把沒完成的稿子繼續改下去。她在印度支那的法國學校裡長大,教學用的是越南語和法語,到了晚年,她愈發地為自己當年學業證書上的優秀成績而自豪起來。「我是整個印度支那的第一名。」後來她曾很鄭重地對我說,那時她像孩子一樣,驕傲極了,雙眼放光。「你知不知道,別人都在說這個小女孩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這個瘦弱而滿身野性的小女孩,當時是西貢孩子的榜樣,她的拼寫和語法都那麼出眾,大人不無艷羨地拿她來教育自己的孩子;可是也正是這個小女孩,在以後的日子裡對我們的語言卻越來越粗暴,她擾亂了規則,創造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詞語和它們的位置以最快的速度,以世界上最簡單的方式──至少看上去如此──導向意義的純粹性。
莒哈絲就是這樣說話的。也許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對自己說話時,有時也是這樣的,秘密地。無論如何,莒哈絲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對於莒哈絲來說,文學和電影是一回事,觀眾、讀者是國王。她給予它一種激情,而這激情主要是從我們在最隱秘、最不為人所知的地方所耗盡的強烈感覺中,從禁地中榨取來的。別人經常指責她自私、自戀,指責她那種吞噬了自己的愛。從她出版第一本書開始,瑪格麗特‧莒哈絲就對自己的天賦確信不疑。很快,她便把自己看成一個完完全全的天才。她建造了自己的塑像。在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她不停地談論著這個叫做莒哈絲的人。她不再清楚自己是誰,誰是這個寫作的莒哈絲。不得不重新回過頭去讀自己的作品時,她在未出版的一本簿子的留邊處用一貫那種細密的字體寫著──就在死前不久:「這是莒哈絲寫的?」「這不像是出自莒哈絲之手。」
誰是真正的莒哈絲?這個狡黠的莒哈絲啊,手上有這麼多的面具,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故意將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段隱藏起來,搞亂線索,以此為樂。這個自傳專家、職業懺悔師的莒哈絲成功地讓我們相信了她的謊言。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裡,瑪格麗特‧莒哈絲更相信的是自己小說中人物的存在,而不是切實陪伴過她的情人和朋友。在她看來,「真實」這個詞本身就是靠不住的,而現實是那麼多變,她根本無能為力。就像她所喜愛的一個女主人公那樣,瑪格麗特‧莒哈絲也生活在船上。四周是狂風暴雨。事實的確如此,每當我們想搞清楚她是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總是一片沙泥。只有她寫作的時候會出現暫時的平靜。也只有在此時,她才終於和自己合為一體:「我知道,在我寫作的時候,有點什麼東西正在形成。我讓這東西作用於自己,它也許能在我身上產生某種女性化的特徵……就像我轉向一片空曠的場地。」
一邊是瑪格麗特‧莒哈絲真實的生活,另一邊則是她所講述的生活。如何區分真實生活與故事,真實生活和謊言呢?在歲月的流程中,她一直想要通過寫作重建自己的生活,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部傳記。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於將不同版本的莒哈絲會聚在一起,彼此觀照,我不敢說能夠揭示一個如此喜歡躲避的人的真相。我想要照亮那些不為人所知的區域,那是她用自己的天賦一手炮製的:童年結束和那個中國男人的關係,她在世界大戰中和解放戰爭中的態度,她愛情、文學和政治的激情。因為瑪格麗特的生活是一個世紀的生活,一個深深融於時代的女人的生活,一個與這個世紀所有戰鬥緊密相關的人的生活。
在她死後,人們找出她一本私人簿子,在撕下的一頁紙上,她寫道:「有人說他們不喜歡自己的書,如果確實有這種人存在,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戰勝自己的羞怯……我喜歡自己的書。我對自己的書很感興趣。書裡的人物就是我生活中的人物。」瑪格麗特‧莒哈絲自己也不清楚是什麼時候開始想成為一個作家的。這一點已經在時光的黑暗隧道中迷失了,她說,但是應該是在童年行將結束的時刻。「我自以為我在寫作,但事實上我從來就不曾寫過,我以為我在愛,但我從來也不曾愛過,我什麼也沒有做,不過是站在那緊閉的門前等待罷了。」必須按字面意義來理解《情人》裡的這些話。
傳記的門一直緊閉著。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我問瑪格麗特‧莒哈絲,她能否接受我寫她的傳記,她聳了聳肩,又重新回到她的書上,她為我沖了杯咖啡,之後又談到了別的事:那一天是談政治。那個時候,有一本關於她的書快要出版了,她企圖推遲它的出版。我到後來才明白她為何如此惱火憤怒。莒哈絲討厭別人挖掘她的生活。她恨,根本是恨除她之外的人寫她。她對自己生命流程中的某些片段遮遮掩掩並非出於偶然。不准進入。莒哈絲花了那麼大的耐心來構建自己這樣一個人物,我想,我可能永遠也等不來她同意的那一天。我接受了她的建議。我買了她最早出的那些書,按照編年的順序來讀,但是我在這次閱讀中產生了很多疑問,有生平上的,也有文學上的。我又去看了她。我的內心有這麼多的問題在撞來撞去,以至於在她的面前我只有沉默。這天下午是她先開始說的。她給我看了釘在辦公桌上的一張照片,是她的小哥哥,接下去她談了很多……用她那嘶啞而獨一無二的嗓音,用那樣一種斷裂的語言,她談到了印度支那,談到了她的童年,她一生中所經受的種種背叛,還有她的恐懼,這份一直不曾離去的恐懼。
瑪格麗特‧莒哈絲在童年和少年時代非常痛苦。也許這痛苦能夠解釋她叛逆的能力。她從來就是個叛逆而憤怒的女人,一個為自由而受難的使徒。政治上的自由,還有性的自由。因為,她自然是個關於愛情的作家,但是她也是個為了女性事業而奮鬥的戰士,她充滿激情地捍衛著女性的樂趣。她一直要求享有肉體歡娛的權利,並且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偉大的情人。她喜歡做愛,並且善於激起愛的力量,她喜歡肉體的歡娛,喜歡背棄,喜歡愛的極致。她探尋著極限,要吸乾所有的能量:她在肉體的歡娛中追尋絕對。你們也許還記得,在《情人》裡,她寫道:「我身上本來就具有慾望的地位。我在十五歲時就有了一副耽於逸樂的面目,儘管我還不懂得什麼叫逸樂。」莒哈絲一生聽憑慾望的支配,直至死亡。慾望是她行動的綱領。她從未曾逃離,不管是以背棄的名義,還是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就是因為沒有把慾望激發起來。慾望就在於把它引發出來的人身上,除非它根本就不存在,否則只要那麼看一眼,它就會出現。它是性的直接媒介,要麼就什麼也不是。」於是我在瑪格麗特‧莒哈絲還活著的時候就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我們有過好幾次談話。她那時已經深為記憶障礙所折磨了。時而清晰時而模糊。有些日子她能想起很多事,她的童年,在拉丁區讀大學的青年時代,還有對她自己還喜歡著的幾本書的深刻分析──因為那時她已經開始詆毀自己的作品了,有些日子則非常悲傷,她的自得、自戀,她重新燃起的某些仇恨,屢次中斷了我們的談話。但是整個過程中,瑪格麗特始終是活潑的,她那種令人讚賞的活潑,有的時候,會讓她放聲大笑,這笑驅走了一切,抹去了她的怨恨,她又變得迷人起來。我很快明白過來,她並非她自身的檔案保管員,她,是個畢生為遭到劫掠的童年而哭泣的人,是個捍衛自己不同風格的寫作的理論家。
必須到別的地方去尋找。殖民地圖書館裡的檔案,某些浸潤著肉慾的場景,她曾經住過的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所顯示出來的力量,還有過去曾經同行的同伴的追憶,丟在一邊、沒有發表的文章,私人的、已經和菜譜混在一堆的日記簿……我更是一直在傾聽,整日整日地傾聽那些曾經與之分享過生命、愛情和夢想的男男女女。
很多人都接受了這場追尋真相的遊戲,為了她。在這個過程中,我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成了朋友。在此我應該對所有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是我要特別提到四個人,如果沒有他們的珍貴幫助,這項工作也許永遠也無法完成,他們是讓‧馬斯科羅——瑪格麗特的兒子,是他把沒有發表的檔案交給我;迪奧尼斯‧馬斯科羅,前者的父親,瑪格麗特的同伴,是他讓我閱讀了她的私人日記和信簡;還有莫尼克‧安泰爾姆,在這項工作中,她一直給予我支持和幫助;最後是揚‧安德烈亞,這位我和瑪格麗特之間殷勤的信使。在最後的幾個月裡,也是揚將瑪格麗特的話記錄下來,交給我。比如說她對於我在寫作方面所提的問題的回答。是在我收到的最後的問題回答中,她說寫作沒有一點神祕之處,她還說,在生活中,沒有秘密可言。
然而秘密依舊存在。我只希望有一些能夠得到澄清,即使仍有相當一部分陰影和神秘存在——儘管我們追尋了許久,找了許多證明,還發現了她沒有拿去發表的很多東西。瑪格麗特‧莒哈絲今天也仍然在迴避我們。也許這樣很好。有的時候,傳記所能做的也不過是假設。讓讀者自己去找真相吧。就像她本人的書,一向都要缺上幾塊拼板的,漏洞和空白仍然存在。
瑪格麗特‧莒哈絲的一本傳記?它早就來了:書中的一切遠比作者本人的生活要真實。她還說:「生命的歷史並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沒有的。並沒有什麼中心,也沒有什麼道路,線索。只有某些廣闊的場地、處所,人們總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經有過怎樣一個人,不,不是那樣,什麼人也沒有。」的確,很長時間以來,什麼人也沒有。最多也就是不成體統的一團亂麻中的一點,在這亂麻中,壓力已經退化成暴力。是寫作的慾望將之塑造成社會的人,讓她在這世界上扮演一定的角色,是寫作給了她這個名字:莒哈絲。
死前,她終於把個人的檔案全部移交給現代出版檔案館。她不想保留太多東西。但是就像她自己做的乾燥花那樣,瑪格麗特‧莒哈絲收藏的個人檔案也是毫無章法的。運到里爾街的現代出版檔案館,是十六個紙盒!之中有出版物、校稿、世界各地報紙上的文章;還有手稿、劇本、她的小說的不同版本、隨便塗抹的素描、兒子的練習簿、從街區垃圾箱裡翻出來的畫書、抄下來或經她修改過的菜譜、沒有發表的作品、在反面加過註的照片、扔掉的計畫、《情人》的草稿、拿來寫《痛苦》的藍皮本子、私人日記,還有在夜半撕下來的活頁紙。其中就有這樣一段,沒有標明日期,或許可以算做她的警句吧:「我從來沒有和任何人說過些什麼。關於我的一生,我的憤怒,還有瘋狂奔向歡娛的這肉體,我什麼也沒有說,關於這個黑暗之中,被藏起來的詞。我就是恥辱,最大的沉默。我什麼也沒有說。我什麼也不表達。本質上什麼也沒有說。一切就在那裡,尚無名稱,未經損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