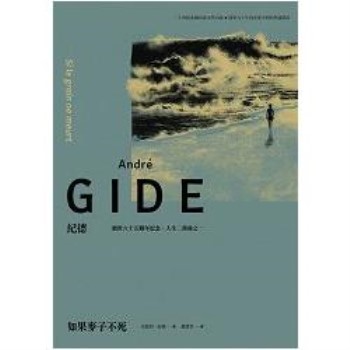【第一部】
我是個需要對話的人,內心一切都在不斷衝突、對辯。儘管多麼想忠於事實,回憶錄永遠都只能呈現一半的真實,因為一切都永遠比說出口的來得複雜。或許只有在小說中,才更貼近真實。
1
我出生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當時我父母住在梅第西街上,一棟位於五樓或是六樓的公寓,幾年之後搬離,所以我對那棟公寓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但是我記得公寓的陽台,或說從陽台所看到的景物:正前方的廣場和水池中的噴泉──更準確地說,我記得父親為我剪的紙龍,我們從陽台投向空中,隨風飄過廣場水池上空,一直飛到盧森堡公園,被高高的栗樹樹枝攔截。
我也記得一張蠻大的桌子,無疑是餐桌,鋪著一塊垂地的桌布;我和門房的兒子溜到桌布下,他和我同年齡,有時會來找我玩。
「你們在下面搞什麼鬼?」保姆大聲問。
「沒什麼。我們在玩。」
我們把帶到桌下當幌子的玩具大聲地搖動,其實我們玩的是別的:我們不是在一起玩,而是兩人緊靠著,後來我才知道我們玩的是叫做「壞習慣」的遊戲。
我們兩個當中,是誰教對方這個玩法的?是誰先開始的?我不知道。必須承認,有時候小孩不必人教就會自己發明這些遊戲。至於我,我不記得到底有沒有人教我,我又是如何發現這種快感的;不過,在我記憶所及之處,它就已經存在了。
我知道把這件事說出來是個錯誤,也清楚會造成的後果;我已預感到人們或許會拿這件事來攻擊我。但是我的自述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真實。就當作我是因懺悔才寫這本自傳的。
在那個純真的年紀,人們希望孩子的心靈只是透明、溫柔、純淨,然而我在自己身上看見的,卻只是陰鬱、醜陋、陰險。
大人帶我到盧森堡公園去,但我不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離得遠遠的,一臉陰鬱,挨在保姆身旁,看著其他孩子們玩。他們用小桶子裝沙子,做了一排排漂亮的沙堆……趁保姆轉過頭去的一瞬,我衝過去踩坍所有沙堆。
我下面要敘述的另一件事更奇怪,可能因為奇怪,我反倒覺得沒那麼可恥。後來我母親常常跟我提起這件事,她的敘述使我的記憶更為鮮明。這件事發生在烏澤,我們每年會去一次,探望我父親的母親、以及其他幾個親戚,其中包括弗洛家的堂兄妹,他們在市中心有一棟帶著花園的古老房子。這件事就發生在弗洛家的這棟房子裡。我堂姊長得非常美,她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她留著一襲黑亮的頭髮,中分,垂向兩邊服貼在兩鬢,更襯托出她如玉石雕刻的側面(我後來也看過她的相片)和晶瑩白皙的肌膚。這皮膚晶亮的光澤,我記憶十分深刻,我更記得跟她見面的那一天,她穿著一件領口開得很低的洋裝。
「快去親吻堂姊問好」,我一走進客廳,母親便說。(我那時應該不超過四歲或五歲。)我走向前,弗洛堂姊把我拉向她,一邊彎下身來,露出肩膀。我面對這晶瑩的肌膚,不知發了什麼瘋,與其把嘴唇湊到她伸過來的臉頰上,我被光滑的肩膀蠱惑住,竟張嘴在上面大大咬了一口。堂姊痛地叫出聲來,我也嚇壞了,滿是噁心地吐著口水。我很快被帶開,大家都太過驚愕,甚至忘了處罰我。
我找到一張那時期我的照片,縮在母親裙邊,穿著一件可笑的格子洋裝,帶著病態、惡意的神情,眼光歪斜。
我六歲時,家搬離梅第西街。我們的新公寓位在杜爾農街二號二樓,聖蘇比街的轉角口,父親的書房窗戶就對著這條街;我房間的窗戶則朝向一個大院子。我記憶最深的是會客室,因為在我沒去學校也不在房間裡時,最常待在那裡,母親厭煩我圍著她轉個不停時,就會叫我去找「朋友皮耶」玩──意思就是自個兒玩。會客室裡五顏六色的地毯印著許多大的幾何圖案,在地毯上和我那「朋友皮耶」打彈珠真是有趣極了。
我有一個小網袋,裝最漂亮的彈珠,這些彈珠是一顆一顆得來,不和其他普通的彈珠混在一起。我每一次握在手裡,都心醉它們的美麗:尤其有一顆小的,黑色瑪瑙,上面有一道赤道和兩條白色回歸線;還有一顆是半透明的光玉髓,淺貝殼色,是我拿來當母彈的珠子。另外裝在一個大帆布袋裡的,是一堆輸輸贏贏的灰色彈珠,後來我找到真正玩伴一起玩彈珠時,就拿它們做賭注。另一個令我樂此不疲的遊戲,是人們稱為萬花筒的神奇東西:一個像望遠鏡的器具,眼睛湊上去看,底端會顯現不停轉換的玫瑰形圖案,是密封在兩片透明玻璃片裡許多移動的彩色玻璃碎片形成的圖案。萬花筒裡面嵌著好幾片鏡子,只消輕輕一轉動,就會反射再折射出瑰麗的玻璃片。玫瑰形圖案的變化讓我目眩神移,不可言喻。我現在還清楚記得那些彩色玻璃片的顏色和形狀:最大的是一片淺紅寶石色,三角形,因為它最重,總是先移動,牽動著其他玻璃片一起。還有一塊深石榴紅色,幾乎呈圓形;一片是鐮刀片狀的翡翠色;一片黃玉色的,形狀我忘了;一片清玉色,還有三小片赤金色。它們從不會同時出現在圖案裡:有些完全被擋在鏡子後面的外緣,有的露出一半;唯有那片淺紅寶石色,因為最重要,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堂姊妹們也喜歡看萬花筒,但不像我這麼有耐心,往往大力搖動一下,再觀察整個變換過的圖案。我不一樣:我的眼睛盯著圖案,緩緩一點一點轉動萬花筒,欣賞玫瑰圖案緩慢的變化。有時,一個小玻璃片輕柔的變動,就會帶動圖案整個大翻轉。我既好奇又驚訝,很快就想拆開萬花筒一探究竟。我剝下底端玻璃,一一拿出裡面的玻璃片,從厚紙板管子裡抽出三片鏡子,之後再組裝回去,但只放回三、四片有顏色的玻璃片。圖案變化少了,也不再令我驚訝,但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每一個變化的軌跡!如何清楚明白樂趣的來源!
然後,我興致一來,拿一些千奇百怪的東西替代小玻璃片裝進去──鵝毛筆的筆尖、蒼蠅翅膀、一節火柴、一根草。結果變得黑乎乎,一點都不繽紛,但是因為鏡子的反射,出現幾何圖形的美麗……總之,我對這個遊戲樂此不疲,玩個幾小時幾天都不厭倦。我相信今日的孩子不識其中樂趣,因此我花了這麼多筆墨來描寫。
我幼年時的其他遊戲──單人紙牌、移印畫、積木,都是一個人玩的遊戲。我沒有任何玩伴……喔,有一個小朋友,但可惜!他並不是玩伴。瑪麗帶我到盧森堡公園時,我經常看見一個同年紀的孩子,纖弱、斯文、安靜,蒼白的臉被一付大眼鏡遮住了一半,鏡片之厚,根本看不清鏡片底下的眼睛。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也或許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們都叫他「羊咩咩」,因為他穿一件白色羊毛大衣。「羊咩咩,您為什麼戴眼鏡?」(我記得沒有和他用平語。)
「我眼睛有毛病。」
「讓我看看。」
他摘下那恐怖的鏡片,他可憐、迷離、眨動的眼神讓我心中一陣刺痛。
我們並不一起玩,除了手牽著手,一句話也不說地散步之外,我不記得我們還做過其他的事。
這段最初始的友誼為時不久。羊咩咩再也不來了。啊!自此之後,盧森堡公園如此寂寥!……但我真正的絕望,是在明白羊咩咩瞎了的時候開始。瑪麗在附近遇到那小男孩的保姆,之後對我母親轉述她們的對話;她低聲地說,怕我聽到,但我還是聽到了這幾個字:「他現在連嘴巴在哪兒都找不到了!」這當然是句無理可笑的話,我也立刻意識到了,因為要吃東西,何須眼睛找嘴巴在哪裡──但是我聽了很難過。我跑回房間裡哭泣,之後好幾天我試著把眼睛緊閉,閉著眼睛走路,努力感受羊咩咩必須承受的體驗。
我父親忙著準備法學院的課程,無暇照顧我。一天中大半時間裡,他都關在有點陰暗的大書房裡,除非他邀我,否則我不能隨便進他書房。一張父親的相片讓我回憶起他的模樣:一把修剪成四方形的鬍子,蠻長而捲曲的黑髮;若非這張相片,我對父親的記憶就只是他極度的溫和。後來母親告訴我,同事們暱稱他「君子」(Virprobus);我又從他一位同事那兒得知,大家經常向他請教事情。
我對父親既崇拜又有點畏懼,書房的嚴肅氣氛更增添我的敬畏。我進他書房像踏進神廟,暗影裡書架像神龕一般矗立,華麗的深色厚地毯吸收了我的腳步聲。一個斜面書架放在兩扇窗戶其中一扇旁邊,書房中央有一張很大的桌子,桌上擺滿書和紙張。父親找出一本厚厚的書,好像是《勃根地風俗誌》或《諾曼第風俗誌》,厚重的對開版,他把書攤開在扶手椅的扶手上,和我一頁一頁一起看,直到碰到蛀蟲辛勞工作的痕跡。那是父親這位法學家之前查閱書中一篇古文時看見的,他讚賞蛀蟲咬的這些祕密曲折的通道,不禁說:「嘿!我孩子看到這個一定覺得有趣。」我的確覺得很有趣,那也是因為他感到有趣,而更加深了我的趣味。但是我對書房的記憶還是與父親讓我在那裡念的書息息相關。就這一點,他的看法很獨特,我母親並不苟同,我經常聽見他們倆討論,對一個幼童的腦袋,應該灌輸什麼養料才適當。關於順從,也會有這樣相似的討論,母親認為孩子不必了解,先要順從,父親卻一直主張要對我解釋一切。我記得很清楚,母親把我比喻為希伯來子民,在得到恩寵之前,最好先經受虔誠法規洗禮。今日,我覺得母親是對的;但在當時,我經常不服從她,老是跟她爭辯,而父親只要一開口,我就百依百順。我想他的教育方式應該是順著心性,而非按照方法,所以他教導那些讓我驚奇、喜歡的事物,也都是他自己所喜歡或驚奇的。那個時代,法國的兒童讀物根本不適合孩子閱讀,我相信他若看到之後我閱讀的那些書籍,例如塞居爾夫人(MmeSégur)的著作,一定很不以為然──我必須承認,當時我和那時代所有兒童一樣,對那些讀物帶著愚蠢的樂趣,看的津津有味。幸而,這還是比不上先前父親念書給我聽時帶給我的樂趣,他念莫里哀戲劇中的某一幕、《奧德賽》或《好聰明的巴特朗先生》(LaFarcedePathelin)裡的片段、辛巴達或阿里巴巴的冒險故事,以及莫里斯桑德(MauriceSand)那本著作《面具》(LesMasques)裡介紹的義大利喜劇中的一些滑稽故事,那本書裡介紹的丑角阿樂甘、可羅碧、波利虛內爾、皮埃羅這些人物我都好喜歡,藉著父親的聲音,我就像聽到他們之間的對話。
這些閱讀如此成功,父親對我的信心如此之大,乃至於有一天開始念《約伯記》給我聽。母親說她也想參與,因此這不是在往常念書的書房裡進行,而是在她覺得特別自在的一間小客廳裡。當然,我不敢發誓說我立即瞭解了這本聖書之美!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次的誦讀讓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僅是內容的莊嚴,還有父親虔敬的聲音和母親的臉部表情,她不時閉上眼睛以便呈現或呵護她的虔誠靜思,只偶爾抬起眼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愛、詢問、和希望。
某些夏季晴朗的晚上,若晚餐不太晚結束、父親又沒有太多工作的話,他會說:
「我的小朋友來和我一起散散步嗎?」
他一向把我叫做「我的小朋友」。
「你們會乖乖的,對不對?」母親說。「別太晚回來喲。」我喜歡和父親一起出門;因為他很少有時間照顧我,我們一起做過的少數的事都帶著一種不尋常的、重要的、有點神祕的氣氛,讓我欣喜迷醉。
我們一邊玩著猜謎或同音異義字的遊戲,一邊沿著杜爾農街往上走,然後穿越盧森堡公園,或是沿著公園外緣的聖米歇大道,直到連接著巴黎天文台的第二個公園。那時候,醫藥學院對面的荒地都還沒有建築;連醫藥學院當時都還不存在。現在這些六層的建築房屋,當時只是一些亂搭的臨時棚子,賣舊衣服或是租售大小輪自行車的攤子。這連接盧森堡公園的第二個公園,外環著一圈柏油──或是碎石子──空地,是大小輪自行車愛好者的場地;他們跨在取代了腳踏車的這個怪異且令人費解的機器上,轉彎、迅速超越我們身邊,消失在夜色裡。我們讚羨他們的大膽和高雅姿態。維持這高大車身平衡的後方小輪小的幾乎看不見,前方細窄的大輪子轉啊轉,騎在上面的人就好像古怪神奇的生物。
夜色降臨,稍遠處一家音樂咖啡館的燈光襯托地更為明亮,音樂聲吸引著我們。我們看不見煤氣燈,只看見圍籬上方透出來的光,把栗樹照的怪異的明亮。我們走過去,圍籬木板並不緊密,眼睛湊上兩片木板間的縫隙,我看見一群黑壓壓興奮的觀眾上方,有一個令人訝異的舞台,一個女歌手在上面唱著庸俗歌曲。
有時候我們還有時間,回頭再穿過諾大的盧森堡公園。過不多久就聽見鼕鼕的鼓聲,表示公園關門時間到了。最後一些散步的人心不甘情不願地朝出口走去,公園管理員緊跟在身後,他們後面寬廣無人的林蔭道,充滿著神祕。那些夜晚,我帶著樹影、瞌睡、怪異的感覺沉沉入睡。
我五歲時,父母親送我到芙蘿小姐以及萊克保夫人家上兒童初級課程。芙蘿小姐住在塞納街。和我一樣年齡小的孩子一臉慘白看著字母或一頁一頁的文字時,那些年齡大的孩子──準確地說那些大女生(芙蘿小姐收了許多年紀稍大的女孩,男孩則只收年紀小的)──興奮地準備一齣將在家長面前演出的話劇。她們準備的是《訟棍》(Plaideurs)裡的一幕,正忙著試戴假鬍子;我好羨慕她們能穿戲服喬裝,一定好玩極了。
至於萊克保夫人家,除了那架古老的Ramsdem發電機之外,我什麼都不記得了。那架機器令我好奇的心癢,一個玻璃圓片黏貼著許多小金屬片,一個手搖把可以轉動玻璃片;大家禁止碰這部機器,就像高壓電線桿上掛的警告牌,「有死亡危險」。一天,萊克保夫人想要轉動機器發電,我們這些孩子邊圍成一大圈,離的遠遠的,因為大家都很害怕,以為會看到女老師被電死;尤其她食指彎曲去碰那個銅球的手還微微發抖。但是沒有一丁點火星冒出……啊!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
我是個需要對話的人,內心一切都在不斷衝突、對辯。儘管多麼想忠於事實,回憶錄永遠都只能呈現一半的真實,因為一切都永遠比說出口的來得複雜。或許只有在小說中,才更貼近真實。
1
我出生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當時我父母住在梅第西街上,一棟位於五樓或是六樓的公寓,幾年之後搬離,所以我對那棟公寓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但是我記得公寓的陽台,或說從陽台所看到的景物:正前方的廣場和水池中的噴泉──更準確地說,我記得父親為我剪的紙龍,我們從陽台投向空中,隨風飄過廣場水池上空,一直飛到盧森堡公園,被高高的栗樹樹枝攔截。
我也記得一張蠻大的桌子,無疑是餐桌,鋪著一塊垂地的桌布;我和門房的兒子溜到桌布下,他和我同年齡,有時會來找我玩。
「你們在下面搞什麼鬼?」保姆大聲問。
「沒什麼。我們在玩。」
我們把帶到桌下當幌子的玩具大聲地搖動,其實我們玩的是別的:我們不是在一起玩,而是兩人緊靠著,後來我才知道我們玩的是叫做「壞習慣」的遊戲。
我們兩個當中,是誰教對方這個玩法的?是誰先開始的?我不知道。必須承認,有時候小孩不必人教就會自己發明這些遊戲。至於我,我不記得到底有沒有人教我,我又是如何發現這種快感的;不過,在我記憶所及之處,它就已經存在了。
我知道把這件事說出來是個錯誤,也清楚會造成的後果;我已預感到人們或許會拿這件事來攻擊我。但是我的自述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真實。就當作我是因懺悔才寫這本自傳的。
在那個純真的年紀,人們希望孩子的心靈只是透明、溫柔、純淨,然而我在自己身上看見的,卻只是陰鬱、醜陋、陰險。
大人帶我到盧森堡公園去,但我不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離得遠遠的,一臉陰鬱,挨在保姆身旁,看著其他孩子們玩。他們用小桶子裝沙子,做了一排排漂亮的沙堆……趁保姆轉過頭去的一瞬,我衝過去踩坍所有沙堆。
我下面要敘述的另一件事更奇怪,可能因為奇怪,我反倒覺得沒那麼可恥。後來我母親常常跟我提起這件事,她的敘述使我的記憶更為鮮明。這件事發生在烏澤,我們每年會去一次,探望我父親的母親、以及其他幾個親戚,其中包括弗洛家的堂兄妹,他們在市中心有一棟帶著花園的古老房子。這件事就發生在弗洛家的這棟房子裡。我堂姊長得非常美,她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她留著一襲黑亮的頭髮,中分,垂向兩邊服貼在兩鬢,更襯托出她如玉石雕刻的側面(我後來也看過她的相片)和晶瑩白皙的肌膚。這皮膚晶亮的光澤,我記憶十分深刻,我更記得跟她見面的那一天,她穿著一件領口開得很低的洋裝。
「快去親吻堂姊問好」,我一走進客廳,母親便說。(我那時應該不超過四歲或五歲。)我走向前,弗洛堂姊把我拉向她,一邊彎下身來,露出肩膀。我面對這晶瑩的肌膚,不知發了什麼瘋,與其把嘴唇湊到她伸過來的臉頰上,我被光滑的肩膀蠱惑住,竟張嘴在上面大大咬了一口。堂姊痛地叫出聲來,我也嚇壞了,滿是噁心地吐著口水。我很快被帶開,大家都太過驚愕,甚至忘了處罰我。
我找到一張那時期我的照片,縮在母親裙邊,穿著一件可笑的格子洋裝,帶著病態、惡意的神情,眼光歪斜。
我六歲時,家搬離梅第西街。我們的新公寓位在杜爾農街二號二樓,聖蘇比街的轉角口,父親的書房窗戶就對著這條街;我房間的窗戶則朝向一個大院子。我記憶最深的是會客室,因為在我沒去學校也不在房間裡時,最常待在那裡,母親厭煩我圍著她轉個不停時,就會叫我去找「朋友皮耶」玩──意思就是自個兒玩。會客室裡五顏六色的地毯印著許多大的幾何圖案,在地毯上和我那「朋友皮耶」打彈珠真是有趣極了。
我有一個小網袋,裝最漂亮的彈珠,這些彈珠是一顆一顆得來,不和其他普通的彈珠混在一起。我每一次握在手裡,都心醉它們的美麗:尤其有一顆小的,黑色瑪瑙,上面有一道赤道和兩條白色回歸線;還有一顆是半透明的光玉髓,淺貝殼色,是我拿來當母彈的珠子。另外裝在一個大帆布袋裡的,是一堆輸輸贏贏的灰色彈珠,後來我找到真正玩伴一起玩彈珠時,就拿它們做賭注。另一個令我樂此不疲的遊戲,是人們稱為萬花筒的神奇東西:一個像望遠鏡的器具,眼睛湊上去看,底端會顯現不停轉換的玫瑰形圖案,是密封在兩片透明玻璃片裡許多移動的彩色玻璃碎片形成的圖案。萬花筒裡面嵌著好幾片鏡子,只消輕輕一轉動,就會反射再折射出瑰麗的玻璃片。玫瑰形圖案的變化讓我目眩神移,不可言喻。我現在還清楚記得那些彩色玻璃片的顏色和形狀:最大的是一片淺紅寶石色,三角形,因為它最重,總是先移動,牽動著其他玻璃片一起。還有一塊深石榴紅色,幾乎呈圓形;一片是鐮刀片狀的翡翠色;一片黃玉色的,形狀我忘了;一片清玉色,還有三小片赤金色。它們從不會同時出現在圖案裡:有些完全被擋在鏡子後面的外緣,有的露出一半;唯有那片淺紅寶石色,因為最重要,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堂姊妹們也喜歡看萬花筒,但不像我這麼有耐心,往往大力搖動一下,再觀察整個變換過的圖案。我不一樣:我的眼睛盯著圖案,緩緩一點一點轉動萬花筒,欣賞玫瑰圖案緩慢的變化。有時,一個小玻璃片輕柔的變動,就會帶動圖案整個大翻轉。我既好奇又驚訝,很快就想拆開萬花筒一探究竟。我剝下底端玻璃,一一拿出裡面的玻璃片,從厚紙板管子裡抽出三片鏡子,之後再組裝回去,但只放回三、四片有顏色的玻璃片。圖案變化少了,也不再令我驚訝,但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每一個變化的軌跡!如何清楚明白樂趣的來源!
然後,我興致一來,拿一些千奇百怪的東西替代小玻璃片裝進去──鵝毛筆的筆尖、蒼蠅翅膀、一節火柴、一根草。結果變得黑乎乎,一點都不繽紛,但是因為鏡子的反射,出現幾何圖形的美麗……總之,我對這個遊戲樂此不疲,玩個幾小時幾天都不厭倦。我相信今日的孩子不識其中樂趣,因此我花了這麼多筆墨來描寫。
我幼年時的其他遊戲──單人紙牌、移印畫、積木,都是一個人玩的遊戲。我沒有任何玩伴……喔,有一個小朋友,但可惜!他並不是玩伴。瑪麗帶我到盧森堡公園時,我經常看見一個同年紀的孩子,纖弱、斯文、安靜,蒼白的臉被一付大眼鏡遮住了一半,鏡片之厚,根本看不清鏡片底下的眼睛。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也或許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們都叫他「羊咩咩」,因為他穿一件白色羊毛大衣。「羊咩咩,您為什麼戴眼鏡?」(我記得沒有和他用平語。)
「我眼睛有毛病。」
「讓我看看。」
他摘下那恐怖的鏡片,他可憐、迷離、眨動的眼神讓我心中一陣刺痛。
我們並不一起玩,除了手牽著手,一句話也不說地散步之外,我不記得我們還做過其他的事。
這段最初始的友誼為時不久。羊咩咩再也不來了。啊!自此之後,盧森堡公園如此寂寥!……但我真正的絕望,是在明白羊咩咩瞎了的時候開始。瑪麗在附近遇到那小男孩的保姆,之後對我母親轉述她們的對話;她低聲地說,怕我聽到,但我還是聽到了這幾個字:「他現在連嘴巴在哪兒都找不到了!」這當然是句無理可笑的話,我也立刻意識到了,因為要吃東西,何須眼睛找嘴巴在哪裡──但是我聽了很難過。我跑回房間裡哭泣,之後好幾天我試著把眼睛緊閉,閉著眼睛走路,努力感受羊咩咩必須承受的體驗。
我父親忙著準備法學院的課程,無暇照顧我。一天中大半時間裡,他都關在有點陰暗的大書房裡,除非他邀我,否則我不能隨便進他書房。一張父親的相片讓我回憶起他的模樣:一把修剪成四方形的鬍子,蠻長而捲曲的黑髮;若非這張相片,我對父親的記憶就只是他極度的溫和。後來母親告訴我,同事們暱稱他「君子」(Virprobus);我又從他一位同事那兒得知,大家經常向他請教事情。
我對父親既崇拜又有點畏懼,書房的嚴肅氣氛更增添我的敬畏。我進他書房像踏進神廟,暗影裡書架像神龕一般矗立,華麗的深色厚地毯吸收了我的腳步聲。一個斜面書架放在兩扇窗戶其中一扇旁邊,書房中央有一張很大的桌子,桌上擺滿書和紙張。父親找出一本厚厚的書,好像是《勃根地風俗誌》或《諾曼第風俗誌》,厚重的對開版,他把書攤開在扶手椅的扶手上,和我一頁一頁一起看,直到碰到蛀蟲辛勞工作的痕跡。那是父親這位法學家之前查閱書中一篇古文時看見的,他讚賞蛀蟲咬的這些祕密曲折的通道,不禁說:「嘿!我孩子看到這個一定覺得有趣。」我的確覺得很有趣,那也是因為他感到有趣,而更加深了我的趣味。但是我對書房的記憶還是與父親讓我在那裡念的書息息相關。就這一點,他的看法很獨特,我母親並不苟同,我經常聽見他們倆討論,對一個幼童的腦袋,應該灌輸什麼養料才適當。關於順從,也會有這樣相似的討論,母親認為孩子不必了解,先要順從,父親卻一直主張要對我解釋一切。我記得很清楚,母親把我比喻為希伯來子民,在得到恩寵之前,最好先經受虔誠法規洗禮。今日,我覺得母親是對的;但在當時,我經常不服從她,老是跟她爭辯,而父親只要一開口,我就百依百順。我想他的教育方式應該是順著心性,而非按照方法,所以他教導那些讓我驚奇、喜歡的事物,也都是他自己所喜歡或驚奇的。那個時代,法國的兒童讀物根本不適合孩子閱讀,我相信他若看到之後我閱讀的那些書籍,例如塞居爾夫人(MmeSégur)的著作,一定很不以為然──我必須承認,當時我和那時代所有兒童一樣,對那些讀物帶著愚蠢的樂趣,看的津津有味。幸而,這還是比不上先前父親念書給我聽時帶給我的樂趣,他念莫里哀戲劇中的某一幕、《奧德賽》或《好聰明的巴特朗先生》(LaFarcedePathelin)裡的片段、辛巴達或阿里巴巴的冒險故事,以及莫里斯桑德(MauriceSand)那本著作《面具》(LesMasques)裡介紹的義大利喜劇中的一些滑稽故事,那本書裡介紹的丑角阿樂甘、可羅碧、波利虛內爾、皮埃羅這些人物我都好喜歡,藉著父親的聲音,我就像聽到他們之間的對話。
這些閱讀如此成功,父親對我的信心如此之大,乃至於有一天開始念《約伯記》給我聽。母親說她也想參與,因此這不是在往常念書的書房裡進行,而是在她覺得特別自在的一間小客廳裡。當然,我不敢發誓說我立即瞭解了這本聖書之美!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次的誦讀讓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僅是內容的莊嚴,還有父親虔敬的聲音和母親的臉部表情,她不時閉上眼睛以便呈現或呵護她的虔誠靜思,只偶爾抬起眼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愛、詢問、和希望。
某些夏季晴朗的晚上,若晚餐不太晚結束、父親又沒有太多工作的話,他會說:
「我的小朋友來和我一起散散步嗎?」
他一向把我叫做「我的小朋友」。
「你們會乖乖的,對不對?」母親說。「別太晚回來喲。」我喜歡和父親一起出門;因為他很少有時間照顧我,我們一起做過的少數的事都帶著一種不尋常的、重要的、有點神祕的氣氛,讓我欣喜迷醉。
我們一邊玩著猜謎或同音異義字的遊戲,一邊沿著杜爾農街往上走,然後穿越盧森堡公園,或是沿著公園外緣的聖米歇大道,直到連接著巴黎天文台的第二個公園。那時候,醫藥學院對面的荒地都還沒有建築;連醫藥學院當時都還不存在。現在這些六層的建築房屋,當時只是一些亂搭的臨時棚子,賣舊衣服或是租售大小輪自行車的攤子。這連接盧森堡公園的第二個公園,外環著一圈柏油──或是碎石子──空地,是大小輪自行車愛好者的場地;他們跨在取代了腳踏車的這個怪異且令人費解的機器上,轉彎、迅速超越我們身邊,消失在夜色裡。我們讚羨他們的大膽和高雅姿態。維持這高大車身平衡的後方小輪小的幾乎看不見,前方細窄的大輪子轉啊轉,騎在上面的人就好像古怪神奇的生物。
夜色降臨,稍遠處一家音樂咖啡館的燈光襯托地更為明亮,音樂聲吸引著我們。我們看不見煤氣燈,只看見圍籬上方透出來的光,把栗樹照的怪異的明亮。我們走過去,圍籬木板並不緊密,眼睛湊上兩片木板間的縫隙,我看見一群黑壓壓興奮的觀眾上方,有一個令人訝異的舞台,一個女歌手在上面唱著庸俗歌曲。
有時候我們還有時間,回頭再穿過諾大的盧森堡公園。過不多久就聽見鼕鼕的鼓聲,表示公園關門時間到了。最後一些散步的人心不甘情不願地朝出口走去,公園管理員緊跟在身後,他們後面寬廣無人的林蔭道,充滿著神祕。那些夜晚,我帶著樹影、瞌睡、怪異的感覺沉沉入睡。
我五歲時,父母親送我到芙蘿小姐以及萊克保夫人家上兒童初級課程。芙蘿小姐住在塞納街。和我一樣年齡小的孩子一臉慘白看著字母或一頁一頁的文字時,那些年齡大的孩子──準確地說那些大女生(芙蘿小姐收了許多年紀稍大的女孩,男孩則只收年紀小的)──興奮地準備一齣將在家長面前演出的話劇。她們準備的是《訟棍》(Plaideurs)裡的一幕,正忙著試戴假鬍子;我好羨慕她們能穿戲服喬裝,一定好玩極了。
至於萊克保夫人家,除了那架古老的Ramsdem發電機之外,我什麼都不記得了。那架機器令我好奇的心癢,一個玻璃圓片黏貼著許多小金屬片,一個手搖把可以轉動玻璃片;大家禁止碰這部機器,就像高壓電線桿上掛的警告牌,「有死亡危險」。一天,萊克保夫人想要轉動機器發電,我們這些孩子邊圍成一大圈,離的遠遠的,因為大家都很害怕,以為會看到女老師被電死;尤其她食指彎曲去碰那個銅球的手還微微發抖。但是沒有一丁點火星冒出……啊!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