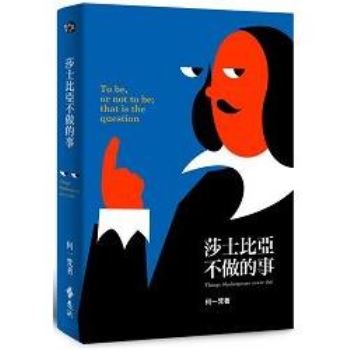〈莎士比亞不要演員演戲〉
──被遺忘的戲劇原貌,莎劇演員最直指人心的演出方式
表演的本質是神秘的
演戲,就這個字最為我們熟悉的意思,就是演員躲在角色後面。但是莎士比亞真的喜歡演戲這件事嗎?
先放下這個問題,看一位彆腳演員的演出。在電影《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中有這樣一個場景:
《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的首演要開始了,但是在後台,莎士比亞注意到準備要上場說開場白的演員,一個臨時被拉來湊數的外行人,有著嚴重的口吃。他很緊張,反覆叨唸著台詞:Two Households, both alike in dignity…(兩個家族,同等尊貴……)
他結巴得那麼厲害,莎士比亞的擔心幾乎轉變成絕望了。他跟劇團經理菲利浦‧亨斯洛(Philip Henslowe)說完蛋了,但老經驗的亨斯洛卻叫他安心。莎士比亞不解,看著這連一句話都說不好的演員問:「怎麼可能?」亨斯洛卻回答:「我不知道,這是個謎!」(I don’t know, it’s a mystery.)
時間到了,亨斯洛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這位口吃的演員推了出去,一下子,他要面對滿場盯著他看的觀眾。他緩步走到舞台正中,全場鴉雀無聲,他環顧劇場上下四方的觀眾,努力地想吐出第一個字:T……T……。突然,像是打破了第一個字母帶來的魔咒,他開始說話了。他說得那麼好,流利又有自信,像是語言自動從他嘴中跑了出來,承載著他的聲音,飛入現場每一個人的耳朵裡。莎士比亞很驚訝,但他不得不承認,it’s a mystery。
我們也應該承認的。不管今天有多少教人如何演戲的方法、工作坊、訓練課程,忘記表演的本質很神秘,認為可以被某種理論或科學的方法掌握,恐怕只會離演戲更遠。
莎士比亞的時代,戲劇正值它的青春期──希臘悲劇的盛況只能在文字中略見端倪,漫長的中世紀也只有宗教戲劇樸素地為傳教服務。對莎士比亞這一代的人來說,他們對劇場的一切不會一無所知,但也不到世故老成。這是戲劇史的青春期,充滿著摸索的動力與好奇,也沒有被太多理論上的成見侷限,甚至汙染。
It’s a mystery成了再精確也不過的形容,或許它可以讓我們停下來,回頭問問一開始的問題:演戲就是演員躲在角色的背後嗎?
從《哈姆雷特》看莎士比亞的演員訓練課莎士比亞也是演員,偶爾會在自己與別人的劇本中演出,他曾是《哈姆雷特》(Hamlet)中的鬼魂父親,是《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中的老人亞當(Adam) ──他好像特別擅長老人的角色。雖然在1603年之後不再活躍於舞台上(至少我們找不到任何記錄),但根據劇中哈姆雷特(Hamlet)給劇團演員的指導,我們知道他對演戲是有心得的。他認為演員要被好好對待,因為他們是時代的縮影與記錄(they are the abstracts and brief chronicles of the time)(2.2.527-8)。
接下來,在三幕二景一開始,他更進一步指出,說台詞的時候,必須讓台詞在舌頭上輕快地跳躍(Speak the speech,…trippingly on the tongue)(3.2.1-2),別像很多演員一樣,只會大聲嚷嚷;別用手在空氣中亂揮舞一通,溫柔點;情感爆發時要有節制;討厭自以為屌(robustious)(3.2.9)的傢伙,戴著假髮撕裂感情,只為了劈開眼光不高的觀眾(groundlings)(3.2.11)的耳膜,他們只喜歡沒語言的啞劇與噪音……
他也建議演員別太溫順(tame)(3.2.16),要讓謹慎成為演員的導師;要讓文字配合行動,行動配合文字(Suit the action to the word, the word to the action)(3.2.17-8);別太過火(overdone)(3.2.20),因為演戲的目的是為了映照自然(mirror up to nature)(3.2.22),顯示她的美德(virtue)(3.2.22)與愚昧(scorn)(3.2.23),還有這個時代的形貌與特色(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3.2.23-4)。過火的演出只會讓無知的觀眾發笑,但不會讓明智的(the judicious)(3.2.26)觀眾哀傷──你必須重視他的意見遠勝過劇場中的其他人。
他還說(當然是幫莎士比亞說的),他看過一些演員,被人高度地讚美,說話、走路卻連個基督徒的樣子都沒有(在那個年代,基督徒就是人的代名詞!),賣弄、大叫,像是大自然沒造好的人類,對人性(humanity)(3.2.34)只有拙劣的模仿。
很多人根據這段文字,認為莎士比亞反對一種宣敘性或雄辯式(declamatory)的風格,而是提倡一種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式的表演,就是現在在電視、電影中看見的那種──這是太簡化了。
事實上,我們只能從他對演員的建議中看見兩件事:一、好好說話;二、不要太過火,雖然這可以討好無知的觀眾。如果我們進一步想想莎士比亞的時代表演與觀眾的關係,並且與今天的表演環境相對照,恐怕會發現莎士比亞要說的,是──不要演戲。
「好看」的演員只是一個陌生人
想了解那時與現在對表演的看法有何不同,可以從問今天的演員一個問題開始:演出上台前,妳/你還會緊張嗎?如果會,又是為什麼?
可能每位演員的理由不一,但根據我教書、演講的經驗,我會緊張,主要是因為我不認識那些台下的聽眾。如果是教書,通常要到四、五週之後,與學生彼此熟悉了,我進教室才會比較自在點。但演員大概沒有四、五次與觀眾彼此熟悉的機會,除非理由特殊,觀眾看戲很少看第二次。特別是知道劇場觀眾總是有同行或是劇場名嘴在其中時,大概上場前的壓力多少會更大一點,不然,演得不好,明天某篇劇評又攻擊一下,總是不好受的。
希望觀眾喜歡,因此有壓力、會緊張,這是正常的。今天觀眾跟演員的關係,基本上,是一群彼此不相識的陌生人。即使觀眾中有朋友來看戲,但心態上,演員不會把「觀眾」這個集合名詞當「朋友」、當家人,特別在商業演出的狀況下。
在這種關係下,演員在表演時,或多或少,很容易為了保護自己,尋求偽裝。分析角色、進入角色生命這件事,有時候(但不是一直如此)是將角色當成一個面具,一個保護殼。更有甚者,有些演員會發展出為了讓自己好看,藉此保護自己的功夫──畢竟是面對陌生人啊!
於是,有時候我們很容易看出,演員不過是在用一套把戲或招數在放電,增加自己的魅力,讓自己更吸睛。很多很多讓自己好看的表演技術,其實都是讓自己躲起來,保護自己──但也只能瞞過那些眼光不高的觀眾。
這種「好看」,卻只讓我感到距離很遠,像是看煙火秀或特技表演一樣,是與我無關的一種景觀。這時演員並沒有與我在一起,不是真的信任我,把我當朋友、當家人。這樣的演員還是把我當消費者,用盡力氣對我進行一種征服。但是,用力愈多,卻離我愈遠,常常,我心裡都感到一陣惋惜。
會惋惜,是因為我知道今天的劇場環境不鼓勵演員信任觀眾,在商業與消費的考慮下,演戲是給觀眾看的,甚至是「把玩」的。影像表演就更不用說了,根本不是跟觀眾「在一起」,跟觀眾一起呼吸,把觀眾當家人。信任你的觀眾,好好說話
我想起莎士比亞時代的演員,特別在1594到1602年這段期間,倫敦只有兩個劇團,每個團有十五個演員左右,他們一週七天都有演出,幾乎天天劇碼不同,一年演的戲到四十齣以上,新戲約佔一半(是的,他們的記憶力是從小訓練的結果,背台詞超快)。更重要的,這麼少的演員這麼密集的演出,使他們在觀眾眼前的曝光率,大概只有今天第四台的周星馳可以比得上。
觀眾很容易記得演員,演員也不難認識觀眾。以1600年為例,所謂的劇場觀眾(playgoer)有兩萬人(台北今天看劇場的人數不到一萬),但重要的是人口的分母:整個倫敦的人口只有二十萬人。換句話說,每十個人,就有一個是劇場觀眾。你可以想像,如果你在那時代當演員,去餐廳吃個飯,那邊會超過十個人吧,就會有個觀眾認出你,彼此哈啦幾句,然後第二天在市場又碰見他……。觀眾在人口中有十分之一,這麼高的比例,讓演員與觀眾彼此熟悉。
這樣的劇場環境,不難想像,是鼓勵演員信任觀眾的。
我跟很多人一樣,遇見不熟的人會害羞,或是用客氣與禮貌保持距離,不會馬上說心裡話,但回家之後就不同了,在家人面前,我自詡為歌王也會有人欣賞,至少不在乎被嘲笑。我常想像,當年的莎劇演員在表演時,會像我在家人面前唱歌──他「落落長」的獨白,是說給自己人聽的,是為了自己人說的。就像有個你認識、你信任的朋友,在告訴你一些道理,一些想法和心情。他是那麼直接地在對你說,你很難不覺得可以與自己無關。
在彼此信任中,莎劇演員對觀眾說話(另一個面向是對上帝說話,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不偽裝,也不用在意自己的不完美被看穿,這不是什麼宣敘性或雄辯式的風格,這不過是對觀眾「好好說話」而已。只是這樣說話,直指了人心。
莎士比亞與他那個時代的劇作家,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自己是詩人(poet),稱呼進劇場的人是「聽眾」(hearer,或是the audience,這個英文字的原意也是「聽的人」),一直到職業生涯的晚期,才稱呼他們為「觀眾」(spectator),意思是「看的人」。因此,演員本來就被期待要好好說話,將詩人用心血提煉的文字,傳給來劇場的人聽的。演出密集,排戲時間也短(往往早上拿到劇本,下午就要演出),不難想像,即便演員的記憶力很強,但一起排戲的時間很短,演員彼此的默契,對角色內在的體悟等等,除非是重演或很厲害的演員,不然,以今天的標準,演戲不容易好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哈姆雷特會批評一些演員過火的演出:雙手在空中揮舞,情緒又聲嘶力竭。這些演員都只想演戲,忘了好好說話。
但莎士比亞寫劇本不是為了閱讀,他的劇本重要,是因為演員的演出讓它們重要。所以,儘管表演上的花招不少,鬥劍、搏擊,甚至噴(雞)血、跳舞……,這些只是確保了舞台的娛樂性,不是表演直指人心的來源。演戲好看,恐怕不是他能奢望的手段,也不是他冀求的。把話說好,讓文字與行動彼此相合,是表演最好的力量。
記憶與演說敘事的能力
另外,從戲劇史來看,在沒有影印機,印刷術也不太發達的時代,知識的傳播主要是依賴口語,所以一個人在成為演員之前,從小教育起,有兩種能力跟今天比特別發達:記憶力──不知道有沒有「過耳不忘」這麼誇張;演說與敘事能力──說得好,人家才容易聽進去。因此,在希臘悲劇與莎士比亞那裡,大段的台詞之所以會出現,顯然是寫劇本的人相信他的演員一定都可以做到。
莎士比亞寫的大段台詞其實很複雜,有抒情的,有議論的,也有敘事的。這些演員不僅很快能記住這些台詞,還能把說話當成一種厲害表演。
安夫人(Lady Ann)的先生明明是被理查三世殺了,卻在送殯時,被理查的一番話說動,答應嫁給他(《理查三世》[Richard III]);布魯圖斯(Brutus)殺了凱撒之後,先是發表一番演說,證明自己的正當性,贏回羅馬人民對他的信任,隨後安東尼(Antony)又發表另一篇演說,馬上贏回民心,讓布魯圖斯成為羅馬人的公敵(《凱撒大帝》[Julies Caesar])。這些場面都不太能用演的(我就在環球劇院,看過兩個年輕演員把布魯圖斯與安東尼的演說「演」得很賣力),因為如果用演的,觀眾的思維就會去想劇情的前因後果,分析為什麼民眾會有這樣的轉變。可是如果用說的,如果演說的魅力夠,台下的觀眾(也被預設成羅馬民眾)會很直接地被打動,這種感染力是當下有效的(immediate),不用透過大腦的推論與仲介(mediate)。
我們今天的演員,在當演員之前,環境並不像以前,那麼鼓勵記憶與說話兩種特質;進學校接受的表演訓練,也多半從對話、分析(人物)關係、揣摩心理特質與情感記憶、建立角色等等開始,讓演員躲在角色後面。一些很古老、很簡單的手段與能力,似乎好像在萎縮中,也連帶地喪失劇本與戲劇語言能展開的廣度。
今天,處理一整段抒情的、私人內在經驗的獨白,這對很多演員都沒有問題,但問題是,像我這樣的觀眾很容易會想:「這是你的事,干我什麼事呢?」
在這種有「你我之別」的劇場中,要不就是冷靜地觀看他人的命運;要不就是一對一單挑,用自身的生命經驗去跟角色「搏感情」。這裡面對應了一個基本的狀況:演員與觀眾不再彼此認識了。
對話取代了詩,也讓演員好好跟觀眾說話的機會消失
我想像當年一個莎劇演員是如何掌握表演訣竅的:
當他還是初試啼聲的新手,面對坐滿三千人的環球劇院,大概一樣緊張,很容易腎上腺素破表,就像一開始在《莎翁情史》中看見的那個結巴演員一樣。但如果他的表現不錯,還可以在這行待下來,他就有機會漸漸認識他的觀眾,就像我上課四、五週後會與我的學生熟悉一樣。然後,表演的自在,會在那個環境中慢慢生成,他會慢慢變成一個愈來愈好的演員,慢慢對著認識的人,對著具體認識的觀眾,像朋友、像家人一樣,好好說話。他會因此成為一個好演員,至少是莎士比亞期待的,而且不太費力。莎士比亞的年代是現代文明初生的階段,戲劇也是在它的青春期。我們在那邊看到很多戲劇原來的樣貌,喪失的、遺忘的,或者被懷念,或者成為提醒。其中,信任觀眾,將他們視為自己人,對之好好說話,恐怕是今天眾聲喧譁的劇場藝術中,最樸實的提醒之一。
之後,戲劇走到十七世紀的新古典主義,到十九世紀的佳構劇(the well-made play)、通俗劇(the melodrama),再到寫實主義,到電視、電影的興起,到各種以肢體與畫面為主的劇場風格……,我們的劇場環境不一樣了。我們很難把觀眾當自己人了,對話取代了詩,也讓演員好好跟觀眾說話的機會消失,而是成為要在陌生人面前盡力求好的一群。然後,上台前,開始緊張了……
再惋惜一次,我們的表演環境對演員已經沒有這種優勢了。但是,我還是相信,演員在意識中,還是應該信任觀眾,把觀眾當自己人、當家人。必須如此,如果表演希望能直指人心的話。
至於這本書,我也會試著信任讀者,並且好好說話。
──被遺忘的戲劇原貌,莎劇演員最直指人心的演出方式
表演的本質是神秘的
演戲,就這個字最為我們熟悉的意思,就是演員躲在角色後面。但是莎士比亞真的喜歡演戲這件事嗎?
先放下這個問題,看一位彆腳演員的演出。在電影《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中有這樣一個場景:
《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的首演要開始了,但是在後台,莎士比亞注意到準備要上場說開場白的演員,一個臨時被拉來湊數的外行人,有著嚴重的口吃。他很緊張,反覆叨唸著台詞:Two Households, both alike in dignity…(兩個家族,同等尊貴……)
他結巴得那麼厲害,莎士比亞的擔心幾乎轉變成絕望了。他跟劇團經理菲利浦‧亨斯洛(Philip Henslowe)說完蛋了,但老經驗的亨斯洛卻叫他安心。莎士比亞不解,看著這連一句話都說不好的演員問:「怎麼可能?」亨斯洛卻回答:「我不知道,這是個謎!」(I don’t know, it’s a mystery.)
時間到了,亨斯洛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這位口吃的演員推了出去,一下子,他要面對滿場盯著他看的觀眾。他緩步走到舞台正中,全場鴉雀無聲,他環顧劇場上下四方的觀眾,努力地想吐出第一個字:T……T……。突然,像是打破了第一個字母帶來的魔咒,他開始說話了。他說得那麼好,流利又有自信,像是語言自動從他嘴中跑了出來,承載著他的聲音,飛入現場每一個人的耳朵裡。莎士比亞很驚訝,但他不得不承認,it’s a mystery。
我們也應該承認的。不管今天有多少教人如何演戲的方法、工作坊、訓練課程,忘記表演的本質很神秘,認為可以被某種理論或科學的方法掌握,恐怕只會離演戲更遠。
莎士比亞的時代,戲劇正值它的青春期──希臘悲劇的盛況只能在文字中略見端倪,漫長的中世紀也只有宗教戲劇樸素地為傳教服務。對莎士比亞這一代的人來說,他們對劇場的一切不會一無所知,但也不到世故老成。這是戲劇史的青春期,充滿著摸索的動力與好奇,也沒有被太多理論上的成見侷限,甚至汙染。
It’s a mystery成了再精確也不過的形容,或許它可以讓我們停下來,回頭問問一開始的問題:演戲就是演員躲在角色的背後嗎?
從《哈姆雷特》看莎士比亞的演員訓練課莎士比亞也是演員,偶爾會在自己與別人的劇本中演出,他曾是《哈姆雷特》(Hamlet)中的鬼魂父親,是《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中的老人亞當(Adam) ──他好像特別擅長老人的角色。雖然在1603年之後不再活躍於舞台上(至少我們找不到任何記錄),但根據劇中哈姆雷特(Hamlet)給劇團演員的指導,我們知道他對演戲是有心得的。他認為演員要被好好對待,因為他們是時代的縮影與記錄(they are the abstracts and brief chronicles of the time)(2.2.527-8)。
接下來,在三幕二景一開始,他更進一步指出,說台詞的時候,必須讓台詞在舌頭上輕快地跳躍(Speak the speech,…trippingly on the tongue)(3.2.1-2),別像很多演員一樣,只會大聲嚷嚷;別用手在空氣中亂揮舞一通,溫柔點;情感爆發時要有節制;討厭自以為屌(robustious)(3.2.9)的傢伙,戴著假髮撕裂感情,只為了劈開眼光不高的觀眾(groundlings)(3.2.11)的耳膜,他們只喜歡沒語言的啞劇與噪音……
他也建議演員別太溫順(tame)(3.2.16),要讓謹慎成為演員的導師;要讓文字配合行動,行動配合文字(Suit the action to the word, the word to the action)(3.2.17-8);別太過火(overdone)(3.2.20),因為演戲的目的是為了映照自然(mirror up to nature)(3.2.22),顯示她的美德(virtue)(3.2.22)與愚昧(scorn)(3.2.23),還有這個時代的形貌與特色(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3.2.23-4)。過火的演出只會讓無知的觀眾發笑,但不會讓明智的(the judicious)(3.2.26)觀眾哀傷──你必須重視他的意見遠勝過劇場中的其他人。
他還說(當然是幫莎士比亞說的),他看過一些演員,被人高度地讚美,說話、走路卻連個基督徒的樣子都沒有(在那個年代,基督徒就是人的代名詞!),賣弄、大叫,像是大自然沒造好的人類,對人性(humanity)(3.2.34)只有拙劣的模仿。
很多人根據這段文字,認為莎士比亞反對一種宣敘性或雄辯式(declamatory)的風格,而是提倡一種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式的表演,就是現在在電視、電影中看見的那種──這是太簡化了。
事實上,我們只能從他對演員的建議中看見兩件事:一、好好說話;二、不要太過火,雖然這可以討好無知的觀眾。如果我們進一步想想莎士比亞的時代表演與觀眾的關係,並且與今天的表演環境相對照,恐怕會發現莎士比亞要說的,是──不要演戲。
「好看」的演員只是一個陌生人
想了解那時與現在對表演的看法有何不同,可以從問今天的演員一個問題開始:演出上台前,妳/你還會緊張嗎?如果會,又是為什麼?
可能每位演員的理由不一,但根據我教書、演講的經驗,我會緊張,主要是因為我不認識那些台下的聽眾。如果是教書,通常要到四、五週之後,與學生彼此熟悉了,我進教室才會比較自在點。但演員大概沒有四、五次與觀眾彼此熟悉的機會,除非理由特殊,觀眾看戲很少看第二次。特別是知道劇場觀眾總是有同行或是劇場名嘴在其中時,大概上場前的壓力多少會更大一點,不然,演得不好,明天某篇劇評又攻擊一下,總是不好受的。
希望觀眾喜歡,因此有壓力、會緊張,這是正常的。今天觀眾跟演員的關係,基本上,是一群彼此不相識的陌生人。即使觀眾中有朋友來看戲,但心態上,演員不會把「觀眾」這個集合名詞當「朋友」、當家人,特別在商業演出的狀況下。
在這種關係下,演員在表演時,或多或少,很容易為了保護自己,尋求偽裝。分析角色、進入角色生命這件事,有時候(但不是一直如此)是將角色當成一個面具,一個保護殼。更有甚者,有些演員會發展出為了讓自己好看,藉此保護自己的功夫──畢竟是面對陌生人啊!
於是,有時候我們很容易看出,演員不過是在用一套把戲或招數在放電,增加自己的魅力,讓自己更吸睛。很多很多讓自己好看的表演技術,其實都是讓自己躲起來,保護自己──但也只能瞞過那些眼光不高的觀眾。
這種「好看」,卻只讓我感到距離很遠,像是看煙火秀或特技表演一樣,是與我無關的一種景觀。這時演員並沒有與我在一起,不是真的信任我,把我當朋友、當家人。這樣的演員還是把我當消費者,用盡力氣對我進行一種征服。但是,用力愈多,卻離我愈遠,常常,我心裡都感到一陣惋惜。
會惋惜,是因為我知道今天的劇場環境不鼓勵演員信任觀眾,在商業與消費的考慮下,演戲是給觀眾看的,甚至是「把玩」的。影像表演就更不用說了,根本不是跟觀眾「在一起」,跟觀眾一起呼吸,把觀眾當家人。信任你的觀眾,好好說話
我想起莎士比亞時代的演員,特別在1594到1602年這段期間,倫敦只有兩個劇團,每個團有十五個演員左右,他們一週七天都有演出,幾乎天天劇碼不同,一年演的戲到四十齣以上,新戲約佔一半(是的,他們的記憶力是從小訓練的結果,背台詞超快)。更重要的,這麼少的演員這麼密集的演出,使他們在觀眾眼前的曝光率,大概只有今天第四台的周星馳可以比得上。
觀眾很容易記得演員,演員也不難認識觀眾。以1600年為例,所謂的劇場觀眾(playgoer)有兩萬人(台北今天看劇場的人數不到一萬),但重要的是人口的分母:整個倫敦的人口只有二十萬人。換句話說,每十個人,就有一個是劇場觀眾。你可以想像,如果你在那時代當演員,去餐廳吃個飯,那邊會超過十個人吧,就會有個觀眾認出你,彼此哈啦幾句,然後第二天在市場又碰見他……。觀眾在人口中有十分之一,這麼高的比例,讓演員與觀眾彼此熟悉。
這樣的劇場環境,不難想像,是鼓勵演員信任觀眾的。
我跟很多人一樣,遇見不熟的人會害羞,或是用客氣與禮貌保持距離,不會馬上說心裡話,但回家之後就不同了,在家人面前,我自詡為歌王也會有人欣賞,至少不在乎被嘲笑。我常想像,當年的莎劇演員在表演時,會像我在家人面前唱歌──他「落落長」的獨白,是說給自己人聽的,是為了自己人說的。就像有個你認識、你信任的朋友,在告訴你一些道理,一些想法和心情。他是那麼直接地在對你說,你很難不覺得可以與自己無關。
在彼此信任中,莎劇演員對觀眾說話(另一個面向是對上帝說話,那是另一個故事了!),不偽裝,也不用在意自己的不完美被看穿,這不是什麼宣敘性或雄辯式的風格,這不過是對觀眾「好好說話」而已。只是這樣說話,直指了人心。
莎士比亞與他那個時代的劇作家,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自己是詩人(poet),稱呼進劇場的人是「聽眾」(hearer,或是the audience,這個英文字的原意也是「聽的人」),一直到職業生涯的晚期,才稱呼他們為「觀眾」(spectator),意思是「看的人」。因此,演員本來就被期待要好好說話,將詩人用心血提煉的文字,傳給來劇場的人聽的。演出密集,排戲時間也短(往往早上拿到劇本,下午就要演出),不難想像,即便演員的記憶力很強,但一起排戲的時間很短,演員彼此的默契,對角色內在的體悟等等,除非是重演或很厲害的演員,不然,以今天的標準,演戲不容易好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哈姆雷特會批評一些演員過火的演出:雙手在空中揮舞,情緒又聲嘶力竭。這些演員都只想演戲,忘了好好說話。
但莎士比亞寫劇本不是為了閱讀,他的劇本重要,是因為演員的演出讓它們重要。所以,儘管表演上的花招不少,鬥劍、搏擊,甚至噴(雞)血、跳舞……,這些只是確保了舞台的娛樂性,不是表演直指人心的來源。演戲好看,恐怕不是他能奢望的手段,也不是他冀求的。把話說好,讓文字與行動彼此相合,是表演最好的力量。
記憶與演說敘事的能力
另外,從戲劇史來看,在沒有影印機,印刷術也不太發達的時代,知識的傳播主要是依賴口語,所以一個人在成為演員之前,從小教育起,有兩種能力跟今天比特別發達:記憶力──不知道有沒有「過耳不忘」這麼誇張;演說與敘事能力──說得好,人家才容易聽進去。因此,在希臘悲劇與莎士比亞那裡,大段的台詞之所以會出現,顯然是寫劇本的人相信他的演員一定都可以做到。
莎士比亞寫的大段台詞其實很複雜,有抒情的,有議論的,也有敘事的。這些演員不僅很快能記住這些台詞,還能把說話當成一種厲害表演。
安夫人(Lady Ann)的先生明明是被理查三世殺了,卻在送殯時,被理查的一番話說動,答應嫁給他(《理查三世》[Richard III]);布魯圖斯(Brutus)殺了凱撒之後,先是發表一番演說,證明自己的正當性,贏回羅馬人民對他的信任,隨後安東尼(Antony)又發表另一篇演說,馬上贏回民心,讓布魯圖斯成為羅馬人的公敵(《凱撒大帝》[Julies Caesar])。這些場面都不太能用演的(我就在環球劇院,看過兩個年輕演員把布魯圖斯與安東尼的演說「演」得很賣力),因為如果用演的,觀眾的思維就會去想劇情的前因後果,分析為什麼民眾會有這樣的轉變。可是如果用說的,如果演說的魅力夠,台下的觀眾(也被預設成羅馬民眾)會很直接地被打動,這種感染力是當下有效的(immediate),不用透過大腦的推論與仲介(mediate)。
我們今天的演員,在當演員之前,環境並不像以前,那麼鼓勵記憶與說話兩種特質;進學校接受的表演訓練,也多半從對話、分析(人物)關係、揣摩心理特質與情感記憶、建立角色等等開始,讓演員躲在角色後面。一些很古老、很簡單的手段與能力,似乎好像在萎縮中,也連帶地喪失劇本與戲劇語言能展開的廣度。
今天,處理一整段抒情的、私人內在經驗的獨白,這對很多演員都沒有問題,但問題是,像我這樣的觀眾很容易會想:「這是你的事,干我什麼事呢?」
在這種有「你我之別」的劇場中,要不就是冷靜地觀看他人的命運;要不就是一對一單挑,用自身的生命經驗去跟角色「搏感情」。這裡面對應了一個基本的狀況:演員與觀眾不再彼此認識了。
對話取代了詩,也讓演員好好跟觀眾說話的機會消失
我想像當年一個莎劇演員是如何掌握表演訣竅的:
當他還是初試啼聲的新手,面對坐滿三千人的環球劇院,大概一樣緊張,很容易腎上腺素破表,就像一開始在《莎翁情史》中看見的那個結巴演員一樣。但如果他的表現不錯,還可以在這行待下來,他就有機會漸漸認識他的觀眾,就像我上課四、五週後會與我的學生熟悉一樣。然後,表演的自在,會在那個環境中慢慢生成,他會慢慢變成一個愈來愈好的演員,慢慢對著認識的人,對著具體認識的觀眾,像朋友、像家人一樣,好好說話。他會因此成為一個好演員,至少是莎士比亞期待的,而且不太費力。莎士比亞的年代是現代文明初生的階段,戲劇也是在它的青春期。我們在那邊看到很多戲劇原來的樣貌,喪失的、遺忘的,或者被懷念,或者成為提醒。其中,信任觀眾,將他們視為自己人,對之好好說話,恐怕是今天眾聲喧譁的劇場藝術中,最樸實的提醒之一。
之後,戲劇走到十七世紀的新古典主義,到十九世紀的佳構劇(the well-made play)、通俗劇(the melodrama),再到寫實主義,到電視、電影的興起,到各種以肢體與畫面為主的劇場風格……,我們的劇場環境不一樣了。我們很難把觀眾當自己人了,對話取代了詩,也讓演員好好跟觀眾說話的機會消失,而是成為要在陌生人面前盡力求好的一群。然後,上台前,開始緊張了……
再惋惜一次,我們的表演環境對演員已經沒有這種優勢了。但是,我還是相信,演員在意識中,還是應該信任觀眾,把觀眾當自己人、當家人。必須如此,如果表演希望能直指人心的話。
至於這本書,我也會試著信任讀者,並且好好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