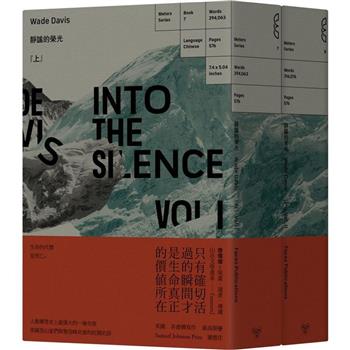▍序
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早晨,在高懸於海拔兩萬三千英尺(約七一一〇公尺)處一個雄踞在東絨布冰川(East Rongbuk Glacier)上,只比聖母峰北坳岩面邊緣低一點點的冰架營地中,探險隊隊長艾德華・諾頓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Edward Norton)送別了兩名即將孤注一擲來嘗試攻頂的同伴。其中三十七歲的喬治・雷・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是當時英國登山界的翹楚,而年僅二十二的山帝・爾文(Sandy Irvine)則是青年才俊的牛津學者,登山經驗趨近於零。至為關鍵的,是時間。天氣雖然晴朗,但南方的天際有捲起千堆雪,足可驚濤裂岸的雲海,而這顯示季風已經抵達孟加拉,不久就會席捲喜馬拉雅山區,然後如一名登山者所說的,「途經之處將灰飛煙滅,無人倖免。」但馬洛里還是不改其樂天的本色。這樣的他在寄回英國的信中寫道:「我們這次絕對要一帆風順地攻頂,願上帝與我們同在,否則就算是咬著牙含著風,我們也要一步步跺到聖母峰。」
諾頓比較樂觀不起來。「毫無疑問地,」他私下對探險隊的攝影師,在喜馬拉雅探險資歷豐富的約翰・諾艾爾(John Noel)說,「馬洛里知道自己這一趟希望渺茫。」口出此言,或許代表記憶中逝去生命的重量壓在了諾頓的心上:一九二二年,七名雪巴人(Sherpa)被留在山上一命嗚呼,外加這一季又添了兩條雪巴冤魂;一九二一年,蘇格蘭醫師亞歷山大・凱拉斯(Dr. Alexander Kellas)於入山與偵察途中埋骨崗巴宗(Kampa Dzong)。更不用說有多少人曾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了。馬洛里本身是一名身段與力量過人的登山大家,但連他都曾在聖母峰三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諾頓見識過崇山峻嶺的冷酷無情。以北坳為起點,攻頂的路線會經過北脊,而北脊會在極富戲劇性地抽高數千英尺之後,融入東北脊,然後東北脊又會接棒通往聖母峰頂。就在前一天,他跟霍華・森默維爾(Howard Somervell)曾從北脊高度兩萬六千八百英尺(約八一六八公尺)的一處前進營出發。避開了席捲東北脊的刺骨寒風,他們向上攻抵了切開聖母峰北壁,並從形如金字塔的聖母峰峰體底座急墜一萬英尺,直達絨布冰川的大雪溝。森默維爾在兩萬八千英尺(約八五三四公尺)處放棄。凍得發抖的諾頓繼續挺進,但身體顫動到他懷疑自己是不是染上了瘧疾。當天稍早爬在黑色岩石上的時候,他誤判形勢地脫下了護目鏡。抵達雪溝之際,他眼前已經開始出現疊影,勉強站著已經用盡他所有的力氣。他只得在海拔二八一二六英尺,距離峰頂僅九百英尺處掉頭,之後他得到了森默維爾的搭救,並在森默維爾的協助下通過了被雪覆蓋的岩板。在撤退回北坳的過程中,森默維爾自己也突然崩潰,無法呼吸。他重擊自己的胸膛,鬆開了阻塞物,然後咳出了一整片喉嚨內襯。
到了早晨,諾頓已經失去了視覺,暫時性因為陽光而變得目盲。在極度的痛苦中,他思考了馬洛里的攻頂計畫。馬洛里與爾文捨棄了北壁,改而選擇取道東北脊,那兒只有兩道障礙阻擋著通往峰頂金字塔的路:首先是本體為黑岩,存在感十足的巨塔,名為「第一台階」,再過去的「第二台階」是一百英尺的斷崖,沒有辦法行走,只能加以攀登。爾文的經驗不足固然令他擔心,但諾頓並未對此一搭檔的組成加以干預。馬洛里已經全神貫注到老僧入定。身為無役不與、英國探險隊的三朝元老,世上再沒有人比他對聖母峰的狀況更明瞭。
兩天之後,六月八日的早晨,馬洛里與爾文踏出了高營,朝聖母峰邁進。隨著透光的雲堤通過了山脈的頭頂,燦爛的朝陽也騰出了位子給柔和的雲影。諾艾爾・歐德爾(Noel Odell)做為從旁襄助他們的優秀登山者,最後看到他們活著是在午後十二點五十分。他遠遠從峭壁上眺望著模糊的馬洛里與爾文:兩個微小的人影在山脊上踽踽前進。隨著雲霧緩緩湧入,兩人留給世人的記憶也被裹上了一團謎霧,惟有歐德爾親眼目睹。馬洛里與爾文從此再無聲息,而他們的失蹤除了讓一整個國家久久不能自已,也就此成為了人類登山史上難再有事件能出其右的無解之謎。
歐德爾從未須臾質疑過兩人在大限之前抵達了聖母峰頂,也衷心相信讓兩人從印度出發跋涉數百英里,穿越圖博,只為來到山腳下,背後推動著他們的是何等崇高而美好的使命。歐德爾用筆,寫下了他對兩位故人的永恆思念:「我最後的那驚鴻一瞥,看到的是一個秉性如此迷人,任誰都會忍不住要與之親近的靈魂,是天賦的才華洋溢與身心所散發出的無比潛能;我看到的,是他正『勇往直前』,並與伴他同行的另一個正直之人分享著那一幕的神聖莊嚴。能親眼目睹那一幕,是生而有涯之凡人的殊榮;而在有幸能親炙這一幕的幸運兒當中,更寥寥有人能向前邁去,終與那超凡入聖的絕景融為一體。」
▍第五章 馬洛里登場(節錄)
一九二一年的四月十二日早上,喬治・馬洛里的形單影隻地站在船艏的上層甲板,望穿了破曉時那若明還暗的藍色背景,見證了海霧的升起;而同時間蒸汽船薩丁尼亞號駛過了直布羅陀海峽,進入了地中海。不是很喜歡長途旅行的他,從四天前在梅西河的伯肯海德上船之後,就一直過得有點悽慘,主要是沿著歐洲岸邊下到聖文森角(Cape St. Vincent)的過程為何謂濕冷下了最好的註腳,同時老舊的薩丁尼亞號本身就潮濕狹小到讓人幽閉恐懼感大作。被他留在英格蘭的除了愛妻茹絲,還有三個年幼的孩子,依序分別是六歲與四歲的女兒克萊兒(Clare)與貝里姞(Beridge),還有還在襁褓中,才七個月大的小兒子約翰(John)。在一封家書當中,他抱怨自己在船上的起居空間,還不如自己在法國待了十六個月的一戰西線。置身於船身外殼的呻吟聲與引擎勉強自己運轉的金屬敲打聲中,外加全天候有燈光照進他的房間,馬洛里在船上可說毫無隱私可言,對此他說「你完全不會有有僻靜或獨居的感覺」。前線的坑道與壕溝是低於地表的存在,姑且不論橫行的鼠患,「你至少可以享有一點孤獨,一點其他地方或許都體驗不到,大地像是啞掉了的孤獨」。
此外馬洛里想從旅伴身上獲得安慰的希望,也同樣落空了。「目前為止,」他在海上短短一天後就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看都不想看到他們——甚至應該說,我的天啊,我厭煩死他們了。」用餐真的是一大考驗,其中晚餐時間又最讓人坐立難安。「我會被夾在一個弗雷澤上校跟一個名叫侯利歐奇,不知道來幹嘛的傢伙之間,其中侯利歐奇從上船以來,就沒有在餐桌上跟左右鄰座開啟過任何話題——所幸他的餐桌禮儀還算是相當得宜。上校是個高高瘦瘦、十分骨感的英裔印度人,外表有點嚇人——但個性倒是非常溫和,而且動作似乎也是我所見過最慢吞吞的一個。我覺得他內心應該是個好人,但就是非常不懂得聊天的藝術,由此跟他講話乾到不行——好的話題落到他的手上,會活活被用亂棍打死,不然又是被他踐踏倒滿身都是灰。我只能倒抽一口冷氣。」
被馬洛里形容為「快活說書人」的船長是他一個小小的避風港,另外就是船上有一名印度陸軍的退伍老兵也有一點類似的效果。這名退役軍人老兵曾經在庫特(Kut)被奧圖曼土耳其人俘虜,但也許是老天眷顧,他竟然從美索不達米亞沙漠的死亡行軍中活了下來。要知道,當時所有的阿拉伯部落都會跑出來對戰俘丟石頭,扒走傷者身上的衣著,甚至還會用沙子塞住戰俘的嘴,不讓他們大呼小叫。這些文字所對應的畫面,讓馬洛里一想到就縮一下。而在信裡對茹絲描述這位印度老兵時,他會躲回到自尊心的制高點上,穿戴上他從進入劍橋就讀之後就慢慢打造出的保護盔甲。「雖然教養差又熱情氾濫,但這人還算善良。」馬洛里貶中帶褒地介紹了對方,但也沒忘了補上一槍說,「但他的問題不在於他醜到讓人受不了,或是個野蠻的食人族,不是這樣的,他的問題在於他無聊透頂。」
真正能馬洛里徹底放鬆的,是開闊的風,是像鷹巢般能讓他居高臨下鳥瞰一切的船艏,是能讓他釋放能量的體能活動。做為運動,他會在甲板上走個十三圈來湊成一英里,還會做一整套肌肉體操來讓人「腰軟筋開」,至少他是這樣對茹絲說的。早在他還在索姆河擔任基層砲兵軍官的時候,他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是在身上帶著一本叫做《傑佛瑞之書》(Book of Geoffrey;典出美國作家華盛頓・爾文﹝Washingon Irving﹞的《見聞札記》﹝The Sketch Book of Geoffery Crayon, Gent.﹞),但永遠不會出版的手稿,裡頭集結了所有他希望以嶄新的方式傳給下一代的道德觀與愛國情操,而如今他也會時不時拿出來複習裡頭的字句。此外他還會閱讀大文豪狄更斯的惡漢小說《馬丁・翟述偉》(Martin Chuzzlewit),品嘗西裔美籍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的作品,狼吞虎嚥他朋友兼前追求者,同性戀英國作家利頓・斯特拉齊(Lytton Strachey)所撰的傳記作品——《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不過說來說去,他最常做的事情還是思念著茹絲,也思念著家鄉。
等到直布羅陀的灰影緩緩地消解,巨巖的全副立體感與輪廓終於以蔚藍的地中海蒼穹為背景,顯露出在他的眼前,他抑鬱的內心終於得以撥雲見日。「隨著日光慢慢升起,巨巖的樣貌也捨棄了模糊不清的邊際,重拾起斬釘截鐵的確切外形,」他在信裡對茹絲說道,「無比壯觀,一如詩人布朗寧(Robert Browning)所說,在宏偉到令人歎為觀止之際,也仍得以保持著單純到極致的美麗——你想像不出世上還能有比這更耀眼的岬角。」他反射性地思考起了登山者該走什麼樣的路線登頂。「巨巖有著非常純粹的表面,其一刀切的垂直程度實在名不虛傳,由此成功登頂的人幾乎可以縱身一躍,就從最高點跳進海面,我估計垂直距離大約會落在七百到八百英尺之間。」
對馬洛里而言,地中海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遠離「波濤洶湧的狂野海洋」,溫暖而明亮的地方。隨著體感溫度的上揚,一種愉悅的改變也降臨在了他的身上:「我感覺到我們進入了一個舒爽的世界,萬里無雲的晴空高掛天上,四目所及都是靜謐而耀眼的海洋。」在北方,粉嫩的雲堤從西班牙的土地上升起,蒼白的地平線外矗立著「潔淨而光芒四射、雪線深及腰際的山脈……創造出雪山聳立於海面上,無法言喻的宜人絕景」。
嶄新的美景每天都會不斷更新,船的右舷橫躺著北非的海岸,距離近到馬洛里靠著雙筒望遠鏡就可以區別出一個個小村子裡的一棟棟屋子,甚至還能辨識出從霧霾與塵埃瀰漫的地平線中升起的斜坡上,種著的莊稼分別是玉蜀黍跟小麥。在天空的另外一端,盤旋在落日之上的,是阿特拉斯山脈(Atlas Mountains)的白色諸峰,遠看就像非洲頭頂上的王冠。四月十五日,就在要登陸馬爾他的前夕,他在給茹絲的信裡是這麼說的:「地中海在日照中美不勝收,還有蒸汽船踽踽前行帶來的平靜步調,而我獨自坐在船艏看著開闊的海面,也看著陸地與我擦身而過……我們將在馬爾他停留六個小時,而我說什麼也要去賞賞花。再會了我甜美的天使,我對妳的愛永無止盡,還有許許多多的吻要給我們的孩子。」
過了馬爾他,下一站便是埃及。隨著薩丁尼亞號進入蘇伊士運河,兩岸可以看見的是散落著的各式戰鬥殘骸,那是戰爭初期由土耳其攻擊所留下的遺跡。那片蒼涼寂寥的地景,這「以戰爭之名集結的醜惡團塊」讓馬洛里油然生起一種「鄙視與反感」。在他的想像中,薩丁尼亞號彷彿是在沙灘上滑翔而過,平靜無波地穿越了運河,唯一的可以挑剔的只有在內心不斷加深的鬱結。原本他對這樣的低迷心情不以為意,他想著那不過是起源於席捲船上所有乘客與船員的痢疾,畢竟連船長都無法與之匹敵而倒了下去。但這種低落的心情不斷向下探底,就這樣當船噴著汽出了紅海,接近到亞丁的燃料補給站之際,馬洛里突然內心一股悸動,感受到了一種黑暗的直覺、一種不祥的預感,由此他在給茹絲的信中提到了「災難或危險的逼近」。到了熱到讓人睡不著的夜裡,他赤條條地躺在臥舖上,任由風扇扇葉攪動著停滯軟爛的空氣。來到白天,眼前所見不是大海就是地平線,能打破那種單調的,只有成群的鼠海豚跟逐浪的飛魚偶爾躍出海面。在橫越完印度洋,眼看要抵達可倫坡的前夕,他再一次陷入了憂鬱當中。「這文明生活的表象,全都是空洞的騙局一場。」他在五月二日的信中寫道。「大海有多美多吸引人,就有多邪惡、多深沉……海中有一道不安的靈魂——即便在徹底平靜無波的狀態下,當海面真的就像凍結在了沉靜當中,其心臟也彷彿仍繼續隨著緩和的長浪在搏動著,而在船上的我們只能無止盡地隨之慵懶而溫和地一起起伏跌宕,就像是要偕海浪一同前往時間的盡頭一樣……那感覺就像是我們身後被自然力量的殘虐陰影追趕著,容不得我們片刻忘記大自然能展現出什麼量級的暴力。」
不過瞬息萬變畢竟是他最突出的個性,馬洛里很快就在一個禮拜後找回了那個熱情洋溢的自己。五月九日他一睜開眼睛,就殷切地期待起了加爾各答。在這之前,他便已經心有所感於印度之令人驚嘆,如他在稍早登岸的馬德拉斯(Madras;今清奈)就待了好幾個小時仍流連忘返。按照他在接近孟加拉灣時寫給茹絲的信中所言,他在馬德拉斯的經驗可說「驚奇到無法言喻——光是這麼多人同時出現在一個小空間裡,就非常難以想像,更別說每轉一個彎,後頭都有不可思議的光景揭露著堪比金字塔跟西敏寺的差距,迥異於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與風俗民情。」
惟隔天五月十日,殘酷的現實在加爾各答重新集結,因為加爾各答將沒有人等著為他接風洗塵。前一晚他在薩丁尼亞號上收到探險隊長霍華─貝瑞的來信,信中指示他要自行登上碼頭,然後頂著豔陽走到兩英里外的海關,因為聖母峰委員已經指派了數千磅的裝備與補給品,要由他負責完成報關程序。帶著對英屬印度知之甚詳且對當地行事作風瞭若指掌的輕鬆口吻,這封信在結論裡要馬洛里先為做為探險隊命脈的補給品確保好通往大吉嶺的輸送無虞之後,再逕自閒步前往火車站,搭乘前往山區的夜車。「我這晚於五點動身前往大吉嶺,隔天中午才抵達目的地。」馬洛里在從加爾各答寫給茹絲的信中說。「我將在此接受孟加拉總督的招待——這裡非常豪華、非常舒適,但我並不期待跟那些官差打交道,而寧可待在我估計布洛克目前身處的聖母峰大飯店裡。其他人現在都已經到大吉嶺了,只有凱拉斯例外,最新的消息是他在四月五日爬了一座山,而這也讓瑞彭顯然有點緊張。這裡現在熱到會滴汗,但我還滿喜歡趁早餐之前去溜達溜達。先這樣,喬治。」
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早晨,在高懸於海拔兩萬三千英尺(約七一一〇公尺)處一個雄踞在東絨布冰川(East Rongbuk Glacier)上,只比聖母峰北坳岩面邊緣低一點點的冰架營地中,探險隊隊長艾德華・諾頓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Edward Norton)送別了兩名即將孤注一擲來嘗試攻頂的同伴。其中三十七歲的喬治・雷・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是當時英國登山界的翹楚,而年僅二十二的山帝・爾文(Sandy Irvine)則是青年才俊的牛津學者,登山經驗趨近於零。至為關鍵的,是時間。天氣雖然晴朗,但南方的天際有捲起千堆雪,足可驚濤裂岸的雲海,而這顯示季風已經抵達孟加拉,不久就會席捲喜馬拉雅山區,然後如一名登山者所說的,「途經之處將灰飛煙滅,無人倖免。」但馬洛里還是不改其樂天的本色。這樣的他在寄回英國的信中寫道:「我們這次絕對要一帆風順地攻頂,願上帝與我們同在,否則就算是咬著牙含著風,我們也要一步步跺到聖母峰。」
諾頓比較樂觀不起來。「毫無疑問地,」他私下對探險隊的攝影師,在喜馬拉雅探險資歷豐富的約翰・諾艾爾(John Noel)說,「馬洛里知道自己這一趟希望渺茫。」口出此言,或許代表記憶中逝去生命的重量壓在了諾頓的心上:一九二二年,七名雪巴人(Sherpa)被留在山上一命嗚呼,外加這一季又添了兩條雪巴冤魂;一九二一年,蘇格蘭醫師亞歷山大・凱拉斯(Dr. Alexander Kellas)於入山與偵察途中埋骨崗巴宗(Kampa Dzong)。更不用說有多少人曾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了。馬洛里本身是一名身段與力量過人的登山大家,但連他都曾在聖母峰三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諾頓見識過崇山峻嶺的冷酷無情。以北坳為起點,攻頂的路線會經過北脊,而北脊會在極富戲劇性地抽高數千英尺之後,融入東北脊,然後東北脊又會接棒通往聖母峰頂。就在前一天,他跟霍華・森默維爾(Howard Somervell)曾從北脊高度兩萬六千八百英尺(約八一六八公尺)的一處前進營出發。避開了席捲東北脊的刺骨寒風,他們向上攻抵了切開聖母峰北壁,並從形如金字塔的聖母峰峰體底座急墜一萬英尺,直達絨布冰川的大雪溝。森默維爾在兩萬八千英尺(約八五三四公尺)處放棄。凍得發抖的諾頓繼續挺進,但身體顫動到他懷疑自己是不是染上了瘧疾。當天稍早爬在黑色岩石上的時候,他誤判形勢地脫下了護目鏡。抵達雪溝之際,他眼前已經開始出現疊影,勉強站著已經用盡他所有的力氣。他只得在海拔二八一二六英尺,距離峰頂僅九百英尺處掉頭,之後他得到了森默維爾的搭救,並在森默維爾的協助下通過了被雪覆蓋的岩板。在撤退回北坳的過程中,森默維爾自己也突然崩潰,無法呼吸。他重擊自己的胸膛,鬆開了阻塞物,然後咳出了一整片喉嚨內襯。
到了早晨,諾頓已經失去了視覺,暫時性因為陽光而變得目盲。在極度的痛苦中,他思考了馬洛里的攻頂計畫。馬洛里與爾文捨棄了北壁,改而選擇取道東北脊,那兒只有兩道障礙阻擋著通往峰頂金字塔的路:首先是本體為黑岩,存在感十足的巨塔,名為「第一台階」,再過去的「第二台階」是一百英尺的斷崖,沒有辦法行走,只能加以攀登。爾文的經驗不足固然令他擔心,但諾頓並未對此一搭檔的組成加以干預。馬洛里已經全神貫注到老僧入定。身為無役不與、英國探險隊的三朝元老,世上再沒有人比他對聖母峰的狀況更明瞭。
兩天之後,六月八日的早晨,馬洛里與爾文踏出了高營,朝聖母峰邁進。隨著透光的雲堤通過了山脈的頭頂,燦爛的朝陽也騰出了位子給柔和的雲影。諾艾爾・歐德爾(Noel Odell)做為從旁襄助他們的優秀登山者,最後看到他們活著是在午後十二點五十分。他遠遠從峭壁上眺望著模糊的馬洛里與爾文:兩個微小的人影在山脊上踽踽前進。隨著雲霧緩緩湧入,兩人留給世人的記憶也被裹上了一團謎霧,惟有歐德爾親眼目睹。馬洛里與爾文從此再無聲息,而他們的失蹤除了讓一整個國家久久不能自已,也就此成為了人類登山史上難再有事件能出其右的無解之謎。
歐德爾從未須臾質疑過兩人在大限之前抵達了聖母峰頂,也衷心相信讓兩人從印度出發跋涉數百英里,穿越圖博,只為來到山腳下,背後推動著他們的是何等崇高而美好的使命。歐德爾用筆,寫下了他對兩位故人的永恆思念:「我最後的那驚鴻一瞥,看到的是一個秉性如此迷人,任誰都會忍不住要與之親近的靈魂,是天賦的才華洋溢與身心所散發出的無比潛能;我看到的,是他正『勇往直前』,並與伴他同行的另一個正直之人分享著那一幕的神聖莊嚴。能親眼目睹那一幕,是生而有涯之凡人的殊榮;而在有幸能親炙這一幕的幸運兒當中,更寥寥有人能向前邁去,終與那超凡入聖的絕景融為一體。」
▍第五章 馬洛里登場(節錄)
一九二一年的四月十二日早上,喬治・馬洛里的形單影隻地站在船艏的上層甲板,望穿了破曉時那若明還暗的藍色背景,見證了海霧的升起;而同時間蒸汽船薩丁尼亞號駛過了直布羅陀海峽,進入了地中海。不是很喜歡長途旅行的他,從四天前在梅西河的伯肯海德上船之後,就一直過得有點悽慘,主要是沿著歐洲岸邊下到聖文森角(Cape St. Vincent)的過程為何謂濕冷下了最好的註腳,同時老舊的薩丁尼亞號本身就潮濕狹小到讓人幽閉恐懼感大作。被他留在英格蘭的除了愛妻茹絲,還有三個年幼的孩子,依序分別是六歲與四歲的女兒克萊兒(Clare)與貝里姞(Beridge),還有還在襁褓中,才七個月大的小兒子約翰(John)。在一封家書當中,他抱怨自己在船上的起居空間,還不如自己在法國待了十六個月的一戰西線。置身於船身外殼的呻吟聲與引擎勉強自己運轉的金屬敲打聲中,外加全天候有燈光照進他的房間,馬洛里在船上可說毫無隱私可言,對此他說「你完全不會有有僻靜或獨居的感覺」。前線的坑道與壕溝是低於地表的存在,姑且不論橫行的鼠患,「你至少可以享有一點孤獨,一點其他地方或許都體驗不到,大地像是啞掉了的孤獨」。
此外馬洛里想從旅伴身上獲得安慰的希望,也同樣落空了。「目前為止,」他在海上短短一天後就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看都不想看到他們——甚至應該說,我的天啊,我厭煩死他們了。」用餐真的是一大考驗,其中晚餐時間又最讓人坐立難安。「我會被夾在一個弗雷澤上校跟一個名叫侯利歐奇,不知道來幹嘛的傢伙之間,其中侯利歐奇從上船以來,就沒有在餐桌上跟左右鄰座開啟過任何話題——所幸他的餐桌禮儀還算是相當得宜。上校是個高高瘦瘦、十分骨感的英裔印度人,外表有點嚇人——但個性倒是非常溫和,而且動作似乎也是我所見過最慢吞吞的一個。我覺得他內心應該是個好人,但就是非常不懂得聊天的藝術,由此跟他講話乾到不行——好的話題落到他的手上,會活活被用亂棍打死,不然又是被他踐踏倒滿身都是灰。我只能倒抽一口冷氣。」
被馬洛里形容為「快活說書人」的船長是他一個小小的避風港,另外就是船上有一名印度陸軍的退伍老兵也有一點類似的效果。這名退役軍人老兵曾經在庫特(Kut)被奧圖曼土耳其人俘虜,但也許是老天眷顧,他竟然從美索不達米亞沙漠的死亡行軍中活了下來。要知道,當時所有的阿拉伯部落都會跑出來對戰俘丟石頭,扒走傷者身上的衣著,甚至還會用沙子塞住戰俘的嘴,不讓他們大呼小叫。這些文字所對應的畫面,讓馬洛里一想到就縮一下。而在信裡對茹絲描述這位印度老兵時,他會躲回到自尊心的制高點上,穿戴上他從進入劍橋就讀之後就慢慢打造出的保護盔甲。「雖然教養差又熱情氾濫,但這人還算善良。」馬洛里貶中帶褒地介紹了對方,但也沒忘了補上一槍說,「但他的問題不在於他醜到讓人受不了,或是個野蠻的食人族,不是這樣的,他的問題在於他無聊透頂。」
真正能馬洛里徹底放鬆的,是開闊的風,是像鷹巢般能讓他居高臨下鳥瞰一切的船艏,是能讓他釋放能量的體能活動。做為運動,他會在甲板上走個十三圈來湊成一英里,還會做一整套肌肉體操來讓人「腰軟筋開」,至少他是這樣對茹絲說的。早在他還在索姆河擔任基層砲兵軍官的時候,他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是在身上帶著一本叫做《傑佛瑞之書》(Book of Geoffrey;典出美國作家華盛頓・爾文﹝Washingon Irving﹞的《見聞札記》﹝The Sketch Book of Geoffery Crayon, Gent.﹞),但永遠不會出版的手稿,裡頭集結了所有他希望以嶄新的方式傳給下一代的道德觀與愛國情操,而如今他也會時不時拿出來複習裡頭的字句。此外他還會閱讀大文豪狄更斯的惡漢小說《馬丁・翟述偉》(Martin Chuzzlewit),品嘗西裔美籍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的作品,狼吞虎嚥他朋友兼前追求者,同性戀英國作家利頓・斯特拉齊(Lytton Strachey)所撰的傳記作品——《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不過說來說去,他最常做的事情還是思念著茹絲,也思念著家鄉。
等到直布羅陀的灰影緩緩地消解,巨巖的全副立體感與輪廓終於以蔚藍的地中海蒼穹為背景,顯露出在他的眼前,他抑鬱的內心終於得以撥雲見日。「隨著日光慢慢升起,巨巖的樣貌也捨棄了模糊不清的邊際,重拾起斬釘截鐵的確切外形,」他在信裡對茹絲說道,「無比壯觀,一如詩人布朗寧(Robert Browning)所說,在宏偉到令人歎為觀止之際,也仍得以保持著單純到極致的美麗——你想像不出世上還能有比這更耀眼的岬角。」他反射性地思考起了登山者該走什麼樣的路線登頂。「巨巖有著非常純粹的表面,其一刀切的垂直程度實在名不虛傳,由此成功登頂的人幾乎可以縱身一躍,就從最高點跳進海面,我估計垂直距離大約會落在七百到八百英尺之間。」
對馬洛里而言,地中海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遠離「波濤洶湧的狂野海洋」,溫暖而明亮的地方。隨著體感溫度的上揚,一種愉悅的改變也降臨在了他的身上:「我感覺到我們進入了一個舒爽的世界,萬里無雲的晴空高掛天上,四目所及都是靜謐而耀眼的海洋。」在北方,粉嫩的雲堤從西班牙的土地上升起,蒼白的地平線外矗立著「潔淨而光芒四射、雪線深及腰際的山脈……創造出雪山聳立於海面上,無法言喻的宜人絕景」。
嶄新的美景每天都會不斷更新,船的右舷橫躺著北非的海岸,距離近到馬洛里靠著雙筒望遠鏡就可以區別出一個個小村子裡的一棟棟屋子,甚至還能辨識出從霧霾與塵埃瀰漫的地平線中升起的斜坡上,種著的莊稼分別是玉蜀黍跟小麥。在天空的另外一端,盤旋在落日之上的,是阿特拉斯山脈(Atlas Mountains)的白色諸峰,遠看就像非洲頭頂上的王冠。四月十五日,就在要登陸馬爾他的前夕,他在給茹絲的信裡是這麼說的:「地中海在日照中美不勝收,還有蒸汽船踽踽前行帶來的平靜步調,而我獨自坐在船艏看著開闊的海面,也看著陸地與我擦身而過……我們將在馬爾他停留六個小時,而我說什麼也要去賞賞花。再會了我甜美的天使,我對妳的愛永無止盡,還有許許多多的吻要給我們的孩子。」
過了馬爾他,下一站便是埃及。隨著薩丁尼亞號進入蘇伊士運河,兩岸可以看見的是散落著的各式戰鬥殘骸,那是戰爭初期由土耳其攻擊所留下的遺跡。那片蒼涼寂寥的地景,這「以戰爭之名集結的醜惡團塊」讓馬洛里油然生起一種「鄙視與反感」。在他的想像中,薩丁尼亞號彷彿是在沙灘上滑翔而過,平靜無波地穿越了運河,唯一的可以挑剔的只有在內心不斷加深的鬱結。原本他對這樣的低迷心情不以為意,他想著那不過是起源於席捲船上所有乘客與船員的痢疾,畢竟連船長都無法與之匹敵而倒了下去。但這種低落的心情不斷向下探底,就這樣當船噴著汽出了紅海,接近到亞丁的燃料補給站之際,馬洛里突然內心一股悸動,感受到了一種黑暗的直覺、一種不祥的預感,由此他在給茹絲的信中提到了「災難或危險的逼近」。到了熱到讓人睡不著的夜裡,他赤條條地躺在臥舖上,任由風扇扇葉攪動著停滯軟爛的空氣。來到白天,眼前所見不是大海就是地平線,能打破那種單調的,只有成群的鼠海豚跟逐浪的飛魚偶爾躍出海面。在橫越完印度洋,眼看要抵達可倫坡的前夕,他再一次陷入了憂鬱當中。「這文明生活的表象,全都是空洞的騙局一場。」他在五月二日的信中寫道。「大海有多美多吸引人,就有多邪惡、多深沉……海中有一道不安的靈魂——即便在徹底平靜無波的狀態下,當海面真的就像凍結在了沉靜當中,其心臟也彷彿仍繼續隨著緩和的長浪在搏動著,而在船上的我們只能無止盡地隨之慵懶而溫和地一起起伏跌宕,就像是要偕海浪一同前往時間的盡頭一樣……那感覺就像是我們身後被自然力量的殘虐陰影追趕著,容不得我們片刻忘記大自然能展現出什麼量級的暴力。」
不過瞬息萬變畢竟是他最突出的個性,馬洛里很快就在一個禮拜後找回了那個熱情洋溢的自己。五月九日他一睜開眼睛,就殷切地期待起了加爾各答。在這之前,他便已經心有所感於印度之令人驚嘆,如他在稍早登岸的馬德拉斯(Madras;今清奈)就待了好幾個小時仍流連忘返。按照他在接近孟加拉灣時寫給茹絲的信中所言,他在馬德拉斯的經驗可說「驚奇到無法言喻——光是這麼多人同時出現在一個小空間裡,就非常難以想像,更別說每轉一個彎,後頭都有不可思議的光景揭露著堪比金字塔跟西敏寺的差距,迥異於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與風俗民情。」
惟隔天五月十日,殘酷的現實在加爾各答重新集結,因為加爾各答將沒有人等著為他接風洗塵。前一晚他在薩丁尼亞號上收到探險隊長霍華─貝瑞的來信,信中指示他要自行登上碼頭,然後頂著豔陽走到兩英里外的海關,因為聖母峰委員已經指派了數千磅的裝備與補給品,要由他負責完成報關程序。帶著對英屬印度知之甚詳且對當地行事作風瞭若指掌的輕鬆口吻,這封信在結論裡要馬洛里先為做為探險隊命脈的補給品確保好通往大吉嶺的輸送無虞之後,再逕自閒步前往火車站,搭乘前往山區的夜車。「我這晚於五點動身前往大吉嶺,隔天中午才抵達目的地。」馬洛里在從加爾各答寫給茹絲的信中說。「我將在此接受孟加拉總督的招待——這裡非常豪華、非常舒適,但我並不期待跟那些官差打交道,而寧可待在我估計布洛克目前身處的聖母峰大飯店裡。其他人現在都已經到大吉嶺了,只有凱拉斯例外,最新的消息是他在四月五日爬了一座山,而這也讓瑞彭顯然有點緊張。這裡現在熱到會滴汗,但我還滿喜歡趁早餐之前去溜達溜達。先這樣,喬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