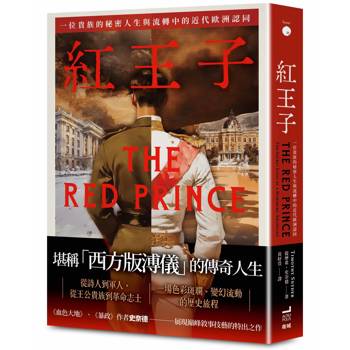序曲
從前從前,城堡裡住著一位年輕貌美的公主,芳名瑪麗亞.克里斯蒂娜(Maria Krystyna)。她在城堡裡讀著書,總習慣從終章讀起,以開頭作結。而後納粹來了,史達林主義者隨後跟上。本書說的就是她的家族故事,因此我們也要從結局說起。
※※※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午夜前一小時,一名烏克蘭上校逝世於基輔的蘇聯監獄。他曾在維也納當過間諜,先是於二戰期間抵抗希特勒,接著在冷戰初期對抗史達林。他躲過蓋世太保的追捕,卻未能逃離蘇聯反情報部門的掌心。有一天,烏克蘭上校告訴同事他要出門吃午餐,之後維也納便再也沒人見過他。他被紅軍綁架、送上飛機押往蘇聯,並受到嚴刑拷打。他死於監獄醫院,而後葬身無名塚裡。
烏克蘭上校有一名兄長,他也擔任過上校,同樣曾抵抗納粹。他憑藉過人勇氣,在德國各座監獄和集中營裡熬過整場戰爭。蓋世太保的酷刑使他半身癱瘓、單眼失明。二戰結束後,兄長歸國欲拿回家族遺產。家產位於波蘭,兄長也自命為波蘭人。可家產已於一九三九年遭納粹奪走,一九四五年再次被共產黨沒收充公。納粹的審訊者得知其家族有德國背景,欲逼迫上校承認自己種族上是德裔。可他斷然拒絕。如今,他在新入主的共產政權身上聽到同一套說辭。他們說,他在種族上屬於德裔,因此無權在新生的波蘭擁有地產。納粹奪走的,會由共產黨收下。
與此同時,波蘭上校的幾個孩子都難以適應新的共產秩序。女兒在申請醫學院時必須填寫家庭的社會階級,選項有工人、農民與知識分子——馬克思官僚制度的標準分類。這位苦惱的年輕小姐在猶豫久久之後,決定寫下「哈布斯堡」。這是實話。申請醫學院的人正是年輕的公主克里斯蒂娜・哈布斯堡。她的父親是那位波蘭上校,前述的烏克蘭上校則是她的叔叔,兩人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親王、皇帝的後裔、歐洲最顯赫家族的成員。
※※※
公主的父親艾伯赫特(Albrecht)和王叔威廉(Wilhelm)生於十九世紀末,在帝國當道的世界中長大成人。當時他們家族仍統治著哈布斯堡君主國,那是歐洲最自豪、最古老的王國,北至烏克蘭的連綿山區,南至亞得里亞海的溫暖水域。哈布斯堡含納十多個歐洲民族,六百年來王權從無動搖。在民族主義興起的年代,烏克蘭上校威廉與波蘭上校艾伯赫特成長過程中便被教導要保衛並壯大家族帝國。他們後來分別成為波蘭王子與烏克蘭王子,效忠領土更加廣袤的君主國,臣服於哈布斯堡皇帝。
此種皇室民族主義是兩人父親史蒂芬(Stefan)的主意。他屏棄帝國家族傳統的四海一家主義,自命為波蘭人,盼能成為波蘭的攝政或親王。長子艾伯赫特是他的忠誠繼承人;么子威廉卻是離經叛道,選擇投向另一民族。不過兩個兒子都貫徹了父親的基本理念。史蒂芬認為,民族主義的崛起在所難免,但帝國的瓦解卻非必然。讓各民族自成一國並無法解放少數民族;恰恰相反,他料想到,這麼做只會讓歐洲成為一眾難登大雅之堂的弱小國度,只能依附更強大的國家才能生存。史蒂芬認為,歐洲人倒不如將自身民族理念寄託於更偉大的皇權——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在事事不盡如人意的歐洲,哈布斯堡是上演民族大戲的絕佳舞臺,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史蒂芬心想,那就讓民族政治繼續延燒吧,只要不脫離這座寬容帝國的舒適領土便好,畢竟這裡有著自由的媒體與議會。
因此,對哈布斯堡家族史蒂芬這支血脈、乃至於對王朝本身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一場悲劇。戰爭期間,哈布斯堡的敵人——俄羅斯、英國、法國、美國——都將民族情緒化為抵抗皇室的力量。戰後,哈布斯堡王朝分崩離析、遭到開腸破肚,民族主義就此成為歐洲霸主。一九一八年的慘敗讓選擇烏克蘭的么子威廉尤感創痛。一戰前,烏克蘭土地本是由哈布斯堡與俄羅斯帝國分治。威廉一直自問的民族問題也就應運而生:他能否一統烏克蘭,將之併入哈布斯堡王朝?他能否為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烏克蘭,就如父親統治波蘭的心願?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似乎原本有能力成事。
威廉開創了哈布斯堡的烏克蘭分支,他學習當地語言、於一戰期間指揮烏克蘭部隊、與自己選擇的這個民族緊緊相依。一九一七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摧毀俄羅斯帝國之時,烏克蘭正待征服,他的機運也來臨了。一九一八年,威廉奉哈布斯堡皇帝之命前往烏克蘭草原,他努力培養平民的民族意識,協助窮人保住從富人手中拿走的土地。他成了舉國的傳奇人物——會說烏克蘭語的哈布斯堡貴族、愛民如子的大公——紅王子。
※※※
紅王子威廉穿過奧地利軍服、哈布斯堡大公朝服、巴黎流亡人士的便裝,也曾配有金羊毛勳章領飾,偶爾還以女裝示人。他能揮舞軍刀、操作手槍、掌控船舵,亦懂得使用高爾夫球桿;有必要時他能擺布女人,欲尋歡時便找男人作樂。他通曉多種語言:大公夫人母親所說的義大利語、大公父親的德語、英國皇室友人的英語、父親欲統治國度的波蘭語,還有自己欲統御土地的烏克蘭語。他並非白璧無瑕,但話說回來,白壁無瑕也無法打造民族國家。每次民族革命,就如每次魚水之歡,都是在借鑒前人。而每個開國元勳都曾輕狂風流過。威廉對自己的政治忠誠度與開放的性關係都表現得毫不羞恥。在他看來,自己的忠誠或慾望無法由旁人定義與約束。然而,在這種滿不在意的表象下,卻隱藏著他特有的道德信條:憑藉身上巴黎飯店房間的香水氣息,憑藉奧地利護照上偽造者的墨跡,他拒絕讓國家的權力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
歸結到底,威廉在身分認同上的態度與兄長艾伯赫特並無太大差異。艾伯赫特重視家族,他效忠波蘭,是父親的優秀兒子。在極權主義的年代,兩兄弟全然不知曉彼此作為,卻又有著相似的行事作風。兩人都知道民族身分可以改變,但拒絕屈就於威脅。艾伯赫特在納粹的拷問下否認自己是德裔。雖然他的家族曾統治德意志土地數百年,但他拒絕接受納粹那種認定民族是由出身界定的種族觀。他已選定了波蘭。威廉則是甘冒大險監視蘇聯,盼著能為烏克蘭爭取西方強權庇護。在接受蘇聯祕密警察審訊的那幾個月,他也堅持只說烏克蘭語。兄弟倆都沒能從極權政權的凌遲下恢復元氣,而他們所代表的歐洲也未能重新振作。納粹和蘇聯都認定民族代表著不可動搖的歷史事實,無關人民當下的意志。正是因為兩者曾以如此暴力的手段統治大半歐洲,此種種族觀念才延續至今,歷史的不死之手竟仍悄悄掌控我們。
哈布斯堡家族卻有著更靈活的史觀。王朝可以永久延續,而少有王朝會自認為不值得延續下去。史達林掌權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希特勒則只有八分之一。哈布斯堡卻是在位數百年。而出生於十九世紀的史蒂芬和兩個兒子——艾伯赫特與威廉——也沒有理由相信二十世紀會是家族的末日。畢竟,對這個在神聖羅馬帝國滅國後仍存續下來的神聖羅馬皇族而言、對這個撐過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統治家族而言、對這個撐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保守派皇室而言,民族主義算什麼?在一戰開打前的歲月裡,哈布斯堡王朝也適應了現代觀念,但他們卻像是迎向意外之風的水手,相信旅程會繼續,只是路線稍有不同。史蒂芬和兒子們在面對民族時,並沒有民族必將勝利、帝國則飄搖而亡的預感。他們相信,波蘭和烏克蘭的自由能成為哈布斯堡王朝擴張歐洲版圖的助力。他們認為時間存在著無限潛能,生命裡的各種時刻也充滿榮耀的曙光,就如一滴露水等待晨曦映照出自己的七彩光芒。
即便這滴露水最後被踩在長筒軍靴的黑色鞋底下又如何?這些哈布斯堡人在生前打了敗仗,也未能為他們的民族掙得自由。他們和自己選定的民族一樣,被納粹和史達林主義者踩在腳下。然而,曾審判與裁決他們的專制者也已消逝。有鑑於納粹和共產統治的恐怖,我們不可能視二十世紀的歐洲史為邁向美好未來的進步之路。出於同一原因,我們也很難將一九一八年哈布斯堡的垮臺作為自由時代的開端。那我們又該如何評價歐洲當代史呢?也許這些哈布斯堡人,連同他們已然倦怠的永恆之感,以及對多彩當下的滿懷希望,可以提供我們些許啟發。畢竟過去的每一刻都充滿未發生和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之事——如烏克蘭君主國或哈布斯堡王朝復辟;也蘊含看似不可能但事實證明可能之事——如統一的烏克蘭國度或包含著自由波蘭、正在統合的歐洲。若過往如此,那麼如今亦然。
從前從前,城堡裡住著一位年輕貌美的公主,芳名瑪麗亞.克里斯蒂娜(Maria Krystyna)。她在城堡裡讀著書,總習慣從終章讀起,以開頭作結。而後納粹來了,史達林主義者隨後跟上。本書說的就是她的家族故事,因此我們也要從結局說起。
※※※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午夜前一小時,一名烏克蘭上校逝世於基輔的蘇聯監獄。他曾在維也納當過間諜,先是於二戰期間抵抗希特勒,接著在冷戰初期對抗史達林。他躲過蓋世太保的追捕,卻未能逃離蘇聯反情報部門的掌心。有一天,烏克蘭上校告訴同事他要出門吃午餐,之後維也納便再也沒人見過他。他被紅軍綁架、送上飛機押往蘇聯,並受到嚴刑拷打。他死於監獄醫院,而後葬身無名塚裡。
烏克蘭上校有一名兄長,他也擔任過上校,同樣曾抵抗納粹。他憑藉過人勇氣,在德國各座監獄和集中營裡熬過整場戰爭。蓋世太保的酷刑使他半身癱瘓、單眼失明。二戰結束後,兄長歸國欲拿回家族遺產。家產位於波蘭,兄長也自命為波蘭人。可家產已於一九三九年遭納粹奪走,一九四五年再次被共產黨沒收充公。納粹的審訊者得知其家族有德國背景,欲逼迫上校承認自己種族上是德裔。可他斷然拒絕。如今,他在新入主的共產政權身上聽到同一套說辭。他們說,他在種族上屬於德裔,因此無權在新生的波蘭擁有地產。納粹奪走的,會由共產黨收下。
與此同時,波蘭上校的幾個孩子都難以適應新的共產秩序。女兒在申請醫學院時必須填寫家庭的社會階級,選項有工人、農民與知識分子——馬克思官僚制度的標準分類。這位苦惱的年輕小姐在猶豫久久之後,決定寫下「哈布斯堡」。這是實話。申請醫學院的人正是年輕的公主克里斯蒂娜・哈布斯堡。她的父親是那位波蘭上校,前述的烏克蘭上校則是她的叔叔,兩人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親王、皇帝的後裔、歐洲最顯赫家族的成員。
※※※
公主的父親艾伯赫特(Albrecht)和王叔威廉(Wilhelm)生於十九世紀末,在帝國當道的世界中長大成人。當時他們家族仍統治著哈布斯堡君主國,那是歐洲最自豪、最古老的王國,北至烏克蘭的連綿山區,南至亞得里亞海的溫暖水域。哈布斯堡含納十多個歐洲民族,六百年來王權從無動搖。在民族主義興起的年代,烏克蘭上校威廉與波蘭上校艾伯赫特成長過程中便被教導要保衛並壯大家族帝國。他們後來分別成為波蘭王子與烏克蘭王子,效忠領土更加廣袤的君主國,臣服於哈布斯堡皇帝。
此種皇室民族主義是兩人父親史蒂芬(Stefan)的主意。他屏棄帝國家族傳統的四海一家主義,自命為波蘭人,盼能成為波蘭的攝政或親王。長子艾伯赫特是他的忠誠繼承人;么子威廉卻是離經叛道,選擇投向另一民族。不過兩個兒子都貫徹了父親的基本理念。史蒂芬認為,民族主義的崛起在所難免,但帝國的瓦解卻非必然。讓各民族自成一國並無法解放少數民族;恰恰相反,他料想到,這麼做只會讓歐洲成為一眾難登大雅之堂的弱小國度,只能依附更強大的國家才能生存。史蒂芬認為,歐洲人倒不如將自身民族理念寄託於更偉大的皇權——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在事事不盡如人意的歐洲,哈布斯堡是上演民族大戲的絕佳舞臺,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史蒂芬心想,那就讓民族政治繼續延燒吧,只要不脫離這座寬容帝國的舒適領土便好,畢竟這裡有著自由的媒體與議會。
因此,對哈布斯堡家族史蒂芬這支血脈、乃至於對王朝本身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一場悲劇。戰爭期間,哈布斯堡的敵人——俄羅斯、英國、法國、美國——都將民族情緒化為抵抗皇室的力量。戰後,哈布斯堡王朝分崩離析、遭到開腸破肚,民族主義就此成為歐洲霸主。一九一八年的慘敗讓選擇烏克蘭的么子威廉尤感創痛。一戰前,烏克蘭土地本是由哈布斯堡與俄羅斯帝國分治。威廉一直自問的民族問題也就應運而生:他能否一統烏克蘭,將之併入哈布斯堡王朝?他能否為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烏克蘭,就如父親統治波蘭的心願?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似乎原本有能力成事。
威廉開創了哈布斯堡的烏克蘭分支,他學習當地語言、於一戰期間指揮烏克蘭部隊、與自己選擇的這個民族緊緊相依。一九一七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摧毀俄羅斯帝國之時,烏克蘭正待征服,他的機運也來臨了。一九一八年,威廉奉哈布斯堡皇帝之命前往烏克蘭草原,他努力培養平民的民族意識,協助窮人保住從富人手中拿走的土地。他成了舉國的傳奇人物——會說烏克蘭語的哈布斯堡貴族、愛民如子的大公——紅王子。
※※※
紅王子威廉穿過奧地利軍服、哈布斯堡大公朝服、巴黎流亡人士的便裝,也曾配有金羊毛勳章領飾,偶爾還以女裝示人。他能揮舞軍刀、操作手槍、掌控船舵,亦懂得使用高爾夫球桿;有必要時他能擺布女人,欲尋歡時便找男人作樂。他通曉多種語言:大公夫人母親所說的義大利語、大公父親的德語、英國皇室友人的英語、父親欲統治國度的波蘭語,還有自己欲統御土地的烏克蘭語。他並非白璧無瑕,但話說回來,白壁無瑕也無法打造民族國家。每次民族革命,就如每次魚水之歡,都是在借鑒前人。而每個開國元勳都曾輕狂風流過。威廉對自己的政治忠誠度與開放的性關係都表現得毫不羞恥。在他看來,自己的忠誠或慾望無法由旁人定義與約束。然而,在這種滿不在意的表象下,卻隱藏著他特有的道德信條:憑藉身上巴黎飯店房間的香水氣息,憑藉奧地利護照上偽造者的墨跡,他拒絕讓國家的權力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
歸結到底,威廉在身分認同上的態度與兄長艾伯赫特並無太大差異。艾伯赫特重視家族,他效忠波蘭,是父親的優秀兒子。在極權主義的年代,兩兄弟全然不知曉彼此作為,卻又有著相似的行事作風。兩人都知道民族身分可以改變,但拒絕屈就於威脅。艾伯赫特在納粹的拷問下否認自己是德裔。雖然他的家族曾統治德意志土地數百年,但他拒絕接受納粹那種認定民族是由出身界定的種族觀。他已選定了波蘭。威廉則是甘冒大險監視蘇聯,盼著能為烏克蘭爭取西方強權庇護。在接受蘇聯祕密警察審訊的那幾個月,他也堅持只說烏克蘭語。兄弟倆都沒能從極權政權的凌遲下恢復元氣,而他們所代表的歐洲也未能重新振作。納粹和蘇聯都認定民族代表著不可動搖的歷史事實,無關人民當下的意志。正是因為兩者曾以如此暴力的手段統治大半歐洲,此種種族觀念才延續至今,歷史的不死之手竟仍悄悄掌控我們。
哈布斯堡家族卻有著更靈活的史觀。王朝可以永久延續,而少有王朝會自認為不值得延續下去。史達林掌權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希特勒則只有八分之一。哈布斯堡卻是在位數百年。而出生於十九世紀的史蒂芬和兩個兒子——艾伯赫特與威廉——也沒有理由相信二十世紀會是家族的末日。畢竟,對這個在神聖羅馬帝國滅國後仍存續下來的神聖羅馬皇族而言、對這個撐過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統治家族而言、對這個撐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保守派皇室而言,民族主義算什麼?在一戰開打前的歲月裡,哈布斯堡王朝也適應了現代觀念,但他們卻像是迎向意外之風的水手,相信旅程會繼續,只是路線稍有不同。史蒂芬和兒子們在面對民族時,並沒有民族必將勝利、帝國則飄搖而亡的預感。他們相信,波蘭和烏克蘭的自由能成為哈布斯堡王朝擴張歐洲版圖的助力。他們認為時間存在著無限潛能,生命裡的各種時刻也充滿榮耀的曙光,就如一滴露水等待晨曦映照出自己的七彩光芒。
即便這滴露水最後被踩在長筒軍靴的黑色鞋底下又如何?這些哈布斯堡人在生前打了敗仗,也未能為他們的民族掙得自由。他們和自己選定的民族一樣,被納粹和史達林主義者踩在腳下。然而,曾審判與裁決他們的專制者也已消逝。有鑑於納粹和共產統治的恐怖,我們不可能視二十世紀的歐洲史為邁向美好未來的進步之路。出於同一原因,我們也很難將一九一八年哈布斯堡的垮臺作為自由時代的開端。那我們又該如何評價歐洲當代史呢?也許這些哈布斯堡人,連同他們已然倦怠的永恆之感,以及對多彩當下的滿懷希望,可以提供我們些許啟發。畢竟過去的每一刻都充滿未發生和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之事——如烏克蘭君主國或哈布斯堡王朝復辟;也蘊含看似不可能但事實證明可能之事——如統一的烏克蘭國度或包含著自由波蘭、正在統合的歐洲。若過往如此,那麼如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