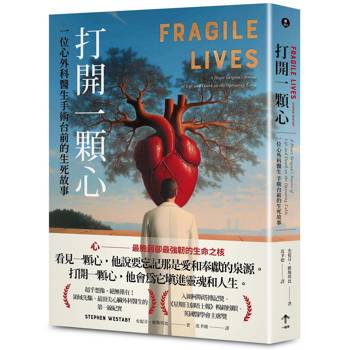節錄自第一章:〈乙醚圓頂廳〉
多死幾個肌肉細胞、血液中的乳酸濃度多出一分半毫、大腦再腫脹那麼一點點——最細微的差距,便會造成生死兩隔、成敗二分、希望變絕望。死神常駐於每個外科醫師的肩頭,何況死就死了,絕無其他可能。沒有再來一次這種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十八歲,剛在倫敦市中心的查令十字醫院醫學院就讀,這只是第一學期的第一週,學校的對面就是醫院。當時的我想親眼看看活生生跳動的心臟,而不是解剖桌上那種黏黏滑滑的死肉。學校大廳的警衛告訴我,對街的醫院每個禮拜三都有心臟手術,去乙醚圓頂廳準沒錯;上到不會有人去的最頂樓,找到屋簷下的一道綠門。不過他警告我,千萬別被逮到。臨床前的學生是不准去那裡的。
我出發尋找乙醚圓頂廳時是傍晚時分,天色已經暗了,岸濱街下著毛毛雨。原來,乙醚圓頂廳是個陳舊的鉛灰玻璃圓頂,就在古老的查令十字醫院手術室上方。自從入學面試後,我就再也沒踏進過神聖的醫院入口。我們這些學生得通過解剖學、生理學和生物化學的考試,才能得到那樣的特權。所以,我沒有從正門的希臘式門廊走進去,而是偷偷從亮著藍燈的急診室溜進去,然後找到電梯——一台搖搖晃晃的老舊箱式升降機,專門用來載送病房設備和屍體到地下室。
我擔心自己可能會遲到、手術可能已經結束——還擔心那道綠門可能會上鎖。不過,門倒沒鎖。綠門背後是條滿布灰塵的昏暗走廊,堆放著過時的麻醉機器和廢棄手術儀器。離我前方十碼的地方,能看見圓頂下手術燈的亮光。這是手術室的舊高台觀眾席,設有玻璃,莊重地與下方不到十英尺處手術台上的大戲隔開距離。觀眾席還有欄杆以及弧形的木製長椅,這些長椅被那些曾經的準外科醫師們焦躁不安的臀部磨到表面都光滑了。
我緊抓著欄杆坐下。只有我和死神,透著因水氣而模糊的玻璃,仔細凝視著眼前的一切。那是一場心臟手術,病人的胸腔還開著。我移動位置,想找到最佳視角,最後停在外科醫師頭頂正上方。他很有名,起碼在我們醫學院裡是大人物;長得又高又瘦,儀表堂堂,手指修長。一九六〇年代時,心臟外科手術尚新,還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動這類手術的醫師少之又少,訓練有素的醫師更是不多。他們往往是技術老練的一般外科醫師,因為拜訪過某些先驅的醫學中心,才自願開立新的醫療服務。他們學習的步調緊張又快速,代價則是用人命來計算。
在場的兩名手術助理和刷手護士,彎著腰擠在張開的傷口邊,緊張地來回遞送著手術器械。他們目光的焦點和我著迷的對象就在那裡——一顆跳動的人類心臟。其實與其說是跳動,更像是蠕動,還插著連接人工心肺機的插管和導管。排成圓柱形的碟片在貯血槽中轉動,槽裡裝滿富含氧氣的血液,還有一台簡陋的滾軸泵擠壓著導管,促使維生所需的血液流回體內。儘管我定睛仔細觀察,卻也只能看到心臟,因為病人全身都被綠色的覆蓋巾遮著,不讓在場的人知道身分。
主刀醫師不安地換著腳站三七步,腳上是一雙從前外科醫師用來防止襪子沾染血液的超大白色手術靴。手術團隊已經置換了病人的二尖瓣,不過,那顆心臟還是難以脫離人工心肺機。就連第一次看到跳動人類心臟的我,都覺得它看起來很無力,鼓脹得像顆氣球,雖然還有搏動,卻沒有在抽送血液。在我身後的牆上,有個標示著「對講機」的盒子。我轉動開關,這下子,這齣大戲就有了聲音。
在放大的嘈雜背景聲中,我聽見主刀醫師說:「我們再試最後一次。增加腎上腺素,通氣,試著不用心肺機看看。」
現場鴉雀無聲,眾人都凝視著這個奮力活命的器官。
「右冠狀動脈裡有空氣。」第一助理說,「給我一根抽氣針。」他把針推進主動脈,帶泡沫的血液嘶嘶滲進傷口,接著,病人的血壓開始好轉。
眼看時機出現,主刀醫師轉身跟體外循環師說:「馬上關掉!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體外循環關閉。」體外循環師回答。他的口吻更像在陳述事實,語氣中沒多大信心。
人工心肺機一關,這顆心臟就全靠自己了,左心室要將血液泵往全身,右心室則要將血液泵進肺部,兩邊都在使勁努力。麻醉醫師充滿希望地盯著螢幕,一邊監控血壓和心率。幾位醫師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搏,他們一言不發地拔掉心臟的插管,縫合傷口,每個人都非常希望這顆心臟能有力起來。它先是無力地顫動了一會兒,隨後,血壓開始慢慢下降。某個部位在出血——雖然量不大,但卻停不下來。出血點似乎在心臟背面,某個處理不到的地方。
抬起心臟的動作造成了顫動。這下心臟又開始扭動,就像一袋蠕動的蟲子,卻不是正常收縮,只是受到紊亂的電活動影響而持續蠕動。它在白費力氣。麻醉師花了點時間才發現螢幕上的端倪。「VF,」他大喊。我不久後學到,這是心室顫動(ventricular fibrillation)的意思。「準備電擊。」
主刀醫師早有預料,他把去顫電擊板緊緊壓在那顆心臟上。「三十焦耳。」滋的一聲!沒有效果。「加到六十。」
滋!這次,心臟去顫了,但接著就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沒了心電活動,就像個濕漉漉的購物紙袋。我們稱這為「心搏停止」(asystole)。
血液繼續流進胸腔,主刀醫師用手指戳了戳心臟,左右心室隨即收縮。他又再戳一次,心律開始恢復。「太慢了。給我一針腎上腺素。」他又急又狠地把針從右心室穿進左心室,注入一股透明液體。然後,他用修長的手指按摩心臟,想把這強力的興奮劑推進冠狀動脈。
受惠的心肌很快有了反應。跟教科書上寫的一模一樣,心率開始加快,血壓開始飆升,越升越高,高得幾乎要撐破縫線。接著,如同慢動作鏡頭般,主動脈插管處縫合的傷口破了。嘩的一聲!一道深紅色噴泉就像間歇泉那樣噴發,灑在手術燈上,把幾個在場的醫師濺了一身,連綠色的覆蓋巾都濕透了。有人小聲地說道:「噢,慘了。」豈止是慘而已——他們輸掉了這場戰役。
還來不及用手指堵住主動脈的破洞,那顆心臟就滴血不剩了。血液從手術燈上滴下,大理石地板上到處是細細的紅色血流,都黏住橡膠靴底了。麻醉師發狂似地把一袋袋的血擠進靜脈,卻完全沒用。生命正快速消逝。剛剛施打的腎上腺素效力一過,這顆腫脹的心臟就像吹氣球一樣鼓脹起來,然後就不動了。永遠停了。
幾位醫師在絕望中沉默地佇立著,這已經是每週的例行公事。資深的主刀醫師走出了我的視線,麻醉醫師也關掉呼吸器,等待心電圖變平。他拔掉了病人氣管上的導管,接著也消失在我的視線裡。病人的大腦已經死了。
多死幾個肌肉細胞、血液中的乳酸濃度多出一分半毫、大腦再腫脹那麼一點點——最細微的差距,便會造成生死兩隔、成敗二分、希望變絕望。死神常駐於每個外科醫師的肩頭,何況死就死了,絕無其他可能。沒有再來一次這種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十八歲,剛在倫敦市中心的查令十字醫院醫學院就讀,這只是第一學期的第一週,學校的對面就是醫院。當時的我想親眼看看活生生跳動的心臟,而不是解剖桌上那種黏黏滑滑的死肉。學校大廳的警衛告訴我,對街的醫院每個禮拜三都有心臟手術,去乙醚圓頂廳準沒錯;上到不會有人去的最頂樓,找到屋簷下的一道綠門。不過他警告我,千萬別被逮到。臨床前的學生是不准去那裡的。
我出發尋找乙醚圓頂廳時是傍晚時分,天色已經暗了,岸濱街下著毛毛雨。原來,乙醚圓頂廳是個陳舊的鉛灰玻璃圓頂,就在古老的查令十字醫院手術室上方。自從入學面試後,我就再也沒踏進過神聖的醫院入口。我們這些學生得通過解剖學、生理學和生物化學的考試,才能得到那樣的特權。所以,我沒有從正門的希臘式門廊走進去,而是偷偷從亮著藍燈的急診室溜進去,然後找到電梯——一台搖搖晃晃的老舊箱式升降機,專門用來載送病房設備和屍體到地下室。
我擔心自己可能會遲到、手術可能已經結束——還擔心那道綠門可能會上鎖。不過,門倒沒鎖。綠門背後是條滿布灰塵的昏暗走廊,堆放著過時的麻醉機器和廢棄手術儀器。離我前方十碼的地方,能看見圓頂下手術燈的亮光。這是手術室的舊高台觀眾席,設有玻璃,莊重地與下方不到十英尺處手術台上的大戲隔開距離。觀眾席還有欄杆以及弧形的木製長椅,這些長椅被那些曾經的準外科醫師們焦躁不安的臀部磨到表面都光滑了。
我緊抓著欄杆坐下。只有我和死神,透著因水氣而模糊的玻璃,仔細凝視著眼前的一切。那是一場心臟手術,病人的胸腔還開著。我移動位置,想找到最佳視角,最後停在外科醫師頭頂正上方。他很有名,起碼在我們醫學院裡是大人物;長得又高又瘦,儀表堂堂,手指修長。一九六〇年代時,心臟外科手術尚新,還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動這類手術的醫師少之又少,訓練有素的醫師更是不多。他們往往是技術老練的一般外科醫師,因為拜訪過某些先驅的醫學中心,才自願開立新的醫療服務。他們學習的步調緊張又快速,代價則是用人命來計算。
在場的兩名手術助理和刷手護士,彎著腰擠在張開的傷口邊,緊張地來回遞送著手術器械。他們目光的焦點和我著迷的對象就在那裡——一顆跳動的人類心臟。其實與其說是跳動,更像是蠕動,還插著連接人工心肺機的插管和導管。排成圓柱形的碟片在貯血槽中轉動,槽裡裝滿富含氧氣的血液,還有一台簡陋的滾軸泵擠壓著導管,促使維生所需的血液流回體內。儘管我定睛仔細觀察,卻也只能看到心臟,因為病人全身都被綠色的覆蓋巾遮著,不讓在場的人知道身分。
主刀醫師不安地換著腳站三七步,腳上是一雙從前外科醫師用來防止襪子沾染血液的超大白色手術靴。手術團隊已經置換了病人的二尖瓣,不過,那顆心臟還是難以脫離人工心肺機。就連第一次看到跳動人類心臟的我,都覺得它看起來很無力,鼓脹得像顆氣球,雖然還有搏動,卻沒有在抽送血液。在我身後的牆上,有個標示著「對講機」的盒子。我轉動開關,這下子,這齣大戲就有了聲音。
在放大的嘈雜背景聲中,我聽見主刀醫師說:「我們再試最後一次。增加腎上腺素,通氣,試著不用心肺機看看。」
現場鴉雀無聲,眾人都凝視著這個奮力活命的器官。
「右冠狀動脈裡有空氣。」第一助理說,「給我一根抽氣針。」他把針推進主動脈,帶泡沫的血液嘶嘶滲進傷口,接著,病人的血壓開始好轉。
眼看時機出現,主刀醫師轉身跟體外循環師說:「馬上關掉!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體外循環關閉。」體外循環師回答。他的口吻更像在陳述事實,語氣中沒多大信心。
人工心肺機一關,這顆心臟就全靠自己了,左心室要將血液泵往全身,右心室則要將血液泵進肺部,兩邊都在使勁努力。麻醉醫師充滿希望地盯著螢幕,一邊監控血壓和心率。幾位醫師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搏,他們一言不發地拔掉心臟的插管,縫合傷口,每個人都非常希望這顆心臟能有力起來。它先是無力地顫動了一會兒,隨後,血壓開始慢慢下降。某個部位在出血——雖然量不大,但卻停不下來。出血點似乎在心臟背面,某個處理不到的地方。
抬起心臟的動作造成了顫動。這下心臟又開始扭動,就像一袋蠕動的蟲子,卻不是正常收縮,只是受到紊亂的電活動影響而持續蠕動。它在白費力氣。麻醉師花了點時間才發現螢幕上的端倪。「VF,」他大喊。我不久後學到,這是心室顫動(ventricular fibrillation)的意思。「準備電擊。」
主刀醫師早有預料,他把去顫電擊板緊緊壓在那顆心臟上。「三十焦耳。」滋的一聲!沒有效果。「加到六十。」
滋!這次,心臟去顫了,但接著就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沒了心電活動,就像個濕漉漉的購物紙袋。我們稱這為「心搏停止」(asystole)。
血液繼續流進胸腔,主刀醫師用手指戳了戳心臟,左右心室隨即收縮。他又再戳一次,心律開始恢復。「太慢了。給我一針腎上腺素。」他又急又狠地把針從右心室穿進左心室,注入一股透明液體。然後,他用修長的手指按摩心臟,想把這強力的興奮劑推進冠狀動脈。
受惠的心肌很快有了反應。跟教科書上寫的一模一樣,心率開始加快,血壓開始飆升,越升越高,高得幾乎要撐破縫線。接著,如同慢動作鏡頭般,主動脈插管處縫合的傷口破了。嘩的一聲!一道深紅色噴泉就像間歇泉那樣噴發,灑在手術燈上,把幾個在場的醫師濺了一身,連綠色的覆蓋巾都濕透了。有人小聲地說道:「噢,慘了。」豈止是慘而已——他們輸掉了這場戰役。
還來不及用手指堵住主動脈的破洞,那顆心臟就滴血不剩了。血液從手術燈上滴下,大理石地板上到處是細細的紅色血流,都黏住橡膠靴底了。麻醉師發狂似地把一袋袋的血擠進靜脈,卻完全沒用。生命正快速消逝。剛剛施打的腎上腺素效力一過,這顆腫脹的心臟就像吹氣球一樣鼓脹起來,然後就不動了。永遠停了。
幾位醫師在絕望中沉默地佇立著,這已經是每週的例行公事。資深的主刀醫師走出了我的視線,麻醉醫師也關掉呼吸器,等待心電圖變平。他拔掉了病人氣管上的導管,接著也消失在我的視線裡。病人的大腦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