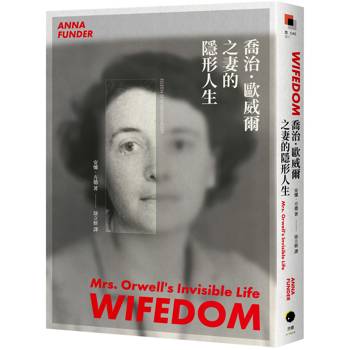黑箱子
穿著厚重黑色西裝的男人站在舞台上,下巴卡在白色領口上腫了一圈,右手拿著魔杖。他身後是一口黑箱子,就像是棺材直立著,帶有一道門;他身前的椅凳上擺著他的禮帽。箱子的一邊站著一名穿著黑色緊身衣、黑絲襪和黑色高跟鞋的女人,不知為何微笑著。男人彎腰鞠躬,寬闊額頭上冒出的汗水閃閃發亮。
他已經決定今天不會把她鋸成兩半,做了個手勢示意她走進箱子,關上門後又走到椅凳前。他聳聳肩。
「天靈靈地靈靈?」他說,彷彿我們都懂這個笑話,看著他伸手進禮帽裡摸索著,然後拉出──一條手帕。
我們大笑。
「這可不是魔術!」他說完,坐在椅凳上擦掉眉毛上的汗。「我跟各位說,人生的魔術,」他說,「就是不要期望太多。」
觀眾席間傳來緊張的笑聲,一陣偌長的沉默後,觀眾又尷尬笑了幾聲,他回頭看著箱子嘆了口氣。
「該做的還是得做。」他說完便走回到箱子前,「記住,」他伸手握著門把說,「不要期望太多。」
他打開門──什麼都沒有,觀眾都樂了。
「喔糟糕,我做了什麼?」他大叫起來,伸出雙手、雙臂在箱子裡上下摸來摸去,裡面什麼也沒有。他回到椅凳前查看禮帽內,但裡頭空空如也,於是他戴起帽子,回到依然敞開的箱子前。
「我想只能這樣了,最好把箱子關上。」他關上門時,觀眾一片驚呼。
因為她就在門後,站在箱子外面。
女人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微笑,舉起手朝他揮了揮。
無論是誰都能取代她的角色。
他彎腰鞠躬,這是他的魔術,但問題是:她剛剛在哪裡?
她其實並沒有出現在傳記裡,為歐威爾作傳的作家是七名男性,研究著一名男性,他們個個都很出色,每一位講述的故事都稍有不同,有時偏向英雄主義和諒解,有時則朝向某種無可言喻的複雜所形成的「暗黑深淵」,但是他們都很少提及歐威爾生命中的女性有多麼重要。到頭來,這些傳記漸漸就像是有所缺漏的虛構故事。
於是,我追溯到源頭,找到了其他事實和其他人物,是那些遭到遺忘的人物。艾琳便漸漸活靈活現起來,一位曾在政府單位與她共事的人認為,她比起那裡的其他人都「更加優秀」,從來沒有傳記作家引述這句細節。另一位同事兼友人說她的「性格羞怯而謙遜」,不過「總是默默保持正直的氣度,我從未見她動搖過」。我發現了一位女性,她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艾琳對歐威爾的愛「相當深切,不過也抱持著一種體貼而能理解的興趣」,她注意到他「超乎尋常的政治天真」,這點似乎讓一位傳記作家很煩惱,於是改寫了她的話,反而讓歐威爾具有「超乎尋常的政治同情心」。而且她反對有人因為歐威爾的雙頰凹陷、貌似基督的臉就稱他為「聖喬治」,她說,這只是因為他缺了一、兩顆牙。
艾琳逗得我大笑,我決定走進黑箱子將她拉出來。
站在箱子外面,從在乎的人眼中看起來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只棺材大小的黑箱子在搖晃,傳出微弱的哼唧聲,有時是煙霧,偶爾也能聽見喊叫聲。那裡一片黑暗。下筆如神的日子裡(並不多),我覺得自己就像到冥府中尋找尤麗蒂絲(Eurydice)的奧菲斯(Orpheus),特別是在那一片幽暗中,遇見了仇敵的化身:一隻兇猛的三頭犬。這隻擋住去路的塞伯拉斯(Cerberus),名為「遺漏—瑣碎—默許」。而最驚人的是,這頭猛獸也是我的老朋友,我想著,如果我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或許就能通過這場考驗,找到艾琳。
我確實找到她了,卻是在支離破碎的事實裡,像是咬在口中的玩具一樣被撕碎──一顆藍色的眼睛、包覆在西裝外套下的一角肩胛骨。一位曾經獲得牛津大學獎學金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三四年發表了反烏托邦的詩,叫做〈世紀之末,一九八四〉(End of the Century, 1984),這個人曾經兩度將同事組織起來對抗上司的霸凌。艾琳只是有如滄海一粟的凡人,卻強悍地不似凡人;而她的小名叫小豬(Pig),只是已經無人記得為什麼。
我將艾琳拉出箱子之後,就有了一段事實組成的人生、一個碎片拼湊出的女人。我考慮過要寫成小說,寫一本相較於那些傳記的反虛構故事,但是我不斷發現她被人用某種狡猾的方法隱藏起來,簡直著迷不已,小說無法呈現出這些。
然後我發現了那些書信。
艾琳和她最好的朋友諾菈.塞姆斯.邁爾斯之間有魚雁往返,二○○五年諾菈的外甥發現了六封信,那時歐威爾的傳記都已經寫成了,作家也就無法借助這些書信。我很想知道如果他們能先讀到信會怎麼做,一位知名的歐威爾學者指出,這些信件揭露出「充滿愛意的本質」,確實如此,但真相卻遠勝於此。
諾菈於一九○六年出生、一九九四年逝世,她的生平鮮有人知,而她寫給艾琳的信也沒有留下痕跡。顯然,諾菈在牛津大學聖休學院(St Hugh’s)中是相當活潑的女學生,她年少時的戀人英年早逝,畢業後嫁給了醫生夸塔斯.聖勒傑.邁爾斯(Quartus St Leger Myles,也稱為Q),定居在布里斯托,夫妻倆沒有小孩。諾菈和艾琳十分親近,艾琳甚至在遺囑中指定諾菈,若是自己早亡,她想要諾菈來照顧她的兒子。
寫給諾菈的信可以回溯到艾琳舉行婚禮後不久,一路寫到西班牙內戰、夫妻倆在摩洛哥的時光,然後進入戰時倫敦大轟炸期間。信件內容令人豁然開朗,好像在歐威爾過世超過半個世紀之後,有人打開了一扇通往他私生活的門,揭露出一位生活在門後的女人(以及在那裡寫作的男人),讓人以全新的角度審視之。
現在已經不可能寫成小說了,否則這些書信會淪為「素材」,而且讓我的解讀壓過了她本身的聲音。艾琳的聲音十分令人興奮,我想要讓她活起來,同時揭發出抹除她的邪惡魔術技法,這些手段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大影響力。我打算寫下納入一切的虛構故事。
於是我花費數月、數年,深深埋首於歐威爾的研究中。我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歐威爾資料庫中找到了艾琳大學時期的筆記本與寫給歐威爾的信,她的筆跡清楚而圓潤。艾琳和歐威爾在一九四四年領養了兒子,取名為理查.布萊爾(Richard Blair),我跟著他一同旅行加泰隆尼亞,追溯歐威爾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留下的足跡。最後我來到蘇格蘭的朱拉島(Isle of Jura),待在歐威爾寫出最後一本書《一九八四》的那間屋子,和他當時房東的孫子一起喝威士忌。
大概是機緣巧合,希薇亞.托普(Syliva Topp)於二○二○年出版了《艾琳:喬治.歐威爾的養成》(Eileen: The Making of George Orwell),書中有許多我未曾找到的資料,讓我閱讀時興奮不已,只是我們解讀資料的觀點不同,所以描繪出的艾琳也不一樣。
尋找艾琳的過程中,我也樂於閱讀歐威爾對權力運作的剖析。而找到了艾琳,就有可能揭示權力如何影響女性:一名女性是怎麼樣先埋沒在家庭生活中,接著隱沒在歷史裡。
但是我相當重視歐威爾的作品,我無論如何都不願意貶低他的作品,或是他。我擔心我講述的故事可能會讓他面臨被「取消」的風險。只是,艾琳當然已經被取消了,凶手正是父權。我需要找到方法將這一切,包括作品、丈夫和妻子,在我腦海中排列成星座,每顆星維持著彼此之間的位置。
因此,我制定了一套基本規則,要寫出不說謊的虛構故事:艾琳會活在她寫的那些書信裡──有六封寫給她最好的朋友、三封寫給她的丈夫,還有幾封寫給其他人的信。我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寫下這些信,我知道那時的碗盤就凍結在水槽裡、知道她正血流不止、知道他和另一個女人上床──而且她也知情。在這個故事裡,字字句句都是她的,有時我會根據所發生的事寫成一幕,而大多時候我只會扮演電影導演的角色,指揮現場的演員,例如擦擦眼鏡、地毯上的灰、一隻貓從她腿上跳開。(未完)
穿著厚重黑色西裝的男人站在舞台上,下巴卡在白色領口上腫了一圈,右手拿著魔杖。他身後是一口黑箱子,就像是棺材直立著,帶有一道門;他身前的椅凳上擺著他的禮帽。箱子的一邊站著一名穿著黑色緊身衣、黑絲襪和黑色高跟鞋的女人,不知為何微笑著。男人彎腰鞠躬,寬闊額頭上冒出的汗水閃閃發亮。
他已經決定今天不會把她鋸成兩半,做了個手勢示意她走進箱子,關上門後又走到椅凳前。他聳聳肩。
「天靈靈地靈靈?」他說,彷彿我們都懂這個笑話,看著他伸手進禮帽裡摸索著,然後拉出──一條手帕。
我們大笑。
「這可不是魔術!」他說完,坐在椅凳上擦掉眉毛上的汗。「我跟各位說,人生的魔術,」他說,「就是不要期望太多。」
觀眾席間傳來緊張的笑聲,一陣偌長的沉默後,觀眾又尷尬笑了幾聲,他回頭看著箱子嘆了口氣。
「該做的還是得做。」他說完便走回到箱子前,「記住,」他伸手握著門把說,「不要期望太多。」
他打開門──什麼都沒有,觀眾都樂了。
「喔糟糕,我做了什麼?」他大叫起來,伸出雙手、雙臂在箱子裡上下摸來摸去,裡面什麼也沒有。他回到椅凳前查看禮帽內,但裡頭空空如也,於是他戴起帽子,回到依然敞開的箱子前。
「我想只能這樣了,最好把箱子關上。」他關上門時,觀眾一片驚呼。
因為她就在門後,站在箱子外面。
女人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微笑,舉起手朝他揮了揮。
無論是誰都能取代她的角色。
他彎腰鞠躬,這是他的魔術,但問題是:她剛剛在哪裡?
她其實並沒有出現在傳記裡,為歐威爾作傳的作家是七名男性,研究著一名男性,他們個個都很出色,每一位講述的故事都稍有不同,有時偏向英雄主義和諒解,有時則朝向某種無可言喻的複雜所形成的「暗黑深淵」,但是他們都很少提及歐威爾生命中的女性有多麼重要。到頭來,這些傳記漸漸就像是有所缺漏的虛構故事。
於是,我追溯到源頭,找到了其他事實和其他人物,是那些遭到遺忘的人物。艾琳便漸漸活靈活現起來,一位曾在政府單位與她共事的人認為,她比起那裡的其他人都「更加優秀」,從來沒有傳記作家引述這句細節。另一位同事兼友人說她的「性格羞怯而謙遜」,不過「總是默默保持正直的氣度,我從未見她動搖過」。我發現了一位女性,她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艾琳對歐威爾的愛「相當深切,不過也抱持著一種體貼而能理解的興趣」,她注意到他「超乎尋常的政治天真」,這點似乎讓一位傳記作家很煩惱,於是改寫了她的話,反而讓歐威爾具有「超乎尋常的政治同情心」。而且她反對有人因為歐威爾的雙頰凹陷、貌似基督的臉就稱他為「聖喬治」,她說,這只是因為他缺了一、兩顆牙。
艾琳逗得我大笑,我決定走進黑箱子將她拉出來。
站在箱子外面,從在乎的人眼中看起來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只棺材大小的黑箱子在搖晃,傳出微弱的哼唧聲,有時是煙霧,偶爾也能聽見喊叫聲。那裡一片黑暗。下筆如神的日子裡(並不多),我覺得自己就像到冥府中尋找尤麗蒂絲(Eurydice)的奧菲斯(Orpheus),特別是在那一片幽暗中,遇見了仇敵的化身:一隻兇猛的三頭犬。這隻擋住去路的塞伯拉斯(Cerberus),名為「遺漏—瑣碎—默許」。而最驚人的是,這頭猛獸也是我的老朋友,我想著,如果我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或許就能通過這場考驗,找到艾琳。
我確實找到她了,卻是在支離破碎的事實裡,像是咬在口中的玩具一樣被撕碎──一顆藍色的眼睛、包覆在西裝外套下的一角肩胛骨。一位曾經獲得牛津大學獎學金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三四年發表了反烏托邦的詩,叫做〈世紀之末,一九八四〉(End of the Century, 1984),這個人曾經兩度將同事組織起來對抗上司的霸凌。艾琳只是有如滄海一粟的凡人,卻強悍地不似凡人;而她的小名叫小豬(Pig),只是已經無人記得為什麼。
我將艾琳拉出箱子之後,就有了一段事實組成的人生、一個碎片拼湊出的女人。我考慮過要寫成小說,寫一本相較於那些傳記的反虛構故事,但是我不斷發現她被人用某種狡猾的方法隱藏起來,簡直著迷不已,小說無法呈現出這些。
然後我發現了那些書信。
艾琳和她最好的朋友諾菈.塞姆斯.邁爾斯之間有魚雁往返,二○○五年諾菈的外甥發現了六封信,那時歐威爾的傳記都已經寫成了,作家也就無法借助這些書信。我很想知道如果他們能先讀到信會怎麼做,一位知名的歐威爾學者指出,這些信件揭露出「充滿愛意的本質」,確實如此,但真相卻遠勝於此。
諾菈於一九○六年出生、一九九四年逝世,她的生平鮮有人知,而她寫給艾琳的信也沒有留下痕跡。顯然,諾菈在牛津大學聖休學院(St Hugh’s)中是相當活潑的女學生,她年少時的戀人英年早逝,畢業後嫁給了醫生夸塔斯.聖勒傑.邁爾斯(Quartus St Leger Myles,也稱為Q),定居在布里斯托,夫妻倆沒有小孩。諾菈和艾琳十分親近,艾琳甚至在遺囑中指定諾菈,若是自己早亡,她想要諾菈來照顧她的兒子。
寫給諾菈的信可以回溯到艾琳舉行婚禮後不久,一路寫到西班牙內戰、夫妻倆在摩洛哥的時光,然後進入戰時倫敦大轟炸期間。信件內容令人豁然開朗,好像在歐威爾過世超過半個世紀之後,有人打開了一扇通往他私生活的門,揭露出一位生活在門後的女人(以及在那裡寫作的男人),讓人以全新的角度審視之。
現在已經不可能寫成小說了,否則這些書信會淪為「素材」,而且讓我的解讀壓過了她本身的聲音。艾琳的聲音十分令人興奮,我想要讓她活起來,同時揭發出抹除她的邪惡魔術技法,這些手段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大影響力。我打算寫下納入一切的虛構故事。
於是我花費數月、數年,深深埋首於歐威爾的研究中。我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歐威爾資料庫中找到了艾琳大學時期的筆記本與寫給歐威爾的信,她的筆跡清楚而圓潤。艾琳和歐威爾在一九四四年領養了兒子,取名為理查.布萊爾(Richard Blair),我跟著他一同旅行加泰隆尼亞,追溯歐威爾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留下的足跡。最後我來到蘇格蘭的朱拉島(Isle of Jura),待在歐威爾寫出最後一本書《一九八四》的那間屋子,和他當時房東的孫子一起喝威士忌。
大概是機緣巧合,希薇亞.托普(Syliva Topp)於二○二○年出版了《艾琳:喬治.歐威爾的養成》(Eileen: The Making of George Orwell),書中有許多我未曾找到的資料,讓我閱讀時興奮不已,只是我們解讀資料的觀點不同,所以描繪出的艾琳也不一樣。
尋找艾琳的過程中,我也樂於閱讀歐威爾對權力運作的剖析。而找到了艾琳,就有可能揭示權力如何影響女性:一名女性是怎麼樣先埋沒在家庭生活中,接著隱沒在歷史裡。
但是我相當重視歐威爾的作品,我無論如何都不願意貶低他的作品,或是他。我擔心我講述的故事可能會讓他面臨被「取消」的風險。只是,艾琳當然已經被取消了,凶手正是父權。我需要找到方法將這一切,包括作品、丈夫和妻子,在我腦海中排列成星座,每顆星維持著彼此之間的位置。
因此,我制定了一套基本規則,要寫出不說謊的虛構故事:艾琳會活在她寫的那些書信裡──有六封寫給她最好的朋友、三封寫給她的丈夫,還有幾封寫給其他人的信。我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寫下這些信,我知道那時的碗盤就凍結在水槽裡、知道她正血流不止、知道他和另一個女人上床──而且她也知情。在這個故事裡,字字句句都是她的,有時我會根據所發生的事寫成一幕,而大多時候我只會扮演電影導演的角色,指揮現場的演員,例如擦擦眼鏡、地毯上的灰、一隻貓從她腿上跳開。(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