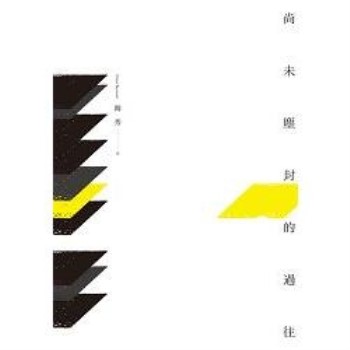一九八七年
初次捧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書中的內容,曾經與沈從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先生等等許多的長輩與朋友充分地討論過。當然,關於正文內容以及兩篇極有份量的附錄〈一九五八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覺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銳與獨特的。但是,我感覺書中這篇〈自序〉最是觸動大陸作家的內心。夏先生細說從頭,講到五十年代初韓戰期間曾經為美國軍人編寫《中國手冊》,他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禮節〉、〈幽默〉二小章,也參與了一些其他篇章的寫作,其中包括人文地理的部份。自序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五十年代後期《時代》週刊刊印了一個中國特輯(該期人物封面是毛澤東),居然也報導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週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夏先生笑聲琅琅,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中之一自然是因為當初這個部份沒有什麼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大陸作家們看到這裡也大笑,笑到眼淚都流了出來,原因卻是不同的。他們看到了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的夏先生,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的學者,對大陸文化人的處境知之甚詳,同情有加,英文棒到《時代》週刊一字不動地轉載,而且,他可以那樣的得意。「得意」這個詞,大陸作家們是絕對不會用在自己身上的。他們的笑裡飽含了羨慕,羨慕著夏先生有向學的自由、思考與寫作的自由,也有出版的自由。因之,大陸作家們的歡笑終至化為淚水。他們珍惜夏先生的鴻文巨製,他們更珍惜夏先生有條件保持一位獨立文化人的真性情。那是他們夢寐以求卻至今也辦不到的。真的面對面認識夏公這位傳奇人物,卻是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的事情。那一天,台北《聯合報副刊》的小說家蘇偉貞與她的先生張德模來到紐約,約了我到皇后區法拉盛去。那時候,我剛剛從康州返回曼哈頓,身心俱疲,一臉憔悴。但是,那一天的約會卻是非常的要緊,與來自台灣的偉貞夫婦是頭一次見面,與同住紐約的夏公、鼎公也是頭一次見面。法拉盛的中餐館裡,一桌五個人,談得很開心。那一天,我帶了一瓶香水送偉貞。偉貞的表情好像充滿好奇心的小女孩,馬上旋開瓶蓋,在耳朵後面輕輕點了兩點,席上飄起輕柔的香氛。鼎公與德模面帶微笑正襟危坐,夏先生卻看得很專注,很有趣。那時候,我就覺得,鼎公與德模是屬於東方的,夏公卻是屬於西方的。他的專注裡有著許多的內容,我馬上想到他的小說史,想到他對女性作家深切的同情與理解。回程中,與夏公同時搭乘地鐵。他比我年長二十五歲,卻非常地紳士,一直在幫我找位子。當時我就想,自己想必是一臉的病容,害得夏公操心。同車的還有偉貞夫婦,所以一路上他都在講中文,親切地噓寒問暖。臨別,夏公用便條紙寫下他在曼哈頓西區一百一十五街的住家地址、電話,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 Kent Hall 的辦公室地址。很客氣地表示,「保持聯絡」。這位大學問家真是一位謙謙君子。我心裡這樣想,一邊也遞給他我們在曼哈頓上東城七十二街的地址、電話。夏公看看地址,微笑點頭,「好地方」。那一段時期,我們極為忙碌,我忙中偷閒寫《折射》,甚至擠出時間完成了短篇小說〈骨灰〉。心情可以用「肝腸寸斷」來形容。除了聯合國以及美國使團的大量活動之外,大陸作家張承志來訪,與台北文壇的瘂弦先生、偉貞、李牧先生、魏子雲先生通信極勤。與大陸的吳祖光先生、鄭萬隆、朱曉平、張笑天、張守仁、楊良志、焦世宏(焦菊隱先生的女公子)諸君也通信不止。其間,甚至寫了一些關於大陸新銳小說作者莫言的讀後感給鼎公,也寄了幾本大陸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給鼎公。一直到了十月八日,才寫信問候並寄了剛剛寫完的小說〈電話〉給夏公,因為七月那次見面,我知道夏公與祖光先生是舊識,而〈電話〉裡面的一個重要角色正是祖光先生。同時寄上的還有短篇小說〈下班之後〉(這篇文字在幾經修改後收入允晨版《長日將盡》時,改名為〈下班以後〉)。
想不到的,十月三十日卻收到了夏公給我的第一封信。信紙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米色書信用紙,格式自然應當是橫寫,夏公的信卻是將信紙「放倒」直寫,字字分明。抬頭很正式:韓秀女士。
關於我們的初次見面,夏先生談到他的觀感。他同許多頭一次和我見面聊天的華人一樣認為,「您是美國人,可是國語講得這樣好。今晚把你寄我的大作〈下班之後〉也拜讀了,對你北京味道很重的白話,也感到很驚奇。文字實在流暢,而且有味道,『洋人』能寫這樣好的中文,實在太不容易了。」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例如李玉靜十幾、二十多年的人生經歷,「雖然主要憑她的回憶,讀來也很動人」。甚至對於這位苦命的女子為兩次婚姻而受苦,最後決定出走,不回婆家。也認為是「很好的決定」。甚至「秦芳和李師傅的強烈對比,也很有意思,你對北京縫衣廠的情形很熟悉,也很不容易」。更讓我感動的是,夏先生對我這個新手真是鼓勵有加,「最近聯副刊了你的新作〈不惑之年〉,我已把三份報保留起來,日內即要拜讀。您寫小說專寫大陸,而你自己時間在北京又不太長,可你真花工夫,在關心,在研究大陸人的生活。蘇偉貞愛刊登你的小說,我想聯副的讀者群也都愛讀你的小說的。望你繼續努力,多寫!」在最後,夏先生提到星期天晚上,在一個 Cocktail Party 上又同吳祖光見面了。而且告訴我,他們兩人這已經是第三次見面了,第一次在巴黎,第二次是兩、三年前在紐約。關於這次重逢,夏先生這樣說,「這次他重來,因為『退黨』,更受歡迎了。他講了一段退黨的經過,很有趣。」夏先生還告訴我,祖光先生還會再來,如果我願意同祖光先生聚一聚的話,他很願意「作陪」。而且告訴我他的電話是 7496853,「有事可打電話連絡」。夏先生來信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八七,十月21日」。這樣中文與阿拉伯數字相連的寫法專屬夏公,在有信件來往的朋友中是獨一無二的。捧讀這封充滿關懷的來信,真正是汗如雨下。我就在想,偉貞說話做事都謹慎,夏公打聽韓秀何許人的時候,偉貞恐怕祇說了聯副小說作者這一小段,背景方面,恐怕也只是提及駐節美國駐聯合國使團以及稍早駐節北京美國大使館這兩段,所以,夏公會說我在北京的時間「又不太長」,於是驚奇於我這個「洋人」的中文「這樣好」、「實在流暢」。以為是我「關心」與「研究」的結果。夏公是極敏銳、極聰慧的長者。我自然應該實話實說,我這個「洋人」在兩歲的年紀便去到中國,並且再無洋人的呵護,直接地浸泡到中國人的汪洋大海之中。除了江南的兩年之外,北京的十四年、山西的三年、新疆的九年、重返北京的將近兩年,如此這般,近三十年的時光,不但中國話講得好是應當的,中文寫得流暢也是應當的。在那三十年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是怎樣與許多的中國老百姓同呼吸共命運的,在我十月八日的信裡完全沒有提,在後來給夏公的信裡也都沒有提。我在想,遲遲早早,謎底總是會揭曉的。
至於〈下班之後〉,這篇不算太尖銳的小說,夏公卻看得十分仔細。關於「縫衣廠」,我的「熟悉」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事情。我在三十歲的年紀進入這家工廠,在一年多的日子裡,李玉靜、秦芳、李師傅,這些人物就和我整天地面對著面,我知道她們的喜怒哀樂,我了解她們的困頓與掙扎。誠實書寫並非難事,但是,也並不需要跟夏公說太多,老人家絕對不需要聽這麼多苦澀的故事。
當年夏公看到的只是這些小說的雛形。是一腔熱血的產物。到了新世紀,這些文字才得以細細推敲,重新擺放,找到更好的表現方式。然而,到了這個時候,夏公的健康情形已不復當年,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請他看書信以外的任何文字。然則,在我修訂這些小說的時候,卻常常想著夏公對於華文小說的期許,以此要求著自己。這是後話。
關於祖光先生「退黨」一事,我心中有數,關於短篇小說〈電話〉,我也知道祖光伯伯的觀感。因為就在這一年的六月底我已經收到了祖光伯伯和鳳霞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的來信。這封信用藍墨水寫在普通的信紙上。整封信的口氣完全是這兩位長輩一向的直率、坦誠、熱情、一針見血。
初次捧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書中的內容,曾經與沈從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先生等等許多的長輩與朋友充分地討論過。當然,關於正文內容以及兩篇極有份量的附錄〈一九五八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覺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銳與獨特的。但是,我感覺書中這篇〈自序〉最是觸動大陸作家的內心。夏先生細說從頭,講到五十年代初韓戰期間曾經為美國軍人編寫《中國手冊》,他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禮節〉、〈幽默〉二小章,也參與了一些其他篇章的寫作,其中包括人文地理的部份。自序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五十年代後期《時代》週刊刊印了一個中國特輯(該期人物封面是毛澤東),居然也報導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週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夏先生笑聲琅琅,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中之一自然是因為當初這個部份沒有什麼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大陸作家們看到這裡也大笑,笑到眼淚都流了出來,原因卻是不同的。他們看到了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的夏先生,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的學者,對大陸文化人的處境知之甚詳,同情有加,英文棒到《時代》週刊一字不動地轉載,而且,他可以那樣的得意。「得意」這個詞,大陸作家們是絕對不會用在自己身上的。他們的笑裡飽含了羨慕,羨慕著夏先生有向學的自由、思考與寫作的自由,也有出版的自由。因之,大陸作家們的歡笑終至化為淚水。他們珍惜夏先生的鴻文巨製,他們更珍惜夏先生有條件保持一位獨立文化人的真性情。那是他們夢寐以求卻至今也辦不到的。真的面對面認識夏公這位傳奇人物,卻是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的事情。那一天,台北《聯合報副刊》的小說家蘇偉貞與她的先生張德模來到紐約,約了我到皇后區法拉盛去。那時候,我剛剛從康州返回曼哈頓,身心俱疲,一臉憔悴。但是,那一天的約會卻是非常的要緊,與來自台灣的偉貞夫婦是頭一次見面,與同住紐約的夏公、鼎公也是頭一次見面。法拉盛的中餐館裡,一桌五個人,談得很開心。那一天,我帶了一瓶香水送偉貞。偉貞的表情好像充滿好奇心的小女孩,馬上旋開瓶蓋,在耳朵後面輕輕點了兩點,席上飄起輕柔的香氛。鼎公與德模面帶微笑正襟危坐,夏先生卻看得很專注,很有趣。那時候,我就覺得,鼎公與德模是屬於東方的,夏公卻是屬於西方的。他的專注裡有著許多的內容,我馬上想到他的小說史,想到他對女性作家深切的同情與理解。回程中,與夏公同時搭乘地鐵。他比我年長二十五歲,卻非常地紳士,一直在幫我找位子。當時我就想,自己想必是一臉的病容,害得夏公操心。同車的還有偉貞夫婦,所以一路上他都在講中文,親切地噓寒問暖。臨別,夏公用便條紙寫下他在曼哈頓西區一百一十五街的住家地址、電話,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 Kent Hall 的辦公室地址。很客氣地表示,「保持聯絡」。這位大學問家真是一位謙謙君子。我心裡這樣想,一邊也遞給他我們在曼哈頓上東城七十二街的地址、電話。夏公看看地址,微笑點頭,「好地方」。那一段時期,我們極為忙碌,我忙中偷閒寫《折射》,甚至擠出時間完成了短篇小說〈骨灰〉。心情可以用「肝腸寸斷」來形容。除了聯合國以及美國使團的大量活動之外,大陸作家張承志來訪,與台北文壇的瘂弦先生、偉貞、李牧先生、魏子雲先生通信極勤。與大陸的吳祖光先生、鄭萬隆、朱曉平、張笑天、張守仁、楊良志、焦世宏(焦菊隱先生的女公子)諸君也通信不止。其間,甚至寫了一些關於大陸新銳小說作者莫言的讀後感給鼎公,也寄了幾本大陸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給鼎公。一直到了十月八日,才寫信問候並寄了剛剛寫完的小說〈電話〉給夏公,因為七月那次見面,我知道夏公與祖光先生是舊識,而〈電話〉裡面的一個重要角色正是祖光先生。同時寄上的還有短篇小說〈下班之後〉(這篇文字在幾經修改後收入允晨版《長日將盡》時,改名為〈下班以後〉)。
想不到的,十月三十日卻收到了夏公給我的第一封信。信紙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米色書信用紙,格式自然應當是橫寫,夏公的信卻是將信紙「放倒」直寫,字字分明。抬頭很正式:韓秀女士。
關於我們的初次見面,夏先生談到他的觀感。他同許多頭一次和我見面聊天的華人一樣認為,「您是美國人,可是國語講得這樣好。今晚把你寄我的大作〈下班之後〉也拜讀了,對你北京味道很重的白話,也感到很驚奇。文字實在流暢,而且有味道,『洋人』能寫這樣好的中文,實在太不容易了。」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例如李玉靜十幾、二十多年的人生經歷,「雖然主要憑她的回憶,讀來也很動人」。甚至對於這位苦命的女子為兩次婚姻而受苦,最後決定出走,不回婆家。也認為是「很好的決定」。甚至「秦芳和李師傅的強烈對比,也很有意思,你對北京縫衣廠的情形很熟悉,也很不容易」。更讓我感動的是,夏先生對我這個新手真是鼓勵有加,「最近聯副刊了你的新作〈不惑之年〉,我已把三份報保留起來,日內即要拜讀。您寫小說專寫大陸,而你自己時間在北京又不太長,可你真花工夫,在關心,在研究大陸人的生活。蘇偉貞愛刊登你的小說,我想聯副的讀者群也都愛讀你的小說的。望你繼續努力,多寫!」在最後,夏先生提到星期天晚上,在一個 Cocktail Party 上又同吳祖光見面了。而且告訴我,他們兩人這已經是第三次見面了,第一次在巴黎,第二次是兩、三年前在紐約。關於這次重逢,夏先生這樣說,「這次他重來,因為『退黨』,更受歡迎了。他講了一段退黨的經過,很有趣。」夏先生還告訴我,祖光先生還會再來,如果我願意同祖光先生聚一聚的話,他很願意「作陪」。而且告訴我他的電話是 7496853,「有事可打電話連絡」。夏先生來信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八七,十月21日」。這樣中文與阿拉伯數字相連的寫法專屬夏公,在有信件來往的朋友中是獨一無二的。捧讀這封充滿關懷的來信,真正是汗如雨下。我就在想,偉貞說話做事都謹慎,夏公打聽韓秀何許人的時候,偉貞恐怕祇說了聯副小說作者這一小段,背景方面,恐怕也只是提及駐節美國駐聯合國使團以及稍早駐節北京美國大使館這兩段,所以,夏公會說我在北京的時間「又不太長」,於是驚奇於我這個「洋人」的中文「這樣好」、「實在流暢」。以為是我「關心」與「研究」的結果。夏公是極敏銳、極聰慧的長者。我自然應該實話實說,我這個「洋人」在兩歲的年紀便去到中國,並且再無洋人的呵護,直接地浸泡到中國人的汪洋大海之中。除了江南的兩年之外,北京的十四年、山西的三年、新疆的九年、重返北京的將近兩年,如此這般,近三十年的時光,不但中國話講得好是應當的,中文寫得流暢也是應當的。在那三十年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是怎樣與許多的中國老百姓同呼吸共命運的,在我十月八日的信裡完全沒有提,在後來給夏公的信裡也都沒有提。我在想,遲遲早早,謎底總是會揭曉的。
至於〈下班之後〉,這篇不算太尖銳的小說,夏公卻看得十分仔細。關於「縫衣廠」,我的「熟悉」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事情。我在三十歲的年紀進入這家工廠,在一年多的日子裡,李玉靜、秦芳、李師傅,這些人物就和我整天地面對著面,我知道她們的喜怒哀樂,我了解她們的困頓與掙扎。誠實書寫並非難事,但是,也並不需要跟夏公說太多,老人家絕對不需要聽這麼多苦澀的故事。
當年夏公看到的只是這些小說的雛形。是一腔熱血的產物。到了新世紀,這些文字才得以細細推敲,重新擺放,找到更好的表現方式。然而,到了這個時候,夏公的健康情形已不復當年,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請他看書信以外的任何文字。然則,在我修訂這些小說的時候,卻常常想著夏公對於華文小說的期許,以此要求著自己。這是後話。
關於祖光先生「退黨」一事,我心中有數,關於短篇小說〈電話〉,我也知道祖光伯伯的觀感。因為就在這一年的六月底我已經收到了祖光伯伯和鳳霞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的來信。這封信用藍墨水寫在普通的信紙上。整封信的口氣完全是這兩位長輩一向的直率、坦誠、熱情、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