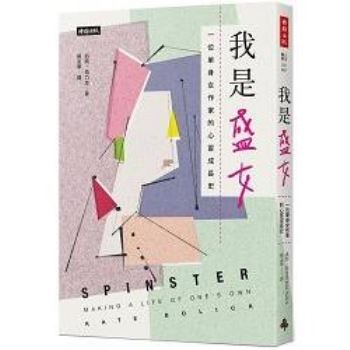第二章 單身心願
如何找到五位精神導師,是個跟一連串虛構事物有關的真實故事──真實的慾望、外來的期待、莫名的渴望,和似是而非的半真相──它們構築了一個生命,並容許幻想和真實並存其中。當我準備下筆時,曾以為我會從第一位精神導師開始依序而下,卻發現是一個前奏導向了那主要事件,這前奏即是母親與我的一堆心願,故事亦由此開始。
母親有次告訴我,她小時候曾躺在床上召喚未來將要與她結婚的男人。那個片刻他在哪裡?在想什麼?長相如何?他們何時會相遇?她有時會溜進後院,抱住一棵樹,練習如何擁抱丈夫。
一九六八年二月,她與她的命運相遇了,那時她剛滿二十四歲,地點是賓州一處滑雪度假村。他們於排隊等待升降椅時偷偷地相互打量:有著一頭鬈髮的可愛傢伙,圍著錯誤的白色的圍巾(他在北卡羅萊納州長大,第一次滑雪);一位曲線玲瓏的棕髮女郎,身穿黃綠色滑雪裝(她來自新英格蘭,對滑雪坡瞭若指掌)。後來,回到度假村的主建築,他們喝著熱可可開始調情,發現兩人都住在華盛頓特區,她剛去賈柏公司上班,而他是陸軍情報官,正在學習中文。他向她要電話號碼。她說她在電話簿上。他喜歡她的狂妄。十一個月後,他們在紐伯利港鎮外的一座小教堂結婚──就我的觀點,這快得嚇人,但在當時很常見。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酷愛收集他們新婚頭幾年那些真的非常浪漫的故事,而且聽他們說了無數次,到最後從對話到服裝我都可以鉅細靡遺地重新描述。
然而,當我開始認真思考我的五位精神導師,我逐漸領悟,從人口統計學來說,我的父母在歷史上不尋常的時刻做了一連串非常尋常的決定──剛好提供了一個方便的例子,讓我瞭解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婚姻趨勢。
他們是珠聯璧合的一對:她帶來他所渴望的穩定感,同時也分享他的冒險;他樂於溝通又充滿愛心,是個與她那老是抽著雪茄的粗暴父親完全相反的人。他們婚後不久,他便奉派移防琉球,在亞洲特別行動部隊擔任必須用到中文的職位;他於一個多月之後打電報回家,這封電報後來被裱了框掛在紐伯特港家中的牆上,電文為:
爭取到宿舍委託書已寄
愛妳道格他們住在基地之外琉球人的社區,直到他被改派到越南。她搬回美國跟父母同住,並在紐伯利港擔任英文老師(埃德娜‧米萊小時候上過這所學校,如今已廢校)。父親後來告訴我,那是一段「刺激又暈頭轉向的時間。戰爭的趨勢,請假、休假,痛苦、焦慮。」
一九七一年七月,他完成了一年的服役期,他們回到華盛頓特區,讓他可以用退伍軍人獎學金進入法學院;她在特殊兒童委員會(一個專業的代言團體)找到工作。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出生;四年又一天後,我弟弟克禮斯多福出生;一九七七年,我們搬回紐伯利港,父親在市中心成立了個人的律師事務所,母親回學校教書。
每次看到這些數字,我都重新驚訝一次。一八九○,只有五十四%的家庭有一對已婚的夫妻。到一九五○,這個數字成長到六十五%。我父母結婚時,他們的同儕八十%為已婚夫妻。
受教育、離家、進入某行業、結婚、生小孩──直到不久前,這個因循守舊但能快速完成美國夢的過程,是如此理所當然。然而,一如貝蒂‧傅瑞丹 一九六三年的名著《覺醒與挑戰: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所揭露的,即使是當時,人行道已有了裂縫。一九六二年有項問卷調查說明了一件頗為特別的事,大多數的已婚女性聲稱她們是快樂的,但只有十%樂見女兒追隨她們的腳步。她們藉由這項調查小聲耳語:別急著結婚;多過一點自己的生活;去上大學。
事情果然這樣發生。一九七○年,已婚家庭比例驟降到六十一%。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九,離婚率倍增。
母親撫養我的時候,她們已不必再小聲耳語。一九六○年代末期,方興未艾的第二波女性運動到一九七○早期已迅速從大都市中心擴展到小城鎮。紐伯利港並非女性主義的溫床,但母親和她的姊妹淘成立了「婦女投票聯盟」的地方分會,一九八○年,她三十六歲時成為該分會的主席。「『假如』妳真的決定要生小孩,才生。」我相信當我可以思考這方面的事時,她會這麼說。
有一次她意外地向我吐露一件事,她說這輩子最快樂的時間是二十一歲的時候,那是認識我父親的前幾年,她開著金龜車馳過高速公路,想去哪裡都可以隨心所欲。「我有自己的車、自己的工作,想要的衣服全都有了,」她充滿渴望地回憶著。她若晚幾年出生,就可以多享受十年這樣無拘無束的快意生活。然而她並未這樣做,她把自己的野心擺到一邊,養大兩個小孩後才在三十多歲中期開始尋找自己喜歡的事,卻只發現她已落後許多。她和家人在一起時非常快樂,但同時也是焦慮的,這份緊張對於我的成長有著巨大影響。
青少年時,母親寫了一篇短文當成我高中畢業的禮物之一,起因是一位鄰居看見我走過街上。這位先生告訴她:「凱特頗有妳的風範,相同的窄肩挺得好直。」母親對這個比較感到很高興,並得出結論:即使她過世許久,她仍經由我而活著,活在我的行為舉止裡。我對她說我很喜歡那篇文章,內心其實揪成一團。真是這樣嗎?我注定要一輩子像她嗎?
妳若是女兒,母親的臉是妳的第一面鏡子,如果妳的五官像她──以我們的情況是榛眼棕髮、雀斑、嬌小的骨架和所謂「挺直的窄肩」──我敢打賭,妳會無意識地接收她對她自己的看法和態度。母親雖不至於認為自己不漂亮,但自認普通,於是我很自然地相信了她,認為自己並無特殊之處。
她常生動地描述她笨拙的青少年時期,我甚至可以隨時召喚那個膽怯的女孩──在我的腦海裡,她總是癱靠在一排寄物櫃旁(我們除了外型相似,也是校友),髮型鬆塌無趣,身穿過時又不合身的格子衣裙,總是可憐兮兮地獨來獨往。我跟這個雙胞胎似的魅影形影不離,即使我和她完全不一樣:我非常外向且是體育健將。大家最愛說的一個家庭故事就是:因為我母親的學科成績不佳,升學顧問居然建議她申請美容美髮學校。「我甚至不愛梳『自己』的頭髮!」我母親抱怨道。
這個笑話要強調的是,可見她多麼成功地從那個可悲又無可救藥的女孩脫胎換骨,成為眾所倚重且公認堅強的女人。她從十幾到二十幾歲,都對自己毫無信心和安全感──而後在三十四歲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向後轉:辭去中學英文教師的工作,即使沒有任何專業證書,仍說服《紐伯利港每日新聞報》雇用她擔任專題編輯。兩年後,她辭去全職的工作,重新打造自己成為特約記者,替全國性的雜誌和報社撰寫旅行故事。因為我父親自己開業,他可以在她奉命飛去希臘或德國採訪的時候,替代她處理家務。她三十九歲時(我十歲),發現胸部有腫瘤並割除了一邊的乳房。手術成功,這個疤痕促使她活得更加全然也更加勇敢。她在復原期間加倍投入於特約記者的工作,接下更具挑戰性的題目,報導重要的社會議題,並出版了幾本青少年歷史書。她真正的野心是出版小說;她利用稀少的空閒時間撰寫短篇小說,並參加了一個寫作團體。
一九九○,我高三那年,她出馬競選小鎮高中的學校董事。我有時會陪她到紐伯利港的大街小巷逐家敲門,分送競選傳單。每個人都說我們長得好像。她的競選照片相較於我所知的溫暖又慷慨的母親,更為強悍也更光鮮:短髮梳成略似頭巾的嚴肅髮型,雙眼因刷了睫毛膏而顯得更加炯炯有神,豐滿的嘴唇抿出充滿決心與毅力的線條。她把真正的自己保留在真正的生活裡;她贏了選戰之後並未獨抱勝利而是分享,她舉辦公開的聚會,鼓勵其他女性出來競選公職,並教她們如何達成目標。
雖然,我們心底深處都知道,癌症隨時可能復發。
我們是個愛說話,活著就要拚命說話的家庭,幾乎每件事都曾拿出來公開討論。當我還是個小小孩時,每天晚上,母親或父親會來替我蓋被子,我總是往被窩深處躺得更舒服後,唱歌似地說出我最愛的句子:「我們來談……」我們談剛才讀過的書,或晚餐之後的散步,或明天早餐要吃什麼。我說你聽,你說我聽;任何事都好。每件事都說,更好!我認為每一段親密關係,包括友誼,都是沿著類似的對話河流建立起來的。以我的想法,親密就是說話。
但我們如實正視這顆滴答響的定時炸彈,是在那年的情人節,那時我母親第一次知道她有復發的狀況。那是她主辦的活動,我們三個是她挑選的來賓。她把餐桌佈置得非常漂亮,在每個人的盤子放上精選的小禮物(我特別記得我的禮物是放在扁平塑膠水袋裡的兩條泰國鬥魚)在我們開始吃飯前,她說了一段很入世的禱告,說她如何感謝到現在還活著,可以從事她關心的工作,嫁給她愛的人,看著孩子長大。
我低頭看著放在腿上的手,用意志力請求她趕快說完,並對我的缺乏耐心感到羞愧。我寧可不要談這個特殊的題目。幸好我那重視運動的學校讓我得以分神。我向來喜愛跑步,也跑得很快;生命裡能比贏得八百公尺賽跑這種強烈快樂更好的事,似乎不多。高三的時候,我已經是田徑隊和足球隊的雙料隊長。
我在母親適應不良的同一所學校成了社交蝴蝶,在學校的舞會和週五晚上的足球比賽之間飛來飛去。我在青少年時期與母親最大的戰爭是服裝。一九八九那一年,我無比渴望一件腳踝有拉鍊、白色的Guess牛仔褲。她的反對從價錢太貴,到它是如何地不實用,然後直接攻擊我的個性:她的女兒怎會變成如此膚淺的人,一心只想要這麼浮華的東西?我生氣地瞪著她──在我的腦海裡,她早已永遠地凍結在那套一成不變的制服裡:肥胖的白色跑鞋、鬆垮的卡其褲、平價的馬球衫、披在肩上的圓領毛衣──祈求她拋開高高在上的態度,關心一下她的外表,即使只有一次也好。
我的愛情生活也同樣平淡無奇。高一時,我愛上了高二的B(他擅長的運動項目是棒球、曲棍球和足球)。他聰明、有趣、善良,我的父母乾脆把他當成家人。我們三年都在一起,直到我高中畢業。
前往緬因州就讀小小的文學院後,我又戀愛了,對象是W。大二時,朋友在學校的大餐廳介紹我們認識,握手時我突然感覺一股電流衝過手臂。我們認識之後不久,他跑到我的宿舍房間敲門。我開門時,他像隻蜂鳥般在門口飛來飛去。他跑來告訴我,月亮美得不得了,我一定得去看看。穿著睡衣的我立刻套上冬季大衣,跟著他跑了出去。
我們在一起的第一個夏天,空閒的時間就待在他波士頓家中後院、將要改裝的穀倉裡,油漆和寫作(他),閱讀和寫作(我),上床,在果園裡長時間散步,摘取明天要放在早餐穀片碗裡的黑莓。他母親擁有一小群老是全身泥污的山羊和一隻叫聲彷彿被綁在鐵軌上的女人、名叫迪克的孔雀。我原想取消那年秋天去愛爾蘭讀書的計畫,但我終究沒有取消,也還是經常見面;那年十月,我母親的癌症再度出現,我因她的第二次乳房切除手術飛回美國的時候,是他到機場接我並陪我度過。那年冬天重返校園時,我們已是幾乎分不開的一對。不過這是一九九○,不是一九六○。我因為所有非常明顯的理由(他好奇的頭腦、乾冷的幽默感和巨大的藍眼睛)而愛W。但,因為我們兩人都想成為藝術家,且快畢業了,摩擦開始在我們平常分享的親密感與發展自我所必須的自主性之間出現了。
或者,想要更有自主性的人是我;他對自己早就很有自信。而我需要走的路還很長。
畢業後,W和我分居兩岸──他去了家人在瑪莎葡萄園島上的夏季住屋,我則前往西岸奧勒岡州的波特蘭──我們努力經由電話、互訪和寫信(網路電話當時還不普遍)維持長距離的交往關係。我們也決定,當我們分居兩地的時候,各自可以認識其他人,只要不告訴對方。
我也跟家人保持密切的聯繫。我弟弟非常享受紐約的大學新鮮人生活。我的父母則工作、跟朋友相聚、處理紐伯利港的公眾事物;他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出門去拯救海濱,或辯論土地分區管理法。當時,母親第二個乳房的癌症也已爆發並割除,現在應該沒有任何事需要擔心了。她甚至還在前一年競選連任,這激怒了她的敵對陣營──他們發現,她的第一個任期完全不買他們的帳,也不去他們那些老好男孩所組成的、基礎深厚的王國朝拜──她竟然因此而接獲恐嚇信件。結果:她獲得了小鎮選舉史上最壓倒性的勝利。
來到波特蘭,我在令人堪慮的失敗街(Failing Street)一棟快要倒塌但住滿各種充滿抱負的藝術家的大屋裡,找到一個房間,為了付房租,我兼了四個工作:一星期三天在邦恩諾柏書店擔任活動企畫;四個早上在帶狀商業區一家日本外賣餐館掌管登記;四個晚上在一家墨西哥餐館端盤子;隨機的週末則前往一家很小的文學期刊兼差,工資是幾杯馬丁尼和文字編輯課程。
我在小學四年級就下定決心要把教室書架上的傳記全部讀完,那是兩排芥茉色的精裝厚書。有多位總統(我最喜歡長臉瘦削、雙眼深情的亞伯拉罕‧林肯),以及班哲明‧富蘭克林和貝蒂‧羅斯(雖然我不懂何以值得用一整本傳記來寫「縫製第一面美國國旗的人」)。這些傳主都有不可思議的成就,但這不是重點;吸引我的是閱讀一個跟我同樣是小孩的人如何長大成「重要人物」。我把他們聚集在一起,當成我擅自領養來的一票叔叔和阿姨──這些大人雖然不是我的父母,但他們為我開啟許多扇生命之門,若非遇上他們、憑我個人之力絕對無法想像的。如今,為了學習成為詩人,我開始閱讀最鍾愛的幾位詩人的傳記:伊莉莎白‧碧莎普 、羅伯‧羅威爾 、席薇亞‧普拉絲 和安妮‧薩克頓 。我的一些問題只有曾在這觀點特殊之行業悠遊過的行家才能回答。例如:詩人是天生或後天養成?怎樣才能讓一首詩被刊載?我能靠寫詩養活自己嗎?我要如何平衡從事創意工作所產生的壓力,以及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除了自我放逐而離鄉背井,四位詩人很巧合地都跟我一樣來自麻州東北部的小小角落,或許毫不重要,但我相信這事實仍給了我些許無意識的慰藉。
我當然不至於期待詩人的生活跟傳記裡那些總統的生活,同樣直截了當,但我居然找不到這些問題的解答,也很意外。
大學時代,我對席薇亞‧普拉絲和安妮‧薩克頓成年後的世界只有模糊的印象,只覺得她們似乎極為正常:兩人都結了婚,有小孩、有房子。當時周遭環境非常動盪,所以我很容易對東岸的生活產生特殊幻想:想像她們放鬆地坐在推剪得漂亮平整之寬闊草坪的孔雀型戶外躺椅上,整天的辛勤寫作雖然疲憊但很愉悅,一手拿著加了東尼水的冰涼琴酒,另一手鬆鬆地夾著一根香菸──即使我不抽菸也受不了琴酒,更不可能連續兩個小時毫無旁騖地寫詩。
但我二十三歲了,發現普拉絲結婚時跟我同齡,而薩克頓早在十九歲就已嫁為人婦,我的心跳差點停止。我愛W,但結婚是我腦袋裡最遠、最後的一件事。我的目標只專注於事業:弄清楚怎樣當個作家;經濟獨立。然後才是婚姻。
但這並不是說,如果有機會,我不會暈頭轉向地愛上一個「聲音有如上帝之雷鳴」的「歌手、說書人、獅子和浪跡世界的人」──這是普拉絲對泰德‧休斯 曾有的描述。我甚至也可能笨到跟他結婚。然而,三十歲之前就已生好兩個小孩(薩克頓是二十七歲),同時還要成為一個認真的詩人,以及全心奉獻的配偶,這可是我的理智必定會叫我避開的大災難──或者,這是我自以為是的說法,我那時還不知道,自己這麼有遠見,其實必須歸功於第二波女性運動。
如何找到五位精神導師,是個跟一連串虛構事物有關的真實故事──真實的慾望、外來的期待、莫名的渴望,和似是而非的半真相──它們構築了一個生命,並容許幻想和真實並存其中。當我準備下筆時,曾以為我會從第一位精神導師開始依序而下,卻發現是一個前奏導向了那主要事件,這前奏即是母親與我的一堆心願,故事亦由此開始。
母親有次告訴我,她小時候曾躺在床上召喚未來將要與她結婚的男人。那個片刻他在哪裡?在想什麼?長相如何?他們何時會相遇?她有時會溜進後院,抱住一棵樹,練習如何擁抱丈夫。
一九六八年二月,她與她的命運相遇了,那時她剛滿二十四歲,地點是賓州一處滑雪度假村。他們於排隊等待升降椅時偷偷地相互打量:有著一頭鬈髮的可愛傢伙,圍著錯誤的白色的圍巾(他在北卡羅萊納州長大,第一次滑雪);一位曲線玲瓏的棕髮女郎,身穿黃綠色滑雪裝(她來自新英格蘭,對滑雪坡瞭若指掌)。後來,回到度假村的主建築,他們喝著熱可可開始調情,發現兩人都住在華盛頓特區,她剛去賈柏公司上班,而他是陸軍情報官,正在學習中文。他向她要電話號碼。她說她在電話簿上。他喜歡她的狂妄。十一個月後,他們在紐伯利港鎮外的一座小教堂結婚──就我的觀點,這快得嚇人,但在當時很常見。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酷愛收集他們新婚頭幾年那些真的非常浪漫的故事,而且聽他們說了無數次,到最後從對話到服裝我都可以鉅細靡遺地重新描述。
然而,當我開始認真思考我的五位精神導師,我逐漸領悟,從人口統計學來說,我的父母在歷史上不尋常的時刻做了一連串非常尋常的決定──剛好提供了一個方便的例子,讓我瞭解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婚姻趨勢。
他們是珠聯璧合的一對:她帶來他所渴望的穩定感,同時也分享他的冒險;他樂於溝通又充滿愛心,是個與她那老是抽著雪茄的粗暴父親完全相反的人。他們婚後不久,他便奉派移防琉球,在亞洲特別行動部隊擔任必須用到中文的職位;他於一個多月之後打電報回家,這封電報後來被裱了框掛在紐伯特港家中的牆上,電文為:
爭取到宿舍委託書已寄
愛妳道格他們住在基地之外琉球人的社區,直到他被改派到越南。她搬回美國跟父母同住,並在紐伯利港擔任英文老師(埃德娜‧米萊小時候上過這所學校,如今已廢校)。父親後來告訴我,那是一段「刺激又暈頭轉向的時間。戰爭的趨勢,請假、休假,痛苦、焦慮。」
一九七一年七月,他完成了一年的服役期,他們回到華盛頓特區,讓他可以用退伍軍人獎學金進入法學院;她在特殊兒童委員會(一個專業的代言團體)找到工作。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出生;四年又一天後,我弟弟克禮斯多福出生;一九七七年,我們搬回紐伯利港,父親在市中心成立了個人的律師事務所,母親回學校教書。
每次看到這些數字,我都重新驚訝一次。一八九○,只有五十四%的家庭有一對已婚的夫妻。到一九五○,這個數字成長到六十五%。我父母結婚時,他們的同儕八十%為已婚夫妻。
受教育、離家、進入某行業、結婚、生小孩──直到不久前,這個因循守舊但能快速完成美國夢的過程,是如此理所當然。然而,一如貝蒂‧傅瑞丹 一九六三年的名著《覺醒與挑戰: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所揭露的,即使是當時,人行道已有了裂縫。一九六二年有項問卷調查說明了一件頗為特別的事,大多數的已婚女性聲稱她們是快樂的,但只有十%樂見女兒追隨她們的腳步。她們藉由這項調查小聲耳語:別急著結婚;多過一點自己的生活;去上大學。
事情果然這樣發生。一九七○年,已婚家庭比例驟降到六十一%。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九,離婚率倍增。
母親撫養我的時候,她們已不必再小聲耳語。一九六○年代末期,方興未艾的第二波女性運動到一九七○早期已迅速從大都市中心擴展到小城鎮。紐伯利港並非女性主義的溫床,但母親和她的姊妹淘成立了「婦女投票聯盟」的地方分會,一九八○年,她三十六歲時成為該分會的主席。「『假如』妳真的決定要生小孩,才生。」我相信當我可以思考這方面的事時,她會這麼說。
有一次她意外地向我吐露一件事,她說這輩子最快樂的時間是二十一歲的時候,那是認識我父親的前幾年,她開著金龜車馳過高速公路,想去哪裡都可以隨心所欲。「我有自己的車、自己的工作,想要的衣服全都有了,」她充滿渴望地回憶著。她若晚幾年出生,就可以多享受十年這樣無拘無束的快意生活。然而她並未這樣做,她把自己的野心擺到一邊,養大兩個小孩後才在三十多歲中期開始尋找自己喜歡的事,卻只發現她已落後許多。她和家人在一起時非常快樂,但同時也是焦慮的,這份緊張對於我的成長有著巨大影響。
青少年時,母親寫了一篇短文當成我高中畢業的禮物之一,起因是一位鄰居看見我走過街上。這位先生告訴她:「凱特頗有妳的風範,相同的窄肩挺得好直。」母親對這個比較感到很高興,並得出結論:即使她過世許久,她仍經由我而活著,活在我的行為舉止裡。我對她說我很喜歡那篇文章,內心其實揪成一團。真是這樣嗎?我注定要一輩子像她嗎?
妳若是女兒,母親的臉是妳的第一面鏡子,如果妳的五官像她──以我們的情況是榛眼棕髮、雀斑、嬌小的骨架和所謂「挺直的窄肩」──我敢打賭,妳會無意識地接收她對她自己的看法和態度。母親雖不至於認為自己不漂亮,但自認普通,於是我很自然地相信了她,認為自己並無特殊之處。
她常生動地描述她笨拙的青少年時期,我甚至可以隨時召喚那個膽怯的女孩──在我的腦海裡,她總是癱靠在一排寄物櫃旁(我們除了外型相似,也是校友),髮型鬆塌無趣,身穿過時又不合身的格子衣裙,總是可憐兮兮地獨來獨往。我跟這個雙胞胎似的魅影形影不離,即使我和她完全不一樣:我非常外向且是體育健將。大家最愛說的一個家庭故事就是:因為我母親的學科成績不佳,升學顧問居然建議她申請美容美髮學校。「我甚至不愛梳『自己』的頭髮!」我母親抱怨道。
這個笑話要強調的是,可見她多麼成功地從那個可悲又無可救藥的女孩脫胎換骨,成為眾所倚重且公認堅強的女人。她從十幾到二十幾歲,都對自己毫無信心和安全感──而後在三十四歲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向後轉:辭去中學英文教師的工作,即使沒有任何專業證書,仍說服《紐伯利港每日新聞報》雇用她擔任專題編輯。兩年後,她辭去全職的工作,重新打造自己成為特約記者,替全國性的雜誌和報社撰寫旅行故事。因為我父親自己開業,他可以在她奉命飛去希臘或德國採訪的時候,替代她處理家務。她三十九歲時(我十歲),發現胸部有腫瘤並割除了一邊的乳房。手術成功,這個疤痕促使她活得更加全然也更加勇敢。她在復原期間加倍投入於特約記者的工作,接下更具挑戰性的題目,報導重要的社會議題,並出版了幾本青少年歷史書。她真正的野心是出版小說;她利用稀少的空閒時間撰寫短篇小說,並參加了一個寫作團體。
一九九○,我高三那年,她出馬競選小鎮高中的學校董事。我有時會陪她到紐伯利港的大街小巷逐家敲門,分送競選傳單。每個人都說我們長得好像。她的競選照片相較於我所知的溫暖又慷慨的母親,更為強悍也更光鮮:短髮梳成略似頭巾的嚴肅髮型,雙眼因刷了睫毛膏而顯得更加炯炯有神,豐滿的嘴唇抿出充滿決心與毅力的線條。她把真正的自己保留在真正的生活裡;她贏了選戰之後並未獨抱勝利而是分享,她舉辦公開的聚會,鼓勵其他女性出來競選公職,並教她們如何達成目標。
雖然,我們心底深處都知道,癌症隨時可能復發。
我們是個愛說話,活著就要拚命說話的家庭,幾乎每件事都曾拿出來公開討論。當我還是個小小孩時,每天晚上,母親或父親會來替我蓋被子,我總是往被窩深處躺得更舒服後,唱歌似地說出我最愛的句子:「我們來談……」我們談剛才讀過的書,或晚餐之後的散步,或明天早餐要吃什麼。我說你聽,你說我聽;任何事都好。每件事都說,更好!我認為每一段親密關係,包括友誼,都是沿著類似的對話河流建立起來的。以我的想法,親密就是說話。
但我們如實正視這顆滴答響的定時炸彈,是在那年的情人節,那時我母親第一次知道她有復發的狀況。那是她主辦的活動,我們三個是她挑選的來賓。她把餐桌佈置得非常漂亮,在每個人的盤子放上精選的小禮物(我特別記得我的禮物是放在扁平塑膠水袋裡的兩條泰國鬥魚)在我們開始吃飯前,她說了一段很入世的禱告,說她如何感謝到現在還活著,可以從事她關心的工作,嫁給她愛的人,看著孩子長大。
我低頭看著放在腿上的手,用意志力請求她趕快說完,並對我的缺乏耐心感到羞愧。我寧可不要談這個特殊的題目。幸好我那重視運動的學校讓我得以分神。我向來喜愛跑步,也跑得很快;生命裡能比贏得八百公尺賽跑這種強烈快樂更好的事,似乎不多。高三的時候,我已經是田徑隊和足球隊的雙料隊長。
我在母親適應不良的同一所學校成了社交蝴蝶,在學校的舞會和週五晚上的足球比賽之間飛來飛去。我在青少年時期與母親最大的戰爭是服裝。一九八九那一年,我無比渴望一件腳踝有拉鍊、白色的Guess牛仔褲。她的反對從價錢太貴,到它是如何地不實用,然後直接攻擊我的個性:她的女兒怎會變成如此膚淺的人,一心只想要這麼浮華的東西?我生氣地瞪著她──在我的腦海裡,她早已永遠地凍結在那套一成不變的制服裡:肥胖的白色跑鞋、鬆垮的卡其褲、平價的馬球衫、披在肩上的圓領毛衣──祈求她拋開高高在上的態度,關心一下她的外表,即使只有一次也好。
我的愛情生活也同樣平淡無奇。高一時,我愛上了高二的B(他擅長的運動項目是棒球、曲棍球和足球)。他聰明、有趣、善良,我的父母乾脆把他當成家人。我們三年都在一起,直到我高中畢業。
前往緬因州就讀小小的文學院後,我又戀愛了,對象是W。大二時,朋友在學校的大餐廳介紹我們認識,握手時我突然感覺一股電流衝過手臂。我們認識之後不久,他跑到我的宿舍房間敲門。我開門時,他像隻蜂鳥般在門口飛來飛去。他跑來告訴我,月亮美得不得了,我一定得去看看。穿著睡衣的我立刻套上冬季大衣,跟著他跑了出去。
我們在一起的第一個夏天,空閒的時間就待在他波士頓家中後院、將要改裝的穀倉裡,油漆和寫作(他),閱讀和寫作(我),上床,在果園裡長時間散步,摘取明天要放在早餐穀片碗裡的黑莓。他母親擁有一小群老是全身泥污的山羊和一隻叫聲彷彿被綁在鐵軌上的女人、名叫迪克的孔雀。我原想取消那年秋天去愛爾蘭讀書的計畫,但我終究沒有取消,也還是經常見面;那年十月,我母親的癌症再度出現,我因她的第二次乳房切除手術飛回美國的時候,是他到機場接我並陪我度過。那年冬天重返校園時,我們已是幾乎分不開的一對。不過這是一九九○,不是一九六○。我因為所有非常明顯的理由(他好奇的頭腦、乾冷的幽默感和巨大的藍眼睛)而愛W。但,因為我們兩人都想成為藝術家,且快畢業了,摩擦開始在我們平常分享的親密感與發展自我所必須的自主性之間出現了。
或者,想要更有自主性的人是我;他對自己早就很有自信。而我需要走的路還很長。
畢業後,W和我分居兩岸──他去了家人在瑪莎葡萄園島上的夏季住屋,我則前往西岸奧勒岡州的波特蘭──我們努力經由電話、互訪和寫信(網路電話當時還不普遍)維持長距離的交往關係。我們也決定,當我們分居兩地的時候,各自可以認識其他人,只要不告訴對方。
我也跟家人保持密切的聯繫。我弟弟非常享受紐約的大學新鮮人生活。我的父母則工作、跟朋友相聚、處理紐伯利港的公眾事物;他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出門去拯救海濱,或辯論土地分區管理法。當時,母親第二個乳房的癌症也已爆發並割除,現在應該沒有任何事需要擔心了。她甚至還在前一年競選連任,這激怒了她的敵對陣營──他們發現,她的第一個任期完全不買他們的帳,也不去他們那些老好男孩所組成的、基礎深厚的王國朝拜──她竟然因此而接獲恐嚇信件。結果:她獲得了小鎮選舉史上最壓倒性的勝利。
來到波特蘭,我在令人堪慮的失敗街(Failing Street)一棟快要倒塌但住滿各種充滿抱負的藝術家的大屋裡,找到一個房間,為了付房租,我兼了四個工作:一星期三天在邦恩諾柏書店擔任活動企畫;四個早上在帶狀商業區一家日本外賣餐館掌管登記;四個晚上在一家墨西哥餐館端盤子;隨機的週末則前往一家很小的文學期刊兼差,工資是幾杯馬丁尼和文字編輯課程。
我在小學四年級就下定決心要把教室書架上的傳記全部讀完,那是兩排芥茉色的精裝厚書。有多位總統(我最喜歡長臉瘦削、雙眼深情的亞伯拉罕‧林肯),以及班哲明‧富蘭克林和貝蒂‧羅斯(雖然我不懂何以值得用一整本傳記來寫「縫製第一面美國國旗的人」)。這些傳主都有不可思議的成就,但這不是重點;吸引我的是閱讀一個跟我同樣是小孩的人如何長大成「重要人物」。我把他們聚集在一起,當成我擅自領養來的一票叔叔和阿姨──這些大人雖然不是我的父母,但他們為我開啟許多扇生命之門,若非遇上他們、憑我個人之力絕對無法想像的。如今,為了學習成為詩人,我開始閱讀最鍾愛的幾位詩人的傳記:伊莉莎白‧碧莎普 、羅伯‧羅威爾 、席薇亞‧普拉絲 和安妮‧薩克頓 。我的一些問題只有曾在這觀點特殊之行業悠遊過的行家才能回答。例如:詩人是天生或後天養成?怎樣才能讓一首詩被刊載?我能靠寫詩養活自己嗎?我要如何平衡從事創意工作所產生的壓力,以及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除了自我放逐而離鄉背井,四位詩人很巧合地都跟我一樣來自麻州東北部的小小角落,或許毫不重要,但我相信這事實仍給了我些許無意識的慰藉。
我當然不至於期待詩人的生活跟傳記裡那些總統的生活,同樣直截了當,但我居然找不到這些問題的解答,也很意外。
大學時代,我對席薇亞‧普拉絲和安妮‧薩克頓成年後的世界只有模糊的印象,只覺得她們似乎極為正常:兩人都結了婚,有小孩、有房子。當時周遭環境非常動盪,所以我很容易對東岸的生活產生特殊幻想:想像她們放鬆地坐在推剪得漂亮平整之寬闊草坪的孔雀型戶外躺椅上,整天的辛勤寫作雖然疲憊但很愉悅,一手拿著加了東尼水的冰涼琴酒,另一手鬆鬆地夾著一根香菸──即使我不抽菸也受不了琴酒,更不可能連續兩個小時毫無旁騖地寫詩。
但我二十三歲了,發現普拉絲結婚時跟我同齡,而薩克頓早在十九歲就已嫁為人婦,我的心跳差點停止。我愛W,但結婚是我腦袋裡最遠、最後的一件事。我的目標只專注於事業:弄清楚怎樣當個作家;經濟獨立。然後才是婚姻。
但這並不是說,如果有機會,我不會暈頭轉向地愛上一個「聲音有如上帝之雷鳴」的「歌手、說書人、獅子和浪跡世界的人」──這是普拉絲對泰德‧休斯 曾有的描述。我甚至也可能笨到跟他結婚。然而,三十歲之前就已生好兩個小孩(薩克頓是二十七歲),同時還要成為一個認真的詩人,以及全心奉獻的配偶,這可是我的理智必定會叫我避開的大災難──或者,這是我自以為是的說法,我那時還不知道,自己這麼有遠見,其實必須歸功於第二波女性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