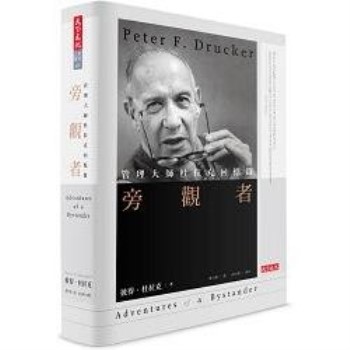真正的商人
亨利伯伯出身自德國小鎮一個小小的猶太社區。家中的兄弟姊妹很多,因為太過窮苦,家裡的孩子一長大,就得離家,亨利伯伯不到十五歲就離鄉背井到美國闖天下。
他用襯衫換來一輛單輪手推車,就這麼做起生意來了。十五年後,亨利伯伯在中西部小鎮開了家小百貨店。那可是該鎮的第一家。又過了十五年,亨利伯伯已飛黃騰達,原本的小百貨店已成了十二樓的建築。
如果有人問亨利伯伯的職業,他會說:「 我是個小販。」這可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最愛的,莫過於進行交易。不管到何處,他都會留心機會。
身為一個真正商人,他認為有責任以低於市價的價格銷售。
他說:「零售只有兩個原則:一是,只要便宜兩分錢就可使其他店家最忠誠的顧客動心;二是,不把東西上架,永遠都賣不出去。其他,就靠你的努力了。」
他也說過:「沒有不理性的顧客,只有懶惰的商人。如果顧客的行為不像你心中預期的,不可說『 他們失去了理性 』。不要試著去『 再教育』你的顧客,這並不是商人的工作。商人的工作就是使顧客滿意,使他們再度上門。若是你認為他們不理性,出去看看,用顧客的眼光來看街上的商品和貨品。最後,你一定會發現,消費者還是理性的,只不過商人看到的現實往往和顧客不同 。」
亨利伯伯曾是美國零售業的改革者。他是採取「包君滿意, 否則退款」策略的第一人。我問他:「如果顧客買了一件衣服,穿過且洗過之後才拿回來 要求退款,怎麼辦?」「當然退給她錢囉,不這樣她怎麼知道那件洋裝有沒有問題?」
一九五○年左右,他的孫子以非常好的價錢把他的伯恩翰百貨賣給一家大型百貨連鎖店。亨利伯伯雖年事已高,還是喜歡到市區走動,於是花了幾天拜訪那家大型百貨連鎖店人員,回家之後就宣布要把自己的股份賣掉。
他的孫子問他:「您看過他們的財務報表了嗎?」
「我聽了那家公司十幾個採購說的話。他們是很聰明,不過他們採買貨品不 是為顧客,而是為了公司。這是錯誤。這樣下來,他們會失去顧客、東西賣不好,也無法獲利。」
結果就在兩年內,易主經營的伯恩翰百貨果然顧客減少、業績日益下滑,轉盈為虧。有很多人的思考是跳躍式的,像蚱蜢一樣,一下子想到絲襪,然後又跳到鈕釦,從一個實驗想到另一個,卻從來沒有一個結論,也沒有什麼概念。但我從亨利伯伯身上學到一件事,那就是好的商人、傑出的藝術家或科學家,他們的思考方式都像起自某一個特定的、非常具體的東西,最後終於得到一個準則。
克雷斯達特是甘迺迪總統和國防部長麥納馬拉(McNamara)面前的紅人,曾任施樂百的總裁和最高執行主管。有一天,麥納馬拉麾下那批「英雄豪傑」中最厲害的一個,也呈報給國防委員會一份計畫書,建議採用截然不同的定價方案。大家都覺得相當不錯,只有克雷斯達特不以為然。
原來克雷斯達特反對這個計畫,因為其中太過複雜、太多假設,一大堆「 假使 」、「但是 」,以及「 當……的時候」。
以前是亨利伯伯和克雷斯達特的天下,之後換亨利伯伯的兒子艾爾文那樣的人獨領風騷,進入系統、原則和抽象概念的時代。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像亨利伯伯和克雷斯達特那樣的認知;我們已經過度依賴沒有經過試驗的定量分析、從假設而非從經驗去推論,並且從一個抽象概念跳到下一個抽象概念,離具體事物愈來愈遠。
那些只會追逐金錢的人,無法明瞭亨利伯伯的話,認為他的觀念很奇怪 — 若是一家公司的採購方針只為公司著想,而不是為了顧客,就不值得投值;在獲利的同時,還要有所貢獻,而不只是靠一點小聰明,以大賺其錢為樂。
亨利伯伯代表的文化正漸漸凋零。我們的社會還是繼續朝著認知與形上學前進。我們已經把「符號」看做是「真實:如金錢、買賣、交易、利率和國民生產 毛額等等。用中古世紀邏輯學家的話來說,整個社會的認知就是—符號取代了實質,實體成了影子 。
(本文摘錄自第10章弗利伯格的世界)
科技不可思議的力量
富勒和麥克魯漢這兩個人簡直是南轅北轍:不管是外表、風格、態度、講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意義都截然不同。富勒渾圓矮胖,說起話來像朗誦史詩;麥克魯漢高大而有稜有角,好用雙關語,經常妙語如珠。
但這兩個人同時在六○年代被奉為英雄,原因相同:他們是科技的吟遊詩人,也是狂熱的科技傳道人。早在成名之前,富勒和麥克魯漢就已和我往來。多年來,他們的聽眾寥寥無幾,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懷疑是否有人能聽見他們的聲音,更別提有人會追隨其後。他們是荒野上的先知 — 似乎離綠洲還有一段遙遠的路,至於他們的應許之地就更遙不可及了。
對富勒而言,經由科技之路,可通往真善美的境地。這樣的科技既龐大又複雜,可把人類環境進一步推向他所謂的「最大動力設計 」、「高能聚合幾何學 」和「無尺寸限制結構 」中的天體和諧。富勒是個超越論者,他的世界是泛神的,認為人愈能和宇宙科技合為一體,也愈接近自己的神性。
麥克魯漢則認為科技是一種人性,而非神性,科技是人的延伸。和達爾文共同研究出進化論的華利斯(Alfred Russel Wallace)曾說:「人單靠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有目的而非有機的進化 — 正因為人會製造工具。」麥克魯漢不知華利斯,但他的觀點和華利斯可謂不謀而合。
對麥克魯漢來說,科技是人自我改善,藉以延伸自己、改變自我、成長並有所轉變的方式。動物經由自然演化發展出一種新的、不同的器官,而成為另一種動物;人也是如此,藉由新的、不同的工具來延伸自己,成為不同的人。
在此之前,科技完全是技術人員的事:工程師建築水壩,人文學者則讀喬依斯、聽巴哈。不過,這些人文學者還是頗能享受科技成果— 如搭飛機或打電話,但其工作的意義、重要性或是過程都不被科技影響,若有影響,也只是一丁點兒,好比鋼筆的發明使他們不必費力去削鵝毛筆,有了燈泡,夜半讀書不會傷眼力。
以前,科技只是一種「技術活動」,到六○年代突然成為一種「人的活動」。人文學者以往總是指定科技非得乖乖待在歷史舞台的側翼不可,現在科技已慢慢走向前台,混在演員當中,甚至搶走主角的光彩。
驚覺這種轉變,人們一開始的反應總是猛烈抗拒。如果有挽回的餘地,一切就容易得多。然而在那一無所知的排拒之下,還是潛藏著一種接納新事物的能力,他們想尋求一種新的整合。因此,富勒和麥克魯漢在一夜之間成為受人矚目的人物。
這一代的人了解到科技必得和形上學、 文化、美學和人類學相結合,且是人類學和人類自我知識的核心。這兩位先知讓人得以一窺這種「新現實」;他們說的話有如神諭,然而這一切更增添他們的魅力。現在富勒已成了世界神話。他也是我所知道的人當中擁有最多名譽博士學位 的,足足有三十五個,或許沒有人需要這麼多的學位吧。
富勒的書本本暢銷,聽他演講的人總是把講堂擠得水泄不通,他是年輕人眼中的英雄人物。但是,當年我倆相識時,年近五十的他還籍籍無名。在將近二十年的光陰裡,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和發明廢寢忘食,家中經濟全靠他太太當祕書來支撐。富勒個性孤僻,友人屈指可數,他們看他明明可以輕而易舉的日進斗金,卻一心一意追求一些愚不可及的想法,不由得一肚子火。
他一逕悠遊在幾何設計的世界裡,富勒的朋友都認為他「 不切實際 」。 但富勒認為,「 不切實際」的是別人,絕不是他!
他還設計出「 最大動力學之屋 」— 一個在平面上的半圓體建築,使地板的面積達到最大、而表面積變成最小,這麼一來,冷、暖氣的需求便可降到最低。就結構而言,不需要任何支撐物,極為輕便。富勒不明白,為什麼人還是寧願居住在那從幾何學的觀點來看極不完美的長方形房屋,也不解為何一定要有平直的牆來擺設家具。
我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常常見到富勒。四○年代,我在本寧頓學院任教時,本寧頓的學生大概是他的第一批聽眾,多年來一直是他的忠實聽眾。富勒最需要的,不是名聲,也不是金錢,而是聽眾,而且愈多愈好。富勒第一次到本寧頓學院來演講時,擔任主持人的我向大家報告,富勒將做四十五分鐘的演說,然後回答問題。但四個小時後,富勒還滔滔不絕,我試著插嘴,他把我叫到旁邊,悄悄的說:「我的開場白還沒結束呢 。」到了凌晨一點,實在太晚了,因此我們不得不中止這場演講。
這實在是個錯誤,我們應該讓他繼續說下去的。自稱為幾何學家的富勒,其實是個先知!我和麥克魯漢相遇,跟認識富勒差不多是同時。那時的他,是密蘇里聖路易斯大學英文系講師,他貌不驚人,高高瘦瘦的。但不久這個相貌平平的英文講師開始有驚人之語。他說,十六世紀現代大學的興起不只改變了教學的方法、上課的模式,也改變了知識的本質,以及大學本來要傳授的東西。新的學習和文藝復興、古代典籍、古典作家的再發掘都沒有關係,和天文、幾何的發現,或是新科學也沒有關連。反之,知識史上的偉大事件是肇因於古騰堡(Gutenberg)的新科 技;創造現代世界觀的是活字印刷,不是佩脫拉克、 哥白尼,也不是哥倫布。
那已是幾十年前的往事,那時的麥克魯漢還沒有說出那句名言:「 媒介即訊息。」
那時我已開始對科技與社會以及科技與文化的關係發生興趣。例如,「裝配線」就是一種工具,但這工具對組織工作中的人和工作者之間的關係衝擊很大、對社會本身的理解亦然,是所謂「 工業社會」這種新觀念的基礎。
我是第一個使用「工業社會」這個名詞的人,但是當時對這個概念還不很清楚。後來,在那幾年的思考中,我慢慢明瞭裝配線不只是「 科技 」,更是有關 工作本質的一種非常理論、高度抽象的概念。
同時我也了解到,在這掌控一切、新的現實環境中,裝配線雖處處可見,而且成為一種象徵,然而在事實上卻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小環節;裝配線作業也只是生產力中最小的一部分。
換言之,科技有別於「人文學者」或「技術專家」的傳統觀點,科技為人類下定義,並影響人類對自己的看法,對人類所生產的事物也具有相當大的衝擊 。
(本文摘錄自第13章荒野上的先知)
要是用錯人,決策無異於一場空
這些通用的高階主管不管多麼超群絕倫,我在訪談中愈了解他們,愈清楚他們只是配角,真正的巨星是史隆。 這裡的大主管,還有許多經理人,無不流露出自信的神采、堅持己見,而且直言無諱,但一提起史隆,語調就為之一變,說到「史隆先生也同意這點」時,更是虔敬地有如引述聖經。
德雷斯達特提起的往事就相當典型。「那一天,我闖進主管會議,請求給凱迪拉克起死回生的機會,有個人說:『你了解吧?要是失敗,你在通用的職位就不保了?』我說:『是的,這點我很清楚。』史隆先生突然大聲說道:『德雷斯達特,你要是不能成功,你在凱迪拉克的工作當然就泡湯了,因為凱迪拉克已經完蛋。但只要通用還在,只要我當家,一定會保留工作給一個有責任感、主動、有勇氣和想像力的人。』他繼續說:『你現在擔心的是凱迪拉克的未來,我關心的則是你在通用的前途 。』」
頭一回見到史隆時,我覺得大失所望。他中等高度,長得又瘦又小,有著一張長長的馬臉,還戴著助聽器。據說紅髮的人個性剛烈,沒錯,他就是有名的不定時炸彈,他那破鑼嗓子有著濃厚的布魯克林口音。
但是,一和他接觸,就可發現他展露一種特別的氣質,令人望之凜然;他手下的團隊更是一群有活力、積極進取、可獨立作業的精英,對他無不肅然起敬。
他對我說:「 杜拉克先生,你或許已經聽說了。我不是提議讓你來通用進行研究的人,可是我的同事看法不同,因此,我得盡到自己的責任,確定你能勝任愉快。有什麼我可以幫得上忙的,歡迎隨時來找我。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必須確定你可以取得一切必要的資料。高階主管開會時,你可以進來旁聽,看看我們運作的程序以及公司的營運之道。還有,杜拉克先生,」他做個總結,「我不會告訴你該研究什麼,或是得提出何種建議。有件事我得讓你明白:本公司有三十五位風格迥異的副總,但彼此還是可以讓步、妥協的。你只要告訴我,你認為什麼是對的,而不要管『誰』才是對的。別擔心管理階層的成員,包括我自己,是不是能採納你的建議或同意你的研究結果。」
史隆和他手下的精英正打算為通用的未來翻開新頁。然而,我發現一點,他們多半把時間花在人事的討論,而非公司政策的研究。史隆雖然積極參與策略的討論,總把主導權交給主管會議裡的專家,但一談到人事的問題,掌握生殺大權的一定是他本人。
有一次,眾主管針對基層員工工作和職務分派的問題討論了好幾個小時。如果我記得沒錯,是一個零件小部門裡的技工師傅之職。走出會議室時,我問史隆:「您怎麼願意花四個小時來討論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職務呢?」他答道:「公司給我這麼優厚的待遇,就是要我做重大決策,而且不失誤。請你告訴我,有哪些決策比人的管理更為重要?我們這些在十四樓辦公的,有的可能真是聰明蓋世,但要是用錯人,決策無異於一場空。落實決策的,正是這些基層員工。至於花多少時間討論云云,那簡直是『屁話 』。杜拉克先生,我們公司有多少部門,您知道嗎?」在我得以回答 這個簡單的問題之前,他猛然抽出那本聞名遐邇的「黑色小記事本 」。
「 四十七個。那麼, 我們去年做了多少個有關人事的決策呢?」這就問倒我了 。
他看了一下手冊,跟我說:「 一百四十三個,每個部門平均三個。如果我們不用四小時好好地安插一個職位,找最合適的人來擔任,以後就得花幾百個小時的時間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你一定認為我是用人最好的裁判。聽我說,根本沒有這種人存在。只有能做好人事決策的人,和不能做好人事決策的人;前者是長時間換來的,後者則是事發後再來慢慢後悔。我們在這方面犯的錯誤確實較少,不是因為我們會判斷人的好壞,而是因為我們慎重其事。還有,」他強調說,「用人第一個定律就是那句老話:『別讓現任者指定繼承人,否則你得到的將只是次級的複製品。』」
「有關用人的決策,最為重要。每個人都認為一家公司自然會有『不錯的人選』,這簡直是『屁話』,重點是如何把人安插在最適當的位置,這麼一來,自然會有不凡的表現。」
(本文摘錄自第14章史隆的專業風采)
亨利伯伯出身自德國小鎮一個小小的猶太社區。家中的兄弟姊妹很多,因為太過窮苦,家裡的孩子一長大,就得離家,亨利伯伯不到十五歲就離鄉背井到美國闖天下。
他用襯衫換來一輛單輪手推車,就這麼做起生意來了。十五年後,亨利伯伯在中西部小鎮開了家小百貨店。那可是該鎮的第一家。又過了十五年,亨利伯伯已飛黃騰達,原本的小百貨店已成了十二樓的建築。
如果有人問亨利伯伯的職業,他會說:「 我是個小販。」這可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最愛的,莫過於進行交易。不管到何處,他都會留心機會。
身為一個真正商人,他認為有責任以低於市價的價格銷售。
他說:「零售只有兩個原則:一是,只要便宜兩分錢就可使其他店家最忠誠的顧客動心;二是,不把東西上架,永遠都賣不出去。其他,就靠你的努力了。」
他也說過:「沒有不理性的顧客,只有懶惰的商人。如果顧客的行為不像你心中預期的,不可說『 他們失去了理性 』。不要試著去『 再教育』你的顧客,這並不是商人的工作。商人的工作就是使顧客滿意,使他們再度上門。若是你認為他們不理性,出去看看,用顧客的眼光來看街上的商品和貨品。最後,你一定會發現,消費者還是理性的,只不過商人看到的現實往往和顧客不同 。」
亨利伯伯曾是美國零售業的改革者。他是採取「包君滿意, 否則退款」策略的第一人。我問他:「如果顧客買了一件衣服,穿過且洗過之後才拿回來 要求退款,怎麼辦?」「當然退給她錢囉,不這樣她怎麼知道那件洋裝有沒有問題?」
一九五○年左右,他的孫子以非常好的價錢把他的伯恩翰百貨賣給一家大型百貨連鎖店。亨利伯伯雖年事已高,還是喜歡到市區走動,於是花了幾天拜訪那家大型百貨連鎖店人員,回家之後就宣布要把自己的股份賣掉。
他的孫子問他:「您看過他們的財務報表了嗎?」
「我聽了那家公司十幾個採購說的話。他們是很聰明,不過他們採買貨品不 是為顧客,而是為了公司。這是錯誤。這樣下來,他們會失去顧客、東西賣不好,也無法獲利。」
結果就在兩年內,易主經營的伯恩翰百貨果然顧客減少、業績日益下滑,轉盈為虧。有很多人的思考是跳躍式的,像蚱蜢一樣,一下子想到絲襪,然後又跳到鈕釦,從一個實驗想到另一個,卻從來沒有一個結論,也沒有什麼概念。但我從亨利伯伯身上學到一件事,那就是好的商人、傑出的藝術家或科學家,他們的思考方式都像起自某一個特定的、非常具體的東西,最後終於得到一個準則。
克雷斯達特是甘迺迪總統和國防部長麥納馬拉(McNamara)面前的紅人,曾任施樂百的總裁和最高執行主管。有一天,麥納馬拉麾下那批「英雄豪傑」中最厲害的一個,也呈報給國防委員會一份計畫書,建議採用截然不同的定價方案。大家都覺得相當不錯,只有克雷斯達特不以為然。
原來克雷斯達特反對這個計畫,因為其中太過複雜、太多假設,一大堆「 假使 」、「但是 」,以及「 當……的時候」。
以前是亨利伯伯和克雷斯達特的天下,之後換亨利伯伯的兒子艾爾文那樣的人獨領風騷,進入系統、原則和抽象概念的時代。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像亨利伯伯和克雷斯達特那樣的認知;我們已經過度依賴沒有經過試驗的定量分析、從假設而非從經驗去推論,並且從一個抽象概念跳到下一個抽象概念,離具體事物愈來愈遠。
那些只會追逐金錢的人,無法明瞭亨利伯伯的話,認為他的觀念很奇怪 — 若是一家公司的採購方針只為公司著想,而不是為了顧客,就不值得投值;在獲利的同時,還要有所貢獻,而不只是靠一點小聰明,以大賺其錢為樂。
亨利伯伯代表的文化正漸漸凋零。我們的社會還是繼續朝著認知與形上學前進。我們已經把「符號」看做是「真實:如金錢、買賣、交易、利率和國民生產 毛額等等。用中古世紀邏輯學家的話來說,整個社會的認知就是—符號取代了實質,實體成了影子 。
(本文摘錄自第10章弗利伯格的世界)
科技不可思議的力量
富勒和麥克魯漢這兩個人簡直是南轅北轍:不管是外表、風格、態度、講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意義都截然不同。富勒渾圓矮胖,說起話來像朗誦史詩;麥克魯漢高大而有稜有角,好用雙關語,經常妙語如珠。
但這兩個人同時在六○年代被奉為英雄,原因相同:他們是科技的吟遊詩人,也是狂熱的科技傳道人。早在成名之前,富勒和麥克魯漢就已和我往來。多年來,他們的聽眾寥寥無幾,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懷疑是否有人能聽見他們的聲音,更別提有人會追隨其後。他們是荒野上的先知 — 似乎離綠洲還有一段遙遠的路,至於他們的應許之地就更遙不可及了。
對富勒而言,經由科技之路,可通往真善美的境地。這樣的科技既龐大又複雜,可把人類環境進一步推向他所謂的「最大動力設計 」、「高能聚合幾何學 」和「無尺寸限制結構 」中的天體和諧。富勒是個超越論者,他的世界是泛神的,認為人愈能和宇宙科技合為一體,也愈接近自己的神性。
麥克魯漢則認為科技是一種人性,而非神性,科技是人的延伸。和達爾文共同研究出進化論的華利斯(Alfred Russel Wallace)曾說:「人單靠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有目的而非有機的進化 — 正因為人會製造工具。」麥克魯漢不知華利斯,但他的觀點和華利斯可謂不謀而合。
對麥克魯漢來說,科技是人自我改善,藉以延伸自己、改變自我、成長並有所轉變的方式。動物經由自然演化發展出一種新的、不同的器官,而成為另一種動物;人也是如此,藉由新的、不同的工具來延伸自己,成為不同的人。
在此之前,科技完全是技術人員的事:工程師建築水壩,人文學者則讀喬依斯、聽巴哈。不過,這些人文學者還是頗能享受科技成果— 如搭飛機或打電話,但其工作的意義、重要性或是過程都不被科技影響,若有影響,也只是一丁點兒,好比鋼筆的發明使他們不必費力去削鵝毛筆,有了燈泡,夜半讀書不會傷眼力。
以前,科技只是一種「技術活動」,到六○年代突然成為一種「人的活動」。人文學者以往總是指定科技非得乖乖待在歷史舞台的側翼不可,現在科技已慢慢走向前台,混在演員當中,甚至搶走主角的光彩。
驚覺這種轉變,人們一開始的反應總是猛烈抗拒。如果有挽回的餘地,一切就容易得多。然而在那一無所知的排拒之下,還是潛藏著一種接納新事物的能力,他們想尋求一種新的整合。因此,富勒和麥克魯漢在一夜之間成為受人矚目的人物。
這一代的人了解到科技必得和形上學、 文化、美學和人類學相結合,且是人類學和人類自我知識的核心。這兩位先知讓人得以一窺這種「新現實」;他們說的話有如神諭,然而這一切更增添他們的魅力。現在富勒已成了世界神話。他也是我所知道的人當中擁有最多名譽博士學位 的,足足有三十五個,或許沒有人需要這麼多的學位吧。
富勒的書本本暢銷,聽他演講的人總是把講堂擠得水泄不通,他是年輕人眼中的英雄人物。但是,當年我倆相識時,年近五十的他還籍籍無名。在將近二十年的光陰裡,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和發明廢寢忘食,家中經濟全靠他太太當祕書來支撐。富勒個性孤僻,友人屈指可數,他們看他明明可以輕而易舉的日進斗金,卻一心一意追求一些愚不可及的想法,不由得一肚子火。
他一逕悠遊在幾何設計的世界裡,富勒的朋友都認為他「 不切實際 」。 但富勒認為,「 不切實際」的是別人,絕不是他!
他還設計出「 最大動力學之屋 」— 一個在平面上的半圓體建築,使地板的面積達到最大、而表面積變成最小,這麼一來,冷、暖氣的需求便可降到最低。就結構而言,不需要任何支撐物,極為輕便。富勒不明白,為什麼人還是寧願居住在那從幾何學的觀點來看極不完美的長方形房屋,也不解為何一定要有平直的牆來擺設家具。
我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常常見到富勒。四○年代,我在本寧頓學院任教時,本寧頓的學生大概是他的第一批聽眾,多年來一直是他的忠實聽眾。富勒最需要的,不是名聲,也不是金錢,而是聽眾,而且愈多愈好。富勒第一次到本寧頓學院來演講時,擔任主持人的我向大家報告,富勒將做四十五分鐘的演說,然後回答問題。但四個小時後,富勒還滔滔不絕,我試著插嘴,他把我叫到旁邊,悄悄的說:「我的開場白還沒結束呢 。」到了凌晨一點,實在太晚了,因此我們不得不中止這場演講。
這實在是個錯誤,我們應該讓他繼續說下去的。自稱為幾何學家的富勒,其實是個先知!我和麥克魯漢相遇,跟認識富勒差不多是同時。那時的他,是密蘇里聖路易斯大學英文系講師,他貌不驚人,高高瘦瘦的。但不久這個相貌平平的英文講師開始有驚人之語。他說,十六世紀現代大學的興起不只改變了教學的方法、上課的模式,也改變了知識的本質,以及大學本來要傳授的東西。新的學習和文藝復興、古代典籍、古典作家的再發掘都沒有關係,和天文、幾何的發現,或是新科學也沒有關連。反之,知識史上的偉大事件是肇因於古騰堡(Gutenberg)的新科 技;創造現代世界觀的是活字印刷,不是佩脫拉克、 哥白尼,也不是哥倫布。
那已是幾十年前的往事,那時的麥克魯漢還沒有說出那句名言:「 媒介即訊息。」
那時我已開始對科技與社會以及科技與文化的關係發生興趣。例如,「裝配線」就是一種工具,但這工具對組織工作中的人和工作者之間的關係衝擊很大、對社會本身的理解亦然,是所謂「 工業社會」這種新觀念的基礎。
我是第一個使用「工業社會」這個名詞的人,但是當時對這個概念還不很清楚。後來,在那幾年的思考中,我慢慢明瞭裝配線不只是「 科技 」,更是有關 工作本質的一種非常理論、高度抽象的概念。
同時我也了解到,在這掌控一切、新的現實環境中,裝配線雖處處可見,而且成為一種象徵,然而在事實上卻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小環節;裝配線作業也只是生產力中最小的一部分。
換言之,科技有別於「人文學者」或「技術專家」的傳統觀點,科技為人類下定義,並影響人類對自己的看法,對人類所生產的事物也具有相當大的衝擊 。
(本文摘錄自第13章荒野上的先知)
要是用錯人,決策無異於一場空
這些通用的高階主管不管多麼超群絕倫,我在訪談中愈了解他們,愈清楚他們只是配角,真正的巨星是史隆。 這裡的大主管,還有許多經理人,無不流露出自信的神采、堅持己見,而且直言無諱,但一提起史隆,語調就為之一變,說到「史隆先生也同意這點」時,更是虔敬地有如引述聖經。
德雷斯達特提起的往事就相當典型。「那一天,我闖進主管會議,請求給凱迪拉克起死回生的機會,有個人說:『你了解吧?要是失敗,你在通用的職位就不保了?』我說:『是的,這點我很清楚。』史隆先生突然大聲說道:『德雷斯達特,你要是不能成功,你在凱迪拉克的工作當然就泡湯了,因為凱迪拉克已經完蛋。但只要通用還在,只要我當家,一定會保留工作給一個有責任感、主動、有勇氣和想像力的人。』他繼續說:『你現在擔心的是凱迪拉克的未來,我關心的則是你在通用的前途 。』」
頭一回見到史隆時,我覺得大失所望。他中等高度,長得又瘦又小,有著一張長長的馬臉,還戴著助聽器。據說紅髮的人個性剛烈,沒錯,他就是有名的不定時炸彈,他那破鑼嗓子有著濃厚的布魯克林口音。
但是,一和他接觸,就可發現他展露一種特別的氣質,令人望之凜然;他手下的團隊更是一群有活力、積極進取、可獨立作業的精英,對他無不肅然起敬。
他對我說:「 杜拉克先生,你或許已經聽說了。我不是提議讓你來通用進行研究的人,可是我的同事看法不同,因此,我得盡到自己的責任,確定你能勝任愉快。有什麼我可以幫得上忙的,歡迎隨時來找我。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必須確定你可以取得一切必要的資料。高階主管開會時,你可以進來旁聽,看看我們運作的程序以及公司的營運之道。還有,杜拉克先生,」他做個總結,「我不會告訴你該研究什麼,或是得提出何種建議。有件事我得讓你明白:本公司有三十五位風格迥異的副總,但彼此還是可以讓步、妥協的。你只要告訴我,你認為什麼是對的,而不要管『誰』才是對的。別擔心管理階層的成員,包括我自己,是不是能採納你的建議或同意你的研究結果。」
史隆和他手下的精英正打算為通用的未來翻開新頁。然而,我發現一點,他們多半把時間花在人事的討論,而非公司政策的研究。史隆雖然積極參與策略的討論,總把主導權交給主管會議裡的專家,但一談到人事的問題,掌握生殺大權的一定是他本人。
有一次,眾主管針對基層員工工作和職務分派的問題討論了好幾個小時。如果我記得沒錯,是一個零件小部門裡的技工師傅之職。走出會議室時,我問史隆:「您怎麼願意花四個小時來討論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職務呢?」他答道:「公司給我這麼優厚的待遇,就是要我做重大決策,而且不失誤。請你告訴我,有哪些決策比人的管理更為重要?我們這些在十四樓辦公的,有的可能真是聰明蓋世,但要是用錯人,決策無異於一場空。落實決策的,正是這些基層員工。至於花多少時間討論云云,那簡直是『屁話 』。杜拉克先生,我們公司有多少部門,您知道嗎?」在我得以回答 這個簡單的問題之前,他猛然抽出那本聞名遐邇的「黑色小記事本 」。
「 四十七個。那麼, 我們去年做了多少個有關人事的決策呢?」這就問倒我了 。
他看了一下手冊,跟我說:「 一百四十三個,每個部門平均三個。如果我們不用四小時好好地安插一個職位,找最合適的人來擔任,以後就得花幾百個小時的時間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你一定認為我是用人最好的裁判。聽我說,根本沒有這種人存在。只有能做好人事決策的人,和不能做好人事決策的人;前者是長時間換來的,後者則是事發後再來慢慢後悔。我們在這方面犯的錯誤確實較少,不是因為我們會判斷人的好壞,而是因為我們慎重其事。還有,」他強調說,「用人第一個定律就是那句老話:『別讓現任者指定繼承人,否則你得到的將只是次級的複製品。』」
「有關用人的決策,最為重要。每個人都認為一家公司自然會有『不錯的人選』,這簡直是『屁話』,重點是如何把人安插在最適當的位置,這麼一來,自然會有不凡的表現。」
(本文摘錄自第14章史隆的專業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