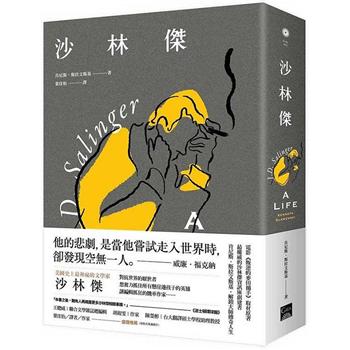五月八日星期二,迫切想躲開麻煩事的沙林傑,出發前往英國。他很清楚《麥田捕手》是他至今寫過的最佳作品,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自尊心,他無法忍受看到《麥田捕手》受到宣傳人員的蹧蹋,也不想看到評論家拆解這部作品。他原本的計畫是在書籍於美國出版時,花上好一段時間去英國進行小島漫遊之旅,並在《麥田捕手》於英國出版前結束旅程,同時希望當他回到紐約時,一切相關騷動都已逐漸平息。當他搭上「伊莉莎白女王號」前往英格蘭時,一定沒有意識到這只是他為了逃避人們檢視的第一步,而此後更是一趟無休無止的逃亡。
他在南安普頓下船後,立刻前往出版社辦公室。漢密爾頓把他當作得勝進入倫敦的耶穌般殷勤招待。他為他獻上伊莎.丹尼森(Isak Dinesen)的《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特別版,那也是霍爾頓.考菲爾德在《麥田捕手》中的愛書。另外還給了他《麥田捕手》的英國版。沙林傑真心喜歡這個版本的內斂封面:在一片紅色與白色的原野上,只極有品味地放上了書名及作者名字,而且沒有任何相片或作者生平細節。
漢密爾頓開始每晚帶沙林傑享受倫敦的夜生活,還帶他去西區看了相當不錯的戲劇演出。於是在這樣的場合中,沙林傑初次體驗到《麥田捕手》出版後可能產生的尷尬處境。漢密爾頓請沙林傑去看戲時,選了兩齣跟埃及艷后有關的戲,擔綱主演的是傳奇演員勞倫斯.奧立佛男爵(Sir Laurence Olivier)和他的妻子費雯.麗(Vivien Leigh)。漢密爾頓稱他們為「奧立佛夫妻」,兩人都是他的朋友,而他之所以選他們的戲,是為了讓沙林傑留下好印象。看完戲之後,奧立佛和費雯.麗邀請漢密爾頓一行人到他們位於切爾西的住處吃晚餐。儘管沙林傑覺得那是「奢華的一晚」,但也很不自在。畢竟在《麥田捕手》中,霍爾頓.考菲爾德表示看過奧立佛於一九四八年演出的電影《哈姆雷特》,並抱怨「我實在看不出勞倫斯.奧立佛有什麼了不起之處,他看起來實在太像個天殺的將軍了,不像那種會搞砸一切的傢伙」。換句話說,霍爾頓覺得奧立佛是個「虛偽的人」,而此時沙林傑卻得和他共桌晚餐,並在明知自己強烈批評過對方的壓力下,優雅地交談。他在這個晚上,愈來愈覺得自己也是個虛偽的傢伙。這件事即便在他回家後,也仍在心上縈繞不去。他於是寫了封長信給漢密爾頓(讀過小說的他應該避開這種場面才對),表示自己跟霍爾頓.考菲爾德的看法不同,也不認為他演戲不真誠,並要求漢密爾頓把他的心情及歉意轉達給奧立佛。漢密爾頓照做了,之後沙林傑還收到這位演員殷勤熱切的回信。
為了好好探索英國,沙林傑在倫敦買了台希爾曼牌的車。他沒有規劃任何行程,只是直接開車穿越英格蘭與蘇格蘭,還去了愛爾蘭跟蘇格蘭的赫布里底群島,沿途所見的一切都吸引著他。他當時寫的信跟明信片中,滿是熱情及孩子氣的喜悅。他曾將車停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的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前,內心掙扎著要去向這位偉大作家致敬,還是跟一名年輕女子去划船。結果終究還是女人勝出。到了牛津之後,他去基督教堂參加了星期日的晚禱,還發誓說在約克郡看到了勃朗特姊妹跑過沼澤地。都柏林非常讓他喜歡,但他真正愛上的是蘇格蘭,還曾表示要在那裡定居。
在英國待了七週之後,沙林傑終於還是忍不住期待看到書籍推出的渴望,決定為了趕上《麥田捕手》在美國的出版時間而回家。他先回倫敦,跟傑米.漢密爾頓再次見面,然後買了回紐約的頭等艙船票。七月五日,他在南安普頓搭上了「毛里塔尼亞號(Mauretania)」,七月十一日晚間抵達紐約,當時距他的小說出版還有五天。他不是獨自回來,那台希爾曼牌的車子也跟著回來了。
□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麥田捕手》在美國及加拿大出版。在〈致艾絲美——獻上愛與齷齪〉獲得成功之後,讀者對這部小說抱持高度期待,評論者之後針對小說提出的評價也比預期的好。這些因為《麥田捕手》而產生的深遠反響,顯示此書帶來的公眾效應不只超越了沙林傑的盼望,或許也遠大於他能應付的程度。
《時代》雜誌調皮地模仿了〈致艾絲美——獻上愛與齷齪〉的標題,針對《麥田捕手》寫了一篇名為〈獻上愛與正常視力〉(With Love & 20-20 Vision)的評論,讚美了小說的深度,還將沙林傑比作林格.拉德納(沙林傑對此感到頗為開心)。根據《時代》雜誌指出「《麥田捕手》送給讀者最驚喜的大禮,或許就是小說家沙林傑本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認為本書「非凡傑出」,《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讚譽本書「出色又引人入勝」,美國西岸的《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則將其認可為「等級甚高的文學作品」。最令沙林傑滿意的是《紐約客》即便一開始抱持保留態度,仍評論《麥田捕手》「傑出、有趣」,而且「意味深長」。
當然,還是有些評論不那麼青睞這部作品,但數量相對較少,而且通常只是在挑剔小說的語言及主角的習慣用語。有一些評論者因為霍爾頓不停使用「天殺的」而深感冒犯,也特別受不了他說「幹」。在一九五一年,任何小說用這種話咒罵人,都會令人感到震驚。因此,《天主世界》(The Catholic World)和《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果然認為這樣的語言「令人反感」又「粗俗」。《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反應則是認為這部小說「不停又不停地碎碎唸,像唸咒一樣……然後偶爾說些猥褻的話」。
《紐約時報》的詹姆斯.史特恩(James Stern)模仿霍爾頓.考菲爾德的語氣,在七月十五日刊出了一篇機智的文章,標題是〈啊,這世界就是個爛地方〉(Aw, the World’s a Crumby Place)。這篇文章以霍爾頓為敘事者,講述了一個名叫海爾嘉(Helga)的女孩在讀了〈致艾絲美——獻上愛與齷齪〉後,立刻興奮地讀完《麥田捕手》。儘管這篇文章看似在奚落沙林傑,甚至是嘲笑他的寫作風格,但海爾嘉仍在文章最後「把這部講『捕手』的書又讀了一遍」,作者還指出「這永遠是(小說)好看的徵兆」。
《麥田捕手》很快就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並持續了七個月,八月時還曾爬到第四名的位置。之所以那麼受歡迎,主要是因為每月選書俱樂部將《麥田捕手》選推的內容寄送給數以千計的家庭,讓本書的讀者群大幅增長,也確保了沙林傑在全國的知名度。
除了他痛恨的超大照片之外,每月選書俱樂部選推《麥田捕手》的版本中,還包含了一篇很長的作者側寫文章。沙林傑之所以願意接受採訪,是因為採訪他的人是《紐約客》的編輯威廉.麥克斯威爾,沙林傑信任這位朋友,也相信他會以最友善的觀點呈現自己的面貌。不過,就跟之前的訪談一樣,他盡可能不透露任何私人細節。
這篇側寫中提到了沙林傑的童年、服役經歷,還有他生涯中最精彩的部分——當然就是他為《紐約客》寫的那些故事,也詳細談論了他工作的專業態度。根據麥克斯威爾指出,沙林傑寫作時會「針對自己寫作主題的技術面向,投入無限的精力、耐心及各種考量,這一切都不可能在定稿中呈現出來。」還補充說,「這樣的作家死後會直接上天堂,作品也不會遭到遺忘。」文章結尾,麥克斯威爾還為了呈現沙林傑的謙遜,刻意引用了他說的一句話,指出寫作能帶來的「報償」實在「不多,但當有了報償,若是真有報償,都是非常美好的」。
最重要的是,麥克斯威爾的這篇訪談強調了沙林傑與紐約的連結,尤其是跟霍爾頓.考菲爾德在書中活動地點相關的部分。透過將沙林傑放進中央公園及其中的淺水湖等場景中,還有他離開寄宿學校後,在中央車站搭乘計程車回家的描寫,麥克斯威爾將焦點放在J.D.沙林傑和霍爾頓.考菲爾德之間的相似處。從宣傳的角度而言,這一招實在太棒了。不過,若作者希望說服讀者自己並不是書中的主角,麥克斯威爾的訪談稿則完全消滅了這種可能。在這篇介紹中,沙林傑本人被拿來跟霍爾頓進行了精密的對照,果然立刻引起讀者的強烈興趣,自然也想知道更多有關作者的細節。這麼一個在意隱私的作家,竟沒料到這種結果,實在令人費解。
麥克斯威爾的文章指出,沙林傑「目前在康乃狄克州的韋斯特波特租屋,為了獲得陪伴及消遣,養了隻名叫班尼的雪納瑞犬,而據他所說,班尼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取悅他,而且一直都是如此」。這項資訊的揭露,一定讓沙林傑非常緊張。韋斯特波特的人口並不多,沙林傑一定開始想像會有讀者跑來尋找一個蹓著雪納瑞犬的高瘦男子(而且他的五官特徵只要透過書衣照片就能知道)。於是,從英國回來的沙林傑,並沒有回到韋斯特波特。他是回到家鄉沒錯,卻還是在逃亡。
□
讀者通常能在《麥田捕手》中獲得足以改變一生的閱讀體驗,而這本書也改變了美國的文化走向,幫助之後的幾個世代定義出新的文化精神。打從故事的第一個句子開始,沙林傑就讓讀者看到了霍爾頓.考菲爾德眼中奇特又奔放的現實樣貌,讓這部美國文學史上最全面的意識流書寫,充滿他漫漶的思緒、感受及回憶。讀者從第一頁開始,就能清楚感受霍爾頓的敘事本質就是雜亂無章,比如開篇的第一個句子就有六十三個字,第一段也超過一整頁,根本就是公然蔑視既有的文學傳統,也立刻意識到自己即將展開一場獨特的閱讀之旅。
儘管有許多反傳統之處,《麥田捕手》卻是傳承了查爾斯.狄更斯的傳統,並透過馬克.吐恩與美國文化鎔鑄成一體。作為《塊肉餘生錄》及《頑童歷險記》的後繼者,《麥田捕手》持續透過青少年的角度去觀察人類,並使用完全忠實於敘事者處境及年齡的語言。這些在紐約街頭被重複說出的粗話之所以會受到部分評論者攻擊,是因為他們沒意識到藏在這些用語底下的幽微諷刺。
讀者也能在小說中感受到其他作家的影響,這似乎也呼應了沙林傑在一九四四年於巴黎時認定自己從海明威手上承接了文學傳統的想法。霍爾頓.考菲爾德的口氣其實就脫胎自海明威於一九二三年發表的故事〈我家老頭〉(My Old Man),而海明威本人也受到了恩師舍伍德.安德森的影響,尤其是他一九二○年的作品〈我想知道為什麼〉。因此就本質上,《麥田捕手》是將三個世代的傑出美國作家連結在一起。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沙林傑》)
他在南安普頓下船後,立刻前往出版社辦公室。漢密爾頓把他當作得勝進入倫敦的耶穌般殷勤招待。他為他獻上伊莎.丹尼森(Isak Dinesen)的《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特別版,那也是霍爾頓.考菲爾德在《麥田捕手》中的愛書。另外還給了他《麥田捕手》的英國版。沙林傑真心喜歡這個版本的內斂封面:在一片紅色與白色的原野上,只極有品味地放上了書名及作者名字,而且沒有任何相片或作者生平細節。
漢密爾頓開始每晚帶沙林傑享受倫敦的夜生活,還帶他去西區看了相當不錯的戲劇演出。於是在這樣的場合中,沙林傑初次體驗到《麥田捕手》出版後可能產生的尷尬處境。漢密爾頓請沙林傑去看戲時,選了兩齣跟埃及艷后有關的戲,擔綱主演的是傳奇演員勞倫斯.奧立佛男爵(Sir Laurence Olivier)和他的妻子費雯.麗(Vivien Leigh)。漢密爾頓稱他們為「奧立佛夫妻」,兩人都是他的朋友,而他之所以選他們的戲,是為了讓沙林傑留下好印象。看完戲之後,奧立佛和費雯.麗邀請漢密爾頓一行人到他們位於切爾西的住處吃晚餐。儘管沙林傑覺得那是「奢華的一晚」,但也很不自在。畢竟在《麥田捕手》中,霍爾頓.考菲爾德表示看過奧立佛於一九四八年演出的電影《哈姆雷特》,並抱怨「我實在看不出勞倫斯.奧立佛有什麼了不起之處,他看起來實在太像個天殺的將軍了,不像那種會搞砸一切的傢伙」。換句話說,霍爾頓覺得奧立佛是個「虛偽的人」,而此時沙林傑卻得和他共桌晚餐,並在明知自己強烈批評過對方的壓力下,優雅地交談。他在這個晚上,愈來愈覺得自己也是個虛偽的傢伙。這件事即便在他回家後,也仍在心上縈繞不去。他於是寫了封長信給漢密爾頓(讀過小說的他應該避開這種場面才對),表示自己跟霍爾頓.考菲爾德的看法不同,也不認為他演戲不真誠,並要求漢密爾頓把他的心情及歉意轉達給奧立佛。漢密爾頓照做了,之後沙林傑還收到這位演員殷勤熱切的回信。
為了好好探索英國,沙林傑在倫敦買了台希爾曼牌的車。他沒有規劃任何行程,只是直接開車穿越英格蘭與蘇格蘭,還去了愛爾蘭跟蘇格蘭的赫布里底群島,沿途所見的一切都吸引著他。他當時寫的信跟明信片中,滿是熱情及孩子氣的喜悅。他曾將車停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的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前,內心掙扎著要去向這位偉大作家致敬,還是跟一名年輕女子去划船。結果終究還是女人勝出。到了牛津之後,他去基督教堂參加了星期日的晚禱,還發誓說在約克郡看到了勃朗特姊妹跑過沼澤地。都柏林非常讓他喜歡,但他真正愛上的是蘇格蘭,還曾表示要在那裡定居。
在英國待了七週之後,沙林傑終於還是忍不住期待看到書籍推出的渴望,決定為了趕上《麥田捕手》在美國的出版時間而回家。他先回倫敦,跟傑米.漢密爾頓再次見面,然後買了回紐約的頭等艙船票。七月五日,他在南安普頓搭上了「毛里塔尼亞號(Mauretania)」,七月十一日晚間抵達紐約,當時距他的小說出版還有五天。他不是獨自回來,那台希爾曼牌的車子也跟著回來了。
□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麥田捕手》在美國及加拿大出版。在〈致艾絲美——獻上愛與齷齪〉獲得成功之後,讀者對這部小說抱持高度期待,評論者之後針對小說提出的評價也比預期的好。這些因為《麥田捕手》而產生的深遠反響,顯示此書帶來的公眾效應不只超越了沙林傑的盼望,或許也遠大於他能應付的程度。
《時代》雜誌調皮地模仿了〈致艾絲美——獻上愛與齷齪〉的標題,針對《麥田捕手》寫了一篇名為〈獻上愛與正常視力〉(With Love & 20-20 Vision)的評論,讚美了小說的深度,還將沙林傑比作林格.拉德納(沙林傑對此感到頗為開心)。根據《時代》雜誌指出「《麥田捕手》送給讀者最驚喜的大禮,或許就是小說家沙林傑本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認為本書「非凡傑出」,《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讚譽本書「出色又引人入勝」,美國西岸的《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則將其認可為「等級甚高的文學作品」。最令沙林傑滿意的是《紐約客》即便一開始抱持保留態度,仍評論《麥田捕手》「傑出、有趣」,而且「意味深長」。
當然,還是有些評論不那麼青睞這部作品,但數量相對較少,而且通常只是在挑剔小說的語言及主角的習慣用語。有一些評論者因為霍爾頓不停使用「天殺的」而深感冒犯,也特別受不了他說「幹」。在一九五一年,任何小說用這種話咒罵人,都會令人感到震驚。因此,《天主世界》(The Catholic World)和《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果然認為這樣的語言「令人反感」又「粗俗」。《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反應則是認為這部小說「不停又不停地碎碎唸,像唸咒一樣……然後偶爾說些猥褻的話」。
《紐約時報》的詹姆斯.史特恩(James Stern)模仿霍爾頓.考菲爾德的語氣,在七月十五日刊出了一篇機智的文章,標題是〈啊,這世界就是個爛地方〉(Aw, the World’s a Crumby Place)。這篇文章以霍爾頓為敘事者,講述了一個名叫海爾嘉(Helga)的女孩在讀了〈致艾絲美——獻上愛與齷齪〉後,立刻興奮地讀完《麥田捕手》。儘管這篇文章看似在奚落沙林傑,甚至是嘲笑他的寫作風格,但海爾嘉仍在文章最後「把這部講『捕手』的書又讀了一遍」,作者還指出「這永遠是(小說)好看的徵兆」。
《麥田捕手》很快就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並持續了七個月,八月時還曾爬到第四名的位置。之所以那麼受歡迎,主要是因為每月選書俱樂部將《麥田捕手》選推的內容寄送給數以千計的家庭,讓本書的讀者群大幅增長,也確保了沙林傑在全國的知名度。
除了他痛恨的超大照片之外,每月選書俱樂部選推《麥田捕手》的版本中,還包含了一篇很長的作者側寫文章。沙林傑之所以願意接受採訪,是因為採訪他的人是《紐約客》的編輯威廉.麥克斯威爾,沙林傑信任這位朋友,也相信他會以最友善的觀點呈現自己的面貌。不過,就跟之前的訪談一樣,他盡可能不透露任何私人細節。
這篇側寫中提到了沙林傑的童年、服役經歷,還有他生涯中最精彩的部分——當然就是他為《紐約客》寫的那些故事,也詳細談論了他工作的專業態度。根據麥克斯威爾指出,沙林傑寫作時會「針對自己寫作主題的技術面向,投入無限的精力、耐心及各種考量,這一切都不可能在定稿中呈現出來。」還補充說,「這樣的作家死後會直接上天堂,作品也不會遭到遺忘。」文章結尾,麥克斯威爾還為了呈現沙林傑的謙遜,刻意引用了他說的一句話,指出寫作能帶來的「報償」實在「不多,但當有了報償,若是真有報償,都是非常美好的」。
最重要的是,麥克斯威爾的這篇訪談強調了沙林傑與紐約的連結,尤其是跟霍爾頓.考菲爾德在書中活動地點相關的部分。透過將沙林傑放進中央公園及其中的淺水湖等場景中,還有他離開寄宿學校後,在中央車站搭乘計程車回家的描寫,麥克斯威爾將焦點放在J.D.沙林傑和霍爾頓.考菲爾德之間的相似處。從宣傳的角度而言,這一招實在太棒了。不過,若作者希望說服讀者自己並不是書中的主角,麥克斯威爾的訪談稿則完全消滅了這種可能。在這篇介紹中,沙林傑本人被拿來跟霍爾頓進行了精密的對照,果然立刻引起讀者的強烈興趣,自然也想知道更多有關作者的細節。這麼一個在意隱私的作家,竟沒料到這種結果,實在令人費解。
麥克斯威爾的文章指出,沙林傑「目前在康乃狄克州的韋斯特波特租屋,為了獲得陪伴及消遣,養了隻名叫班尼的雪納瑞犬,而據他所說,班尼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取悅他,而且一直都是如此」。這項資訊的揭露,一定讓沙林傑非常緊張。韋斯特波特的人口並不多,沙林傑一定開始想像會有讀者跑來尋找一個蹓著雪納瑞犬的高瘦男子(而且他的五官特徵只要透過書衣照片就能知道)。於是,從英國回來的沙林傑,並沒有回到韋斯特波特。他是回到家鄉沒錯,卻還是在逃亡。
□
讀者通常能在《麥田捕手》中獲得足以改變一生的閱讀體驗,而這本書也改變了美國的文化走向,幫助之後的幾個世代定義出新的文化精神。打從故事的第一個句子開始,沙林傑就讓讀者看到了霍爾頓.考菲爾德眼中奇特又奔放的現實樣貌,讓這部美國文學史上最全面的意識流書寫,充滿他漫漶的思緒、感受及回憶。讀者從第一頁開始,就能清楚感受霍爾頓的敘事本質就是雜亂無章,比如開篇的第一個句子就有六十三個字,第一段也超過一整頁,根本就是公然蔑視既有的文學傳統,也立刻意識到自己即將展開一場獨特的閱讀之旅。
儘管有許多反傳統之處,《麥田捕手》卻是傳承了查爾斯.狄更斯的傳統,並透過馬克.吐恩與美國文化鎔鑄成一體。作為《塊肉餘生錄》及《頑童歷險記》的後繼者,《麥田捕手》持續透過青少年的角度去觀察人類,並使用完全忠實於敘事者處境及年齡的語言。這些在紐約街頭被重複說出的粗話之所以會受到部分評論者攻擊,是因為他們沒意識到藏在這些用語底下的幽微諷刺。
讀者也能在小說中感受到其他作家的影響,這似乎也呼應了沙林傑在一九四四年於巴黎時認定自己從海明威手上承接了文學傳統的想法。霍爾頓.考菲爾德的口氣其實就脫胎自海明威於一九二三年發表的故事〈我家老頭〉(My Old Man),而海明威本人也受到了恩師舍伍德.安德森的影響,尤其是他一九二○年的作品〈我想知道為什麼〉。因此就本質上,《麥田捕手》是將三個世代的傑出美國作家連結在一起。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沙林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