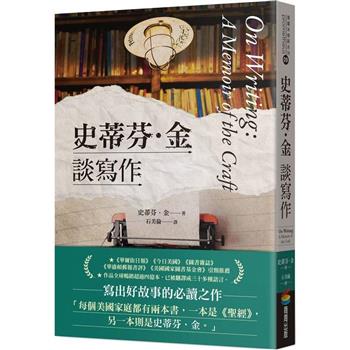我們後來舉家搬到康乃狄克州的史翠福(Stratford)。二年級時,我愛上了住
我家隔壁的美少女,雖然大白天裡她從來沒有正眼瞧過我,但到了晚上,當我躺在床上漸漸沉入夢鄉時,我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逃離白天那個冷漠的真實世界。和藹可親的泰勒女士是我的新老師,她有一頭像極了科學怪人的新娘(Bride of Frankenstein)艾爾莎.藍徹斯特般的灰頭髮和一雙金魚眼,我媽就說過:「每次和她說話時都想把手放在她的眼睛下面,以免她的眼珠子掉下來。」
我們位於三樓的公寓在西大街上,往山下隔一條街,距離泰迪市場不遠處,在布瑞德建築材料行的對面有一大片荒煙蔓草的空地,遠方角落是廢物棄置場,火車鐵軌則從中穿越。這個場景時常浮現在我腦海,也曾多次以不同的名字出現在我不同的作品中。附近的孩子們稱這裡是「貧瘠之地」,而我和我哥則稱這裡為「綠色叢林」。大衛和我在剛搬去不久,便把這裡探究了一番。那是個盛夏,天氣燠熱,感覺很棒,正當我們深入這個酷斃了的綠色神祕的新遊樂場,我卻因為內急不得不找地方解決。
我跟我哥說:「大衛,帶我回家!我需要解放一下(I have to push)!」(這是我們為了這種情況訂的說法。)
大衛對我的話置若罔聞,他說:「就在樹林裡解決吧!」從綠色叢林回我家,大概需要走至少半個小時,我哥才不想因為他那要上廁所的弟弟,而浪費了這寶貴的時光。
「我不行啦!這裡沒有東西可以擦屁股啊!」我有點被我哥的建議嚇到。
「你當然可以啦,就找一些葉子把屁股擦乾淨。牛仔和印地安人都是用這方法。」
一方面,那時候就算跑回家也大概來不及了,我覺得我根本無計可施;另一方
面,我也被牛仔之說迷了心竅。所以我假裝自己是英勇的荷普龍‧卡西迪,荷槍蹲在草叢裡,以免在這私人時刻突然被攻擊。上完之後,我照我哥吩咐的方法,找了一把綠葉小心地把屁股擦乾淨。沒想到這些鮮綠色植物竟然是有毒的常春藤。
兩天後,我從膝蓋後方到肩膀都布滿了一大片紅疹。我的「雞雞」縮得好小,
睪丸卻腫得跟號誌燈一樣大,感覺上好像從屁股一直癢到胸肋骨去。但最慘的是我抓葉子的手,腫得就像米老鼠被唐老鴨用榔頭槌腫了的手一樣,巨大的水泡散布在手指搓揉的地方。在水泡破了之後,留下一塊塊粉紅色的新肉。有六個星期的時間,我一面泡在微溫的藥水澡裡,覺得自己既悲慘又丟臉;同時聽到從門外傳來,我媽和我哥在聽彼得.崔普(Peter Tripp,美國五○年代著名廣播節目主持人)廣播裡的倒數讀秒,以及玩瘋狂八點紙牌遊戲(Crazy Eights)時的笑聲。
說實話,大衛是個很棒的兄弟,但對一個十歲的小孩而言,他顯然聰明過了頭。他的鬼主意常讓他惹上麻煩,後來他不知何時學會(也許是在毒常春藤事件之後),在麻煩來臨前把他那小史蒂芬弟弟一起拖下水來分擔風險。大衛從來沒有要我為他那些通常是聰明至極的鬼把戲承擔「所有」責任——他既不是偷偷幹壞勾當的卑鄙之人,也不是個懦夫——不過好幾次事件裡,我卻得和他分擔責任。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在那次大衛築堤擋住流經叢林的水流,造成西大街大部分低窪地區淹水時,我們兩兄弟都會惹上了麻煩;也是因為被他拖下水,害我倆都在他那有致命危險的學校科學計畫裡差點送命。
好像是一九五八年,我在中央文法學校上課,大衛則在史翠福中學念書。我媽在史翠福洗衣店工作,她是部門裡唯一的白人員工。當時她忙著把被單丟進軋布機時,大衛正計畫著他科學展的實驗。我哥可不是那種在紙上畫畫青蛙解剖圖,或用塑膠磚及上色的衛生紙筒拼拼湊湊蓋「未來之屋」就滿足的人;大衛的目標是得獎。他那年的計畫是「超級愚人大衛電子磁鐵」。大衛對於可以拿來唬人和用他自己名字來命名的事物有極大的狂熱。他後面這項嗜好稍後還促成了《大衛八卦報》(Dave’s Rag) 的產生,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好好談談。
我第一個真正原創的小說靈感——我想人總是會對此心知肚明——是發生在艾克(Ike,譯按:艾森豪總統的暱稱)溫和的八年主政接近尾聲時。我坐在我們位於緬因州德漢鎮家中的廚房餐桌,望著我媽把一張張綠印花貼在印花簿中(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關綠印花郵票多采多姿的故事,可以閱讀《大說謊家俱樂部》一書)。為了讓我媽可以就近照顧她那年邁的雙親,我們金氏三人搬回了緬因州。外婆那時已八十高齡,人胖又有高血壓,眼睛幾乎全盲;外公高壽八十二,骨瘦如柴人又陰陰沉沉的,偶爾會像唐老鴨般脾氣暴躁,只有我媽能應付他。我媽常叫外公「磨人精」。
是我媽的姊妹幫她找了這個工作的,這也許是她們一石二鳥的妙計,一來外公
外婆可以在女兒的照顧下享受天倫之樂,二來也可解決我那嘮叨老媽的問題,她從此可以不用再漂泊不定。之前為了養大她的兩個男孩,我媽漫無目的地從印地安那州流浪到威斯康辛州,再到康乃狄克州,不是一早五點到麵包店烤餅乾,就是在夏天溫度高達一百一十度的洗衣店裡燙衣服。因為那裡溫度實在太高,每逢七月到九月下午一點和三點,洗衣店領班都會拿鹽做成的小丸子給大家吃,以免因大量的汗水流失體內過多的鹽分。
我猜,我媽很不喜歡她的新工作,託她眾姊妹的幫忙,我那自給自足、好笑又有點瘋狂的老媽變成了身邊只有少少現金的小佃農。阿姨們每個月寄來的錢剛好支付日常雜物開銷,所剩不多。她們還會寄來一箱箱的衣服給我們。每到夏末,克拉姨丈和艾拉阿姨(我猜,他們不是我們真正的親戚)會為我們帶來好幾箱的罐裝蔬菜和果醬。我們住的房子是艾瑟琳阿姨和歐瑞姨丈的。我媽一住到這來,就再也跑不掉了。在外公外婆過世後,我媽找了另一份真正的工作。當她最後離開德漢鎮時——我哥和大嫂琳達在她生病辭世前的幾個星期照顧著她——我想她那時早已迫不及待地要離開那個鬼地方了。
讓我們先把一件事情說清楚,這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靈感,沒有所謂的「故事
製造中心」,也沒有「暢銷作家的埋骨之島」;好故事的靈感真的就像是不知從哪冒出來似的,從本來空無一物的空中出現並向你飄過來:兩個原先沒有關連的念頭相遇,就在太陽下創造了新鮮事。你的任務不是去尋找靈感,而是當靈感湧現時,能及時辨識出它們。
當這個特別的靈感—我第一個真正好的靈感—出現的那一天,我媽說她還需要六本印花簿,才能兌換檯燈作為給她姊妹莫莉的耶誕禮物,但她想時間上大概是趕不及了。「我想可能要把檯燈當成她的生日禮物了,」我媽說,「這些討厭的印花看起來總是比實際貼上去的多很多。」我媽對我扮了個鬥雞眼,還吐了吐舌頭。她那樣做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舌頭上都是綠印花的顏色。我心想如果可以在地下室自己製造這些該死的印花該有多好,就這樣靈光一閃,〈快樂印花〉的故事誕生了。偽造綠印花的想法,和看到我媽被染成綠色的舌頭的影像結合在一起,忽然就激發了我的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