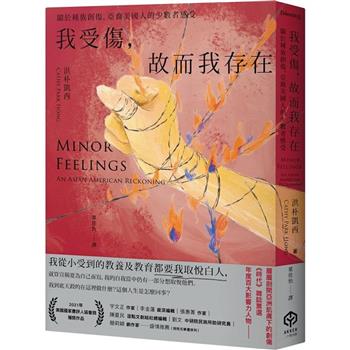一致(節錄)
我的憂鬱症是由一種想像出來的抽搐揭開序幕。
我會連續一小時瞪著鏡子,等待我的眼皮開始抽動或嘴角開始震顫。
「你有看到我在抽搐嗎?」我問我丈夫。
「沒有。」
「這下有看到我在抽搐了吧?」我問我丈夫。
「沒有。」
「這下有看到我在抽搐了吧?」我問我丈夫。
「沒有!」
在大概二十多歲的時候,我的右眼皮是真的有抽搐問題,這個問題後來還蔓延到臉部右側肌肉,導致我的眼睛有時會被擠壓成卡通人物「卜派」的瞇眼模樣。我發現我得了一種罕見的神經肌肉病症,正式名稱是半邊顏面神經痙攣,原因是我耳朵後方的兩條腦神經交纏在一起。二○○四年,當時的我二十六歲,匹茲堡有位醫生靠著置入一小塊海綿分開了那兩條交纏的神經,我的痙攣問題才終於獲得解決。
而在七年後的現在,我開始覺得痙攣問題又回來了——那塊海綿不知為何滑動開來,導致那兩條神經再次打結。我的臉不再是我的臉,而是由顫抖的神經組成且隨時可能叛逃的一張面具。我這台機器出現故障。隨時可能有條神經在不對的時候受到激發,然後開始像不停扭動著亂噴的水管一樣痙攣起來。我一天到晚想著我的臉,想到幾乎可以感覺到自己的神經,而我的神經也似乎隨時都會失控。臉是一個人最赤裸的部位,可是我們總要到受傷後才會意識到這件事,之後滿腦子想的也只有這張臉赤裸展現出的問題。
我總是覺得無法自在的毛病又出現了。我總在公共場合想盡辦法隱藏住我的臉,比如總是用手撐住臉頰,就彷彿我老是不開心,又或者是靜靜地轉頭遙望他處,那樣子就像是在沉思一個問題,但其實我滿腦子只想著:我那容易失控的神經隨時可能讓我的臉抽搐起來。
但其實我的臉根本沒在抽搐。
真正威脅要叛逃的其實是我的心智。我開始變得多疑又容易妄想。我想要有人拿工具把我的頭轉下來,然後裝上另一個沒那麼多神經問題的頭。
「怎麼會有這麼糟糕的想法啊。」我丈夫對我的想法表達不滿。
為了讓自己睡著,我開始攝取威士忌,然後是威士忌搭配安眠藥安必恩,然後是威士忌搭配安必恩、焦慮藥贊安諾和大麻,可是這些都無法幫助我入睡。我只要無法入睡就無法好好思考,只要無法好好思考就無法寫作、社交或跟別人進行對話。我再次成為一個孩子,一個無法說英文的孩子。
我住在一間漂亮且租金穩定的公寓,位於下百老匯區一條狹窄而不起眼的小路上。此區以牛仔褲零售小店聞名,而且這些小店會一起播放Hot 97廣播電台的熱門金曲。我終於過著我想要的紐約生活,不但新婚,而且剛寫完一本書,總之沒有陷入憂鬱症的理由。可是每次只要我感到開心,一種可怕慘劇即將降臨的感受就會隨之而來,所以我會刻意讓自己感覺很糟,希望透過這種先發制人的手段來阻止慘劇真正到來。這樣的焦慮非常消耗我,也導致我陷入深深的憂鬱。有個朋友說,她每次陷入憂鬱時都感覺自己像一隻「從樹上掉下來的樹懶」。這個描述實在精準。在必須出門與外界互動之前,我總是感覺沒勁、身心俱疲,互動結束後又覺得自己被消耗得體無完膚。
我決定找心理治療師來治療我的憂鬱問題。我想找的是韓裔美籍的治療師,因為這樣才不需要花太多時間解釋我的處境。我希望她能只看我一眼就明白我的過去。在安泰保險公司列出提供心理健康照護的數百位紐約治療師中,我找到這樣一位有著韓國姓氏的治療師。我留了訊息給她,她回電給我,我們於是約好了諮商的日期及時間。
在她採光不佳的狹小候診室中掛了一幅裱框的海報,那是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的畫,畫中有個跪地的女人抱著一個裝滿馬蹄蓮的巨大籃子,整個空間也都是用里維拉那種讓人鎮定的色調來進行裝潢:裝著香蒲的棕色花瓶、焦糖色的皮製扶手椅,還有一條顏色像是垂死珊瑚的粉橘色地毯。
治療師打開門。我第一個注意到的是她的臉部尺寸。這位治療師有一張很大的臉。我不知道這是否會對她造成問題,因為韓國女人總是非常在意自己的臉部尺寸,甚至會為此去削下巴骨(在韓國有種常見的稱讚方式:「你的臉小得跟拳頭一樣大!」)。
我走進她的辦公室,在沙發上坐下。她說她會先問一些諮商時必須問的通用性問題。那些問題確實是讓所有人通用的問題:我有在腦中聽見別人說話嗎?有自殺的念頭嗎?這些通用問題讓我獲得很大的慰藉,因為代表我的憂鬱不是我的問題,而不過是很多人都有的典型病症。我用非常消沉的態度回答她的這些問題,過程中或許還故意誇大了我的消沉程度,為的是要向她和我自己證明:我真的有需要來這裡諮商。可是當她問起「童年時曾有任何一段時期感到安穩舒適嗎?」,我卻在回憶中搜尋不到任何答案,於是突然崩潰大哭起來。我跟她說了一切問題的開端——我的憂鬱問題、我的家族史——當我我們的諮商時間結束時,我感覺心靈獲得極度淨化。我跟她說我還想跟她約之後的諮商時間。
「我不確定我還會接收使用安泰保險的患者,」這位治療師口氣不帶絲毫情緒地說。「我會儘快跟你聯絡。」
隔天我直接致電她的辦公室約下一次會面時間,但在之後的二十四小時都沒收到回覆,於是我又兩次留言給她。再隔天,她留了語言訊息表示無法接收我這位患者,因為她已經決定不跟安泰保險合作。我立刻回電留下語音訊息,表示安泰保險會給付我百分之八十的自費支出。她沒有回電。之後的那個星期,我又留了四次語音訊息,一次比一次表現得更走投無路,我還求她給我手機號碼,這樣我們才能進一步透過簡訊討論。然後我開始沒事就打過去,但只要一轉到語音信箱就立刻掛掉電話,只希望能剛好遇到她與患者面談之間的空檔。這件事我每天會做上五、六次,直到我突然想起她可能有裝來電顯示功能,因此感到非常丟臉,結果我那天後來的其他時間都癱在床上無法起身。最後,她留給我一段很簡短的訊息:「要獲得給付需要處理很多書面資料。」我立刻用儲存好的快速撥號功能回電,對著她的答錄機大吼:「我可以處理書面資料的事!」
在等待她回電的同時,我必須去拉勒米(Laramie)參加一場懷俄明大學(University of Wyoming)舉辦的朗誦會。此刻的我已經非常憂鬱,在這個只想把自己的臉切下來的情況下還能想辦法搭上飛機已是奇蹟,之後也在那場朗誦會中表現得一如預期的糟糕。為觀眾朗讀我的詩歌作品根本是讓我被自己的各種局限一次次打醒。我在這場活動中撞見一道巨大的鴻溝,一邊是觀眾對「詩人」這個身分的理解,另一邊則是我怎麼看都無法證明自己是一位「詩人」的困境。我看起來就沒有這個角色該有的樣子。亞洲人就是缺乏存在感。亞洲人總是對自己占據的空間充滿歉意。我們的存在感稀薄到甚至沒被認真當作少數族群看待。我們的種族特色甚至不夠強到具有象徵性地位。我們已經是如此後種族的存在我們根本是矽元素。我用我那如同卡祖笛的粗啞氣音朗誦我的詩。等我讀完之後,所有人都窸窸窣窣地往出口移動。
回到紐約的路上,我在丹佛機場短暫停留了一下,此時我看見治療師的電話號碼出現在我的手機上。「尤妮絲!」我對著電話大吼。「尤妮絲!」這樣直呼她的名字是否太過無禮?我是不是該叫她周醫師才對?我問何時可以再跟她約定下次的諮商時間,但她的口氣很冷淡。「凱西,我很欣賞你的熱情,」她說,「但你最好還是去找別的治療師。」
「處理書面資料沒問題的!我愛處理書面資料!」
「我沒辦法做你的治療師。」
「為什麼不行?」
「我們不適合彼此。」
我很震驚。我皮膚上的每個毛孔都泉湧出疼痛的感受。我不知道治療師可以這樣拒絕病患。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我虛弱地問。
「抱歉,沒有辦法。」
「你不打算告訴我原因嗎?」
「不打算。」
「為什麼?」
「我不可以揭露那項資訊。」
「你是認真的?」
「對。」
「是因為我留下太多語音訊息了嗎?」
「不是。」她說。
「你在跟我認識的人交往嗎?」
「據我所知沒有。」
「那是因為,對你來說,我這人已經沒救了?是嗎?」
「當然不是。」她說。
「好吧,但是你不告訴我原因,我的感覺就會是這樣。你讓我覺得我不該敞開心胸,也不該分享自己的感受,因為大家只會被我的問題嚇跑!這正是一名治療師不該做的事吧?」
「我了解你的感受。」她語調平淡地說。
「如果我在這通電話後做出什麼激烈的事,那完全就是你的錯。」
「是你的憂鬱症讓你說出這種話。」
「是我讓我說出這種話。」我說。
「我有病患在等我。」她說。
「最好別把她也搞到沒救。」我說。
「再見。」
打從有記憶以來,我就一直想證明自己確實存在。身為一位現代的文字工作者,就算我的工作努力程度是別人的五倍,卻總還是會看見自己的雙手逐漸溶解、手臂也開始消失。常常到了晚上,我會在驚醒後不停責備自己,直到破曉的光刃刺入我的雙眼才停止。我的自信心極度貧乏,因為我這輩子都是靠著「有條件的愛」長大,這個社會也總把我當成如繃帶般隨時可替換的存在。
在常見的想像中,亞裔美國人占據著一個曖昧模糊卻又如同煉獄的位置:我們不夠白也不夠黑,非裔美國人不信任我們,白人也無視我們,只有白人想打壓黑人時會利用我們的存在。我們是服務業中的工蟻,是所有大公司中資深又忠貞的成員。我們是負責進行大量數學運算工作的中階經理,整間公司的運轉因此變得滑順,但我們從不會獲得升遷機會,因為我們的臉不是適合進行領導工作的正確「門面」。我們也有內涵不足的問題,大家總認為我們缺乏應有的心智能耐。可是就算我對這一切表現漠然,雙腳仍在水面下瘋狂划動,為了隱藏這種認定自己能耐不足的排山倒海感受,我不管做什麼都採取過度補償的態度。
這世間有大量文學作品在描述自我厭恨的猶太人和自我厭恨的非裔美國人,可是卻沒有足夠的作品在描寫自我厭恨的亞洲人。因為種族而產生的自我厭恨就是用白人看待你的方式來看待你自己,並讓你成為自己最可怕的敵人。你唯一的應對方式就是對自己嚴厲,這件事會變成一種強迫行為,甚至因此帶來安慰,然後一路催逼你直到死亡。你不喜歡自己的長相,也不喜歡自己的聲音。你認為你的亞洲五官定義不明,就彷彿上帝才剛開始捏塑你的五官卻又突然決定放棄。如果一個空間內有太多亞洲人會讓你覺得討厭。到底是誰讓這麼多亞洲人進來的啊?你會在腦中怒氣沖沖地抱怨。你不會跟亞洲人團結在一起,反而因為待在他們身邊而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你的個體界線不再明確,反而是跟另一個群體交融在一起。
我寧願相信這種自我厭恨的亞洲人正隨著我的這一代逐漸消失,可是情況必須取決於我的所在地。
〈摘錄自:《我受傷,故而我存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