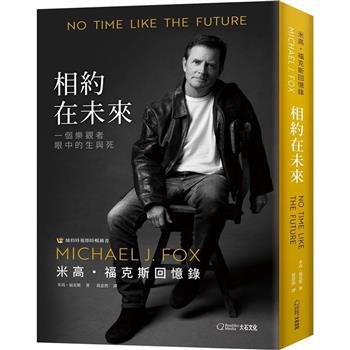一
戀家男人
山姆是唯一在我得了帕金森氏症前生下的孩子,我相信他對當年的情況沒有什麼記憶,或許甚至渾然不覺。我盡了一些爸爸的基本義務,例如在池塘邊抓青蛙;陪他去上親子音樂課,和一群超嚴肅的保母看著他們學奧福啟蒙樂器;設法鼓勵他參加團隊運動,後來發現這行不通(太容易吵起來)。我示範給山姆看怎麼用「兔耳朵法」綁鞋帶,先拉起一條鞋帶折成耳朵,另一條鞋帶套住那隻耳朵,繞過圓圈下方,變成第二隻耳朵。我教他騎腳踏車,從後面輕輕推著他,直到他有信心踩下踏板加速。如今,山姆偶爾也會推著我──坐在輪椅上的我。當然我不需要踩踏板。我小心翼翼地從輪椅起身時,兒子往往會在我邁步前檢查我的鞋帶,鬆了的話就迅速幫我繫好。
我大兒子唯一遇上的問題與時機有關。比起我還在發展中的帕金森氏症 ,我的另一個大問題對他人生的影響更重大──我在山姆出生三年後才戒酒,至今尚未破戒。在他上小學前,我們父子相處的寶貴時光多半是「美樂啤酒時光」。他告訴我,他最早的記憶中就有去冰箱幫我拿啤酒的印象。雖然我不記得我曾經因為喝酒而危害到崔西或山姆,但酒精問題是會逐漸惡化的。
我們剛結婚不久我就堅持要盡快生小孩,非常執著於扮演那個典型的「丈夫/父親」角色。這兩個名詞之間不能有任何間隔;對我來說只當丈夫、不當父親完全沒道理。我相信崔西一定表達過不情願或猶豫,但是我沒有看出她真正的感受,也不了解當了母親後會多麼嚴重地打亂她正在起飛的演藝事業。
最初走錯的這幾步帶來了不良的後果──我們發覺自己的基礎非常不穩。我當上了父親,我愛我的兒子,但某些方面來說,我只是做做當爸爸的樣子。儘管山姆現在是個樂觀的成年人,但他的幼年時期充滿了考驗。他特別容易哭鬧,而且以那麼小的孩子來說異常的悶悶不樂。我沒能幫上什麼忙。此外,當時我有酗酒的毛病,接著又診斷出帕金森氏症,內心的混亂和外部的動盪碰在了一起。總得做出某種改變。
因此我合乎邏輯地向崔西提議我們再生一個孩子。她搖了搖頭,簡直不敢相信。「你在開玩笑嗎?」在那之前尚未證實帕金森氏症會遺傳,因此她不願意生和擔憂疾病會遺傳無關,也不是因為認為我有可能殘疾,無法盡到父親的職責。反之,那是和我的酗酒問題與精神狀態有關,當時我只是想辦法一天撐過一天。為了工作我經常出遠門,可是我在途中感受到的孤獨不會比我在家裡愈來愈深的孤獨感更強烈。我覺得自己有點變成邊緣人,卻不明白那種疏離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喜怒無常,對於我們的婚姻狀況和我的事業方向感到迷惘,而且一想到最近的診斷結果,我根本不知道我的事業是否還有未來。
最後,在某個爛醉的夜晚,我醒來發現崔西站在我身旁。我睡在長沙發上,垂下來的手臂旁邊地板上有一罐打翻的啤酒。她看到這一幕,只問了我一句:「這就是你想要的嗎?」讓我當下就決定從此改變人生的,並不是她口氣中的憤怒,而是厭倦。她把我嚇壞了。崔西已經受夠了這整套酒醉的戲碼。
我答應定期參加戒酒無名會的十二步驟康復計畫,並且請了喬依絲來幫忙。她是位才華橫溢的榮格心理分析師,幫助我撲滅了大火,之後的多年裡她還會再幫我救火很多次。漸漸地,我學會了接受並且理解我的新疾病。酒我可以戒,但帕金森氏症會跟隨我一輩子。治療計畫提供的知識、工具、諮詢也為我照亮了和我的病一起前進的路。我認真努力接受治療,不只是為了變回以前的我,而是為了變得更新、更好。
結婚六年、得知我患了帕金森氏症四年、戒酒三年後,我發現我和我那超級有耐心及愛心的太太的關係更為鞏固了。然後就在那一年,一九九四年,崔西懷了雙胞胎,這兩個額外的寶寶是來彌補我們失去的時間(或者也可能是上帝給我們的驚喜)。奇怪的是,大家都毫不尷尬地直接問我們:生這麼多孩子,又要應付這種會無限惡化的嚴重神經系統疾病,會不會擔心?還有我們難道不怕寶寶也可能遺傳到這種疾病嗎?這問題怎麼想都不恰當,不過答案是:我們不擔心,他們也沒必要擔心。
戀家男人
山姆是唯一在我得了帕金森氏症前生下的孩子,我相信他對當年的情況沒有什麼記憶,或許甚至渾然不覺。我盡了一些爸爸的基本義務,例如在池塘邊抓青蛙;陪他去上親子音樂課,和一群超嚴肅的保母看著他們學奧福啟蒙樂器;設法鼓勵他參加團隊運動,後來發現這行不通(太容易吵起來)。我示範給山姆看怎麼用「兔耳朵法」綁鞋帶,先拉起一條鞋帶折成耳朵,另一條鞋帶套住那隻耳朵,繞過圓圈下方,變成第二隻耳朵。我教他騎腳踏車,從後面輕輕推著他,直到他有信心踩下踏板加速。如今,山姆偶爾也會推著我──坐在輪椅上的我。當然我不需要踩踏板。我小心翼翼地從輪椅起身時,兒子往往會在我邁步前檢查我的鞋帶,鬆了的話就迅速幫我繫好。
我大兒子唯一遇上的問題與時機有關。比起我還在發展中的帕金森氏症 ,我的另一個大問題對他人生的影響更重大──我在山姆出生三年後才戒酒,至今尚未破戒。在他上小學前,我們父子相處的寶貴時光多半是「美樂啤酒時光」。他告訴我,他最早的記憶中就有去冰箱幫我拿啤酒的印象。雖然我不記得我曾經因為喝酒而危害到崔西或山姆,但酒精問題是會逐漸惡化的。
我們剛結婚不久我就堅持要盡快生小孩,非常執著於扮演那個典型的「丈夫/父親」角色。這兩個名詞之間不能有任何間隔;對我來說只當丈夫、不當父親完全沒道理。我相信崔西一定表達過不情願或猶豫,但是我沒有看出她真正的感受,也不了解當了母親後會多麼嚴重地打亂她正在起飛的演藝事業。
最初走錯的這幾步帶來了不良的後果──我們發覺自己的基礎非常不穩。我當上了父親,我愛我的兒子,但某些方面來說,我只是做做當爸爸的樣子。儘管山姆現在是個樂觀的成年人,但他的幼年時期充滿了考驗。他特別容易哭鬧,而且以那麼小的孩子來說異常的悶悶不樂。我沒能幫上什麼忙。此外,當時我有酗酒的毛病,接著又診斷出帕金森氏症,內心的混亂和外部的動盪碰在了一起。總得做出某種改變。
因此我合乎邏輯地向崔西提議我們再生一個孩子。她搖了搖頭,簡直不敢相信。「你在開玩笑嗎?」在那之前尚未證實帕金森氏症會遺傳,因此她不願意生和擔憂疾病會遺傳無關,也不是因為認為我有可能殘疾,無法盡到父親的職責。反之,那是和我的酗酒問題與精神狀態有關,當時我只是想辦法一天撐過一天。為了工作我經常出遠門,可是我在途中感受到的孤獨不會比我在家裡愈來愈深的孤獨感更強烈。我覺得自己有點變成邊緣人,卻不明白那種疏離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喜怒無常,對於我們的婚姻狀況和我的事業方向感到迷惘,而且一想到最近的診斷結果,我根本不知道我的事業是否還有未來。
最後,在某個爛醉的夜晚,我醒來發現崔西站在我身旁。我睡在長沙發上,垂下來的手臂旁邊地板上有一罐打翻的啤酒。她看到這一幕,只問了我一句:「這就是你想要的嗎?」讓我當下就決定從此改變人生的,並不是她口氣中的憤怒,而是厭倦。她把我嚇壞了。崔西已經受夠了這整套酒醉的戲碼。
我答應定期參加戒酒無名會的十二步驟康復計畫,並且請了喬依絲來幫忙。她是位才華橫溢的榮格心理分析師,幫助我撲滅了大火,之後的多年裡她還會再幫我救火很多次。漸漸地,我學會了接受並且理解我的新疾病。酒我可以戒,但帕金森氏症會跟隨我一輩子。治療計畫提供的知識、工具、諮詢也為我照亮了和我的病一起前進的路。我認真努力接受治療,不只是為了變回以前的我,而是為了變得更新、更好。
結婚六年、得知我患了帕金森氏症四年、戒酒三年後,我發現我和我那超級有耐心及愛心的太太的關係更為鞏固了。然後就在那一年,一九九四年,崔西懷了雙胞胎,這兩個額外的寶寶是來彌補我們失去的時間(或者也可能是上帝給我們的驚喜)。奇怪的是,大家都毫不尷尬地直接問我們:生這麼多孩子,又要應付這種會無限惡化的嚴重神經系統疾病,會不會擔心?還有我們難道不怕寶寶也可能遺傳到這種疾病嗎?這問題怎麼想都不恰當,不過答案是:我們不擔心,他們也沒必要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