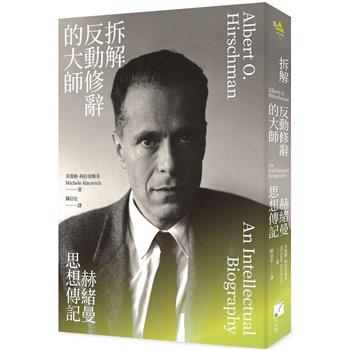災難的目擊者【摘錄自第一章】
奧圖.阿爾伯特對於政治的興趣始於一九二○年代尾聲,在他十四或十五歲之際。到了那個時候,威瑪共和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面貌已出現迅速變化。他對政治議題之所以愈來愈感興趣,原因是他初步閱讀了馬克思、列寧、考茨基、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與奧托.鮑爾(Otto Bauer)的著作。鮑爾在一九三○至三一年冬季舉行於柏林體育宮的一場政治集會上尤其令赫緒曼留下難忘的印象。在那場集會上,鮑爾以長期經濟循環的角度解釋西方經濟體遭遇的危機,為瀰漫於威瑪共和的社會動盪與政治極端主義背後的經濟根源提出一項富有說服力的詮釋。赫緒曼因此首度發現政治經濟學是一項強而有力的分析工具。「如果說有哪一項單一事件說服了他研究經濟學,」阿德爾曼寫道:「那麼就是在體育宮的那一晚;過了五十年後,赫緒曼還是能夠閉上眼睛重述鮑爾那晚的表現。」
這樣的廣泛閱讀是很重要的成長經歷,因為赫緒曼藉由這些閱讀而能夠自由探索許多不同的文化領域。套用阿德爾曼所言:「德語雖是他的母語(Muttersprache),卻不是他的家(Heimat)。」另一方面,形塑自身教育的「Bildung」這種德國傳統,則一直都是赫緒曼抱持的核心態度。
威瑪共和不但深陷經濟與政治動盪,而且制度不穩,政府又孱弱。一次大戰後那些年的政治動盪與經濟危機,最後導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間的惡性物價膨脹。當時的一名目擊者回憶指出,眾人「一片茫然又深受物價膨脹震撼,根本不曉得那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他們喪失了自信,不再覺得能夠掌握自己的人生……也喪失了道德、倫理、正直等這類過往的價值觀」。
政治上,威瑪共和仍是一項未實現的承諾,就算一九二○年代的後半是一段經濟繁榮與文化狂熱的時期,那樣的復甦也是立足在非常脆弱的基礎上。德國的工業家比較感興趣的經常是併購,而不是能夠增加產量的新投資。此外,資金主要來自國外,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大量流入。紐約證券交易所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底崩盤之後,對德國造成的影響極為巨大。美國的銀行開始回收資金,促使德國銀行取消工業部門的短期貸款。工業生產開始下滑,到了一九三二年已減少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的六一%。在歐洲,只有波蘭的狀況比德國更糟。
失業率大幅飆升。到了一九三二年,工作人口當中差不多每三人就有一人登記為失業。就絕對數字而言,一九三○年底有五百萬名工作人口失業,一年後又進一步增至六百萬人。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以及仰賴他們撫養的家屬已占德國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遭受衝擊的對象不只是工業勞工,還有白領工作者、政府員工、各式各樣的中產階級職業,以及小型家庭企業。社會安全網遠遠不足,尤其是因為這場危機整整持續了三年才開始逐漸消退。馬佐爾(Mark Mazower)指出,經濟衰退的時間極長,幅度也極大,工作機會的欠缺又令人深感絕望,以致社會生活的步調都開始改變。「對於男性而言,把一天劃分成一個個小時的做法在許久以前就已經失去意義,」針對馬利恩塔(Marienthal)這座小城市的失業狀況所寫的一份報告指出:「起床、吃午餐與上床睡覺已是一天生活中唯一剩下的幾個基準點。在這三項活動之間的時間,沒有人真的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窮困與絕望廣為普及,「空氣中總是瀰漫著可能迸發暴力與犯罪的氣息」。
這場危機對赫緒曼一家人造成嚴重影響。卡爾雖然保住了工作,但家中的存款一掃而空。海德薇的娘家馬庫色家族也深受打擊,使得海德薇的母親不得不與赫緒曼一家人同住。除此之外,對卡爾而言,職場的情形也開始走下坡。在這個身分政治突然快速成長的階段裡,猶太教與基督教醫院開始各自偏好僱用信奉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醫生。卡爾雖然深受敬重,卻發現自己的職涯發展陷入停滯,只見高階職務一再與他擦身而過,紛紛落入宗教資歷「無可挑剔」的年輕候選人手裡。當初的同化選擇反倒變成了一項不利的條件。
政治情勢迅速出現崩潰。社會民主黨雖是最大的政黨,氣勢卻不斷下滑。他們在一九二
八至一九三○年初主導的大聯合政府施政成效不佳,而他們猶豫不決又短視近利的政治立場也令愈來愈多的選民深感幻滅。在左側,共產黨日益壯大,也愈來愈偏激。納粹黨則是針對許多互相對立的不同選民族群以及利益團體量身打造政治訊息,而因此在眾多群體當中贏得支持,包括保守人士、民族主義者、反猶太人士、小資產階級與中資產階級,以及鄉下地區的居民:史學家伊文思(Richard J. Evans)稱之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社會抗爭政黨」。相對之下,傳統的保守派與中間派政黨則是大量流失共識,結果一九三○年九月的選舉對它們施以一記決定性的重擊。在一九二八年得票率只有二.六%的納粹黨,到了一九三○年已成為第二大黨,囊括一八.二%的選票。威瑪共和的民主制度愈來愈趨脆弱。街頭暴力以及互相對立的準軍事團體之間的衝突大幅增加,每年發生數百起政治暴動,造成數十人死亡。納粹黨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選舉成為國會最大黨,獲得三七.三%的選票,得票率比排名第二的政黨高出一五%以上(社會民主黨的得票率為二一.六%)。
一九三○年的選舉是奧圖.阿爾伯特密切關注的第一場選舉。他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埋首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引導他的,是他在法蘭西文理中學結識的一名年紀較大的朋友艾爾曼(Heinrich Ehrmann)。如同阿德爾曼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為赫緒曼與他的同學提供了一把新鑰匙……讓他們能夠理解發生於自身周遭的那些衝突。」不過,最令赫緒曼著迷的不是馬克思身為革命家或者經濟學家的面向,而是身為史學家的面向(例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這部著作):「他的歷史書遠遠沒有他的經濟著作那麼遵循正統。」
赫緒曼也開始閱讀列寧的作品。列寧的政治分析強調歷史當中無可預測的轉折,全然展現了他對於不可違犯的歷史定律所抱持的強烈懷疑態度,令奧圖.阿爾伯特深感著迷。赫緒曼對於歷史進展以及決策過程的觀點,都受到馬克思與列寧的長久影響。他在六十年後回憶指出,列寧的影響「可以見於我著作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我在《邁向進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當中談到如何在拉丁美洲推行改革。『兜售改革』的概念在某方面而言可以追溯到我早期對列寧的閱讀」。
奧圖.阿爾伯特與烏蘇拉在一九三一年於社會民主黨的青年組織當中開始涉入政治運動,而社會民主黨不但遭受納粹黨的攻擊,也備受共產黨的鄙夷;共產黨員習於把社會民主黨人稱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這「絕對是任何人對於自己的敵人所能夠說出最難聽的話」,赫緒曼表示。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願景和態度雖然嚴重分歧,他卻認定威瑪共和唯一的希望就是由這兩黨合作組成一道共同陣線對抗納粹。
一九三二年,奧圖.阿爾伯特從法蘭西文理中學畢業,決定註冊就讀法學院,因為當時經濟學的課歸在法學院當中。他閱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部分著作(並針對亞當.斯密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寫過短篇論文),但當時的整體情勢實在不利於求學。政治衝突、民族主義以及反猶太主義猖獗不已,右翼極端主義學生更在一九三三年五月攻占圖書館,把數以萬計的書本丟進火堆裡。赫緒曼於是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投注於政治鬥爭當中。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成為德國總理之後,才短短幾週威瑪共和即告瓦解。納粹突擊隊的政治暴力爆發於全國各地,襲擊工會、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辦公室,還有著名左翼人士的住宅。反猶太活動也極為猖獗。二月二十七日,德國國會大廈遭到一名社會邊緣人縱火。希特勒隨即利用這個機會發布命令,禁止表達自由、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這項命令也允許警方在沒有法院裁定的情況下無限期拘押民眾。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舉行的選舉,由於事前與事後都有大量的威嚇與暴力行動,納粹黨因此囊括了四三.九%的選票。選舉結束後不久,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就宣布奧拉寧堡(Oranienburg)將設置一座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三月二十三日,國會通過所謂的《授權法》,賦予總理自行發布命令進行統治的權力,不需經過國會與總統同意,違背威瑪憲法的原則。原本是一項臨時性的緊急立法,卻成了「永久消除公民權利與民主自由的法律或偽法律基礎」。希特勒就此成為德國的獨裁者。
隨著政治與個人自由迅速縮減,政治運動因此變得愈來愈危險。在沒有新聞自由而且禁止公開集會的情況下,奧圖.阿爾伯特、烏蘇拉與他們那個團體決定油印傳單挨家挨戶發放,藉此傳播政治理念。他們的複印機裝設在科洛尼(Eugenio Colorni)的房間裡:他是來自義大利的哲學家,也是烏蘇拉的朋友,當時在德國跟隨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研讀,正在撰寫以萊布尼茲為主題的論文。赫緒曼後來回憶道,科洛尼的旅館房間「成了反法西斯活動與出版品的神經中樞」。在此同時,奧圖.阿爾伯特的朋友彼得.法朗克遭到逮捕,他手上那些列有同志姓名的文件也遭到沒收。赫緒曼因此陷入直接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