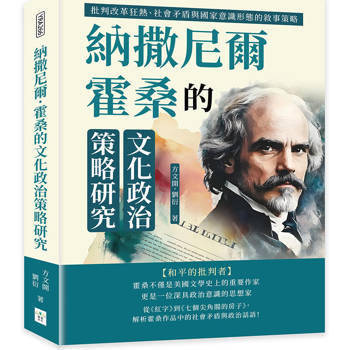第一章 和平主義的文化理論家
之所以把霍桑看成一位文化理論家,主要基於以下三點理由:首先,許多批評家和讀者一直以來都讚揚霍桑,是因為他的歷史知識和他從歷史視角理解問題。實際上他深邃的歷史思想聚焦更多的是時代、運動、資料變化,以及著名的歷史人物。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霍桑都展示出對「人」的關係、情感、身體的歷史性理論掌握。像一些現代歷史學家和唯心理論家一樣,他始終專注於探討,社會力量是如何透過主體性構成被再生產出來的。很顯然,霍桑對19世紀中產階級心理自我的意識形態塑造,貢獻良多。不過,他也反覆把感情、自我反思、自我控制、身分的文化建構作為他的主題,並常常把超心理的關係,看成是這些建構的變形結果。並且,他還探討了這些建構與產生美國性別、階級、個人差異之間的關係。
雖然霍桑在強迫印第安人從東部遷往西部、與墨西哥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組織廢奴主義者反對奴隸制期間寫過相關文章,可是他的小說沒有特別關注種族差別的產生和種族關係。當他的小說涉及種族問題的時候,目的是調查土著居民的狀況(如《大街》),而不是黑人的狀況。然而,霍桑的一些小說針對性地表達了他所專注的情感、自我形象、社會力量的建構與人性的塑造之間的象徵性連繫。讓人好奇的是,在《胎記》(The Birth-Mark)中喬治亞娜的美化,被「移除」的紅色手形是土著居民塗抹在他們臉上的紅色手的縮減版,生動地呈現在喬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幾幅西元 1830~1840年間很流行的「印第安人」畫像中。在《牧師的黑面紗》(The Minister's Black Veil)(西元1836年)中,胡泊牧師的黑面紗在新英格蘭清教徒教民中,引起了廣泛的罪惡感,就像在霍桑的時代,廢奴主義者控告新英格蘭對奴隸實施的共謀犯罪。兩篇小說都展示出緊張的白色焦慮,承認有色──紅色和黑色──是一種公共事務。
其次,霍桑是一名藝術家,用小說挑戰一些自身明顯的意識形態偏好和極限。他透過日記、信件、小說中的人物如海斯特、澤諾比阿、米利亞姆等,來捍衛傳統的家庭生活和性別角色。即使霍桑設定的情節包含著批評意見和不滿,他也會讓這些批評和不滿顯得委婉,只是質疑流行的中產階級思想。如果說有一點霍桑需要悲嘆的,就是身為激進的理論家,海斯特並沒有從紅字中吸取教訓,他用了小說的大部分讓這個字母的意義顯得非常複雜且不確定,它可以代表通姦、作者、多義、字母表的第一個字母、寓言、天使、美國等等。霍桑不僅是海關的檢察官,還是前提和意義產生的檢察官。儘管如此,他還是常常不把文化看作一種給予的權威,而是一種潛在可變的過程、實踐、表演、意義結構和辨識系統。
最重要的是,理查.奧曼的睿智名言:「人類活動儘管不僅僅是政治的,但總是政治的。」總讓人聯想起霍桑那些告誡的戲仿、反寓言和偏執的理論寓言。如果在《奇幻大廳》中霍桑能拋棄懷疑,承認即使是「最忠誠保守的心……也無法同情那些無數理論家的靈魂……他們尋求一種更好、更純潔的生活,不過這在地球上還沒有實現」(10:180-181)。在《地球的大屠殺》(Earth's Holocaust)(西元1844年)中,他更是完全退化成一個狂熱的理論改革家,把自認為仇恨的物品扔入一個巨大的火堆之中。可能沒有小說在闡釋某種思想時有《牧師的黑面紗》那麼生動,那麼富有同情心。
之所以把霍桑看成一位文化理論家,主要基於以下三點理由:首先,許多批評家和讀者一直以來都讚揚霍桑,是因為他的歷史知識和他從歷史視角理解問題。實際上他深邃的歷史思想聚焦更多的是時代、運動、資料變化,以及著名的歷史人物。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霍桑都展示出對「人」的關係、情感、身體的歷史性理論掌握。像一些現代歷史學家和唯心理論家一樣,他始終專注於探討,社會力量是如何透過主體性構成被再生產出來的。很顯然,霍桑對19世紀中產階級心理自我的意識形態塑造,貢獻良多。不過,他也反覆把感情、自我反思、自我控制、身分的文化建構作為他的主題,並常常把超心理的關係,看成是這些建構的變形結果。並且,他還探討了這些建構與產生美國性別、階級、個人差異之間的關係。
雖然霍桑在強迫印第安人從東部遷往西部、與墨西哥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組織廢奴主義者反對奴隸制期間寫過相關文章,可是他的小說沒有特別關注種族差別的產生和種族關係。當他的小說涉及種族問題的時候,目的是調查土著居民的狀況(如《大街》),而不是黑人的狀況。然而,霍桑的一些小說針對性地表達了他所專注的情感、自我形象、社會力量的建構與人性的塑造之間的象徵性連繫。讓人好奇的是,在《胎記》(The Birth-Mark)中喬治亞娜的美化,被「移除」的紅色手形是土著居民塗抹在他們臉上的紅色手的縮減版,生動地呈現在喬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幾幅西元 1830~1840年間很流行的「印第安人」畫像中。在《牧師的黑面紗》(The Minister's Black Veil)(西元1836年)中,胡泊牧師的黑面紗在新英格蘭清教徒教民中,引起了廣泛的罪惡感,就像在霍桑的時代,廢奴主義者控告新英格蘭對奴隸實施的共謀犯罪。兩篇小說都展示出緊張的白色焦慮,承認有色──紅色和黑色──是一種公共事務。
其次,霍桑是一名藝術家,用小說挑戰一些自身明顯的意識形態偏好和極限。他透過日記、信件、小說中的人物如海斯特、澤諾比阿、米利亞姆等,來捍衛傳統的家庭生活和性別角色。即使霍桑設定的情節包含著批評意見和不滿,他也會讓這些批評和不滿顯得委婉,只是質疑流行的中產階級思想。如果說有一點霍桑需要悲嘆的,就是身為激進的理論家,海斯特並沒有從紅字中吸取教訓,他用了小說的大部分讓這個字母的意義顯得非常複雜且不確定,它可以代表通姦、作者、多義、字母表的第一個字母、寓言、天使、美國等等。霍桑不僅是海關的檢察官,還是前提和意義產生的檢察官。儘管如此,他還是常常不把文化看作一種給予的權威,而是一種潛在可變的過程、實踐、表演、意義結構和辨識系統。
最重要的是,理查.奧曼的睿智名言:「人類活動儘管不僅僅是政治的,但總是政治的。」總讓人聯想起霍桑那些告誡的戲仿、反寓言和偏執的理論寓言。如果在《奇幻大廳》中霍桑能拋棄懷疑,承認即使是「最忠誠保守的心……也無法同情那些無數理論家的靈魂……他們尋求一種更好、更純潔的生活,不過這在地球上還沒有實現」(10:180-181)。在《地球的大屠殺》(Earth's Holocaust)(西元1844年)中,他更是完全退化成一個狂熱的理論改革家,把自認為仇恨的物品扔入一個巨大的火堆之中。可能沒有小說在闡釋某種思想時有《牧師的黑面紗》那麼生動,那麼富有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