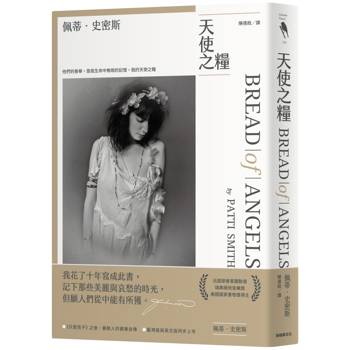序曲
鋼筆劃過紙頁,沙沙作響:叛逆的駝峰、叛逆的駝峰、叛逆的駝峰。「這些字是什麼意思?」鋼筆問道。「我不知道。」手腕回答。它們是正在成形的文字,日後將由駐紮在波蘭北部夏洛蒂山谷的作家,決定它的意義。夏洛蒂,這個名字喚起一個瓷娃娃的臉,一個被孩子遺落在草地上的娃娃,她的主人偷閒去摘野莓。不是太長的時間,卻足夠被人遺忘,流逝的季節裡,被遺棄的娃娃成了雨中的夏洛蒂、雪中的夏洛蒂、被頑皮狗兒撕裂的夏洛蒂。山毛櫸不斷長高的樹影罩住她的瓷腦袋,歷經飄雪的時節,周圍的紅葉一片片枯萎。陽光曬褪了她雙頰的粉暈,卻未能削弱她大理石般的眼眸中,那種冷峻的目光。
為何是瓷製的臉龐?為何不像我的布偶,把鈕釦當眼睛縫在粗布上?對從未擁有之物的傾慕,是從何而來?書裡所描述的,對所謂美好事物的迷戀──亞麻背心、小羊皮手套、軟皮靴子。翻動書頁,如翻找想像中的行李箱,為了尋覓一件天鵝絨斗篷,它足以掩藏受困於笨拙孩童身軀裡的縮小版鐘樓怪人。我那叛逆的駝峰,不甚雅觀卻不可或缺的叛逆駝峰。
我擱下筆,哼起一段久遠的旋律,一首屬於沼澤林地的歌謠。我曾在那徜徉,在疾馳的雲朵下被萬物蠱惑。叛逆的駝峰叛逆的駝峰,踏過蘆葦叢和倔強的蕨類,繞開刺鼻的野草和群飛的蚊蟲。我在腰間綁上一把小鐵鎚和迷你手電筒,把岩石撬開,尋找祕密的核心;向外星飛船發送信號,求它們帶我遠行,我耐心等候,準備隨時啟程。藻類在溪流浮動,蝌蚪流竄其中,我脫下鞋沿著溪走,時時保持警覺,留意一枚硬幣的閃光,那是通往冥界的入口。或尋覓鋸齒狀的碎片,只要嵌入正確的位置,它能和其他碎片接合,拼成一面屬於我的手鏡,手鏡是象牙的質地。
離開書桌,我走入環繞夏洛蒂山谷的森林,勘察最古老樹木的內在結構。年輪包裹著童年的活細胞,一圈一圈的同心圓,封存了四件白洋裝的纖維:漿挺的聖餐禮服、藝術之裙的剩料,一條弟弟給我的如手帕精緻的派對裙,沾著搖滾樂的率真。最後,是一襲潔白無瑕的維多利亞式茶會禮服,我的婚紗,承載著誓言與我為丈夫流下的淚水。有段時間,我愛他勝過自己。
上帝透過壁紙的縫隙低語,一滴水炸裂成一道方程式。森林中,光線傾落。一個老人坐在木桶上唱著:「我在田野找到一枚金幣,誰來幫我兌換?」孩童朝他喊道:「我的娃娃可以,她的錢包裝滿銀幣,但我得先找到她。」僅憑著意志,娃娃現形了,是夏洛蒂。先是一條手臂,接著是軀幹,再來是她驕傲的小腦袋。那對凝固的藍眼珠,曾目睹六翼天使被驅逐,見證過迴盪在宇宙的星火。
「所有人都死了,一切皆被遺忘。」有個聲音在耳邊呢喃。我清點還在世的人,思緒停駐在妹妹臉上,那張純真卻洞悉一切的臉。只要她還在,我們的記憶便得以保存。若有一天,我倆都不在了呢?「為那個未來而寫。」筆低聲說:「為那隻被遺棄的羔羊而寫,牠在閣樓的大火中化作灰燼。」沙漏翻轉,每粒沙都是一個無窮的字眼,存封著萬物生靈的最初與最終。
我看見自己踮起腳尖,伸手去抓一本深紅色的書,那是幼童貪婪好奇的對象。我想探知書中世界,隨著時間流轉,也渴望寫一本書。我深信自己能寫出世界上最長的書,記下日常瑣事。我想用這種方式書寫,讓讀到的人都能在字裡行間照見自己。有些讀者會駐留在我的文字旁,有些會轉身離去。至於我,將從被烈日照射的光丘邊緣噴湧而出,像一個孤單的旅人,尋找童年的花園。
鋼筆劃過紙頁,沙沙作響:叛逆的駝峰、叛逆的駝峰、叛逆的駝峰。「這些字是什麼意思?」鋼筆問道。「我不知道。」手腕回答。它們是正在成形的文字,日後將由駐紮在波蘭北部夏洛蒂山谷的作家,決定它的意義。夏洛蒂,這個名字喚起一個瓷娃娃的臉,一個被孩子遺落在草地上的娃娃,她的主人偷閒去摘野莓。不是太長的時間,卻足夠被人遺忘,流逝的季節裡,被遺棄的娃娃成了雨中的夏洛蒂、雪中的夏洛蒂、被頑皮狗兒撕裂的夏洛蒂。山毛櫸不斷長高的樹影罩住她的瓷腦袋,歷經飄雪的時節,周圍的紅葉一片片枯萎。陽光曬褪了她雙頰的粉暈,卻未能削弱她大理石般的眼眸中,那種冷峻的目光。
為何是瓷製的臉龐?為何不像我的布偶,把鈕釦當眼睛縫在粗布上?對從未擁有之物的傾慕,是從何而來?書裡所描述的,對所謂美好事物的迷戀──亞麻背心、小羊皮手套、軟皮靴子。翻動書頁,如翻找想像中的行李箱,為了尋覓一件天鵝絨斗篷,它足以掩藏受困於笨拙孩童身軀裡的縮小版鐘樓怪人。我那叛逆的駝峰,不甚雅觀卻不可或缺的叛逆駝峰。
我擱下筆,哼起一段久遠的旋律,一首屬於沼澤林地的歌謠。我曾在那徜徉,在疾馳的雲朵下被萬物蠱惑。叛逆的駝峰叛逆的駝峰,踏過蘆葦叢和倔強的蕨類,繞開刺鼻的野草和群飛的蚊蟲。我在腰間綁上一把小鐵鎚和迷你手電筒,把岩石撬開,尋找祕密的核心;向外星飛船發送信號,求它們帶我遠行,我耐心等候,準備隨時啟程。藻類在溪流浮動,蝌蚪流竄其中,我脫下鞋沿著溪走,時時保持警覺,留意一枚硬幣的閃光,那是通往冥界的入口。或尋覓鋸齒狀的碎片,只要嵌入正確的位置,它能和其他碎片接合,拼成一面屬於我的手鏡,手鏡是象牙的質地。
離開書桌,我走入環繞夏洛蒂山谷的森林,勘察最古老樹木的內在結構。年輪包裹著童年的活細胞,一圈一圈的同心圓,封存了四件白洋裝的纖維:漿挺的聖餐禮服、藝術之裙的剩料,一條弟弟給我的如手帕精緻的派對裙,沾著搖滾樂的率真。最後,是一襲潔白無瑕的維多利亞式茶會禮服,我的婚紗,承載著誓言與我為丈夫流下的淚水。有段時間,我愛他勝過自己。
上帝透過壁紙的縫隙低語,一滴水炸裂成一道方程式。森林中,光線傾落。一個老人坐在木桶上唱著:「我在田野找到一枚金幣,誰來幫我兌換?」孩童朝他喊道:「我的娃娃可以,她的錢包裝滿銀幣,但我得先找到她。」僅憑著意志,娃娃現形了,是夏洛蒂。先是一條手臂,接著是軀幹,再來是她驕傲的小腦袋。那對凝固的藍眼珠,曾目睹六翼天使被驅逐,見證過迴盪在宇宙的星火。
「所有人都死了,一切皆被遺忘。」有個聲音在耳邊呢喃。我清點還在世的人,思緒停駐在妹妹臉上,那張純真卻洞悉一切的臉。只要她還在,我們的記憶便得以保存。若有一天,我倆都不在了呢?「為那個未來而寫。」筆低聲說:「為那隻被遺棄的羔羊而寫,牠在閣樓的大火中化作灰燼。」沙漏翻轉,每粒沙都是一個無窮的字眼,存封著萬物生靈的最初與最終。
我看見自己踮起腳尖,伸手去抓一本深紅色的書,那是幼童貪婪好奇的對象。我想探知書中世界,隨著時間流轉,也渴望寫一本書。我深信自己能寫出世界上最長的書,記下日常瑣事。我想用這種方式書寫,讓讀到的人都能在字裡行間照見自己。有些讀者會駐留在我的文字旁,有些會轉身離去。至於我,將從被烈日照射的光丘邊緣噴湧而出,像一個孤單的旅人,尋找童年的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