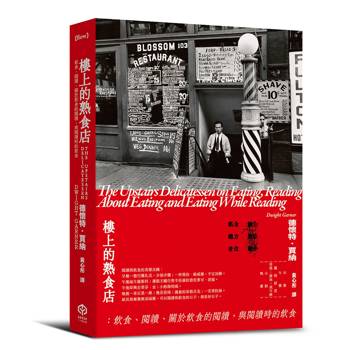〈早餐〉(選摘)
這是一天早晨的開始,也是這本書的開始。我們來喝杯咖啡吧。我從十一歲起就強迫自己每天喝咖啡,用Folgers速溶咖啡粉沖泡而成,水溫一定要燙,糖要多到幾乎攪不動。我所欣賞的男性小說家和女性小說家——都是些異議分子,與社會格格不入,卻總是冷靜自持——都喝黑咖啡,通常還會配上一支菸。查爾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就是那種典型的會喝黑咖啡的男人。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也曾在《漫長的告別》(The Long Goodbye)中寫道:「我去廚房煮咖啡,而且是一大壺咖啡。濃郁,強烈,苦澀,燙口,無情而又墮落,那是勞碌男人的命根子。」據說巴爾扎克(Balzac)一天要喝五十杯咖啡;他的膀胱應該被放在博物館裡展示才對。紐約市需要一家有賣名叫「齊克果」這種獨特飲品的咖啡店。索倫.齊克果的喝法是先裝滿一杯的糖,直到糖堆超出杯緣,再將超濃的黑咖啡從頂端倒下去,讓金字塔慢慢融解,接著喝掉這杯令人望而生畏的成品。我曾經按照他的方法泡過一次,那讓我覺得自己像個狼人。M.F.K.費雪告訴我們,咖啡是一個絕對不能貪便宜的東西。也許她是對的,不過那些對飲食很講究的人,無論他們談到的是雞蛋、魚、油、香草,還是優格,他們都會說那是絕對不能貪便宜的東西,於是你購物明細上的金額就會越發趨近於一張超速罰單的罰金。
很多人都對喝咖啡這件事嚴肅得要命。比方說,哎,我親愛的克莉就是這樣的人,她可以——我不誇張——為了一杯好喝的馥芮白走三公里。而我就相對理智了。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從來沒有喝過一杯難喝的咖啡,就像我從來沒有讀過一篇難看的羅麗.摩爾(Lorrie Moore)的短篇小說,雖說她還是有相較出色與相較沒那麼出色的作品。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對喝咖啡這件事有一套自己的要求。六○年代初,當他在巴德學院(Bard College)任教時,他和索爾.貝婁(Saul Bellow)成了室友,索爾.貝婁在附近買了一棟破舊的豪宅,但是一個人住在那裡常覺得孤單。艾里森讓貝婁認識到了好咖啡的魅力。貝婁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曾有一名化學家教他如何用一般的實驗室濾紙和常溫水泡咖啡,再用bain-marie隔水燉煮鍋(鍋內有兩層鍋壁)加熱咖啡,但絕對不能煮沸。」
克莉時常為了那些沒能正常發揮效能的精密咖啡器具而感到苦惱。她老是對奶泡器做細微的調整。或許,就像克里斯托佛.索倫提諾(Christopher Sorrentino)在他的小說《逃亡者》(The Fugitives)裡寫到的,人們在挑選意式濃縮咖啡機時,遠比他們在選擇情人的時候更為謹慎。如果你的咖啡機功能很基本,就像我偏好的那種,那麼你可以試試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他的非虛構作品《查理與我》(Travels with Charley)中提到的祕訣。他說,要是想讓咖啡「閃閃發亮」,那就把蛋白和蛋殼丟進沸騰的咖啡壺裡。史坦貝克的祕訣是瑞典的一種傳統做法:蛋白和蛋殼能夠去除咖啡裡的雜質,降低苦味並增強咖啡因。但我死也不願嘗試。就像我寧可去死,也不願用蘿利.科爾溫(Laurie Colwin)的方法喝咖啡。身為小說家的科爾溫曾寫過兩本觀察幽微的飲食書:《家常菜》(Home Cooking),及《更多家常菜》(More Home Cooking)。這兩本我都非常喜歡,我做飯的時候也總是會把那兩本已經被我翻爛的書拿出來參考。不過,科爾溫喝咖啡的習慣卻讓我不寒而慄。「你一眼就能辨別我和姊姊是否來過,」她在書中這樣寫道:「因為我們兩個都會把大家早上杯子裡喝剩的咖啡集中起來,倒在冰塊上,然後喝掉。」這也太噁了吧,蘿利。好吧,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怪癖。理查.布羅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怪癖則是用女友的照片來當自己小說的封面。當你掃視這些封面時,不免想起他曾這樣評論道:「對我而言,她是完美的情人,因為她有豐滿堅實的胸部,而且支持民主黨。」他也在《草坪的復仇》(Revenge of the Lawn)中這樣寫道:「有時候生活不過是咖啡和一杯咖啡給予的親密關係。」
一杯咖啡能在一天當中創造出一段休憩時刻。如果你能學著縮短早上最後一杯咖啡與晚上第一杯酒的間隔時間,那麼你就已經朝頓悟邁出了一小步。法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在《午餐詩集》(Lunch Poems)中,描寫到他在一個陰鬱的雨天早晨泡咖啡時,手中溫熱的盤子就像是「地球唯一的熱源」。奧哈拉擔心自己會再次變得默默無名,他的咖啡為他提供了短暫的依靠,彷彿他是由一顆九伏特小電池供電的收音機。被低估的小說家查爾斯.萊特(Charles Wright)也在他的小說《假髮》(The Wig)中寫過一個與其相似的雨天早晨。他描寫了沖泡「用男性荷爾蒙調味過的、能讓你在星期一早晨直面白人」的咖啡的場景。
我要在這裡很羞恥地承認,我有一個自己的幸運馬克杯。那是倫敦報紙《衛報》(The Guardian)送的。雖然不確定我是怎麼認定它會為我帶來好運的,但我會在重要的截稿日一邊從中啜飲咖啡,一邊摸摸它的肚子,彷彿它是佛陀似的。在洗碗機中的數千趟旅程已讓它有些磨損。每當我發現孩子們偷偷用它喝東西時,我總會大聲呵斥他們;畢竟他們可是在玩弄我的因果。我在文學中見過最棒的馬克杯,是在娜姆瓦麗.塞珀爾(Namwali Serpell)那本震撼人心的小說《古老漂流》(The Old Drift)中,一位女性角色手裡揮舞著的那個馬克杯,上面寫著:去殖民化你的馬子(DECOLONISE YOUR PUSSY)。
我曾斷斷續續在曼哈頓待過一陣子,有時住在僅有幾輛特斯拉(Tesla)那麼大的公寓裡。出門買咖啡反而比較省事。我很喜歡美國小說家奧特莎.莫什菲格(Ottessa Moshfegh)在她的小說《我的休憩與放鬆之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所闡釋的觀點,說明比起星巴克(Starbucks),她更喜歡去雜貨店買咖啡的原因。她說,在雜貨店你不用「面對那些點布里歐麵包和去奶泡拿鐵的客人,沒有流鼻涕的小孩與瑞典的互惠生(au pairs),沒有將自己打理得一絲不苟的專業人士,也沒有正在約會的男女」。她又補充道:「雜貨店的咖啡是勞工階級的咖啡——是給大樓管理員、送貨員、修繕工人、餐廳雜工和家庭幫傭喝的。」雜貨店的店員會記得你的名字,還有你喜不喜歡加牛奶。
要抨擊星巴克很簡單,它就是一家假木材裝潢的頂級配方咖啡的工業化供應商。在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的小說《蟻類》(Antkind),敘事者更是毫不留情地開嗆。「星巴克是給笨蛋喝的時髦咖啡,」他說,「它是咖啡界的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不過我得幫星巴克說句話,有一次我和家人在國內自駕遊,喝了好幾天休息站的噁爛咖啡後,當我們突然看見一家星巴克時,我們所有人都在車裡興奮地跳起來。星巴克是菁英主義嗎?名聲狼藉的前福斯新聞(Fox News)主持人比爾.歐萊利(Bill O'Reilly),以前常常誇耀自己從來不去星巴克,因為他比較喜歡長島(Long Island)當地一家「警察和消防員經常光顧的」咖啡店。麥克.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曾在《Slate》狠狠嘲諷歐萊利這種「反向虛榮」的心態。「比爾,你猜怎樣?」他寫道,「警察和消防員也喜歡喝好咖啡!而且完全喝得起。星巴克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大眾化意識的品牌之一,要是你願意偶爾踏進那裡,你就該知道這一點的,你這個虛榮的傢伙。」
世界上最虛榮的咖啡——至少是最貴的咖啡——麝香貓咖啡,主要產自印尼,由在麝香貓腸胃裡發酵過的咖啡果實製成。我應該會用拉爾夫.艾里森的實驗室濾紙來過濾。這種咖啡一磅要價六百美金。在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的小說《告白者》(The Committed)中,咖啡商處理這東西的態度,就像邁爾.蘭斯基(Meyer Lansky)的手下在準備老大最愛吃的起司薄餅那般小心翼翼。不過,那些喝麝香貓咖啡的人完全比不上班尼.薩拉札(Bennie Salazar),這個在珍妮佛.伊根(Jennifer Egan)活力四射的小說《時間裡的痴人》(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中,從音樂人轉型為製作人的角色。班尼會在他的咖啡裡撒金箔,因為他聽說金箔有催情的效果(其實並沒有)。
我幾乎每天都會去咖啡廳看書、寫作,有時待一兩個小時,有時兩三個小時(書評人的生活很像碩士生)。在我的經驗裡,咖啡廳總是會發生一些神奇的事。舉例來說:住在加里森的時候,我常開十五分鐘的車到皮克斯基爾咖啡館(Peekskill Coffee House)。我很喜歡那裡,因為它就像一間毛茸茸的大客廳,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兩千年代末的某日下午,我帶著當時才上小學二、三年級的海蒂一起去那家咖啡廳。在我們排隊點餐的時候,我注意到身後站著一位老先生,眼睛直勾勾盯著她看,臉上還帶著一抹微笑。他目光停留的時間有點長。我不禁心想,這個變態是誰啊?我朝他挑了挑眉,用眼神質問他:「你想幹嘛?」他這才趕緊自我介紹。他說他叫羅伯.謝珀森(Rob Shepperson),是一名繪本插畫家。他向我們解釋,一年前他曾在皮克斯基爾咖啡館,坐在桌前糾結要怎麼畫他繪本裡的女主角。而我們那天也在咖啡館。他不管怎麼畫都不滿意,直到他看見海蒂,便悄悄將她畫了下來。於是,海蒂的臉就成了《回憶銀行》(The Memory Bank)的主角小希(Hope)的臉,插圖旁配著卡羅琳.考曼(Carolyn Coman)的文字。要是我們那天沒有剛好和羅伯一起排隊,我也沒有誤會他是一個怪人,大概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件事。那是一本感情豐沛且機智有趣的書,書中充滿了以我那感情豐沛且機智有趣的女兒為原型的插圖。羅伯是個很棒的人,他甚至慷慨地將幾張有簽名的手稿寄給我們。
* * *
比起咖啡,我現在越來越常喝茶,因為它對我的神經和腸胃比較溫和。我每次喝茶時都會想起,我此生唯一讀過兩遍的心靈勵志書——湯姆.霍金森(Tom Hodgkinson)的《悠哉悠哉過日子:遊手好閒的生活藝術》(How to Be Idle)。霍金森對咖啡厭惡到了極點,他認為咖啡是給「心懷罪惡感的拚命三郎、嗜錢如命者,以及過度追求社會地位卻內心空洞的瘋子」喝的,反觀茶,在他看來,則是「自古以來詩人、哲學家與冥想者的飲品。」
說到茶,那就不能不提喬治.歐威爾,和他那篇堪稱經典的文章——〈一杯好茶〉(A Nice Cup of Tea)。它是這位絕頂聰明且率真坦誠的作家寫過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歐威爾首先注意到,你鮮少能在食譜書的索引中找到「茶」這個條目。這讓他非常惱火,因為,他寫道:「茶是人類文明社會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更教人氣憤的是,「關於泡茶的最佳方式,居然會引起眾人激烈的爭論。」歐威爾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茶包尚未普及,人們還保有好好用茶葉泡茶的習慣,不過其中提到的大多數原則,直到今天也依然適用。
歐威爾對於泡一杯好茶,有十一條原則。其中有三條是真正重要的:第一、茶要濃。(「我主張一杯濃茶勝過二十杯淡茶。」)第二、應以茶杯就壺口,而非以茶壺就杯口。(「在注水的那一刻,水應該是沸騰的,因此注水時茶壺應持續置於火上加熱。」)第三、不宜加糖。(「如果你加糖毀了茶本身的味道,你怎麼還敢說自己是真的愛喝茶?)他建議「試著不加糖喝兩個星期的茶,之後你大概就再也不會想加糖了。」跟歐威爾不同,有時候我喜歡在茶裡加蜂蜜。寫作很難,因為思考本身就很難,在寫作當下,那一絲甜味,彷彿可以為你注入你當下需要的那一丁點額外的智商。
克里斯多福.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超過半個世紀後,延續了歐威爾的論點。「下次你去星巴克或類似的地方點茶,請不要害怕回絕他們匆忙丟進茶包的那杯熱水。」他在《Slate》寫道,「那根本不是你點的東西。你一定要看到店員先放茶包,並確保水是滾燙的。要是身後有人嘀咕或是歎氣,你正好可以把握此次機會向他們傳達這項理念。如果你有耐心,你也可以試著在家用茶葉和濾網泡茶。你用不著向我道謝,新年快樂。」
你甚至可以開一間小書店,店裡只賣有關茶葉貿易的悲慘歷史的書。莉迪亞.R.戴蒙德(Lydia R. Diamond)在她的劇作《蒼蠅研究》(Stick Fly)中,解釋了其中的某些原因。《蒼蠅研究》描述了一個富裕的非裔美國家族勒維一家,相約在瑪莎葡萄園島的房子共度夏日週末。即便在早餐的餐桌上,一家人的對話也十分尖銳。
金柏:你覺得印度香料奶茶怎麼樣?
泰勒:我認為名過其實了。我喜歡簡單一點的茶……比如伯爵茶、英式早餐茶、大吉嶺紅茶……
金柏:你還真是殖民者的粉絲啊……
在傑伊.麥金納尼(Jay McInerney)的《如此燦爛,這個城市》(Bright Lights, Big City),敘事者在一家與《紐約客》頗為相似的雜誌社工作。「通常,」他寫道,「這裡的人說話的樣子,就好像他們從小喝唐寧(Twinings)英式早餐茶長大。」我在一九八○年代末曾應徵過《紐約客》的一個基層職位。當時差點就錄取了,但我最後沒有拿到那份工作,一部分是因為我不能不看鍵盤打字(到現在還是不會)。我猜,另一部分是因為我給人的感覺,就是那種完全不懂唐寧英式早餐茶的人。
英國詩人埃德蒙.布倫登(Edmund Blunden)在他的回憶錄《戰爭的密語》(Undertones of War)中,憶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下午茶的儀式對於壕溝裡的士兵而言,蘊含著如此濃重的「家」的意涵。一杯茶在戰場的殺戮中所帶來的不協調感,更進一步加深了書中景況之慘痛。「在一個天氣和暖的下午,我在路上遇見我們隊裡的一名下士,他年紀很輕且性格開朗,當時正在泡茶。」布倫登寫道,「我祝他午茶愉快,接著走過三條壕溝,這時一顆炮彈毫無預警地落在我身後,只見煙霧漸漸散開,我心想他應該能幸運地撿回一條命。不料一聲慘叫隨即從那個方向傳來,那顆炮彈炸得異常猛烈。三分鐘前,距離下士置於小火苗上沸騰的便攜式小鍋不遠的那面背牆,轉眼間已被炮彈炸得焦黑發臭。那一團團燒焦的肉塊、那血肉模糊的泥牆、木踏板下的眼珠,和稀爛的骨頭,怎能是他生命裡唯一的答案呢?」場景接著變得越發令人毛骨悚然。布倫登繼續描述道:「正當我們驚恐地盯著這副駭人的景象時,那名下士的哥哥繞過拐角走了過來。」布倫登最終死於一九七四年,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存活下來,都要歸功於他的個子矮小,讓他「不容易被當成目標」。茶在英國小說中可謂無處不在,從而成為故事場景設置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主人離開去泡茶的時候,敘事者就有時間獨自坐在那裡,仔細觀察四周,釐清思緒。
我不用阿薩姆茶包泡茶的時候,我都用PG Tips——一個歷史悠久、價格親民的英國品牌,茶葉由肯亞、錫蘭與阿薩姆紅茶混合而成。茶包屬於「展露真實自我的風格,沒有花俏的棉線與茶標。每一隻立體茶包都像一個放大了的「Snap 'n' Pop」——一種只要丟到地上就會劈啪作響的新型小爆竹。PG Tips總讓我想到范.莫里森(Van Morrison)的〈肺結核床單〉(T.B. Sheets)。這是一首關於肺結核的歌,老實說這並不是一個我應該在泡茶時想到的主題,但事情偏偏就是如此。美國小說家萊特(Wright)在他的小說《信使》(The Messenger)中,描寫了自己窮到買不起食物的窘境。為了抵抗飢餓,他會在熱茶裡放入大量的肉桂,將那股香氣吸入鼻腔,接著一口氣乾掉那杯茶。
* * *
我們到底應該把早餐這件事看得多重要?也許它的重要性確實不容小覷:據說莉茲.波頓(Lizzie Borden)掄起斧頭的那天早上,就是吃了一頓糟糕的早餐。它無疑是人類分析得最少的一餐。當新冠肺炎爆發、居家隔離政策全面啟動時,早餐的意義也隨之改變。以前的我們可能只是在便利商店匆匆買杯咖啡和玉米瑪芬,然後像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就在身後訓斥我們似的趕著去上班。現在的我們則會多花一點時間吃早餐,讓它延長並填滿一天當中更多的時間。
我在這裡要先向美食作家瑪麗恩.坎寧安(Marion Cunningham)道歉,她寫了一本非常精彩的早餐食譜,還有瑪莉.西蒙斯(Marie Simmons),她寫的那本《好蛋食光》(The Good Egg)雖然多達四百六十四頁,但是內容並不無聊。不過就一般而言,早餐食譜往往是多餘且沒有必要的存在。像我就是買了太多本,卻幾乎沒怎麼翻開過。即便是為了一個工作忙碌的上午做準備,你需要的食譜也都能在你應該有的那些書裡找到:《廚藝之樂》(The Joy of Cooking)、埃德娜.劉易斯(Edna Lewis)的《鄉村料理的滋味》(The Taste of Country Cooking),以及阿曼達.赫塞的《紐約時報精選食譜》(The Essential New York Times Cookbook)。如果這些食譜還不能滿足你的需求,那你不是(a)一家小咖啡館的老闆,就是(b)花太多時間思考早餐要吃什麼了。
我們多數人在早上都比較脆弱,任何一點輕忽冷落皆能造成傷害。我喜歡在家人的陪伴下享用早餐,桌上放著三份以上的報紙,還有美味的烤麵包。對話必須慢慢展開。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小說的讀者經常對身為麻瓜的德思禮一家對待哈利的方式感到震驚,他們不讓哈利跟他們一起吃早餐,而是等到早餐結束後,才將一碗罐頭濃湯從貓門推進他的房間。從海格邀請哈利進屋、在爐火上烤「六根肥大、多汁且微焦的香腸」的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哈利終於交到了朋友。這些香腸不僅美味可口,它們或許還是哈利人生中第一次得到有人出於善意與同情而準備的食物。
一個人吃早餐也是有好處的。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堅持獨自享用早餐,並認為這個習慣拯救了他的婚姻。沒有人能比亨特.斯托克頓.湯普森用更具野性魅力的方式來為此辯護,他在《大白鯊出獵》(The Great Shark Hunt)一書中穿插了以下段落──
我喜歡一個人吃早餐,並且幾乎從不在正午前吃。任何一個生活作息亂到沒救的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當中都需要至少一個穩定心緒的心錨,而我的心錨就是早餐。無論是在香港、達拉斯,還是在家裡——也不管我有沒有上床睡覺——早餐對我而言都是一場只能獨自完成的個人儀式,而且要以一種放縱的心態進行。食物份量一定要夠:四杯血腥瑪麗、兩顆葡萄柚、一壺咖啡、幾份仰光可麗餅、半磅的香腸、培根或醃牛肉馬鈴薯餅撒上辣椒丁、一份西班牙烘蛋或班尼迪克蛋、一夸脫牛奶、一顆切碎的檸檬用於餐桌上的即興調味,再加上一片佛島萊姆派、兩杯瑪格麗特和六條最純的古柯鹼當做甜點……對了,還要有兩三份報紙、所有的郵件和留言、一支電話、一本用來規劃接下來二十四小時行程的筆記本,外加至少一個好的音樂庫……這一切都應該在戶外、在熾熱的太陽底下,而且最好是以全裸的狀態完成。
湯普森是一個善於替自己塑造傳奇形象的人。他的文字宛如熊熊烈焰,不要照單全收才是明智之舉。湯普森追隨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腳步,也會吃有如山崩般豐盛的美式早餐。只要情況允許,馬克.吐溫就會點「一份有一點五英吋厚、在煎臺上滋滋作響的、熱騰騰的巨無霸紅屋牛排,」在那之後還有蘑菇、咖啡、餅乾和蕎麥蛋糕。我喜歡想像邱吉爾、湯普森和馬克.吐溫在天堂吃完早餐後放下刀叉,一起悠悠哉哉地回去睡回籠覺的畫面。
我們都喜歡早餐的食物,因為它讓我們回想起學步期的味覺與感官記憶,那是我們得到最多認可的時候。「餵我和愛我,」迪斯基寫道,「其實是相似的要求。」在我們小的時候,我們的嘴巴往往知道大腦不知道的事。身為大人,誰不想在晚餐的時候吃早餐的食物呢?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九二○年代牛津餐飲俱樂部的會員,他們的特色是會定期反著過一天:早上穿著晚宴服喝白蘭地、抽雪茄;晚餐時則在月光下享用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