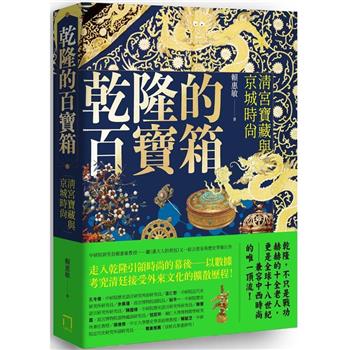〈西洋紡織品的用途〉
北京市民重視門面、排場,在家飾用品和衣著方面都很講究,朝鮮使臣俞彥述《燕京雜識》記載:「國俗專以誇矜炫耀為能事。市肆間雜貨山積,金碧眩眼,極其富麗。」家中什物宏麗奇巧自然少不了西洋的器物,以下從文集、旗人子弟書、抄家檔案來看旗人家庭的裝飾。清人生活中,冬天穿著歐洲來的哆羅呢、羽緞、嗶嘰衣裳成為時尚。
英國東印度公司記錄中國人喜好毛織:「中國人認為身薄而質優的織物,銷售的比厚身的織物好。總的來說,銷售織物是盈利的。」有所謂「洋氊勝紫貂」的諺語。乾隆五十七年(1790)馬戞爾尼到中國來,由使團副使喬治.斯當東編寫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提到:「北京商舖有來自南方各省的茶葉、絲織品和瓷器,有的是來自韃靼的皮貨。我們非常有興趣的看到貨品中居然還有少量的英國布匹。」官員購買薄的毛織品如哆羅呢、嗶嘰、羽紗、羽緞的數量較多,而氈毯類的厚毛織品數量較少。巴羅估計清朝政府官員的普通服飾一套10英鎊(1英鎊等於3兩),禮服約30英鎊。一雙鍛子靴20先令,一頂帽子也是這價格。如果飾以繡品和金絲銀線,價格在200到300英鎊之間。
比起英國的紡織品,俄國的紡織品更受歡迎。〔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蒙古及蒙古人》一書描述他走過北方城市的店鋪,在烏里雅蘇台看到這裡的店鋪經營的棉布如褡褳布、大布、洋大布及俄國各色印花布等。1880年,烏里雅蘇台周圍地區的草原上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居民穿的都是俄國棉布做的衣服。在烏里雅蘇台經營的北京人,在庫倫也有自己的店鋪。在慶寧寺附近的漢商經營商品主要是俄國貨,例如紡織品中有:士兵呢、棉絨布,各種顏色的厚棉布、各種顏色的羽毛絨和細平布。庫倫的北京店鋪裡的毛、棉織品大多數是歐洲產品。歸化城出售的布疋也都是外國貨,中國生產的只有絲織品,棉布只有大布一種。張家口的買賣城可以說是中國對俄貿易的集中點,幾乎全部的俄國呢絨和各種絨布,以及俄國出口的毛皮製品都先運到張家口上堡買賣城的貨棧。然後批發給下堡,再轉運往中國本土。多倫諾爾販售的歐洲商品,如斜紋布、府綢、印花布和德國呢,不過德國呢往往是在俄國呢的仿冒品。俄國呢子有邱利亞耶夫和巴布金兩家廠商出產的呢子,莫羅佐夫廠出產的粗平布和棉絨布,以及黑白兩種油性軟革稱為香牛皮。多倫諾爾的貨物來自恰克圖,主要的商人也都是山西人。
俄國呢子越來越普及,特別是中國北方地區,俄國呢子粗劣、厚重,較適合北方寒冷氣候。1850年間,俄國呢子行銷上海、蘇州、廣東地區,與歐洲產品競爭,更超越英德的呢子。《澳門月報》載來自俄羅斯的產品主要是一種粗糙的哆囉呢,這種呢多半在俄國織的,但也有一定的數量來自比利時和薩克森。它的寬度是62到64英吋。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北方口岸常見到的是俄國的紡織品,運進上海、寧波的俄國呢子比英國進口的多12倍。
除此之外,西洋紡織品在宮廷用途還有下列幾項:
(一)賞賜蒙古王公、官員
清朝與蒙古關係密切,蒙古王公、喇嘛每年派人到北京朝貢,喀爾喀蒙王公所設立的行館稱為外館,位於安定門外附近偏西的郊區。北京城裡王府井大街東交民巷附近的內館為科爾沁等內蒙古王公朝覲住所。清朝皇帝於紫光閣筵宴蒙古王公、喇嘛,賞給緞、貂皮等。嘉慶年間,自俄羅斯進口的呢絨多,皇帝下令:「命理藩院通行內外眾扎薩克蒙古王公等,嗣後年班圍班請安時。俱著正穿石青馬褂,不得穿黃馬褂及反穿馬褂。著為例。」石青馬褂為藍色的哦噔紬。根據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的觀察,庫倫的店鋪裡的毛織品和棉紡織品大多數是歐洲產品。對喀爾喀蒙古王公來說,石青馬褂應取自俄羅斯的毛織品較為便利。
朝鮮使者《皇都雜詠》載:「喇嘛僧滿雍和宮,錦帽貂裘抗貴公。乾隆蓋是英雄主,賺得蒙蕃盡彀中。」喇嘛穿戴錦帽、貂裘來自皇帝的賞賜,金梁《雍和宮志略》提到喇嘛的法衣必須按照月令季節穿著,皇帝賞給「皮襖銀」。
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禪額爾德尼到北京,皇帝很高興,賞賜他和其他使臣許多東西,絲綢、瓷器之外,還包括許多洋貨,如洋花緞、海龍皮、豹皮、玻璃碗、玻璃盤、玻璃瓶。《律藏》中說:「持守清淨戒條的比丘也可積聚財物。」《諸續部》經典中也說:「持咒師若按燒施的規定享用飲食,也可以積累如須彌山一般的財富。」信徒奉獻喇嘛精巧珍器、稀世之寶,代表他們的誠心,乾隆皇帝深信藏傳佛教,因此對喇嘛的賞賜也特別多。
石青馬褂,中國稱為燕尾青的深藍色呢絨,宮廷侍衛亦穿著這料子做馬褂。同治十三年(1874),皇帝大閱於南苑命「文案營務翼長委員等穿天青馬褂,佩刀入隊。……侍衞均穿天青馬褂。」或許俄羅斯的呢子,穿起來衣冠楚楚,展現男性氣概,《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也多處提到男性穿著石青馬褂。
(二)《皇朝禮器圖式》的服飾定制
許多學者討論乾隆皇帝認為「本朝定制」為呈顯滿洲特色,實則展示中西貿易成果。根據張仲禮研究,清代的士紳以上占人口百分之二,以乾隆1億5千萬人口計算,起碼有30萬人以上,要能供應眾多士大夫以上需求,非得興盛貿易不可。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定品官雨帽並將雨服一類,根據《皇朝禮器圖式》記載:「皇帝雨冠二,謹按乾隆十六年欽定皇帝雨冠羽緞為之明黄色。」「皇帝雨衣三,謹按乾隆十六年欽定皇帝雨衣羽緞為之,明黄色如雨衣二之制。」職官雨冠「按乾隆三十二年欽定職官雨冠,用紅色氊及羽紗、油紬惟其時,藍布帶。民公、侯、伯、子、男,一品至三品文武官,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上書房翰林,南書房翰林,奏事處,批本處行走人員皆用之。」「謹按乾隆八年,欽定職官雨衣,用紅色,制如常服褂而加領,長與坐齊前施掩襠,氊及羽紗、油綢惟其時。民公、侯、伯、子、男,一品至三品文武官,御前侍衛,各省巡撫皆服之。」
官員大量使用羽紗、羽緞,這些進口的紡織品,價格不斐。在《中國古代當鋪鑒定秘籍》收錄乾隆二十四年(1758)抄本《當譜集》就有許多的洋貨。舉例來說,經絲緯毛望日光地起金星有羽毛的為羽毛縐,無羽毛的為縐。其物花素丕袍料二則,重23兩。每尺1.15兩,袍料重17兩,每尺1.3兩。羽緞線道粗發亮無花銀十兩之數也,每尺重1.7兩。宮廷許多舊的毛皮或綢緞放久了,找內務府買賣人變價。羽緞、羽紗即便是舊些,價格還不低。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李廷榮變價羽緞,每庹(相當於5尺)銀2兩,每尺0.4兩。羽紗每庹銀一兩,每尺0.2兩。
(三)佛教器物
壁畫繪於布縵上,再懸掛在牆壁上。壁畫內容都以宗教故事為題材。壁畫以黃、紅、藍三種顏色為主色,用對比手法突出主題。《西藏密教研究》提到格魯派在寺廟堂內的柱及兩側的壁上,都掛著布製的幡及稱為唐卡的掛軸式的布製佛畫,以裝飾堂內的莊嚴。乾隆五十年(1785)員外郎五德庫掌大達色催長舒興來說太監常寧傳旨:「方壺勝境中層樓上明間成做拉古里一件、壁衣一件。欽此。」挑得內庫石青倭緞一塊,做拉古里毘盧帽用。紫綠石青回子紬三疋,做拉古里刷子用。大紅緞一疋,做拉古里頂面刷子裡。用石青回子紬一疋,做壁衣邊用。紫回子紬一疋,做壁衣心子用。
(四)蒙古包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記載清宮建造蒙古包的事務,最有名的是熱河避暑山莊萬樹園照的蒙古包。據昭槤,《嘯亭雜錄》載:「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黃幄殿,可容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上親賜卮酒,以及新降諸王、貝勒、伯克等,示無外也,俗謂之大蒙古包宴。」黃幄殿蒙古包7丈2尺,蒙古包內天花板、圍牆用庫紅地金花回子紬、石青回子紬做成。其他還有5丈2尺花頂蒙古包二架;二丈五尺備差蒙古包二十四架。蒙古包前有遮陽平頂棚,四周有窗,內設寶座及地毯,使用回子綢當圍帳等。乾隆曾多次向粵海關訂購西洋紋樣的氈毯,作為蒙古包的主要地毯材料。可見西洋錦在乾隆朝的武備儀式中,特別是行圍和大閱中擁有顯著的地位。雖然西洋錦在宮廷使用的織物中只占一小部分,其重要性卻不可低估。
阿.馬.波茲德涅耶夫描述他經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時,官員的接待室房炕上鋪著大紅呢子,同樣的紅呢坐墊,四壁墻下各放著一張窄長的桌子,上面也鋪著大紅呢子。
(五)包裝器物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許多玉器用回子布包裝,在檔案中也可以找到相關檔案。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十六日太監常寧「將玉有盒圓洗一件、玉壺一件,配得回子布套呈進交乾清宮訖。於四月二十二日將玉圓洗一件,配得回子布套呈進。」
《皇朝禮器圖式》武備皇帝大閱鹵簿櫜鞬載:「本朝定制:皇帝大閱鹵簿櫜鞬,鞬以銀絲緞為之,綠革緣,天鵝絨裡,面綴金環,繫明黄緌。櫜以革,蒙銀絲縀,後輭壺三,以革為之。皆飾金絲花,銜東珠。」櫜鞬用來包裝弓箭,以銀絲緞製作。現存故宮博物院之織金銀緞面皮櫜鞬,為織金銀卷草文緞面。根據梅玫的研究,從清宮檔案中所提到的西洋錦名字上看,它們有一個顯著的特徵:這些錦緞上幾乎全部織有金線或銀線,或兩者兼有。這一特徵在北京故宮的舊藏西洋錦中也得到印證。織有金屬線的絲綢是歐洲絲綢中最為昂貴和精美的品種,其華麗耀眼也許深深吸引乾隆皇帝,使他連帶亦偏愛作為紡織原材料的西洋金銀線,屢屢傳旨向外洋購買。
(六)車轎帷幔
皇室冬天乘坐的車駕使用氈呢。如內務府成造皇太后、皇貴妃成用車幃二分需用黃哆囉呢96.38尺。皇太后圓頂車上做哆羅呢圍一分、上緞下接哆羅呢圍一分、春紬袷裏圍一分、紗圍一分、狼皮褥一箇、衣素褥一箇、靠背一箇。哆羅呢是寬幅絨適合做轎子圍屏,內務府鑾儀衛成做八人抬的暖轎需用哆羅呢35.48尺。巫仁恕研究明代的轎子說:「明代的暖轎應室外披有厚布料以防寒,而涼轎則是圍以竹簾。」《北平市工商業概況》記載,清乾嘉年間,其時王公貴族以及達官富戶類,皆出入乘坐轎車,需用圍墊較夥。且各蒙古王公於入覲之便,常大批採購此項圍墊,攜歸蒙地,視為極珍貴之禮品。以故治斯業者,先後繼起,並力謀業務之發展,兼製桌圍椅墊、帘帳枕褥。一時出品繁而購者眾、獲利頗厚。車圍墊之材料,以藍白洋布、市布、褡褳布、蒲絨為大宗。還有俄國來的回錦(似薄帆布)、哈喇等。
(本文選自:「第三章:清宮的西洋紡織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