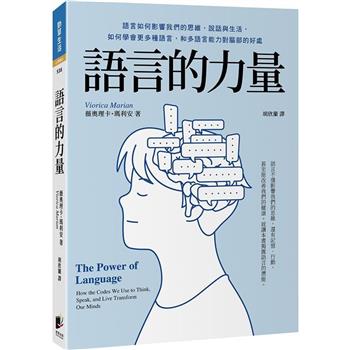第一部分 個人自我
語言的局限意味著我世界的局限。
——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
—— Ludwig Wittgenstein
第1章 驚人的思維方式
Mind Boggling
我們生活在一個代碼的世界裡。有些代碼像軟體一樣嚴謹,有些像母語一樣流利。有些像數學一樣超越人類的經驗範圍。有些則充滿偏執。有些則像詩歌。它們都是語言,這些是我們思維的代碼。
雖然你可能還沒意識到,你的大腦已經使用了多種代碼,例如數學、音樂、口語、手語。人類的大腦是為了適應多種交流代碼而建構而成,當我們學習時,會向新體驗和知識敞開大門。我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世界,而我們的大腦開始產生變化。
許多人仍然錯過學習其他語言(例如西班牙語、華語或印地語)的好處,僅僅只是因為多語能力的影響可能被誤解,被貶低,甚至被政治化。但是,懂得多種語言可以帶來新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在其他方面是無法實現的——就像學習數學讓我們可以做其他原本無法想像的事情,例如開發人工智慧、潛入海洋深處或登陸其他星球——就像學習樂譜使我們能夠聽到千里之外或幾百年前創作的音樂模式,學習另一種語言則開啟另一種編碼現實和思維的新方式。
如果你曾玩過Boggle字母盤遊戲,那麼你很有可能會因為另外一個玩家在你寫字時轉動格盤而大動肝火。甚至你自己可能就是那個被其他玩家吼的人,這都是因為有時候你的大腦已經有新發現:轉動格盤會改變你的視角,讓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到相同字母,找出更多的單字,進而提高分數。
就像翻轉Boggle字母盤一樣,每一種我們知道的新語言會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獲得和解釋資訊,進而改變我們的思考和感受、我們的感知和記憶、我們做出的決定、我們的想法和見解,和我們的行為舉止。從一種新的方向看遊戲棋盤,會活化大腦中不同的神經元,不同的神經網路會對「我看到了什麼單字?」這個問題產生新的答案。同樣的,在日常生活中,大腦會根據輸入的語言組織方式,提供不同答案。
一個單字可以傳達一種複雜的概念,例如重力、基因組或是愛,透過將大量的訊息編碼為小型通訊單位,最佳化儲存和學習。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的概念,是語言和思維科學的根本。
然而僅僅一種符號系統只能讓你到這樣的程度。學習和使用多種符號系統不僅會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還會改變大腦本身結構。效果不僅有加成作用,而且還有轉化性質。
當你得知全球大多數人口都使用雙語或多語,這個事實可能令人感到訝異。現今世界上使用七千種以上的語言。最常用的語言是英語和華語,分別超過10億以上的人使用,使用印地語和西班牙語則各超過5億人,其次是法語、阿拉伯語、孟加拉語、俄語和葡萄牙語。說多種語言是人類的常態,而非例外。想想看:印尼語是印尼最常使用的語言,超過94%的人口使用印尼語,但它僅僅是20%人口所使用的主要語言。爪哇語是當地最常見的主要語言,但只有30%的人會說爪哇語。在歐洲、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許多國家,兒童從出生就成長於兩種或多種語言的環境中,然後在學校或成年後學習其他語言。盧森堡、挪威和愛沙尼亞等國家有超過九成的人口使用雙語或多語。歐洲約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會說兩種語言(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會說三種或更多種語言),加拿大人一半以上的人會說兩種語言。對於那些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而言,數字甚至更高——在歐盟國家,擁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當中,超過八成的人表示自己掌握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
使用多種官方語言是許多國家的國家政策。例如,加拿大有兩種官方語言、比利時有三種官方語言、南非則有九種官方語言。在印度,憲法承認二十幾種官方語言,並且預設能使用多種語言。全球範圍內有大約66%的兒童接受雙語教育,而 且在許多國家,外語需求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即使傳統上只使用一種語言的美國,懂得一種以上語言的美國人口數目也在迅速增加。在美國,超過五分之一的人表示在家會說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2020年的數據為22%)——此數字已於過去四十年中倍增,並且還在持續上升,在大城市則接近50%。
然而,我們才剛開始了解多語思維。為何如此?因為科學在玩Boggle字母盤時一直沒有切換角度。大部分的研究歷來聚焦在單語人群上,而且迄今仍然如此,這表示我們對大腦和人類能力的了解僅來自單語者的角度,結果不但有限且不完整,甚至在許多情況下是錯誤的。
當研究人類心智時僅專注於單語者,這就像心臟病和糖尿病的研究僅用於白人男性,而且假設研究結果適用於所有人一樣。我們現在知道心臟病在女性中的變化與男性不同,糖在北美和南美的原住民群體中代謝方式不同。會說超過一種語言或方言以上的人,其語言、認知和神經結構不同於只會說一種語言的人。長久以來,這些差異被視為雜音而非訊號,被視為問題而非典型的人性複雜系統。
將語言多樣性排除在研究之外會帶來什麼危險?舉一個歷史性的例子,就是由凱文.柯立芝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1924年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規定美國接受移民的國家(西北歐國家)與限制移民的國家(東南歐,亞洲和非洲國家)。這種歧視政策旨在「改善」美國的基因庫,其理由是基於我們現在所知有誤的,關於不同種族和族群智力有誤的智能心理研究:優生學研究。它沒有考慮到語言和文化差異,而是基於從那些通常不懂測試語言的人那裡收集到的數據。想像一下,一名農夫剛在愛麗斯島(按:Ellis Island,於1892∼1954年間為美國移民管理局的所在地)下船,突然被不會說的語言進行「智力」測驗,結果會如何。在這些測試中,會說英語、和英語相似的語言、或屬於日耳曼語族的語系的人,表現比那些說和英文不太相似語言的人表現更好,有什麼奇怪的嗎?
雖然《1924年移民法》最後被廢除了,但是帶有偏見的移民政策依然存在。對會說多種語言的人缺乏瞭解,持續導致對人類能力不全面和不準確的看法,限制個人機會,對移民和外語抱持負面態度,以及帶有偏見的教育和社會政策。在科學研究中納入會說多種語言的人,可以更精準回應有關人類狀況的問題。
直到最近,我們才有研究多語大腦的工具。科學和科技的進步為我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可以偵測大腦中的血液含氧濃度;「腦電圖」(EEG)可以記錄大腦的電活動;眼動追蹤(eye tracking)則可以記錄瞳孔移動和擴張情況;還有機器學習和大量國際線上數據收集。
我們實驗室進行的研究利用眼動追蹤技術,揭露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觀看的事物、注意力集中的方向以及記憶內容,都會受到我們已了解的語言,和當時所使用語言的影響。
在這些實驗中,雙語者坐在桌子旁,被要求在移動各種物體,同時記錄他們的眼動。巧妙之處在於,有些物體的名稱在不同語言之間會有部分重疊,例如英語單字marker和俄語單字marka(郵票)、英語單字glove和俄語單字glaz(眼睛)、英語單字shark和俄語單字sharik(氣球)。在進行論文研究時,我經常在商店內尋找可以作為實驗刺激物的品項;現在,這些實驗可以在網路上使用個人網路攝影機進行。眼球運動分析揭露,當雙語者聽到某種語言的單字(例如英語中的mark、glove或shark)時,他們會對另一種語言中名字部分重疊的物體(如俄語中的marka/郵票、glaz/眼和sharik/氣球)產生眼動反應。
與只用英語的使用者相比,雙語和僅僅使用一種語言者(單語者)都會觀察名字在英語中重疊的物體(如麥克筆marker和大理石marbles,或矛spear 和演說家speaker),但只有會俄語和英語的雙語者,會觀察在兩種語言中名字互相重疊的物品,如marker和marka/郵票,或spear和spichki/火柴)。英語單語者不會觀察名稱在俄語中重疊的物品,就像他們不會對其他擺出來的物體投注更多的注意力一樣。透過完全相同的刺激物對雙語者和單語者進行的測試,表明眼球運動對跨語言競爭對手的反應,是由雙語思維中另一種語言的平行活化(parallel activation)所引起。
另一種史楚普任務(Stroop task)非常簡易巧妙,是讓人們說出以不同顏色墨水印刷的顏色單字,例如用黑色墨水印刷的單字為BLACK(黑色的),而綠色墨水印書的單字則稱為GREEN(綠色的)。當被要求說出墨水顏色,並忽略單字內容時,會出現一種情況,當詞彙為「BLACK」時,人們說墨水顏色是黑色的速度通常比詞彙為「GREEN」時更快。多語者通常在史楚普測驗中表現得更好。他們有能力將注意力集中於墨水的顏色(相關訊息),並忽略詞彙的內容(無關訊息),這是因為多語者總是專注使用其中一種語言時,控制其他熟知語言的競爭,產生這種「副產品」。隨著時間推移,對多語競爭的控制可以使大腦更能專注於相關訊息,並忽略無關訊息,這是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的一項特徵。
使用多語的影響不僅限於執行功能,還擴展到記憶、情緒、感知以及其他方面的人類經驗。在一項研究中,我們發現,當中英雙語者被要求命名一座單手舉起、遙望遠方的雕像時,他們在說英語時更傾向說「自由女神像」,而說華語時則是「毛主席」。當被問及二戰時日本於何地、何時發動首次進攻,他們說英語時更傾向回答「珍珠港,1941年」,當說華語時則是「盧溝橋,1937年」(前者指對美國的攻擊,後者則是指早四年對中國襲擊的事件)。再者,當被要求說出一位雖然身體有嚴重缺陷卻仍大獲成功的女性時,他們說英語時更傾向回答「海倫凱勒」;說華語時則是「張海迪」(按:中國著名殘疾人士)。這些雙語者都知道這兩個答案,但是其中哪一個答案出現在腦海中的速度和可能性,取決於那時所說的語言。由於語言和文化緊密交織,語言充當文化的媒介,改變語言也會改變文化框架。
即使是和生活當中的個人記憶——我們的童年時期、人際關係、個人經歷相關——也會隨多語者的語言而變化。當人們使用特定語言來回憶過去時,會更有可能想起說該語言時所發生的事件。在另一項研究中,雙語者在說母語時,記得童年(移民到美國之前)事件的可能性更高,而當他們說英語時,比較容易記得後來生活(指移民到美國之後)的事件。
在我其中一堂講座上,有一位學生傳給我一條訊息,她決定親自做實驗:「我想親身嘗試這個論點,所以當我和媽媽用 FaceTime 通話時,我要求她在通話開始時,用漢語問我一個和記憶有關的問題,然後在通話結束前,用英語再次問我同樣的問題。(此舉顯然不是最好的客觀科學實驗,但是嘗試時仍很有趣!)她問的問題是:『關於操場,妳最早的記憶是什麼?』當她用粵語問我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和父母在舊公寓的操場玩的時候,但當她用英語問我這個問題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幼稚園操場玩的『公主遊戲』。雖然我一開始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對於同樣問題的起初反應是兩種不同的情境,但是我愈思考,就愈覺得有意思。我小時候和父母在操場上玩時說的是粵語,而我在幼稚園就讀時是用英語上課。」
研究發現記憶的可及性會因語言而異,即語言依賴性記憶現象(Language-Dependent Memory phenomenon),對法律案件中採訪雙語證人、獲取創傷事件的記憶、以及為雙語客戶提供心理治療都會帶來影響。
記憶的浮現也會反過來塑造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和使用的框架。語言甚至可以影響人們對愛與恨的經歷。在使用母語和非母語時,「我愛你」聽起來的感受不同。母語對情感的沖擊力更強。因此有些多語者覺得需要一些情感距離時,會更傾向使用非母語。使用另一種語言並不會讓《星艦迷航》的瓦肯人失去情感,但是它可以讓情感從母語的強烈聯繫當中脫離。正如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名言:「如果你用一個人聽得懂的語言與他交談,他會記在腦中。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語言與他交談,他會記在心裡。」
雖然這似乎來很極端,但是當多語者使用母語和另一種語言時,對人、事或物的感受會迥然不同。被詛咒或禁忌用語冒犯的可能性,會隨著母語和第二語言而變。多語者不僅表示感覺不同,而且他們身體的生理反應也會不同(如測量喚醒電位〔arousal potentials〕或事件相關電位的膚電反應,與測量腦部活動的fMRI),他們的大腦在不同語言之間會做出不同的情感決定。積極、消極情緒與語言之間的明確關係會因人而異。對有些人而言,使用第二語言具有更積極的含義,因為它與自由、機會、財務健全和免於迫害有關,而母語則與貧窮、迫害和困苦相關。對於其他人來說,情況恰恰相反——第二語言與移民後的挑戰、歧視和缺乏親密關係有關,而母語與家人、朋友和父母的愛有關。許多人介於兩者之間,對於每種語言都有積極和消極的混合體驗。
現今有大量在外語效應(Foreign Language Effect)範疇下的研究指出,人們使用非母語時,在道德判斷到財政分配等各項領域中,做出的決定更合乎邏輯也更理性。2例如,用於研究道德和倫理的典型電車難題,有一個版本是一輛電車正朝五名看不見它的工人疾馳而去。此時你正站在火車軌道上方的橋上,旁邊是一位背著沉重背包的大塊頭。如果你把這個人從橋上推到下方的鐵軌上,他就會喪命,但是這樣做會讓電車戛然而止,從而救下五名工人。那麼,犧牲一個人救下五條命的方法可行嗎?